- +1
他们在北极的冰原上跋涉,如同一群“流浪的昆虫”
【编者按】
19世纪末,探险家们着迷于全世界唯一一块尚未标记在地图上的神秘区域——北极。1879年7月8日,美国探险船“珍妮特号”从旧金山起航,开始了前往北极的未知之旅。在北极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旅行目的地的今天,再回望当年这段艰苦卓绝的旅程或许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本文摘自记录“珍妮特号”极地远征故事的《冰雪王国》一书的《永不绝望》一节,讲述了“珍妮特号”沉没后,探险队员们悲壮的徒步冰海之旅,由澎湃新闻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德隆带着探险队员们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冰海长征,一寸一寸地朝着他们熟悉的世界——至少是能看到人的地方——挪动着步伐。他们的队伍在冰上拉出去好几英里长,用梅尔维尔的说法,就像一群“流浪的昆虫”。他们被冻得四肢僵硬,劳动量惊人,但奇怪的是居然很开心——开心他们终于摆脱了困在船上的监禁,欣慰他们又可以活动了,而且正热切地建立起同甘共苦的纽带。他们的目标是俄国中部和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但在他们的想象中,此行的目的地是家,是回到妻子、母亲和女友身边,那里有肥嫩的鸡肉和新鲜的果蔬,有柔软的床铺和温暖的炉火,有饶舌的八卦也有捏造的故事,即使国人认为他们不能完全算是凯旋,但起码也会对他们报以激赏的欢呼。
德隆和邓巴带着野外望远镜和便携式棱镜指南针,在远处的浓雾中艰难攀爬,他们在队伍的最前方,把黑旗插在冰里,给后面的队员指路。他们称之为“路”,但事实上他们冒险的路线不过是一条没有那么危险的迂回路径,要穿越各种裂缝、冰丘、冰脊、闪着微光的融雪水塘的迷宫,这一切的形态无一稳定,不断变化。也就是说,船长和他的冰区引航员——后者早先的雪盲症已经痊愈了——前行所依靠的,不过是他们最好的直觉。
他们喊道,跟上队伍!沿路前进!后面的人听到这个词难免会觉得荒谬可笑。正如达嫩豪所说,所谓的“路”上只有“齐膝的雪”和“需要一队工程人员才能夷平的隆起的冰块”。然而,他们步履沉重地蹒跚着,皮肤晒伤,嘴唇皴裂,穿着味道发酸的生皮,带着裂开的冰镜,唱着船歌,顽强地行进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坚冰、碎冰块和雪地中。
6月的阳光只要穿过浓雾,就有一种奇怪的穿透力,仿佛瞄准雪地发射X射线。在强光照射下,肮脏的冰原有时会出现一些生命的迹象——蟹爪、熊粪、蚌壳、白骨、鹅毛、植物种子、浮木、海绵,如此等等。回旋的海水和翻腾的冰块把一切新的旧的动植物都搅在一起,变成一锅北极大杂烩。
安布勒医生照顾病人;阿列克谢和阿涅奎因照顾狗。而其他人每天都过得像挽畜一样,辛劳地拽着麻绳和帆布挽具。他们要用临时改装的雪橇拖拉重达8吨以上的补给和装备,雪橇厚重的橡木条板用光滑的鲸鱼骨钉在一起,其上的横木是用威士忌酒桶的桶板制成的。除了3条备受摧残的小船之外,他们还要拖拽很多东西,包括药箱、弹药、炖锅、炉灶、帐篷杆、船桨、来复枪、航行日志和日记、船帆、科学仪器、木筏子,以及200多加仑的炉用酒精。
说到食物,他们起初盘点了3960磅肉糜饼、1500磅硬面包、32磅牛舌、150磅李比希浓缩牛肉汁、12.5磅猪蹄,还有大量的小牛肉、火腿、威士忌、白兰地、巧克力和烟草。每一磅、每一盎司在一开始都仔细称量过,然后又同样仔细地分配给各辆雪橇和队员,除了病号之外,每个人拖拉的重量基本相当。
一趟拖不走这么多东西,他们要搬两趟——有时得三趟,才能把东西从后面拖到前面。这意味着对许多搬运者来说,每前进1英里,事实上要来回跨越5英里。这样西西弗斯式的苦役做一整天,可能意味着要一刻不停地跋涉25英里甚至更远。就算在坚实的硬地上这也是奴隶的劳动,而这到处是开裂的洞口和纵横交错的海水水道,其地形之艰难超乎想象——德隆说,眼前的景观“混乱得可怕”。
队员们往往不得不把船放下水,通过一条窄窄的水道,再跳上来重新把船放在雪橇上。有时他们需要用一大片浮在水面上的冰块作为渡船,通过水道前往另一侧的冰岸。“修路队员们”得用镐在结着硬壳的冰中凿出一个光滑的凹槽,砍去高高的冰丘顶端,或者在冰雪融化之后形成的碧绿池塘上修建德隆所谓的“堤道”或“浮桥”。
梅尔维尔说,每天的行程结束时,大家全都累瘫了。有人因为疲惫而晕厥。还有人因体温过低而发抖,那是因为浸在冰水中的时间太长了。德隆往往会选择跟队员们一起拖拉重物,他说“世上没有比我们更疲惫、更饥饿的人了……每一块骨头都酸痛”。达嫩豪也跟船长一样,注意到每个人每天“都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辛苦的一天”。
尽管过着像驴子一样的生活,艰难至此,但出发后刚开始那几周,大多数人却出奇地满足。几乎每个人都说过自己很开心。他们睡得很香、胃口很大,每天的生活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是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
“我们现在活得很有尊严……身体极其健康,”德隆起初惊奇地写道,“每个人都欢快活泼,整个营地看上去生机勃勃……处处都有歌声。”梅尔维尔注意到队员们总是在“高声喧哗”,往往还会发出“大笑和善意的调侃……没有哪一条船在经历了如此严苛的困境之后会像这样,几乎没有人抱怨”。每当他们在冰上行走,都会唱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和旅行歌,像《去都柏林的崎岖路》之类的:
吵吵闹闹的一群人见我步履蹒跚,
和我一起加入混战。
我们迅速排除了障碍,
走上去都柏林的崎岖路。
虽然冰面粗粝难行,但冰景有时也很美。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浮冰群的底面,哗啦啦的响声不断,听起来悦耳宜人,就像上百万只昆虫拍打着羽翼。在有些地方,队员们会看到古怪而素朴的界碑闪着超凡脱俗的碧蓝光芒,这是由古老的压缩冰块隆起而成的。在浮冰的某些地段,会有一种海藻留下一片亮红褐色的东西——人们称之为“雪藻”。
德隆写到过太阳光如何穿透浓雾,它“闪烁着,像醉汉眨着眼睛”。他注意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呻吟声和尖叫声”把浓烈潮湿的空气都变得鲜活起来,那些声音是因为冰块相互碰撞,大型的“雪鼻子”一寸寸隆起所致。不时会有一块巨大的浮冰翻滚着突然颠倒过来,把小鱼儿纳入囊中。鱼儿们喷溅着唾沫,在小空间里蜿蜒回转,疯狂地寻找生路,要逃出这新造的牢狱。

德隆和队员们在6月18日傍晚离开了珍妮特号的沉没地点。出发前,德隆草草写下一张纸条:“我们撤营了,在冰上朝南方出发,希望上帝保佑我们能到达新西伯利亚群岛,在那里乘船前往西伯利亚海岸。”船长把纸条用一片黑色橡胶卷好,放进一个小水桶中,把它留在冰上,希望“有人能看到它”。
像这次航行的几乎一切相关事务一样,德隆预见到了可能会有这次撤退——很久以前就对具体做法进行了详尽无遗的规划。他似乎什么都考虑到了。首先,他决定逆转作息安排:他们将在白天睡觉,在干爽凉快的傍晚行军——6月底,傍晚的温度通常都在零下7摄氏度上下。夜间的冰雪更坚固,有足够的光照——绝不会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如此便避开了正午刺眼的阳光,可以大大降低雪盲症和过热的风险。他们在早上8点吃“晚餐”,然后爬到帐篷里睡一个白天,其间把湿透的皮衣在外面晾干,因为白天的温度有时会超过4摄氏度。
德隆很长时间都在推敲人员组织系列。他把探险队的33个人分成了三个小队,每队大致11个人。每个小队都分配有一条船、一辆雪橇和一个扎营区,由一名军官指挥。每辆雪橇和每条船都有一个名字、一面旗帜,还有一句话刻在上面——其中之一是“凭此徽号汝必得胜”,另一个是“永不绝望”。
在他们回家的漫长征途中,这一由小规模船员队伍组成的系统将是最主要的组织理念。每个小队一起拉货、一起休息、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如果必要,还将共赴黄泉。德隆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希望能在这次远征中注入一种团队精神和团队忠诚的元素: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同伴们失望,谁都想让自己团队的表现超过其他团队。这一简单精巧的系统不仅能够充分调动个人的荣誉感,还能调动起个人对所在团队的自豪感。
德隆认为,把探险队分成小队还有助于防止小小的不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德隆对北极探险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十分警醒,因为哗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他永远忘不了霍尔船长在北极星号航行中的命运。德隆知道,在极度压力下,如果给人们以足够的自由表达不满而不加以遏制,会产生怎样致命的后果——某个错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都可能会在头脑中被无限放大;一个小小的误会事件或曲解的评论可能会在整个团队传播开来。
远征开始时士气高昂,但德隆知道,士气很快就会瓦解,他必须对一切有足够坚实的把握和掌控。他特别担心科林斯,后者一直很愤懑,对德隆的敌意也一直很明显。达嫩豪也是个潜在的导火索——哪怕他连在雪地里走路都摇摇晃晃得像个酒鬼,而且他也不像德隆那样,觉得梅毒致盲让自己变成了废人,因此对于被列入病号名单十分羞恼。德隆深知现有的威胁就有好几个,认为把这些人分在几个不同的小队,在冰面上相隔若干英里,可能会最大限度地遏制暴乱的种子在艰苦考验中日益长大。
在这样一次长征中,必会有抱怨和不满的声音出现,德隆对此确定无疑。他知道在北极冰原上朝着开放水域费力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在各种探险年鉴上,他还不记得看到过哪一次航行的艰难程度可以跟他们此刻相提并论。他估计,他们现在距离西伯利亚海岸有将近1000英里,但也有可能会途经新西伯利亚群岛——地图上对这些岛屿标注得很不清楚,也很少有人知道,那都是一些无人居住的永久冻土层岛屿。当然,也就没有可能会遇到救援。就他所知,地球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他们是否还活着。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达嫩豪所说,他们将在真正意义上“为生存而战”。德隆知道“只要朝正南方向走,我们必会到达开放水域”。几个月来,他们已经沦为牲畜,每天拉着挽具劳作12个小时。然而,至少有6个人病得太重而无法拉货——他们的铅中毒症状减退得很慢,“没有力气”。有些铅中毒患者如果不拉什么东西还能走,有些则虚弱得必须用病号雪橇拉着。最糟糕的是奇普。他连穿衣服的力气也没有,站都站不起来。因为不断地给他服用白兰地和鸦片,安布勒医生注意到奇普“感到非常疼痛、痉挛,而且得不到休息……当前的一切形势均对他的好转无益……他面色苍白,脉搏微弱”。
“怎么才能让他渡过难关?”德隆对老朋友奇普的状况深感忧虑,“昨晚他整夜都在呻吟,翻来覆去。我真的很担心他。”
德隆知道,完成这次撤退的时机稍纵即逝:他们只有能支撑60天的补给。然后或许还能靠吃狗维持几周,但那以后就无以为继了。食物储备有限,北极的夏日也屈指可数。德隆船长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抵达西伯利亚。这是一场与时间和现有的食物量争分夺秒的战役——他们不但要移动得快,还必须高效。然而,在这到处是雪浆和水坑的长路上,他们一样也做不到。德隆以极大的克制轻描淡写道:“我们的前景不怎么令人振奋。”他不知道队员们那点不可或缺的好脾气何时会耗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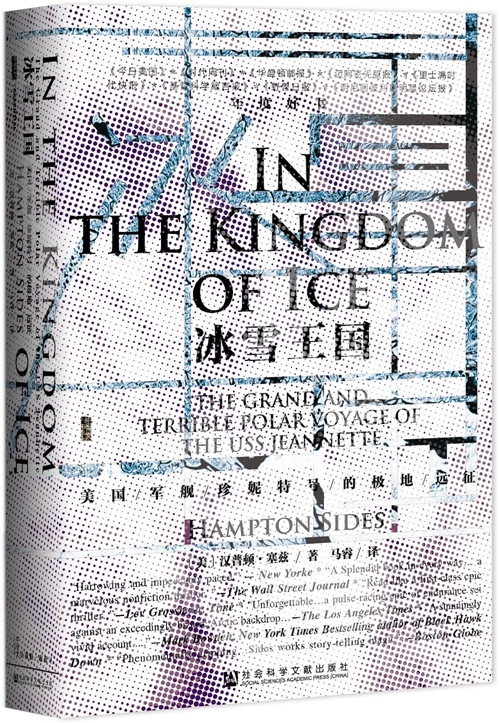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