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吴芳思谈中国经典与七十年代中国经历

吴芳思(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与吴芳思相熟多年,也一直在关注她的著述。她写过中国旅游指南,写过关于敦煌、丝绸之路、秦始皇的学术著作。她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去过中国么?》(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一度引发许多争议。2013年从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之后,吴芳思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与写作。她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古今文学选萃》(Great Books of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7月初,在吴芳思北伦敦竹影婆娑的寓所,与她聊起这本新著、她七十年代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她的其他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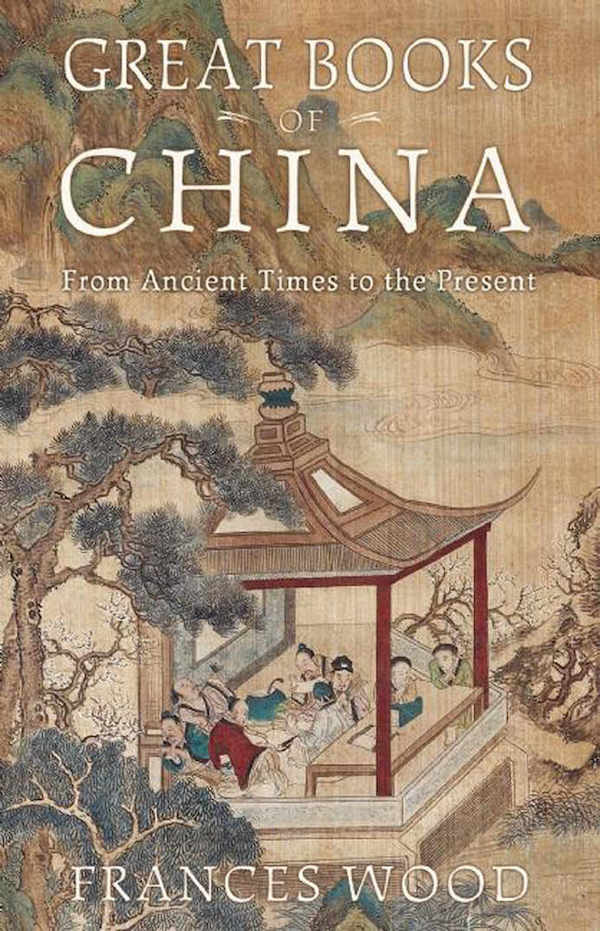
吴芳思:这本书由美国Bluebridge 出版社出版,他们出过各国文学选萃,例如《俄国文学选萃》等,这本《中国古今文学选萃》是其中之一。一开始他们希望我能选一百本书,但我觉得太多,所以最后选了六十六种,而且并不都是文学作品,也有技术类书籍。有些作家也不止一本,比如老舍和鲁迅。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您写到,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 说他在中国时,会有中国导游与他讨论《包法利夫人》,并感叹在法国,不可能有导游会知道李白或杜甫。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了解,要胜过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吴芳思:对,我觉得中国一般读者对西方文学的了解,肯定超过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莎士比亚剧作全集在1954年就被翻译到中国了,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很流行,狄更斯、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的知名度不亚于中国的本土作家。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几乎全无知晓。我也有与班巴诺类似的经历,九十年代时,我在上海乘出租车,有一次就看到司机手边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本书已经翻阅得很破旧了,英国的出租车司机绝对不会读《儒林外史》或《红楼梦》,如果你看到他们读福尔摩斯,那已经很走运了。
在我刚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时,大英图书馆有一个规定——不收藏翻译作品。很奇怪吧,哪有这么多的人能读懂原文呢?
这本《中国古今文学选萃》,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吴芳思:这些作品都是我个人的选择,都是我读过的书。但我也希望覆盖面能比较广,所以我也选了一些在中国文学上有价值,但我个人并不一定喜欢的作品。西方有些大学出版过“中国文学作品选”,其中有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章节的翻译,那些书很有学术价值,但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在这本《选萃》,我对书的定义更广,我希望能包括一些技术书籍、游记、关于园艺或绘画的书,所以,我选择了《天工开物》《鲁班经》《园冶》等,我更希望面对一般读者。
这些书中,哪些是您最喜欢的作品?哪些是您自己并不喜欢但是您觉得还是需要被收入进来的?
吴芳思:我最喜欢《园冶》《天工开物》《儒林外史》《围城》《老残游记》《风雪夜归人》。我在北京看了吴祖光的这出戏,排演得太好了,后来我在《哥伦比亚中国当代戏剧选集》中找到了这个剧作的译本。
我个人不太喜欢的是《易经》《论语》。孔子的东西我很不喜欢,我觉得孔子很保守,他的哲学很势利,总是在说君子和小人,对小人女人都很看不起, 总是在讲那些人际关系。从《论语》中能看出他是很难弄的一个人,什么都要井然有序,否则他就坐立不安,这样的人,我是没有耐心的。我也不喜欢徐霞客。《三国演义》中,我只喜欢关于实用计策的部分,我觉得《西游记》有点像托尔金的《指环王》,我同样不喜欢。

吴芳思:对,对我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选的书都已有西文译本,或至少有些章节被翻译成西文,主要是英文和法文。这样如果读者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他们就可以读到。推荐别人无法读到的书,是没用的。大多数有英文译本,有些是法文译本。并不是说所有的译本都很好,有些译本很糟糕,但至少读者能知道个大概。
我很感兴趣的是您在附录注释中对各个译本的评价。您会说这个译本是triumph, 例如David Hawkes 和John Minford 翻译的《红楼梦》,那当然是最高的评价了。《金瓶梅》Andre Levy的法译本是brilliant, 《肉蒲团》的Patrick Hannan的译本是fine, 有的译本只是good, 而大多数您未作评论。
吴芳思:对我来说,fine比good要更好一些。Good是还过得去,fine是很不错了,翻译不容易,fine 就表达了我的敬意了。比如《围城》的翻译就算不上是好的翻译,这本书特别难翻译,因为里面有许多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的隐喻,你翻译的时候,可能总会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
这本书收入的最后一本是戴厚英的《人啊人》,是您自己1985年的译本,英文书名是Stone of the Wall。您为什么没有用原书名?您和戴厚英熟悉么?
吴芳思:八十年代初我去中国,当时我正在编辑一本女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我就想寻找可以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杨宪益、戴乃迭说有人送了他们一本戴厚英的《人啊人》,他们自己并不喜欢这位作家,但还是推荐了这本书给我。这是第一本让我无法释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伤痕文学,充满了抱怨,读起来让人沮丧。我觉得这本书与众不同,我很喜欢,就着手翻译。翻译之后找出版社并不容易。我不想成为专业的翻译家,戴厚英的其他作品,我也并不喜欢。
我是好几年之后才在慕尼黑遇到戴厚英的,我对她还有些戒备之心,我记得杨宪益夫妇告诉我,她是个红卫兵,我说当年所有的人都是红卫兵吧。他们说“有些红卫兵比一般的红卫兵要糟糕很多”,话是咬牙切齿般说出来的。戴厚英后来被谋杀时,我正好在中国,也听到一些议论,说她的一位穷亲戚谋财害命,因为她把许多钱款捐给寺院,可能是对“文革”期间的作为有罪恶感。我觉得她的一生是个比较悲惨的故事。
我觉得用“humanity”这个概念来翻译“人”太广了,小说中的人特指“中国人”。因为书中有很长一段是关于长城与中国,我就用这个意象做了题目。

吴芳思:我之所以选到八十年代初,是因为八十年代后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过来,许多作家都有经纪人,也有出版社推广他们,我觉得他们已经吸引到足够的注意力了。现在,许多出版社都把眼光投向中国,希望能够挖掘出下一位畅销或得奖的中国作家。
而且,对于后来的许多写作潮流,我并不喜欢,例如所谓“女性作家写作”,《上海宝贝》之类。如果一定要我选,我会选择裘小龙的作品,特别是《红英之死》,那本就是关于戴厚英之死的。
您会不会选张戎的《鸿》?
吴芳思:肯定不会。《鸿》是经纪人和出版社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张戎之前的《宋庆龄传》,之后的《毛泽东传》《慈禧传》,都很差劲,错误百出。可惜的是,许多不了解中国的人以为《鸿》就代表中国,这很让人气愤。
莫言的著作呢?
吴芳思:我也不很喜欢莫言,我只能用good,而不能用fine来描述他的作品。而且,莫言已经有强大的翻译出版推销团队,不需要我介绍。我更希望能介绍八十年代之前不为西方人所知的中国书籍和作品。

吴芳思:是吗?我不认识余秋雨,更不知道他那么不讨人喜欢。编辑给了我这两本书让我写评论,我觉得他的文字确实与阿兰·贝内特和比尔·布莱森很相似,他们写的都是那种让人舒服的文字,心灵鸡汤类。但这两本书的翻译都非常糟糕,有些段落简直就是Google 翻译出来的,我觉得很可惜。我前几天还在与陶瓷专家柯玫瑰(Rose Kerr)提起此事,余秋雨是余姚人,住在余姚瓷窑边上,他写到在余姚的湖里游泳,看到湖底有陶瓷残片。这多有意思啊,就像住在斯达夫郡能够看到湖底的威奇伍德瓷器碎片一样,也不知是他原文就没有写到,还是在翻译中遗失了,一般读者肯定读不到其中的妙处。
七十年代在中国
退休前,您一直是大英图书馆中文部的掌门人。您是怎么开始学习汉语的?怎么会对中国文化那么感兴趣?您的家庭是否很早就与中国有关系?
吴芳思:我一直以为在我之前,我的家族里是没人与中国有关系的。最近几年才发现,我有一位姨父还真与中国有关系。他的父亲是传教士,他自己出生在中国,在烟台上的学。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与中国的关系,也从来没有谈起过中国。
1967年,我去剑桥大学读书,选择学习汉语,主要是因为我对语言很感兴趣,当时我已经会说法语和西班牙语,我就很傲慢得要去学习最难、与西方语言最不同的一种语言。我当时在阿拉伯语、日语或汉语中选择,其实是很随意地选择了汉语。当时我觉得日本人太压抑,人都那么有礼貌,而穆斯林的世界中,妇女很没地位。虽然中国当时也不是很开放,但仍让人觉得那是个真实的地方。
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了四年汉语,因为从没想到会有机会去中国,感觉就像是在学拉丁语。我的一位老师是莎士比亚专家,来英国许多年,但得靠教语言谋生,还有他的太太,也是汉语老师。教我们口语的是台湾来的老师,我们学了许多台湾的客气话。
您七十年代还是有机会去了中国,您2000年的回忆录《在北京练习扔手榴弹:我的“文革”经历》(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 My Par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就写了那段时间的经历。
回到英国后,我先在大英图书馆,然后在亚非学院中工作。1975年,我作为交换学生又回到中国,这是英国文化协会的交流项目,时长一年,我们是第三届。十个中国学生来英国,都是外交部派来的,他们以后都成为大使之类的重要人物,官位很高。而我们这一群有点像乌合之众,有些你也认识,例如奚安竹(Andrew Seaton)、艾华(Harriet Evans)、马克乐(Beth McKillop)、柯玫瑰等。当时那一届外国学生有五十来个欧洲人,十个英国人, 几个意大利人,几个法国人,两个新西兰人,三个澳大利亚人,十个德国人。没有美国学生。当然,还有许多非洲、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学。
我记得BBC的一档“荒岛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 节目采访您时,您选择的八张带到荒岛上去的唱片中,有一张是广播体操的音乐,因为当时你们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和中国学生一样做广播体操。你是不是特别珍惜那段时间?
吴芳思:我在历史班,班里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从工厂里调上来进修的。如果你是文学班的,那班里就只有外国学生。所以我们历史班要比文学班有意思得多。我们和中国学生一样,每天早上要做广播体操。我们还去一家火车头工厂工作,去四季青公社劳动,就在颐和园南面,风景非常漂亮。我们收割麦子,插秧,捆白菜。我们还在北大挖防空洞,挖防空洞都在夜里,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像个英雄。上课时,老师讲课很小心,因为有中国学生,许多事不能公开说。唯一与中国学生不同的是,我们是不能去学军,他们都去学军了,我们留在北京。
扔手榴弹是在语言学院时,体育课的内容。我们先在语言学院,然后去了北大。
那时在北京,你们预感到中国马上就要开始巨大的变化么?
吴芳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中国马上就要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觉得中国永远就会是那样。那时也觉得中国离英国特别遥远,写一封信要两个星期才到,打电话要预约很久。我们也想家,但我们都很年轻,在一起也很开心,以后我们都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这批外国学生。当时我们不敢与中国同学交朋友,根本没办法问中国同学要联系地址之类。
我们也看到,虽然当时仍在“文革”中,中国人也在试图寻找生活的乐趣,并不都是悲惨呀痛苦呀。饭菜很好吃,当时的衣服虽然很简单,但女孩子们还是爱美,外套会束个腰,或在里面穿件很好看的花衬衫。还有布鞋,那么与众不同,也很好看。
我非常想念当时的北京,那时我常骑着自行车从北大进城,都是平房,四合院,那么安静。现在的北京完全不同了。绍兴是另一个我以前非常喜欢的地方,现在也变得太厉害。

您的著作样式很多,您曾写过旅游书《中国蓝色导游》(Blue Guide to China),我的许多英国朋友都曾以您这本书作为旅行指南。对他们来说,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里,您这本书是最实用的旅行指南,书中的幽默也常常让旅途中的烦恼化为烟云。当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最有争议的书大概要数《马可波罗去过中国么?》。这本书出版已经有二十多年,有没有新的资料出现?您还持同样的观点么?
西方人去中国,回来后写下的文字,这一直是您所关注的。2009年,您出版了《中国的魅力:从马可波罗到J. G. 巴拉德》(The Lure of China: Writers from Marco Polo to J. G. Ballard),此书精选了许多作家、探险家、收藏家的小说、游记、回忆录、书信等各种文字的片段。能否请您谈谈这本书?
我希望人们能够把这本书当成是本工具书,可以作为索引和导读,如果读者对哪个年代哪位作家更感兴趣,可以深入阅读下去。
2014年,一战百年纪念时,您出版了一本小书《禁止野餐:一战期间乱象中国的外交》(Picnics Prohibited: Diplomacy in a Chaotic Chin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此书在去年增补出版为 《背叛的盟友:中国与一战》(The 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其中很多内容中国学者都不太知晓,可以说您填补了许多空白。
为了写这本书,我花了许多时间在英国档案馆,研究当时来自北京的外交报告。每次从档案馆出来,都让我非常气愤。许多人认为一战只是欧洲的战役,这是不对的。一战刚刚开始时,日本就侵入青岛,但因为日本已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日本被视为盟友,盟国对它在中国的作为不闻不问。1914年,中华民国只有两岁,在两千多年的王朝之后,国民党极力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但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只是西方的嘲笑。从档案馆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西方外交官对中华民国的评论那么粗鲁,他们说中国的议会很小儿科,这种消极的态度让我气愤。
我非常同情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曾三次试图加入盟国,但到1917年8月才成功,正式宣战。而且,中国在1916年就开始派遣中国劳工,负责前线的后勤保障工作,这些劳工为一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长期被遗忘。凡尔赛条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更是真正的背叛。
还有当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回来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写他们去逛集市,去寺院参观,去野餐,都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快乐时光。他们好像完全不知道,整个中国在挣扎,中国人的生活那么苦难悲惨。
记得当时您为《上海书评》写了一篇题为《被出卖与被背叛:中国与一战》,在文章结尾时,您写道:“如果要在中国庆祝或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值得记住的重要时刻或许是1916年,那年中国派遣了第一批劳工,这些强壮的山东农民,给包括法国总理在内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或者是1917年,那年中国勇敢地对外宣战了。但也许,庆祝应该专属于1919年5月4日,因为这一天真正地回应了那些欧洲盟国在凡尔赛悍然做出的决定,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改变。”
您目前的研究与写作项目是什么?
吴芳思:我现在的兴趣点还是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中国劳工是话题之一,另外,欧洲盟国在凡尔赛会议关于中国命运的那些讨论,也非常有意思,我希望能够根据当时的谈话写出一个剧本。
2017年7月3日采访,8月14日完成整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