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化语境下的“旅行”:移民潮背后的帝国秩序
大航海时代伊始,欧洲殖民者对欧洲之外的“荒蛮土地”的物质掠夺、知识与权力的建构,已经广泛为人们所讨论,而与其相伴而生的旅行书写,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作用?而时至今日,在种种“地球是平的”的全球化表述之中,曾经的帝国意识形态是否还起作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深入地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节选了本书的最后一章,考察全球化的今天,旅行叙事的老传统如何得到回收利用,以描写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移民和置换的当代经验,从而创造关于全球化的主题。小标为编者所加。
20世纪80和90年代,帝国的一个新阶段在世界各地展开。苏联集团瓦解带来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秩序,而通信革命则改变每一种可能性的地图。大规模变迁和加速的人类流动性模式,是这种秩序关键的新元素之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穷国向较富有国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以及大众旅游。在21世纪开始的今天,旅游业是世界上仅次于毒品交易的最大产业。此外,劳动力迁移导致定居者从欧洲向外殖民扩张的逆转。今天,在欧洲和北美每一座城市,都有流散社群存在,它们来自全球多个地方,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前殖民地。几乎一半的苏里南公民居住在荷兰。20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面临急剧的人口衰落,将其先前与南美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西班牙政府开始邀请阿根廷人来居住在乡村,完全改变了阿根廷19世纪邀请欧洲定居者的状况。西班牙重启这一策略,与其原初的种族和种族主义动机是一样的。19世纪最初十年末期,阿根廷试图消除土著人和黑人在人口中的存在;一个世纪后,西班牙试图阻止来自非洲的移民。
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2000年居住在美国的十个人中,有一个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另外百分之十的人中,父母有一方在另一个国家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入学的半数孩子说的语言不是英语。百分之十五的圭亚那人口居住在纽约市。这种人口变迁影响到移民来源地和抵达地的社会、制度、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旅行者仍然旅行,而且旅行书依然有人写、有人读,但是过去三十年间的戏剧性变迁和增速要求我们学会通过流动性思考。“全球化”这个词之出现,旨在为20世纪末全球关系的划时代变化命名。不过其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也许是一个关于进步的叙事之死亡,而这一叙事却为世界各地非常不同状况下的人们分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根据其目的论的设计,包括全人类在内,但它正慢慢失去对移民和行动的控制。到2007年的今天,有关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将在某个时刻平等“发达”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们要记得,不久之前,这还是一个全球共享的期望。我希望证明,本书考察的旅行书写的语词和惯例依然与我们同在,就像它们所编码的帝国关系一样,常常以变异的形式存在。在这个迅速变革的当下,那些惯例继续产生意义、定位主体,并对世界施魔、祛魅、再施魔。
全球新秩序的旅行故事:从殖民地到宗主国的迁移
对许多人来说,新全球秩序的帝国特征,暂时被一种有关自由贸易、人员流动、开放市场、全球同合的合法化语言所遮蔽。不过,人们从前殖民地国家向前殖民者城市的反向流散,主要是由多国资本主义的最新方案引起的,这个方案就是,通过国内外债务和低工资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随着人员流动,巨额财富以债务清算、庇护款、疯狂夸大的利润形式不断从穷国流向富国。富国联盟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新一波的掠夺,以公司利润的名义将极端严厉的社会经济条件强加给弱国的全体居民。国家被迫放弃其监护和再分配功能,不得不为商业阶层服务,满足多国投资者的利益。流动劳工收回部分被掠夺的财富,将其重新分配回到其源头。今天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包括中美洲、墨西哥、加勒比地区、菲律宾、印度,依赖这笔沿着家庭路线寄回的钱维持稳定。
对于这些反向流散者来说,宗主国是一个利己主义和好恶相克的主人。本书自始至终一直在思考,在早先几个世纪里,人们如何通过故事向自己描述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并用故事创造出想象他们所经历变迁的方式。现在情况依然如此。作为研究旅行文学的学者,我在20世纪90年代不由得发现,我读到的日报正在复活我在第五章谓之的生存文学。我用那个术语指称三百年前从遥远的海岸传回欧洲的有关苦难和生存、怪物和奇迹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接近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文类以一种新的伪装重现,这一次是在宗主国自己的边界。各种报纸开始刊登海难故事,例如九百名库尔德人在1999年春天不是在火地岛而是在法国南部海岸搁浅那样的故事。2007年初,在本版付印之时,这些事情依然每天都发生。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早晨,我的报纸报道称,一艘载有五十人,从突尼斯前往西西里的橡皮艇失事。幸存者说,十九人身亡,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大海。偷渡者的故事也回来了,不过今天这些故事讲述的,不是欧洲男孩藏在甲板下前往金银岛,而是东欧家庭紧抱在英法之间隧道里的火车下面,以及非洲男孩被发现在降落欧洲机场的飞机轮子盖里冻死。1998年,偷渡者的故事在美国以一种耸人听闻的形式重现在埃利安 · 冈萨雷斯(Elián González)的戏剧中,这是一位被冲到佛罗里达海岸的五岁古巴孩子。在电视上播出数周后,这个例子在古巴裔美国人当中闹得满城风雨。它充满当代政治以及古老的诗学:有些佛罗里达人说,这孩子是婴儿耶稣转世并且被海豚所救。

有关死亡和拯救的故事大量流通,它们不是从撒哈拉而是从亚利桑那沙漠传出的,就像2000年夏天的那个故事,当时一位年轻的萨尔瓦多母亲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从她死去的怀抱中人们解救出一个婴儿。救助者是边境警卫队,在较老的撒哈拉故事中,这个角色是由路过的贝都因人扮演的。当然,这种对照具有反讽意义。1999年,令人窒息的奴隶船噩梦在来自旧金山港的一则生动报道中重演。十八名中国劳工因在一艘货轮深处一个集装箱中受尽折磨而发疯,而他们的七个同伴已经在那里死去。几个月后,四十三名中国人在一辆将他们从荷兰偷渡过来的卡车后面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一故事令英国举国震惊。那之后数周,在里奥格兰德河岸,一大堆人看着两个试图越界进入美国的人溺水而死。这一事件在电视上进行直播。2001年初,白人对黑人动用私刑的情况死灰复燃,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西班牙南部海岸。囚禁叙事在洛杉矶、迪拜、米兰、曼谷这样的地方重生,表现为与家政服务、血汗工厂、妓院中的卖身契、强制监禁有关的故事。当奴隶制本身被发现在西非卷土重来时,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视之为一个“来自19世纪的景观”。他报道说,在阿比让,姑娘们的价格是五个英镑。与此同时,欧洲发现自己有着成千上万被奴役的女性性奴,她们中许多是俄罗斯人和东欧人。仿佛是一直在附近等待似的,废奴主义自动掸去灰尘重新出现,它由伦敦反奴隶制学会领导,该学会创建于1787年,现在叫反奴隶制国际。生活在1980年的任何人都想象不到,在新千禧年之交,这竟然是我们还会牵肠挂肚的事情。
17和18世纪,上演新全球秩序的故事来自遥远的海岸。在20世纪90年代巩固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中,故事发生在宗主国自己的边界,有时正好就在其居民的眼前。如同过去有关死亡和生存的文学一样,每天在世界报纸出现的戏剧所起的作用,是上演新的行星秩序,一种新近突变的帝国秩序,以及创造其主体、其等级制度、其关系。这些不同之处具有启发性。在17和18世纪,是幸存者讲述海难、囚禁故事偷渡故事等等,他们是按照天意(一个关键词)活下来讲故事者。根据定义,这种故事总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确认一种新型宗主国全球性,并往往是帝国的主体之可行性。这些主体是他们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标题中。今天对这种档案的回收利用,主要讲述死去的无名者;叙述是第三人称。受不同欲望驱使,当代的变体表演的不是离去和归来,而是拒绝和驱逐的戏剧。旅行的劳动者死在走向新生活的途中,幸存者被送回他们来的地方。也有成功故事——许多移民的确取得成功。可是死亡戏剧才是在宗主国的公众想象中有吸引力和产生共鸣的东西。
这到底是怎么啦?在我看来,关于死亡和绝望的戏剧,并不只是反移民偏执狂的一种表达。它们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记录,一种现状核实法,针对的是欢欣鼓舞的超级利润决算和史诗般的并购交易,这些东西占据着商业版面并使那些乘商务舱者痴迷。宗主国在这些叙事中将自己预设成一个要塞,靠暴力的排除得以维持,并遭到绝望者的攻击,而这些人不该比要塞内的那些人得到的更少,只不过他们没那么幸运而已。它是否在向自己展示其愈益加剧的合法性危机?抑或其作用只是提醒在里面的那些人,他们何等幸运并受到怎样的威胁?
尽管存在有关死亡的故事,事实是前殖民地的流散者已经在宗主国落户,采取的方式与殖民主义定居者毫无可比性。今天几乎每一个美国城镇都有一个墨西哥人或中美洲人聚居地。遍布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村落,在美国都有成熟的卫星社群,人员、商品、金钱在那里不停地来回。飞地由此诞生。在佛罗里达有讲佐齐尔族语的公寓群,在纽约有讲纳瓦特尔语的建筑群,都是根据土著人的社会关系重组的。来自瓦哈卡的米斯泰克人拥有一个跨国的网络,从埃斯孔迪多港到安克雷奇。如同启蒙时期的旅行者满载珍品和标本回家一样,当代全球劳动力从另外一个方向归来,带着将会卖掉以支付旅费的成箱衣服、汽车零部件、盒装器具、超大捆绑的货物。正如来自印度的建筑音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回响一样,今天的墨西哥城镇和村庄遍布着两层的房子,其建筑便是钱来自国外的证明。19世纪,英国人的次子们前往印度或加勒比地区去发财;今天来自普埃布拉、圣萨尔瓦多或昆卡的年轻人,被派往洛杉矶、芝加哥或盐湖城,挣取购置土地、创业、支付教育或医疗护理费的现金。最近人们专门为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萨波潘圣母像在加利福尼亚的信徒建造了一个新版圣母像。这个新的化身,被恰当地称作“旅行者”。

“流动”所掩盖的事实:全球财富分配的垂直性
我们常被要求将这种运动想象为“流动”(flow),这个隐喻暗示一个借助重力将会自动到达水平平衡的自然过程。流动是全球化首选的隐喻。流动的水平意象,使得市场表现为完美的平均主义者。像重力一样,无论它产生什么效果,都是根据定义假定要产生的效果。不容对它们有任何怀疑。可是旅行故事却揭露流动隐喻之违反常理。窒息而死的中国工人并没有在卡车后面流动;格兰德河也许一直在流动,但河里溺亡的年轻人没有流动。金钱没有流动。它是被邮寄的,而且寄钱的需要,常常将移居的工人局限在国外名副其实的束缚之中。“流动”掩盖这个事实: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是由人们做出的具有伦理维度的决定运作的。这些决定构建一个在隐喻意义上蔑视重力的世界。它的力量不是水平的,而是垂直的。这些力量将财富抽进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经济贫困和背井离乡却在蔓延。顶层和底层都在我们眼前消退。
正如我提及的某些例子暗示的那样,人类世界的这些大规模重新配置,产生新型的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移居者用一种往往总是“远离”(awayness)的形式,使用他们的公民身份。家乡的社群根据其侨居国外移民的来往,对惯常生活进行重新配置。卫星社群现象往往既在字面意义上,又在存在意义上暗示双重公民身份,就是让自我变成两个,在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中拥有平行的身份。这可以既是一种碎片化的经历,又是一种给予权力的经历。它经常,尽管不是总是,发生在匮乏、不安全、受限选择的条件之下。市场的数学并不区分在出生地挣钱维持的生活与作为移民在外挣钱维持的生活,认识到这一点令人震惊。换言之,流动劳动强加给个人、家庭、社群的无法估算的费用,代际和夫妻关系的中断,导师、管理者、教师的缺席对儿童造成的损失并没有考虑在内—所有这些都被统计数字所掩盖,但是会令任何访问社会结构支离破碎的农村社群的人不知所措。
各种新的流动性正在破坏一种最想当然的人类社会生活规范的垄断地位,也就是逗留的规范性。当萨波潘圣母像生成其旅行的新复制品“旅行者”时,原作则获得一个新的名字,“逗留者”。在那之前,逗留的状态并不需要命名。尽管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世界人口被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处于移民流之中,但是流动性(“别处和远离”)与非流动性(“家和此地”)相对应的规范性背景,不再是世界地缘社会安排的基础,也不是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的唯一标准。我们将会需要新的地理学家,图绘被技术、好奇心、必然性、帝国的巨大动员力再次重新配置的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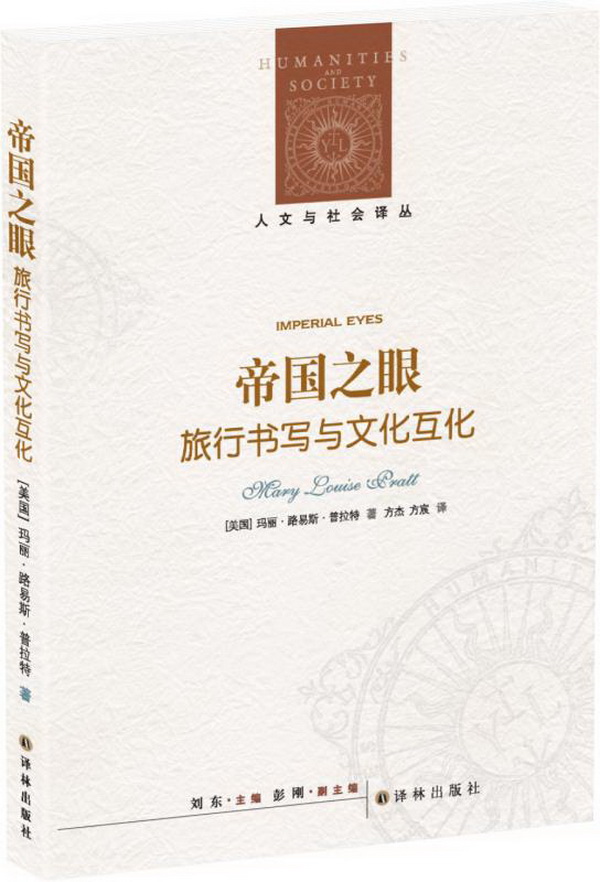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