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元钱购画的“小朋友画廊”:从“苦”慈善到“酷”慈善
在北京,一块钱能做什么?不那么环保的做法是买一个外带的打包盒,“环保”一点的选择是骑一段共享单车。 可从昨天开始,一元钱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它能让我们做出更人性、更有品位、更时尚的选择,可以购买1幅特殊人群的画作(数字版),当作手机屏保, 而每购买一副画作,即向该公益项目以及它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捐赠。最后你还可以分享到朋友圈,加上点儿评语和感慨,在表达爱心的同时顺便展示一下自己不俗的艺术品位。从指尖到屏幕,一元钱打破了我们和“他们”(自闭、脑瘫、精神障碍,智力障碍等特殊人群)的距离。

但是除了冰桶挑战,如此强大的筹款能力还唤醒公众关于罗一笑事件的记忆。这次人们的爱心是否会被错放? 官方网站说这个叫“无障碍艺途”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WABC)的公益组织是“一个针对脑部残疾人群绘画潜能开发课程和艺术展览项目的民非组织”。这里需要划下重点,这是个给特殊人群上课和办艺术展览的公益组织,于是和钱相关的花样疑问接踵而来。它是否具有公募资格?腾讯平台是否会分账?筹集到的善款怎么用?特殊人群是否可以获得版权?腾讯公益和“无障碍艺途”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做了回应。当然除了媒体,更多捐钱的朋友打心眼里并不着急知道钱流向何处,毕竟只有一块钱。有位朋友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无论如何,只有一块钱, 宁可错信,也不能错过帮助一个小朋友”。 况且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被各种眼泪或悲惨故事绑架,而是被暖心抓人的色彩和明亮丰富的主题以及恰到好处的音乐打动,为艺术而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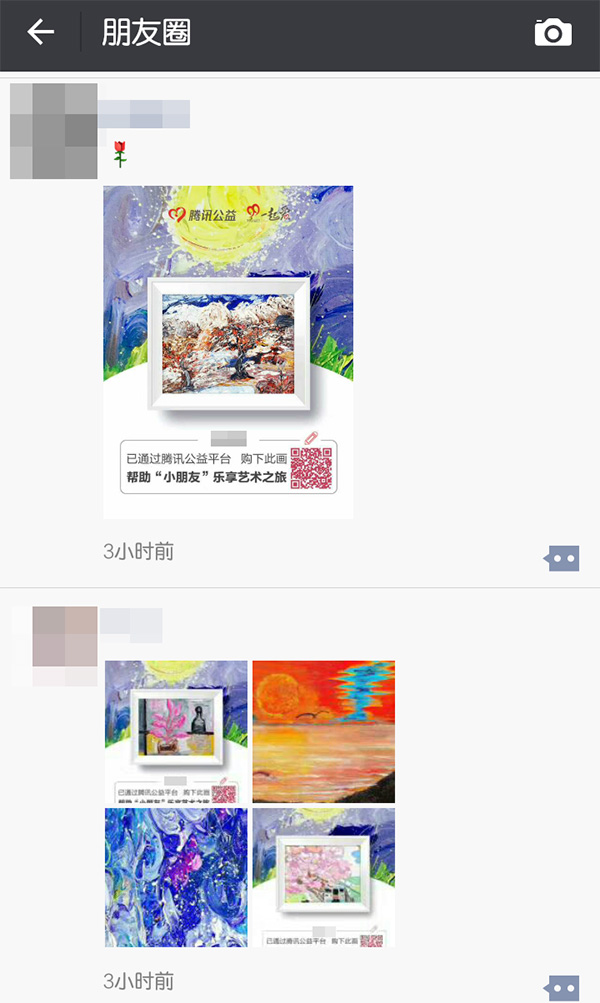
成为筹款人标杆的冰桶挑战还需要一桶水,拿得出手的捐款数和经得起推敲的社交圈,以致于后面直接沦落为名人间的社交游戏。而“小朋友画廊”则巧妙地规避了这样的风险,均值的小额降低爱心的门槛,平台内部资源的整合(腾讯公益和微信朋友圈)让我们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对他人的帮助,降低了行动的门槛。首先, 一元钱,在许多人的数学里,几乎是免费的同义词。这个爱心之举的潜台词是,“免费”获得一幅好看的画作(甚至有网友一开始以为可以一元钱拍下原作)。而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这些媒体技术又让这“爱心之举”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我们只需要付出感动就可以完成对特殊群体的帮助,并且实时地“监控”自己付出的回报。 这当然地得益于腾讯平台的品牌效应和资源整合。在《新京报》对“无障碍艺途”北京工作站的采访中,一位负责人就明确地提到,腾讯公益平台是这次筹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最开始的H5界面,凸显的是腾讯公益而不是WABC或者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一开始只记得腾讯公益,才会有关于腾讯会不会分账的疑问。正是腾讯平台的品牌效应,让许多人在行动前后都不关心发起人是谁,更别说去关注公益的目的是什么;至于帮助的对象中自闭群体和脑瘫的区别,是不是都是“小朋友”,更是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活动的发酵和传播过程中,精神和智力障碍群体被简化或误读为自闭症的“小朋友”,以及为什么各种关于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儿童的故事被调用起来丰富公众对这个群体的想象。
而这“现象级”的成功以及随后的争议也把“无障碍艺途”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WABC)从背景带到了前台。比起钱怎么用的问题,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个公益组织究竟是一个康复组织,还是选秀工作室?官方网站的说明是,“通过建立社区站点工作室的形式,在现有的社区的服务中心开设艺术潜能开发课程,给喜爱绘画的学员一个展示自己、培养兴趣的机会,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康复功能。”我们来做个阅读理解,这里说的是,教学功能为主,康复功能为辅。如果是教学功能为主,我们也忍不住要打个问号。目前被组织无数次提到的明星成员,捷麟和小龙,都在之前接受过绘画训练。 机构负责人现在有些回避“寻找中国的梵高”这个口号了,虽然它依然悬挂在工作室的墙壁上。他们大概也意识到,这个口号会增加他们作为“星探”的嫌疑。因为大家都忍不住要问,这样一个致力于帮助特殊群体的机构能够找到(教出)多少个梵高?如果都是梵高了,那还能是梵高吗?如果只有几个梵高,那其他人呢?

而与这些模糊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创始人对成功的确定,他已经俨然把筹款的成功置换为这种教育+康复模式的成功;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取代了对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有限性的反思和讨论。于是在人们的指尖之间,“一元钱购画”的公益活动背后,一个逻辑链条一环扣一环地完成: 几幅好看的画作被置换为特殊群体的“成功”或者“康复”的标志,被置换为对艺术疗法的肯定,被置换为对某个公益组织的肯定,于是品牌化之路开始。
后人道主义时代的“酷”慈善
其实这样的活动集中反映了“后人道主义时代”的特点。研究媒介和人道主义学者Lillie Chouliaraki定义的后人道主义时代开始于70年代。从那时候开始,在人道主义领域里,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别人这个根本性问题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变。之前,或者因为“共同人性”,帮助我们的同胞或同类是一种 “天经地义”的事情;或者为了社会正义和公正,改变产生经济剥削和苦难的社会关系,消灭不幸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两个宏大叙事都随着冷战结束而失效。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也好,私人慈善基金会也好,都无法通过零散的、短期的、个体化的资助项目解决普遍的,长期的、结构性的不公平问题。而且在各种试图博取旁观者同情的叙事里,各种受助者变成了等待救援、消极被动的“他者”。它在“高高在上”的救助者和“可怜无助”的求助者之间建立新的不平等,恩赐色彩太浓厚,因此也逐渐失去市场。在面对看似无法根除的顽疾和反反复复的问题,昔日富有同情心的公众正在对各种苦难叙事产生免疫和疲劳,不愿意再因为直面“他者之痛”而感到无力甚至愤怒,不愿意再因为无力改变而饱受愧疚感的折磨。于是快乐、正能量、时尚成为了主旋律。
2015年初,瑞森德与众筹网联合发布《2014中国公益众筹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公益众筹以倡导快乐公益为主旋律,让更多人享受公益投资的乐趣,更强调创新、梦想。而在这转变过程中,慈善公益机构越来越多地依靠企业的市场营销逻辑来进行筹款,依靠媒介数字技术来动员,以及通过表现积极主动的受助者和强调捐助者的“感觉良好”来应对同情疲劳的问题。

致力于解决不幸和不公平的慈善公益活动被置入到市场逻辑里,变成争夺爱心的竞争市场。除了平台,不幸能不能看见,会不会得到帮助,还取决于被置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中。正如我在《键盘上的爱心超市》里提到在慈善公益领域看到的各种议题企业家,动用各种市场营销策略和叙事技巧,来使得自己的慈善或者公益项目在爱心超市里胜出。不幸者不是因为自身的不幸而被帮助,不幸者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或者“作品”被看见才被帮助。在“小朋友画廊”里, 艺术作品替换了痛苦和不幸的叙事成为行动的主要动因。积极的受助者和感觉良好的捐助者取代了被动消极的受助者和怀有负疚感的捐助者。

尾声:“一元钱”的责任
在写这篇文章中,这个公益项目还没有安全地渡过“新闻反转期”,各式各样的质疑依然此起彼伏。与其信心满满地讨论扩张计划,该机构是否可以先把自家网站的“信息披露”一栏完善一下,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是否可以对自己项目做一些更深刻的反思,接受更专业的评估?还有“我们”这些事后诸葛,在轻松之间完成了爱心的投资同时是否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在数学里,一块钱很小。但在社会里, 以“我们”的形式被召唤并聚集起来的“一块钱”是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形塑力。如果意识到一块钱背后有着无法估量的社会责任,是否可以让我们在加入这种病毒式狂欢的时候更慎重和冷静?在发完朋友圈之后是否能够把对这个群体的关心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现在我们除了继续关注这个项目的后续报道,是否可以迈出一步,先主动去了解一下自闭,智力障碍,脑瘫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面临着什么样无法化约的困境?也许除了期待“他们”融入“我们”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可能:先改造自己、造就一个可以接受“他们”的社会。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