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灾难危机中的……问题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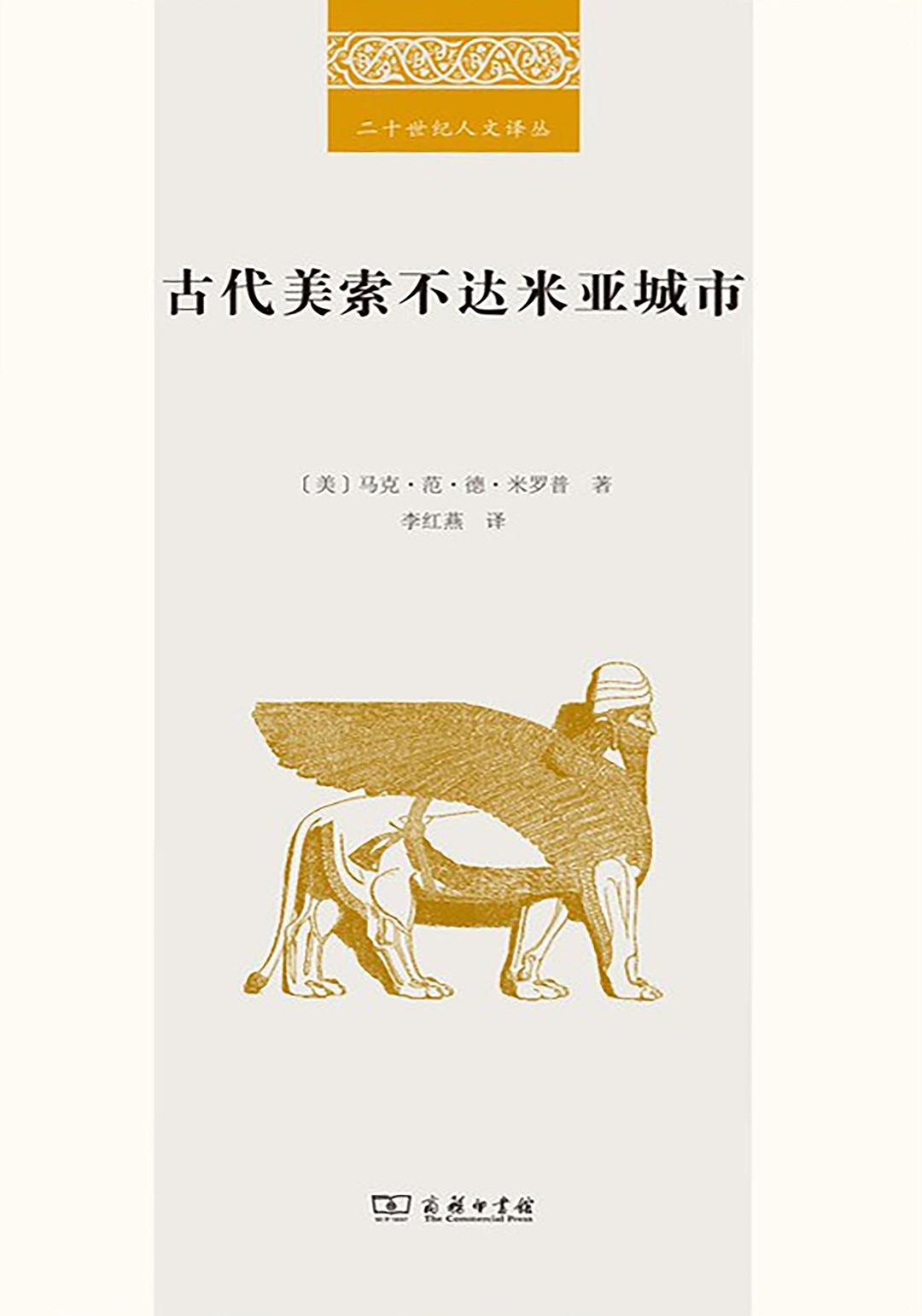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美]马克•范•德•米罗普著,李红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版,284页,96.00元
读美国学者马克·范·德·米罗普(Marc Van de Mieroop)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原书名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1997、1999;李红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感受很深的是作者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作为核心论题而提出的城市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对于并非专门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读者来说,城市史研究的阅读视角可能更接地气,尤其是结合对各种城市人为灾难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更有现实意义。
首先是在城市起源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在西方学者的城市史研究中,虽然关于城市起源的研究基本都会以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起点,但是正如作者所赞同的马里奥·利维拉尼的文章《古代近东城市与现代意识形态》(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City and Modern Ideologies)所清楚地阐明的,现代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进程的观点反映了不同学者及其时代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立场。米罗普说他在本书中提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模型并力图把这个模式融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古代城市”的理想类型之中,就是为了消解关于西方与东方对立、把希腊视为“我们的”文明发源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目的论观点。他认为“殖民式的说教在遭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猛烈批评的20年后,仍然存在于古代近东研究领域”,因此学术界亟须用后殖民时代的视角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装版前言,第5页)但是,米罗普并非简单地提出非西方的城市发展模型并使之与西方模式对立起来,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忽略了许多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东西方对比中存在的细微差别和变化,这就有延续东方学家观点的危险,即认为这些地区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其差异性可以通过把它们的特点归纳进简单的列表来解释。而他的目的是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作为一种类型与古希腊-罗马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观点进行比较,同样是在抽象概念的层面上进行有效性、有争议的对话。(引言,第9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反对西方中心论并不是要简单地论证一个对立性的非西方城市模型,也不是像某些全球史叙事中的那种宽宏接纳与叙事安排,而是要在二者之间建立跨文化、跨地域的对话模式,是在人类文化的整体性观照下的城市史叙事。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引领下,作者的研究得出结论是:“我们可以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符合韦伯和芬利描述的古代城市的类型。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代希腊和罗马之间的相似性大于不同。……我们希望,学者们对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世界都给予严肃的考量。”(252-253页) 虽然在书中作者并没有详细论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代希腊和罗马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对于西方城市史学者来说其间的相似性应该不难体会。
破除西方中心论是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重大议题,相应来说在城市史研究的场域中既有东西方视角的转换与整体性重构的问题,同时也应该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认识和破除政治中心论和权力中心论,只有破除固化的中心论模式才能呈现城市史研究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的多元模式。这既是城市史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史研究中的权力与地缘关系的问题。由此可以引出的具体问题意识很多,比如城市权力结构在某一严重失控时刻发生的变化、城市官僚系统的人员来源、文化背景、政绩考核体系、奖惩机制等等问题。在今天的城市史研究中,无论如何总是可以有各种线索和可能收集这些信息和相关史料,问题意识往往是发掘史料的最好向导。
其次是城市史研究内部的问题意识。一是大部分学者虽然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只探讨这个地区作为最早的城市文化发生地,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之后的发展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是必要的,而不是从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成就跳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人的情况”。(引言,第8页)问题很简单,城市起源只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城市发展应该是更重要的研究重心,但是如果以希腊-罗马城市为典型城市模型的观念来看,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起源叙事之后就结束了被研究的使命。这实际上是一种修正后的西方城市中心论,非西方城市仍然难以进入典型模式研究之中。二是城市史研究被政治研究所遮蔽,城市本身在历史学研究主流视野中只是一个地点方位与物质背景,主流历史叙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精神文化生活往往与城市史研究没有什么实质联系。米罗普指出,人类学、考古学对城市的研究在城市起源的议题结束后就中止了,“他们把后面的发展阶段留给了历史学者。然而,历史学者在关注其他问题,尤其是政治史的问题。同研究古代希腊的历史学者中的情况类似,城市经常被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学者定义为城邦,对它们的研究集中在它们的政治事件,而不是它们作为城市中心的功能”。(12页)“因此,即使在专家的概念中,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最终图像也是非常模糊的。”(13页)
实际上,一方面从历史学科的视角来看,城市史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在二战前后就在美国兴起,但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然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比如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那部影响挺大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1978)中,完全没有谈到城市史研究。另一方面,城市史本身的学术定位、研究方法及其相邻领域都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究竟是“城市传记”(Urban biography)——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2003)在我看来是这类研究视角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个案——还是宏观文明史中的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一直存在困惑与争议。米罗普之所以要强调他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研究属于“纯史学的研究”,表明了他的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定位的期望。他说“我希望阐明,城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种核心机构,整个文明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城市至关重要,如果不了解它们的城市背景,就不能正确地理解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的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引言,第8页)也就是说,要把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第三个问题是在政治史、军事史叙事主导下的历史分期、年代框架基本上把城市史研究视角中的历史连续性割裂了,以朝代更替为区分的历史分期成为历史叙事的主导模式。但是,“现有的分期是有缺陷的,并且容易误导人。它不是认可持续性的模式,而是强调不稳定和变化。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许多方面并不直接依赖被研究的王朝的气运时,这种割裂就更具有误导性了”。(17页)米罗普认为“政治和军事活动只是社会的两个方面,并且虽然它们确实展示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的变化的最重要的证据,这些变化在现代学术界也是被夸大了的”。(16页)他以A.利奥·奥本海姆(A.Leo Oppenheim)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说明“我们应该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到其根本的统一,而不是传统的历史时期的分隔”。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研究中,这样的问题是不难理解的:“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应该比统治阶级的民族或者语言背景更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基本的经济结构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前工业化社会。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从农业出现一直到石油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从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城市的管理功能和经济功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基本没有改变过。我们需要寻找这样的持续性,而不是聚焦政治力量显而易见的变化。”(17页)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中,持续性的确不应被历史叙事中的朝代划分所中断,这种连续性当然是由美索不达米亚特殊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同时要注意的是,承认这种连续性并非要把它视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模式。
毫无疑问,在很多其他城市的发展史上难以看到经济结构比统治阶级的政治结构、政治威权更有力量和更重要的历史情景。但是,从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来看,虽然作者讨论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历史的持续性和变化问题,对于近现代史研究也同样有参考价值,有值得思考的问题意识:无论是否持有历史连续性的观点,城市史研究都是对于绝对化的政治-军事史视角的重要纠正,尤其是对那种前后割裂的辉格历史叙事是一种有效的解毒剂。在政治-军事叙事中的时代剧变当然会在城市舞台上改换布景,甚至会使城市文明脱胎换骨、倒退到被异化的地步,但是历史延续性因素仍然会在城市的毛细血管中存在和流淌。尤其是在那种农村-城市的对立历史叙事中,在各种语言的“包围”“占领”“改造”等词汇中所表达的历史目的论最后都有可能在中、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被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所扬弃。
最后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问题意识是关于史料与历史叙事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史料的问题,比如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物质遗存和文献资料往往很有地域集中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反映曾经存在过的上百座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真实历史:“如果我们把研究只局限在一座城市,那么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大多数问题就面临缺乏或完全缺乏信息的状况。” (15页)而且在其他地区的城市史研究中经常被研究者广泛印证的那些史料种类在美索不达米亚这里是缺失的,例如人口统计表和税收记录。又比如在试图详细研究城市政府的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严重缺乏史料的困难。“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法庭解决土地所有权的争端,这表示市民接受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决定。但是我们能由此推断市民就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向更高一级的机构申诉吗?这样一个结论不能根据现有证据得出,于是变成了学者的直觉。”(123-124页)
因此,米罗普提出的问题意识和解决办法是:“如果我们摒弃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研究领域,尤其是语文学家中间的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资料的局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不那么严重了。文献的有或无通常是复原的前提,人们过于重视已有的材料,并且认为只有文献中提到的才是发生过的。”(18页)但是他认为“缺少资料可能有很多原因,而不是说明一种活动的缺乏。多数学者承认复原的偶然性,但还是从根本上认为一切都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了。相反,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被记录了下来,为什么其他可能的活动没有被记录下来。比如,我们没有食品或手工产品零售的记录,是因为这种销售没有发生,还是我们能换一种方式解释它们没有出现在记录中?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活动能够存在于文字记录之外,甚至只是接受它们可以发生这个事实就能让我们根据所知描绘出更丰富的图景”。(19页)米罗普的质疑既是合理的,也是很有想象力的。这就不仅是大胆假设了,同时也是如何大胆求证的问题。
在这部全面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专著中,具体的问题意识还表现在各个方面,上述只是几个主要方面。其实更应该说,这种关于问题意识的感受既是从阅读中得来的,同时也是从书本之外获得的。由于城市史的研究对象与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其问题意识除了来自学术语境之外,还会来自现实中的城市危机。在生活中人们总是容易被中心城市的外表所迷惑,只有在严重灾难过后,在它崩塌的废墟中才发现它的根基原来是那样的不可靠、那样的脆弱。尤其是在人为造成的巨大灾难中,作为城市根基的基本人性就彻底暴露出它的扭曲与缺失。当人们经历着或耳闻目睹着一座城市的灾难性剧变,过去那种关于某城市的固化假象在顷刻间轰然倒塌,这对于城市史研究反而是一种机遇,在危机意识中催生城市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例如城市的权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城市在区域中的支配性力量与受制约因素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经济模式的竞争应该如何解决、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并存的严重时刻城市的承受底线在哪里等等问题,在城市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该使城市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过去研究中被忽视、被遮蔽的问题。
为了突破文献史料的局限,米罗普把目光投向图像资料,在书中有好几个“图像证史”的研究案例。为了说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政治权力的第二种资源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以发现于乌鲁克的一个石花瓶上的一幅公元前四世纪晚期的浮雕(图2.1是其线描图)为例,画面“展示了一排裸体男子捧着装有农产品的器皿走向一位女神,通过她身后的符号确定其为生育女神伊南娜。在她面前站着城市统治者,描绘的形象比他的仆从更高大,身穿仪式长袍,显然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包括统治者和这位女神的丰产仪式一直到公元前18世纪都很盛行。有理由假设,宗教上的意识形态被祭司用于从乡村人口中抽取农产品,但是具体方法还不为我们所知”。(38-39页)与此相类似的是,“图像学资料也表明了城市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重要性”。(60页)他以从公元前九世纪开始在亚述出现一种可能只被王后佩戴的王冠为例,那是一种具有城墙形状的王冠;图3.1是一幅根据文物复制的线描图,描绘的是头戴这种王冠的王后侧面像。他的阐释是:“这种王冠后来变得非常流行。它是波斯人标准的王冠,而在西方,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人认为它是女神比如库柏勒(Kybele)的标志,显然受到近东的启发。并且它仍然影响着当今王冠的流行形象,正如任何孩子画的国王图像表明的那样。”紧接着是一幅浮雕的照片图像,“献给亚述国王的城市模型” (图3.2),他指出“也许人们把他们城市的模型献给获胜的亚述征服者的图像最能表达交出一个城市是放弃政治力量的象征的思想。还有,这种图像在欧洲源远流长:在拜占庭和文艺复兴艺术中,统治者们献给神一座他们的城市的模型,它成为顺从神的象征”。(同上)这种阐释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在第四章“城市景观”中,为了说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眼里城墙对于一座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相对少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城市的描述中,亚述王宫浮雕提供了最好的记录。城市的典型形象包括一圈或多圈防御墙,墙上设有无数有规律间隔的塔,似乎表明一座设防的要塞和一堵或多堵城墙(图4.4)。同样的观念表现在作为归顺之意献给亚述王的城市模型里——只有一堵墙,有趣的是,也表现在对亚述人的军营描述里(图4.5)。图像学材料中对墙的普遍强调揭示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观念,即它们是一座城市的关键特征”。(80页)这些都是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阐释城市史中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问题,虽然从图像阐释与文献资料对照的角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但是图像史料已经能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城市危机事件中,市民手中的手机拍摄图像、视频已经成为为了历史学家的巨量图史资料的重要来源,城市史研究中的历史图像学方法必然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有所谓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议,前者认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西方经济迥然不同,现代经济学中的观念或模型并不适用于研究它们;“现代主义”流派则认为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经济展现了如此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它们与现代经济之间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米罗普认为“一套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价值观与动机可被证明存在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对利润的渴求、经济资源的最大程度的利用,以及包括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设定价格的市场经济。有许多经验数据证明存在这些经济要素:借贷文件、销售账单、雇佣合同,等等。关键问题在于评估它们在经济中的作用”。(23页)他一方面承认现有的史料无法完全证实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强调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的市场经济对于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虽然“大型的经济实体需要一个官僚体制”,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市场经济。他提醒我们注意由于考古探查都集中在神庙和王宫遗址,因此以神庙和王宫为中心的公共机构的记录远比私人经济的记录要丰富得多,因此不能以此证明国有经济和公权力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27-28页) 同时他提醒我们要关注城市中的食物供应问题,“土地所有权、政治和官僚组织、市场和再分配中心、土地使用和农业技术问题,全部都对我们理解人们获得食物的方式有影响”。(172页)在城市灾难危机中,这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如何获得食物?获得什么和获得多少?在米罗普的研究中仿佛是很遥远或者是很学术的问题一下子就变得很接地气。
在这样的阅读语境中,第六章“城市治理:国王、市民与官员”就变得更有现实意义:“我们能意识到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权力关系的两极:一边是国王和支撑其统治的公共机构,另一边是拥有某种描述不清的权力的全体市民。在这两极之间进行联络的是一群官员。……国王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因时而异,依赖总的政治状况。我的看法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市民的权力和独立性与日俱增,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另一种趋势。”(121页)这样看来,前面所讲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研究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不仅是在经济史领域中有意义,在城市政治史研究中同样有重要意义。
毕竟,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灾难危机中的问题意识已经逐步呈现出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既有历史学意义同时也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会不断出现。我相信在那些可以期待的研究中,国王与官吏不会总是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中唯一的政治力量,而不依附王宫的全体市民将如何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这个问题也能够在对城市市民的研究中得到解决。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