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那些对大众文化既“傲慢”又“偏见”的知识分子都错了?
值得我们思考的严重问题就在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抵抗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表现是恶劣而丑陋的,他们有严重的“傲慢与偏见”,更不用说他们对现代科学发展的低估,以及他们对“现代性”天然的排拒。作为“历史的必然”,大众文化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其内涵,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它还裹挟着种种值得批判的消费文化的严重弊端,甚至是不可容忍的麻痹人类和反文化的罪行,但它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其在初始阶段却遭到了部分贵族知识分子的蓄意谋杀,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和总结的问题。就此而言,凯里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即认为大众具有专门沉迷于事实和普通现实主义的特性。知识分子发现,大众顽固的写实主义使他们不适宜欣赏艺术,从而摒弃更高的美学追求。”其实这是一个双重悖论的命题,其中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怎样对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也就是再也不能用旧有的评判标准来回答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了,许许多多现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都需要我们去重新厘定。

约翰·凯里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大众受教育,阻碍大众对文学艺术的理解,所以才将文学艺术搞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因此所谓的“现代主义”兴起也就源自于此。约翰·凯里的这个理论对一个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无疑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版图上投下了一枚原子弹!我们何曾想过“现代派”的艺术竟是由此而生?用凯里的话来说,就是:“当然,知识分子实际上不能阻止大众学习文化。他们只能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此阻碍大众阅读文学,他们所做的也不过如此。20世纪早期,欧洲知识界就殚精竭虑地决心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场运动在英格兰被称为现代主义。虽然欧洲其他国家对此有不同称法,其要素却基本相同。它不仅变革了文学,还变革了视觉艺术。它既抛弃了那种据说为大众所欣赏的现实主义,也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T.S.艾略特断定:我们文化中的‘目前,诗人必须是难以理解的。’”如果“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起源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蓄谋而成的话,如果约翰·凯里的论断是正确的话,那将是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史的一次颠覆性的改写。从文学艺术的接受史来看,我们从通过大量的翻译著作和许许多多的臆想而杜撰成的所谓文学史教科书所获得的知识是可疑的,那些大量地对现代主义进行吹捧的文字和无端的阐释也就变得一钱不值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虽然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初衷是以反大众的目的而生成的,然而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与改造,已经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审美文化体系,其游戏方法和审美规则已然被系统化,去掉了它原有的目的性,也就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审美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持续了百年的文学艺术潮流,现代主义当中还存有当年遗留下来的一些有毒元素,比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强调的现代艺术就是要证明人的不平等,以及用非人化来对抗大众的观念,都是值得批判的,正如凯里所言:“奥尔特加发现,非人化是现代艺术对抗大众的手段。大众在艺术中寻求人的趣味,如在诗歌中寻求‘诗人背后的人的激情和痛苦’,而不要‘纯艺术的东西’。奥尔特加认为,这些偏爱证明了大众的低下水平,因为‘为艺术作品展现或叙述的人类命运而悲喜,根本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关注人性的满足‘不能与关注独特的美学享受相比’。显然,奥尔特加宣称的艺术上‘独特’和‘真正’的东西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被合理论证所证明。但他提出的现代艺术从本质上排斥大众的观点,却暗示了知识分子的动机而显得有些趣味。”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强调现代艺术是贵族的专利而排斥大众的加入,是它不能够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生存的主要原因,即使像拉美的“爆炸后文学”得到了世界普遍性的认同,它也只是汲取了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部分方法元素而已,它是生长在本民族“土著文学”现实主义土壤上,嫁接了现代主义枝干的文学,这种“杂交”才有了生命力。

而在中国,其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在“五四”以后的1930年代的中国,最适宜现代主义生长的大都市上海,“新感觉派”只是昙花一现,而现代派的诗歌创作群体更是每况愈下。而在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朦胧诗”“先锋戏剧”“新潮小说”等一系列林林总总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很快就被各种各样变体的现实主义大潮所覆盖,就充分证明了大众文化的强大。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以为,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贵族式的现代文学艺术理解不深;二是面对中国汪洋大海似的没有接受教育的大众,甚至是没有阅读能力的大众,即便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也难以展开的现实文化状况,知识分子的传播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约翰·凯里甚至对乔伊斯天书般的现代主义小说《尤利西斯》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我觉得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排除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相反,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文学倒是不排斥大众的读写能力的,但是它创造出来的文学艺术却是另一取向,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中,我们不乏这样的先例,从50年代掀起的“新民歌运动”,到高玉宝、浩然、王老五、李学鳌等工农兵作家,一直到70年代兴起的工农兵“集体创作”,这些现象都是大众文化的极端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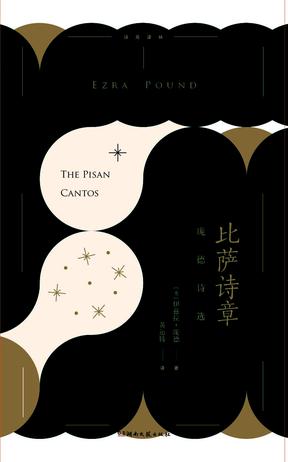
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艺术巨匠们几乎同时以贵族的语气来否定大众的人性,他们重塑和重构大众形象的“目的只有一个:把知识分子从大众中分离出去,攫取语言赋予他们的对大众的控制权”。也许,凯里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20世纪早期,否认大众的人性已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语言学项目”。凯里列举了哈代对大众生活细节的轻蔑、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大众这个“无名怪物”的仇视,甚至分析了用诗歌的意象来辱骂大众的意图所在:“对埃兹拉·庞德来说,除了艺术家,人类只是‘一大群傻瓜’,一群‘乌合之众’,代表能够浇灌‘艺术之树’的‘废物和粪肥’。在庞德的《诗章》中,‘大众’和他们的领袖变形为人粪的急流—‘民众在选举他们的污物’。这种‘大屁眼’的幻象,庞德解释说,就是当代英国的写照。”非但如此,凯里还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未来大众社会的描述,设定了一个可怕的文化语境:“勒庞估计,现代社会由群体接管,‘大众的声音占主导’。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文明,让所有人回到文明社会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常规状态,并最终获得成功。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文明是‘一小部分知识贵族’建立起来的。根据勒庞的预测,文明将被消灭而让位于‘野蛮阶段’。那种认为大众能被教化的乐观开明思想是错误的,统计显示,随着教育的传播,犯罪率实际在增长。学校教育把大众转变成‘社会的敌人’,使年轻人不屑于诚实苦干……”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