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赖国栋︱布罗代尔,欧洲的辩护者
书籍史专家罗杰·夏蒂埃认为,布罗代尔(1902-1985)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然有效,例如“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各种时间尺度的相关性;历史对象的建构方式”,因此他有重新讨论的价值(Roger Chartier, 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Polity,2014)。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合著的《历史学宣言》向当今历史学界发出了类似的倡导,指出“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有必要回归长时段。现阶段重新燃起对布罗代尔的兴趣,可能跟他提出的一些命题、看待历史的宽视野以及强调科技的作用有关。
布罗代尔写了大量著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两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3年;以下简称《地中海》)以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以下简称《资本主义》)。《地中海》以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为区域,从环境的作用、群体的命运、个人史三重结构来说明政治事件或个人如同大海上的波涛,微不足道;历史分析应该从最缓慢的演化而非快速的社会变迁开始。《资本主义》以1400-1800年世界的经济交流为范畴,将专题研究、多层时间和多重空间纳入到资本推动世界性网络形成的框架叙述中来。许多人褒扬前者的开创性,却较少注意到后者在奠定今日全球史或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上的基础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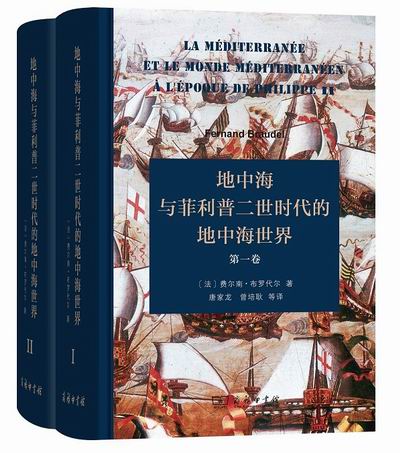
一
《资本主义》的出版过程有些复杂。该书在出版《年鉴》杂志的阿尔芒·科林出版社刊行。第一卷发表于1967年,题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书中描述的物质文明大致包括人口数量、农业、饮食、服装、科技、货币和城市化,它们在世界的不同区域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布罗代尔将第一卷看作是研究全球语境下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第一部分。法文版预告只有两卷,最终却衍生出三卷,均出版于1979年。第二卷的副标题是“形形色色的交换”,关注集市、贸易、道路、交通和商业网络,讨论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文明之间的关系。第三卷的副标题是“世界的时间”,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关注城镇经济与更大规模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着眼于欧洲如何在近代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因而是在为欧洲辩护。他还在1979年重新修订了第一卷,副标题变成了“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1977年,布罗代尔还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作了三次演讲,最终以《关于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再思考》为题结集成书出版,概括了三卷本《资本主义》的要点。这次出版的中译本,将它收在第一卷作为“代译序”,有利于我们看到他试图强调的那些方面。
布罗代尔将近代早期经济看作是三层结构的“楼房”。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和更高层次的资本主义活动,第三层是欧洲经济世界的转移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资本主义》与《地中海》一样,都强调十六世纪是“漫长的”。稍有不同的是它们的分析框架。《资本主义》以欧洲经济重心转移为中心,突出各城市中心与边缘城市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近代欧洲的崛起。《地中海》以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为中心,强调地中海沿岸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乃至冲突和战争。因此,长时段分析是《地中海》写作的框架,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分析是《资本主义》的重心。
《资本主义》大致表达了以下几个命题:首先,在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三分结构中,物质是基础性的。布罗代尔强调物质和日常生活经验。物质生活“无穷地反复,构成现实的系列”,从而表明了文明和文化的规律,“文明在成千上万种乍眼看来互不相关、而实际上也是五花八门的文化财富之间——从思维和智慧到日常生活用品和用具,全部包括在内——建立起联系或者说秩序。”(第一卷,第695页)因此,物质文明是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统称。市场经济则是“指一种相当广泛的交换形式”,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但这种差别“不是一个新特征,而是欧洲从中世纪就有的经常因素”(第二卷,第260页)。

其次,城市是欧洲发展的基本动力,城市化基本上和资本主义是同一回事。布罗代尔认为,欧洲城市的发展始于十一世纪城市复兴时期贸易和市场的拓展,近代的城市化始于1500年,但在十六世纪末显示出衰退的迹象,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他这种解读欧洲城市化的模式强调的不再是海上贸易,而是关注在打造市场经济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的贸易联系。虽然资本主义的形式例如商业、工业和银行存在于十三世纪的佛罗伦萨,但他不愿将资本主义一词运用到中世纪。
再次,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布罗代尔看来,世界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立足生根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第三卷,第71页);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功“需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中立、宽容或软弱”(第一卷,第xxxvi页),中国和伊斯兰地区则是例外,因为中央集权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宗教价值的兴起促进了资本家的积累,同时所有人从现代化过程中受益,因而这种理论不大涉及阶层冲突或资本剥削问题。布罗代尔认为,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共同构成了结构性力量,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资本主义产生于市场经济之后,是市场的破坏者而非保护者。在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问题上,布罗代尔在现代化理论之外,增添了一种解释维度。
最后,历史和现在之间是双向辩证的关系。《资本主义》最后部分“权充结论:历史实在和现时实在”,既可以看作是该著的总结,又可以看作是解读布罗代尔所有著作的钥匙。布罗代尔在此提到,探索历史的目的之一是回到现时:“历史的秘密目标和深邃动机不就是要说明现时吗?”(第三卷,第786页)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是一首由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合奏的多声部、有韵律的歌曲,其中长时段是主调。在写作《资本主义》时,布罗代尔就指出,“从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70年代出现经济衰退以后,今天的情形不是最好的说明吗?除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困难外,石油危机已指日可待”,要改变这种状况,“技术革新是唯一良策”(第一卷,第532页)。这种类比的画面或暗示性的对话,表明了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理解现时。
二
布罗代尔以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关键词写作,一方面确是延续《地中海》中关于长时段和地中海沿岸各大文明之间交流的思考,另一方面是源于战俘营中的构思。《地中海》出版于1949年,修订版刊于1966年。《地中海》第二部分“集体命运和总的趋势”就是谈经济的结构和变化趋向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依次研究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必不可分的中间媒介等问题,最后是战争的不同形式。”(《地中海》,第530页)他在1950年就开始构思《资本主义》。1950年,他在《论历史经济学》一文中提到历史学家有必要“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Weltwirtschaft(经济—世界,这个词在德国思想中难解且多义)的名目下面”研究惯性、阻滞问题(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如果进一步追溯,还可以追溯到他在美因兹、吕贝克战俘营(Offizierslager)里的那段经历。如布罗代尔在1972年的纲要性自传《个人见证》一文中所说,战俘营那段经历奠定了他的许多历史概念和研究主题,研究它们是“在部分上直接回应那段悲剧岁月”(Braudel, “Personal Testimo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4, No.4, 1972, pp.448-467)。1940年6月-1945年5月,布罗代尔都被关在战俘营里,因不是刑事犯和犹太人,而是政治犯,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就可以利用战俘营里的图书馆开展阅读、研究和讲座。他在美因兹的战俘营里,是“大学中心”的“校长”(recteur),有特权在德国人的审查、监视下从大城市图书馆或通过红十字会借调一些书籍和杂志。他甚至还在这一期间的《年鉴》杂志上发表了四篇文章,里面所引的德文参考资料就是这么来的。他在1941年5月1日寄给费弗尔的信函,已经包含《地中海》前五百页的初稿。布罗代尔“几乎全凭记忆撰写了这部关于十六世纪地中海的巨著”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事实(《地中海》,第8页)。
《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老师吕西安·费弗尔直接督促的结果。1952年,费弗尔准备出版一套题为“世界之命运”的通史著作,邀请布罗代尔合写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史,他自己写这一阶段的思维与信仰,布罗代尔考察物质生活史。最终,费弗尔因于1956年去世而未完成自己那部分。而《资本主义》当时考虑写到1800年就结束,一方面是总的计划,另一方面是以长时段的视角观察,认为伦敦“不是一个城邦,而是大不列颠诸岛的首都,民族市场赋予它不可抗拒的力量”,“英格兰确立的经济优势(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优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第一卷,第xlv,xlix页)。

《资本主义》也是与学界前辈竞争的产物。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法国史学革命》,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谈到了布罗代尔的对话对象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桑巴特、熊彼特等关于经济、资本主义的讨论。他们确实是布罗代尔在坚持历史学本位、提倡跨学科交流时的对话对象。如果转变一下角度,从法国史学的内部传统看,布罗代尔也是在跟巴黎大学的老师、犹太裔亨利·奥瑟(Henri Hauser)讨论。奥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Les débuts du capitalisme,1927)中认为,这种经济制度是“现代性的开端”,但主要是由新教推动的。费弗尔至少有五篇文章专门谈到“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这两则术语,认为宗教改革因为鼓励劳动和工作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崛起;资本主义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Febvre, Vivre l’histoire, Robert Laffont/Armand Colin, 2009, p.603)。布罗代尔认为,欧洲的转型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但这种转型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近代早期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这样具有全球影响的中心。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概念一方面要比奥瑟、费弗尔的更严格,更多关联到商业和金融,另一方面与他们的宗教价值说有所偏离。
阅读《资本主义》应该注意到继承和创新,其实也不乏“合作”。1951年起,布罗代尔同时开启了三种出版计划,从这些计划可以大致看到他构想出的世界经济研究蓝图:(1)商业和商人,1952—1973出版了三十六部;(2)货币—价格—情势,1952-1973出版了十一部,(3)港口—道路—交通,1951-1969出版了二十八部,外加1988年一部。其中分别有二十部、六和十七部处理的是地中海沿岸的区域。这些著作以不同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的参考材料。布罗代尔在修订《地中海》期间,寻求“欧洲的近代中国研究之父”(杜希德语)白乐日和印度经济史专家索内尔(DanielThorner)的帮助,以理解文明的连续性及其借鉴和排斥外部革新、影响的能力。布罗代尔将中国和印度看作是可以与欧洲相比较的两大文明。文明的连续,重要原因在于科技的革新,而科技革新来自社会经济的需求和压力,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引发不同的科技需求。《资本主义》提到,“一切都取决于技术,技术起着第一位的作用……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将技术推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第一卷,第532-533页)。在论及中国古代的科技为何有一段时间停滞时,布罗代尔解释说,一方面是廉价的劳动力阻碍了机器的使用,另一方面是社会条件不允许(第二卷,第738页)。布罗代尔对中国文明的观察,依赖于汉学家白乐日、谢和耐等的研究。谢和耐后来致信给伊懋可,谈到科技的作用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中国的技术天赋一直举世瞩目……在西方,自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就有一种鄙视劳动的传统,并对奴隶和农奴征收罚金,而这在中国不大常见。”(Mark Elvin, “Braudel and China”, in John A. Marino, ed., Early Moder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38)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存在偶然的因素。他在《个人见证》一文中谈到偶然阅读到了一大批档案。他在巴黎大学就读时对菲利普二世产生了兴趣,于是选定“菲利普二世、西班牙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为论题。1927年起就利用暑假时间前往西班牙、意大利档案馆查阅档案,他在杜布罗夫尼克档案馆,第一次接触到数量庞大的文献,它们涉及通往伦敦、布鲁日、安特卫普的船只、船货、贸易和保险,从而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对地中海的理解。1937年10月,他在由巴西回国的船上遇到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讲学回国的费弗尔是另一个转变观念的契机。在船上经过二十天与费弗尔讨论后,布罗代尔将论题改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由传统外交史路数转变为侧重讨论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日常生活的缓慢变化。
时代对布罗代尔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1923年他开始从传统外交史的角度思考菲利普二世时期的政策到1937年,法国国内流行的是乡村史或农村史。这种乡土主义源于人们对“扎根”的渴望和背井离乡的忧虑,当然背后还受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促动。布罗代尔在这时似乎反其道而行之,关注的是整体史(histoire globale)。他后来回忆说,他在阿尔及利亚教中学,在巴西教文明史和旅行那几年的经历中获得了长时段的灵感和世界的眼光。1968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事件、政治史对历史学家的影响逐渐增大,微观史逐渐兴起。这一时期,布罗代尔的方法论转变体现在运用计量上。《资本主义》中存在大量的数据统计,开篇就用一章篇幅谈“数字的分量”,而《地中海》修订版也增加了初版“未能发表的地图、草图、图表和插图”,还利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计量(《地中海》,第13页)。因此,重视长时段,强调日常生活的结构,探索欧洲在其他世界的影响虽然是布罗代尔一以贯之的思路,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的研究侧重点和方法还是有所改变的。
三
布罗代尔在世期间及1985年去世后,有一大批学者向他致敬。沃勒斯坦于1976年在宾汉姆顿大学建立研究经济、历史体系和各文明的布罗代尔中心。该中心的杂志《评论》(Review)也于1977年创刊。巴西圣保罗的布罗代尔研究所于1987年创建,在研究取向上强调资本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演变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设置了“布罗代尔高级访问学者项目”,接受国际知名学者在法律、经济、历史与文明,以及政治和社会科学四个系访问研究。
史学作品上,法国之外的一些学者直接表明受到他的影响。例如,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是“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所展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东南亚”的具体实践(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被认为是“遵循年鉴学派传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提到布罗代尔的方法,试图探询每一个分支领域“自身的运转模式(‘逻辑’),以及更具普遍性之趋势与偏重地方性之变种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页)。这份受影响的清单还可以罗列下去。又比如,印度经济史专家乔杜里(K. Chaudhuri)的《欧洲之前的亚洲》(Asia before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旨在向布罗代尔表达“致敬、回忆和对话”(p.3)。

布罗代尔的学生,比如勒华拉杜里起先是追随老师,在法兰西学院的开讲辞中谈“静止的历史”,还提到未来的历史学家“要么是程序员,要么什么都不是”,后来却写了一部微观史的代表作《蒙塔尤》。又比如,另一位学生肖努(Pierre Chaunu)尤其在利用海关档案研究西班牙和美洲贸易关系的《塞维利亚和大西洋》(Séville et l’Atlantique)中运用了计量方法,专注于系列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却转向研究宗教史。从这种影响的谱系来看,无论是《地中海》还是《资本主义》抑或布罗代尔的其他著作,它们之所以让人重新燃起兴趣,大概不在于为世界文明、资本主义、欧洲城市化以及历史学的功能提供的那些解答,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不少可供进一步思考的“一般历史问题”。
总的来说,布罗代尔的论战、对话对象不仅是跨国的,而且是跨学科的,大多数是某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或者说是他的老师辈。因此,布罗代尔的研究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老师谈论过的主题,给那些老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阐释。尼采有一种观点,说学生应该打破对老师的永远跟随,否则就是没有好好地报答他的老师。学生应该做的是在把握老师理念和学术史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他的学术观点从而达到知识创新,甚至说“学生的义务之一是反对老师”(《渡边浩谈日本思想史研究》,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2月21日)。理想的老师,则是能够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弘扬学生的个性,避免将优秀的学生培养成另一个自己。从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费弗尔,以及与第三代学者勒华拉杜里、肖努的研究来看,布罗代尔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没有辜负费弗尔在1942年某部著作“献辞”中所寄予的“厚望”,也是一位理想的老师,让学生带着只能从他那里获得的提问方式进入学术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