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进入电影大师阿巴斯的工作坊,想象力可以将日常声音转化成非凡画面|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阿巴斯是伊朗新浪潮电影开创者、诗意电影大师。他留下了诸多影史经典,多次荣膺国际电影大奖。其电影用镜头凝视平凡人世,纯粹、简朴的故事给人以最单纯的感动。影像风格简洁而富有诗意,洋溢着人文情怀与哲学思考。

多年前,阿巴斯在欧洲多座城市有一次七日电影工作坊,之后汇集成《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一书,详尽而深刻地呈现了阿巴斯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包括电影拍摄技巧、对诗歌和摄影等艺术的感悟、对人生的哲思等,是其一生导演历程与人生之路的珍贵总结。在伦敦工作坊他提醒学员们注意窗外射在地毯上奇异的光线图案、在纽约工作坊他为学员背诵四十年前在布拉格电车上听到的一段难忘的通知......在谈到对创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伴随终身的想象力时,阿巴斯回忆起在孩子时喜欢在黑暗中听广播,用想象力将之视觉化,到自己后来拍电影时,他依然注重电影的声音能够激发观众,“这样点燃我们想象力的电影是真正的创造性作品。”


电影《24帧》《特写》场景
阿巴斯 · 谈电影
在这类工作坊开始时,我经常被问及期待学员拍出什么类型的电影。我能给出的最有用的答案是对于我倾向的那种电影的描述,既是我愿意去看的,也是我愿意去拍的。每个让我感动和感兴趣的故事都有一种真实的元素。对我而言,存在那种以真实可信的方式描绘事物的电影,然后才是其他电影。如同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喜欢谎言,我也不喜欢艺术里的谎言。一部电影是以70mm摄影机(指70mm胶片摄影机)还是小型摄影机拍摄的并不重要,一个故事是疯狂幻想的产物还是从头到尾细致地表现真实事件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观众能够相信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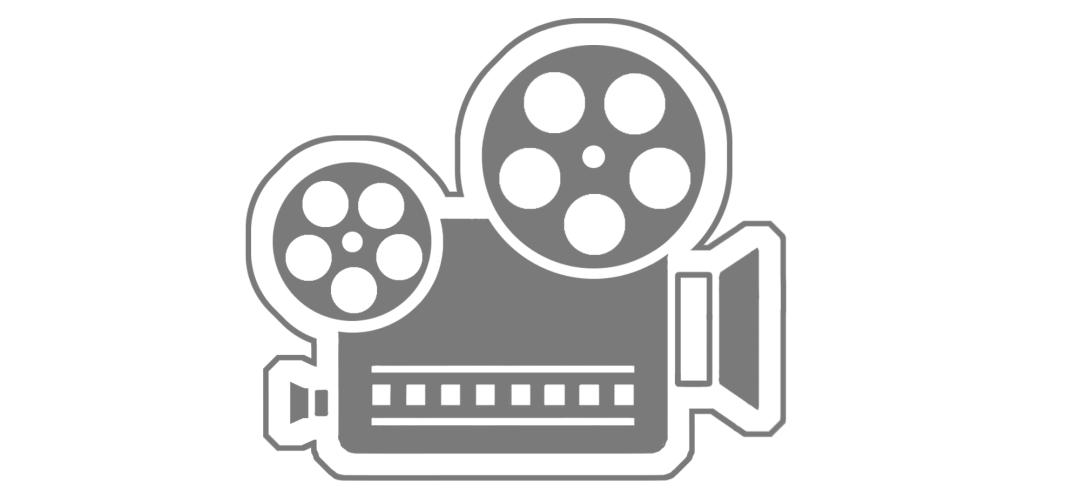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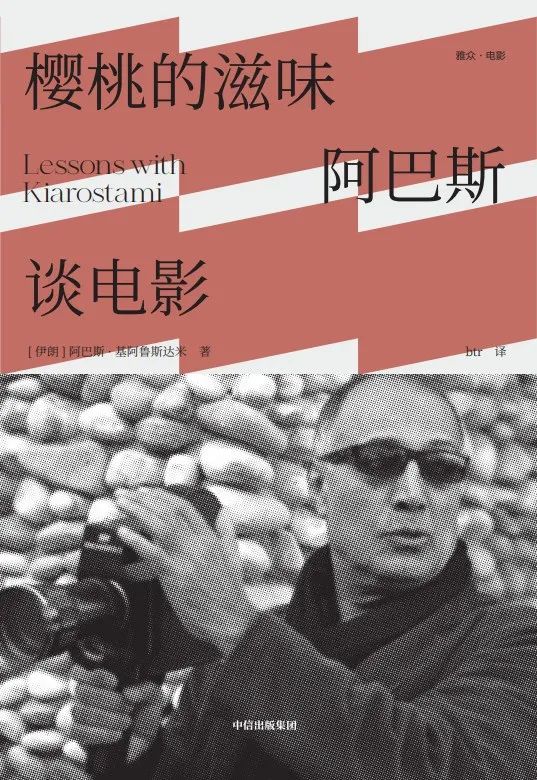
作者: (伊朗)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译者: btr
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5月
电影只不过是虚构的艺术。它从来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寸他见证的东西,他只是记录。真正的纪录片并不存在,因为现实不足以成为建构一整部电影的基础。拍电影总是包含着某种再创造的元素。每个故事都含有某种程度的编造,因为它会带上拍摄者的印记。它反映了一种视角。使用广角镜头拍一个二十秒的俯冲镜头而不是用窄角镜头拍五秒静态,反映了导演的偏见。彩色还是单色?有声还是默片?这些决定都要求导演在表现的过程中加以干涉。
一部电影能够从寻常现实中创造出极不真实的情境却仍与真实相关。这是艺术的精髓。一部动画片可能永远不是真的,但它仍然可能是真实的。看两分钟古怪的科幻电影,如果在令人信服的情境下充满可信的人物,我们就会忘记那全是幻想。我们相信戏剧演员这一分钟躺在舞台上死了,而下一分钟就会站在我们面前鞠躬,接受掌声;或一个角色解释他即将远行,随后从舞台这端漫步到另一端;或他被迫突然暂停动作,以把剑掰直,因为那把软金属做的剑已经在之前的表演中弯曲了。我们理解一位演员可能在一个舞台上、一部电影里“死去”,然后作为另一个人重新出现在某处。
电影未必要表现表面的真实。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且精炼,如果我们控制一个场景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将之向观众表现的话。允许并鼓励创造性是观众与导演间的约定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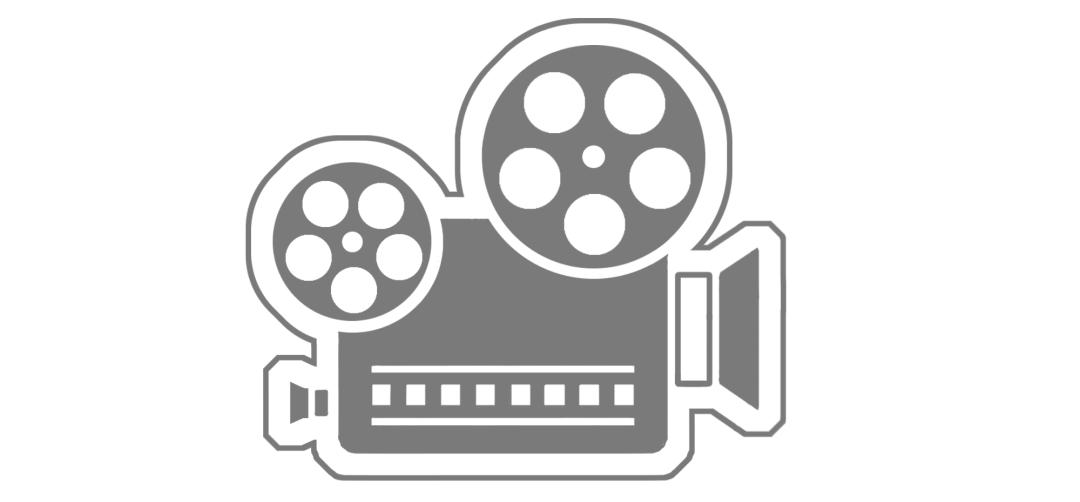

我拍了一部十七分钟的电影,叫《海鸥蛋》,看起来像一镜到底的实时纪录片。画面上三枚蛋摇摇欲坠地立在岩礁上,海浪在周围轰鸣。我们注视着海水狂暴的运动,不断淹没那些蛋,然后退去。这些蛋会在这遭遇中幸免于难,还是会掉进海里从此不见?几分钟后,其中一枚消失了。大海满足了吗?它会不会再吞噬另一枚?我们专心等待着。最终第二枚蛋消失了,随后是第三枚。音轨上音乐响起。剧终。
人们告诉我,在那特定时刻碰巧在这个地方竖起摄影机和三脚架并开始拍摄,暗暗期待有好玩的事发生是多么奇妙。事实是我控制了一切,从那些蛋开始,它们是从当地超市买来的鹅蛋,因为它们比海鸥蛋更容易找到。每次一枚蛋掉落,我们都会听见鸟痛苦的尖叫声,这营造出一种焦虑感。所有这些声音都是另外录制并混合其中的。我总共有大约八小时的素材,拍了超过两天。第一天,大海相对平静;第二天波涛汹涌,不断拍打着海岸。在现实中,仅仅过了两分钟,三枚蛋就全被冲走了。一次又一次,我的助手不断更换着蛋,每次它们几秒钟就消失了。我花了四个月剪辑《海鸥蛋》,全片由二十多个电影段落组成。这个想法来自一个与此类似的工作坊。
《生生长流》讲述的是一位电影导演回到伊朗的一个地区,几年前他曾在那里拍电影,而最近那儿遭遇了地震。这部电影设置在地震发生三天后,但在几个月后才拍摄,那时候大部分瓦砾已被清除并建起了帐篷城。当我要求经历了灾难的人们把他们抢回的少数财产放得杂乱些,以使情景看起来更像几个月前的样子时,很多人拒绝了。在废墟和破坏中,他们开始清洗地毯,并将它们挂在树上晾干,而有些人为了拍电影还借了新衣服来穿。他们的生存本能是强大的,一如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维持自尊的渴望。他们想上演一场与我希望捕捉的现实并不相符的秀。就像我的很多电影一样,《生生长流》既是纪录片又是虚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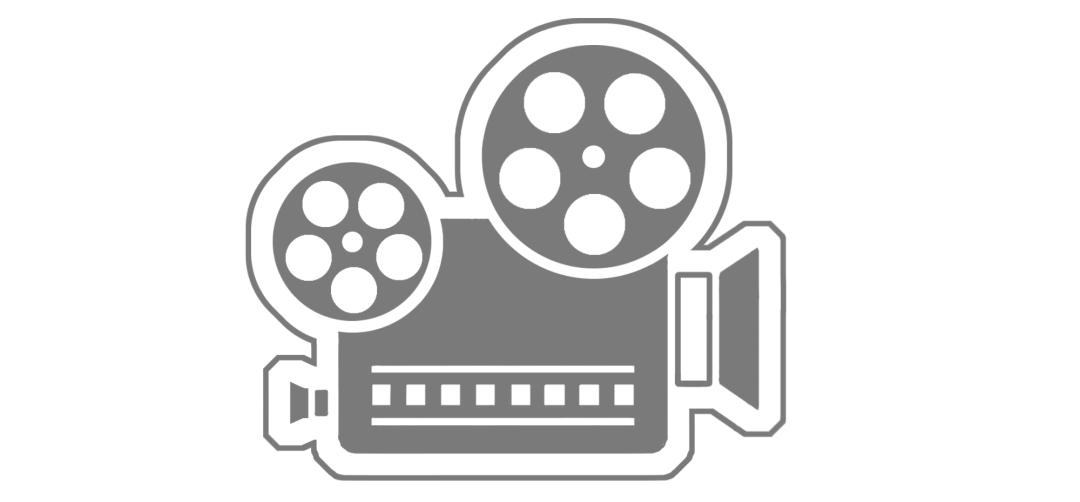

在一个风景画展上,巴尔扎克和画家站在画布前。在这幅画的背景里,远离主要情节处,田地中央有一栋小房子。烟从烟囱里升起。那儿有人。巴尔扎克转向画家。“那栋房子里住了几个人?”他问。
“我不知道,也许六七个。”“你是指一家人?”“也许。是的,一家人。”“有几个孩子?”
画家想了想。“三个。”他说。“他们几岁?”“唔......也许是八岁、十岁和十二岁。”
对话以这样的基调继续,直到那位画家有点恼火似的说道:“巴尔扎克先生,这只是画的背景里的一栋小房子。有几个人住在那儿无关紧要。我并不知道所有这些细节。”“我知道你不在意像这样的事,”巴尔扎克说,“我很清楚你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住在那儿、屋前的花园里有几只公鸡、母亲准备了什么晚餐,以及父亲是否付得起女儿的嫁妆。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看见烟囱里有烟,但我并不相信。对我来说,它看起来不像真的。假如你知道这些事,这会是一幅更好的画。”
作为导演,你需要知道这类细节,知道画框之外正在发生什么事,就算谁都不会看见。对这些事实心知肚明—去年冬天有多寒冷?这间屋子后面种了什么农作物?这家人最近发生了什么悲剧?—会使你的想法更令人信服,令你调教出的演员表演更具体、可信。这些天,在我写下任何东西前,我会在脑海中勾勒某些事物的大致图像,就好像我在拍摄前就在看那部电影了。我能将住在那风景里的人物视觉化。有几部电影在开始拍摄前很久,我就选好了演员。有时候我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尽我所能地认识他们,带着这样的了解来修改剧本。花时间和演员在一起,拍摄前有时要花好几个月,这意味着关于他和他将要扮演的角色,我能够写出一部小说。这是非常有用的过程,尽管我永远不会和扮演那个角色的演员分享这些信息。当他站到摄影机前时,这些东西不太可能对他有什么帮助。
以这样的方式,从内部出发构建一个故事,在一部电影里囊括特定的详尽的细节,会使观众的体验更丰富、深刻。这星期你们有时间来拍只有四五分钟长的电影,摆脱那些复杂的想法、详尽的哲学和心理学或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我们谈到拍电影,就像任何事一样,必须有特定纪律以形成必要的简洁。当你开始拍电影、讲故事时要保持直接、独立。在一部四分钟的电影里,你没有时间详尽探索任何人的过去。最重要的是观众看见和听见了什么。不管人物要什么,不管他们做什么,都需要在身体上表现人的动作。让我们开始以影像、电影的方式思考吧。当你在小组里讲故事时,不要哲理化,不要解释,只描述我们看见和听见的东西。一个导演不会在观众看他的作品前向他们分发书面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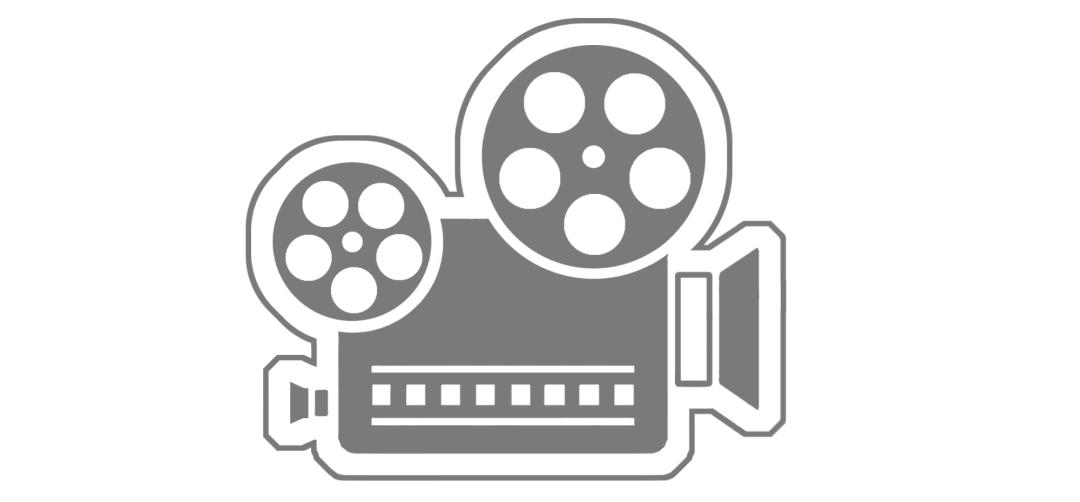

有一种电影——如今很普遍——不要求观众发挥想象力。毕竟,操控一个人的感情并不难。坏电影把你钉在椅子上,它们绑架你。一切都在银幕上,但一切又囿于诠释,导演强行规定了你应该如何感觉。随后,就在灯亮起后的几分钟里,你已经忘记了一切并感到受骗。
我偏爱另一种类型的电影。当观众们——如此脆弱地坐在漆黑的放映厅里——未被剥夺理性,不必屈服于情感勒索时,他们用更有意识的眼睛观看事物。一部好电影让你无法动弹。它挑衅,唤醒内在的东西,在电影结束后很久仍在拷问你。一部好电影需要由你来完成,在你脑海中,有时在很久之后才真正完成。它在你观看时可能会让你睡着,但几星期后你会醒来,满怀热情,肆意想象,并对自己说“我要再看一遍”。我不会介意有人在看我的电影时睡过去,只要他们后来想象过它。
“我简直放不下!”你会听见人们这样讲述读一本书时的体验。为什么那是件好事?伟大的艺术鼓舞人,因此需要某种介入。它太过激动人心,以至无法一次体验完。有些电影迫使我把它关掉再去厨房倒杯饮料,或只是站在窗前凝视。有太多需要思考的东西,所以我只好走开休息一下。以前看电影时,我常常会在某场特别让人印象深刻或感人的戏后离开,甚至会在某个惊人的图像闪过我的眼前后停下来。那时,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结尾,并怀疑我对于这个故事的结论是否会比真正的那个更有趣。在某些情形下,电影到那个点已足够了。我只是不需要再看见更多的东西。我需要距离,哪怕只是几分钟。有时候,当剪辑一部电影时,我希望切到一个完全空旷、无声的场景,持续五分钟。这种效果类似小说里的空白页,给读者一些时间停顿并思考。但我从未鼓起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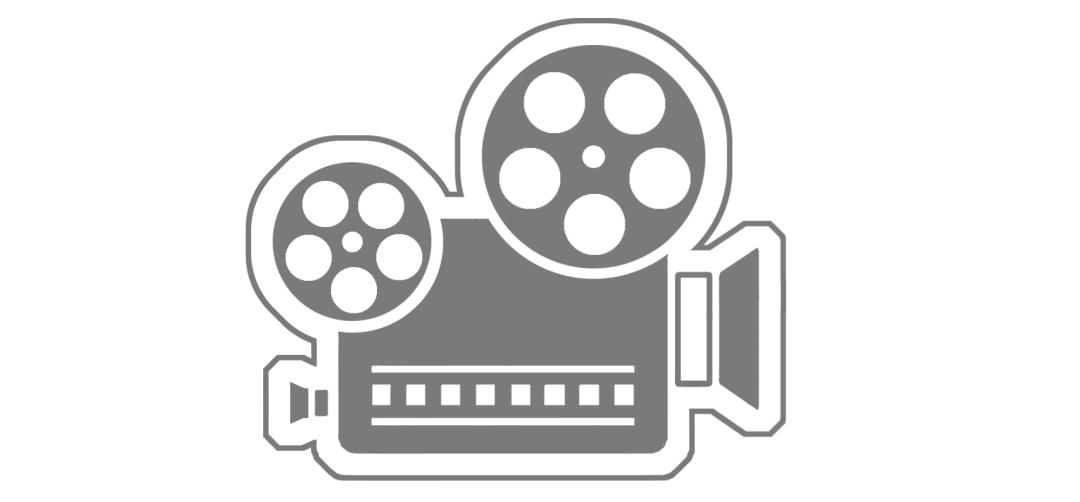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需要想象力。当事情困难时,我们自动开始梦想。我们越拒绝现实,我们就越在想象力中寻求慰藉,我们能掌控的只有这个,没有一个审查系统可以控制它。带着梦,我们穿行于生活的枯燥中,甚至穿越监狱之墙,都不用挪动一英寸。做梦让我们有机会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一些。它给予我们更强的适应能力,接受某些磨难。如果有一种可以量度我们的梦的机器,我们或许会发现地铁工人的想象力永远高涨,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地下世界的黑暗里。鸟儿被囚禁在笼子里时叫得最响。
原标题:《进入电影大师阿巴斯的工作坊,想象力可以将日常声音转化成非凡画面|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