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政治当中,“关爱”是否必要?——一种女性主义进路
原创 埃里克·格雷戈里

《小偷家族》剧照
在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关爱与“平等”“正义”并非对立的概念,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回应了非正义的状况和有需要的人,它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包括我们为了维护、持续以及修复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希望能交织在一个复杂的、维系生命的网络中的所有事物”。
在引言中,我曾指出许多自由主义者惧怕在政治背景下过多地谈论爱的话题,因为他们担心有可能会唤起危险的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和家长式道德主义幽灵。这种担忧让人们普遍反对政治上的泛爱主义(agapism)。在对欲爱式政治表现出同情时,自由主义表示怀疑,因为人们认为它的政治风险太高——过度鼓吹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的概念,会危害到政治行动者的诚信。将爱视作民主公民的政治德行,不仅会威胁到个体享受自由和平等的能力,还会侵蚀那种克服了(“私人的”)偏袒之爱的自由正义的成果。在私人家庭领域,爱属于诗人和看护照顾他人者,但这种观点不适用于公共德行和政治主张领域。人际关系可能需要爱,但是政治要求坚持不徇私地进行理性区别和判断。对于自由主义道德或政治分析而言,爱并不适用。当爱掺杂了政治性后,爱就侵蚀了社会正义。
我的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赞同这些观点,并强调在自由主义的文化中,一种合乎政治公民的爱。爱能够成为一种危险的事物,特别是当它被用于粉饰政治修辞时。出于这个原因,相较于自由平等,博爱(fraternity)已经沦为声名狼藉的“穷表亲”,而正义作为政治制度的首要德行已经完全掩盖了爱的光芒。奥古斯丁主义中罪的概念应当会让奥古斯丁主义者对这样一个事实产生警觉,即最好的道德哲学未必就是最好的政治哲学。但是他们应当抵抗一种自由主义的趋势,将道德上雄心勃勃的公民伦理等同于不可避免地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在下一章中,我将论证对于阿伦特而言,和其他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一样,她因为关注政治的病状(pathologies),而且仅从情感上着手,用仁慈或同情来解释爱,从而曲解了爱。有时,她没有意识到对于良性的政治而言,爱是合法且必要的。如果正义真能给予每个人他或她应得的尊重,那么正义必然也包含要去爱那些应当爱的,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人类繁荣的条件。如果爱能够从对它的批判中得到救赎,我们就能更好地想象出一个正义社会是为何“正好也是一个爱的社会”。
爱是一种政治动机,如果忽视或怀疑这一观点——没有赋予爱本该有的地位——无论是对奥古斯丁主义者还是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在他们评价政治社会和为公民提出民事建议时,都会受到局限。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必须面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它的那些为人熟知的、来自激进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消费主义以及狭隘的理性主义的指控。它还通过破坏自由主义的描述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激发了社会运动?)和规范能力(什么会激发和维持自由主义政治?),来扭曲自由主义的政治进路。自由主义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和政治收益,哪怕是在它关注的程序规则公正性方面,也是如此。自由主义在简单地摒弃其政治心理学中的爱时,却基本没有提出一个一直适用于政治社会的词汇或概念,来组织起其担忧的这种失序之爱。
在重新把爱当作政治行动的一种动机进行思考时,我所做的努力与女性主义理论所做的类似,即根据卡罗尔·吉利根的开创性著作《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来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性评价。伴随着新近出现的“第二波”或“差异”女性主义,吉利根的著作对男性以正义达至道德和女性以关爱达至道德做了区分。和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爱的探究一样,吉利根的研究将这些进路与童年和青春期中个性的形成联系了起来。她认为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具有影响力的的道德发展阶段的模型排除了,并且也没有考虑到,青春期少女与众不同的道德表达。对于吉利根而言,每一条进路都需要一套不同的情感,并对人类状况做出基本假设。学者们对吉利根著作最初的回应关注的是其展现出的性别本质主义,以及根据种族和阶级假设,新浪漫主义倡导的“女性道德”。和那些挑战爱和正义二元论概念的基督教伦理学家一样,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吉利根以及尼尔·诺丁(Nel Noddings)著作中的正义和关爱的两分法发起了挑战。诺丁是首位将“关爱”当作一种道德理论来构建的作者。一些女性主义者尝试从“心理学的”转到“经济学的”方面来论述道德对社会化模式下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影响,这种模式赋予了公共正义权力来对抗私人关爱。有趣的是,这些文献提出了类似米尔班克对西方基督教中仁爱的命运的解读(进一步证实了米尔班克是通过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分析当代社会科学的霸权)。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发展了这套理论,包括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 玛莎·努斯鲍姆、约安·C.特龙托以及伊娃·费德·吉泰,这套理论强调的是道德关爱理论的政治相关性,它既没有忽视正义,也没有忽视权力。这些主张对我关于奥古斯丁式公民自由主义的论述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为了表现女性主义理论是如何发展了吉利根的洞见的,我首先要来论述吉利根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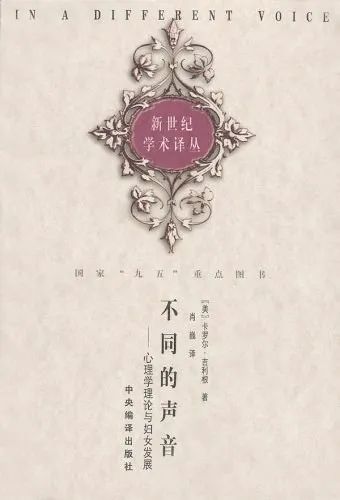
作者: 卡罗尔·吉利根 译者: 肖巍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 1999-2
按照吉利根的观点,正义强调的是平等、普遍的公平、权利、客观的程序规则、义务以及不干涉。关爱强调的是依赖、责任、语境叙述,以及对某个人具体需要的同理心。吉利根认为传统心理学理论在道德方面的发展是失败的,因为它们是在男性价值观假设的前提下运转的,这套男性价值观认为隔离、冲突和自主比亲密关系、依恋和合作更重要。这些假设更适合一种“正义”的方法,并倾向于将“关爱”这种道德边缘化。从男性视角看来,“‘责任’这种道德似乎是不清不楚,没有定论的”,而且从道德上看,它是不成熟的。她略为模棱两可地指出,这两种道德观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有优劣之分或彼此对立的”。这显示出了她将正义和关爱看作道德的两个独立特征的倾向,但是,她也谈及需要“一种相互的尊重和关爱”,甚至是一种“正义和爱融合”。因此,吉利根并没有否定在权利和正义的准则下,女性具有的权益。事实上,考虑到基督教提出的圣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观点,她对女性声音的关注意味着将女性从“女性美德的习俗中固有的”自我否定中解放出来。但是,对于吉利根而言,并不需要放弃这种关爱的语言或它那种与众不同的道德观。这种不同的声音揭示了“贯穿于人一生中的自我和他者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对同情和关爱需求的普遍性”。根据吉利根的观点,她否认了关爱是“一种青春期的理想”,它与男性暴力和那种“强者不需要道德,只有弱者才会关心人际关系”的虚无主义信仰紧密相连。
吉利根认为成熟的道德中,两种观点是融合的。她写道:
权利的道德是以平等为基础,以理解公平为中心的,尽管责任的伦理依赖于平等的概念,但是也必须要承认两者的差异性。权利的伦理是一种平等尊重的表现,平衡了他者和自我的要求,而责任的伦理却建立在能滋生出同情和关爱的理解之上。因此,这标志着尚未成熟和已经成熟的道德的同一性和亲密关系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成熟的道德发现了两者间的互补性。

卡罗尔·吉利根,美国女权主义者、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著有《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等。
然而因为现代道德理论感兴趣的是自由和自治,所以它忽视了关爱。吉利根呼吁采取行动来超越“一种僵化的不许伤害他人的禁令,转而采取对自我和他者做出回应的行动……将心和眼加入到伦理之中,这种伦理维系了思想的活动和关爱的活动”。出于积极的责任,关爱要求去帮助他人;出于消极的义务,它要求不伤害他人。但是吉利根和其他的女性主义者对从这些主张中得出的关于人性良善的一般化或普世性的解释持谨慎态度。因此,吉利根认为她的著作“试图将道德讨论的潮流从如何实现客观性和公正性转移到如何负责地、抱持关爱地进行回应上”。这种后吉利根的争论,一度由对性别的讨论或对关爱与正义关系的元伦理学讨论所主导,它对政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论具有启发性。
“关爱伦理”的政治拥护者,通常以指出女性居于从属地位这一历史条件开场,来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在谈及这些历史条件时,玛丽莲·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认为这是“按照性别对道德劳动进行分工”。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
统治的任务,规制社会秩序以及管理其他的“公共”制度,已经被男人当作他们的特权领域而垄断,而维持私人性人际关系的任务被强加给、或留给了女性……正义和权利是以男性的规范、价值观和德行构建的,而关爱和同情的回应定义了女性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和德行。
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试图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女性和女性的经验是将作为道德导向的爱私人化的动力。正如塞拉·本哈比提出的,“道德自治的定义,以及道德自治的理想……在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的普遍契约主义理论中,导致了女性经验的私人化,也导致了不再从道德的角度对它进行思考”。一些理论家颇具说服力地将女性经验的私人化和“宗教和善的概念的私人化”联系了起来。按照莱奥娜·巴特尼茨基的观点,“这种双重的私人化已经将对善和关爱的关注置于私人领域,而将对正义的讨论留在公共领域中”。这种从属性的爱作为政治争论中的一种道德推理(特别是新康德主义中),它属于一个并不适当的、更大范围的讨论,其通过压制政治行动的表现力和论争性来限制对善的具体讨论。让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者特别感兴趣的是,女性主义批判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相信自由主义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偏见……在政治背景下所有对于关爱的言论都令我们感到尴尬不堪”。在“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新教的感情用事的批判下,这种尴尬在基督教社会伦理领域中更加明显。尼布尔等现实主义者固执地认为“正义感是思想而非心灵的产物”。意志坚定的、理性的正义将引导政治生活的方向。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者已经拒绝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仍旧认为德行的劳动分工是将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基本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的基础。自由派女性主义理论家不同意现代自由主义的这一方面。他们主张自由主义文化规范有效地用公共领域来反对私人领域,用约安·C.特龙托的话说,其原因在于他们重视的仍旧是男性的“生产活动”而不是女性的“关爱活动”。特龙托主张,“由于我们的社会没有注意到关爱的重要性,以及关爱实践的道德品质,我们低估了这个社会中提供关爱的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工作和贡献”。在公共和私人间对自由主义的传统区分,造成了“一种不透明的玻璃,使我们对女性和她们活动的传统领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而进一步低估了关爱的价值。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批判了可疑的自由主义主张,即私人领域的祛政治化特征和将关爱从公共生活中清除。

约安·C.特龙托(Joan C. Tronto),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Moral Boundaries :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Caring Democracy: Markets, Equality, and Justice等。
许多女性主义者简单地(tout court)否定了自由主义,而采用反自由主义或后自由主义的各种立场。这些女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关爱和正义是不相容的,并且高度质疑了区分公共/私人这一做法。在这点上,自由主义简直无可救药。我更同情那些人,他们相信在面对传统主义、传承的权威和宗教教义反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时,自由主义被证明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传统。最近的女性主义思想拒绝简单地将女性主义的关爱和自由主义的正义相对立,并且全盘否定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适当的差异性。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关爱的伦理能够被吸收到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中,而这并不会否定更大的自由主义框架。例如,按照苏珊·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的观点,“对正义最好的理论化……已经整合了关爱和同情的概念,其考虑了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他者的利益和福祉”。奥金曾对这种关爱的伦理进行了批评,她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包含的不仅是相互参与和平等关切他人所需要的概念。奥金反对康德的观点并且重新构建了罗尔斯的观点,认为尊重和公正的原则是以关爱而不是漠然为前提的。最终,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中心是“一种声音,要求要负责、关爱和关注他者”。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指出罗尔斯主义的正义社会要求一系列德行和情感倾向:
对正义的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人,要深怀敬意与赞赏;对行为不公的公职人员表示愤慨;团结那些非正义的受害者;当按照差别原则对某人的所有权进行重新分配时,不会忿忿不平;有充分的自尊;在政治的层面,对和我们对善的定义不同的其他群体,不抱有蔑视或敌意;对贪婪或偏袒这些与正义的要求相冲突的感情感到羞耻。
奥金对罗尔斯忽视了性别,以及没能将其正义原则运用到家庭这个自由社会最为基本的结构中进行了批判。她的批判是基础性的,但也可以用来“改进”罗尔斯式自由主义。她主张修正自由主义,在不危及其他自由主义承诺的情况下,将女性主义的批判考虑在内。她坚持认为,罗尔斯主义者不需要在正义的伦理和关爱的伦理之间做出选择。进而指出,“对女性主义的批判而言,这是一个工具”。

苏珊·穆勒·奥金,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和作家,著有《正义、社会性别与家庭》等。
尽管奥金为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新方向,但我认为特龙托的著作才是对关爱和政治理论最具启发性和深远影响的论述。和奥古斯丁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者一样,特龙托拒绝将政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她写道,“当世界被严格地划分为权力的领域和德行的领域时”,“我们会忽略权力也需要道德基础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就我们当下的目的而言,德行要产生一种权力”。事实上,如同奥古斯丁对他那个时代文化著述的解读一样,特龙托承认“道德理论”自身“表达出权力和特权”。总而言之,自由主义理论为避免政治混乱提供了一种方法。但是,特龙托和许多女性主义者不同,因为她并没有放弃有利于政治实践的元伦理。从理论上说,特龙托出于“权利的倡导者和社群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没有为倡导关爱伦理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这个观点,拒绝以此为动机来让关爱和正义相对立。为此,特龙托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她提出的关爱的政治伦理并没有被提升为一种女性德行。关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问题”。她将“关爱”定义为“一种特定的行为,包括我们为了维护、持续以及修复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希望能交织在一个复杂的、维系生命的网络中的所有事物”。
特龙托拒绝将关爱的关系解读为“二元的”或“个人主义的”,她接受的是政治上的一种可行的解读,即将其视为一种持续地将行动和感觉联合在一起的过程——视为“实践和倾向的结合”。她正确地指出,对关爱更为传统的定义,倾向于“情感化和浪漫化”。如果不对接受关爱和给予关爱进行道德和政治分析的话,它们很容易被私人化。特龙托和其他女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提倡废止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他们也拒绝标志着提倡关爱的社群主义的转向。特龙托并没有将公共领域想象为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她也拒绝将女性主义者主张的那种“给予母亲般关爱”的形象投射到政治实践中。正如尼拉·巴德沃(Neera Badhwar)认识到的那样,“将丈夫和父亲的压迫变为国家的压迫,这并不是通往自由的正确道路”。关爱要怎么做才能变为一个政治理念,而不会沉溺于一种“将政治领域转变为‘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的糟糕信仰?或者更糟,沉溺于对“奴隶道德”的信仰中呢?
特龙托对将关爱解读为拒绝自由主义的解读提出了一个颇为有力的挑战。她主张,自由主义的道德前提不应被破坏,只是被证明为“不完整的”。她试图重新划分道德和政治理论的界限,而且不会“破坏或侵蚀目前已有的道德前提”。事实上,她主张对于公民伦理而言,关爱并不是一种完美的道德理想,特别是在把关爱当成道德理想或者情感后,它会被“大量导入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原则中”。她认为这种应用过于天真和危险。这些人试图假设社会中不存在冲突,他们也不承认权力的关系,特别是没有考虑到种族、阶级和性别在关爱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洞见与奥古斯丁式公民自由主义者有关,他们凭借基督之爱,保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对权力和罪进行全面观察。对于特龙托而言,那些天真的应用激发了“以社群主义进行思考”,这么做会破坏权利和政治平等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的各种关爱理论,“都倾向于只通过他们自身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这扼杀了多样性和差异性”。实际上,特龙托的自由主义认可通常被认为是社群主义的那些事物。她强调依附、社群和社会责任的价值。例如,特龙托主张,“理性的、自治的人的概念是一种符合自由主义理论的虚构概念”。女性主义者谴责这种虚构,因为它以一种超男性化的方式来解读自治,并将其与一种对自由的抽象解读(即将其视作能发起行动的巨大能量)联系到一起。但是,对于特龙托而言,这种虚构是以在自由想象中,在自治和依赖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前提的。关爱的需要不符合那种只关注自治或依赖的自由主义模式。在现实中,特龙托主张,“因为人们有时是自治的,有时是依赖他人的,有时给予那些依赖的人关爱,所以最好把人描述为是相互依存的”。失败的自由想象导致我们在个人主义的“规划”“利益”和承担起对他人需要的社会责任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按照特龙托的观点,需要与政治有关,因为它们出现在社会相互依赖和不平等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人必须工作,这样他人才能实现他们的自治和独立”。对需要的政治回应的重要性被一种自由主义的主导性话语所掩盖,这种话语坚持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并打算用其来“协调甚至是替换正义的概念”。奉行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理论家用一种政治理想替换了关爱,他们坚信政治只与利益有关。自由主义的正义实际上可以掌控,或者至少提供一个不完全的框架,来界定那些并不适合简单归入非正义范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饥荒和贫困救济、吸毒成瘾、无家可归、失业、文盲和环境破坏等政治挑战。这些理论都假设“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如果从关爱的角度入手,“会使我们认识到实现平等是一个政治目标”。为了使实现平等成为政治目标,公民不应简单地把自己当作一种完全自治的受造之物,他们进入这个世界是准备好要去“以物易物”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不应假定一个“奇异世界”,在那里“人在出生前就已长大成人”。

《一念无明》剧照
伊娃·费德·吉泰支持的是她称为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依靠的批判”(dependency critique),“用一个将社会视为平等的社群的概念来掩盖有不平等依靠需求的婴幼儿、老年人、病人和残疾人”。自由主义理论默认它们是依靠照顾者的工作来支持其正义社会的观点的,但它无法根据自身的要求来对这些实践进行描述(除了认为关爱是一种私人选择)。例如,罗尔斯将正义感描述为“由慈爱的父母抚养的孩子理所当然会有正义感”。讽刺的是,即使自由主义的声明只是在最低限度的道德承诺和泛情的前提下运作,对缺乏现实主义的这种指控,却将自由主义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特龙托认为,考虑到依靠和对关爱的需求的现实性,关爱应当对“民主公民的实践”产生影响。但是,一个政治社群要如何对他们面前的各种需求进行区分呢?如果有需要的人并未认识到他们的需要或者拒绝了别人的关爱该怎么办呢?是什么阻止“关爱”滑入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所说的那种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和管理技能”操控的道德中呢?要如何看待我们认为他人的需求是一种自我欺骗的看法呢?或者,用奥古斯丁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是如何平衡关心他人的幸福和承认自己的罪恶倾向的?
特龙托主张,由于家长主义的危险性,“关爱只有在自由、多元、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才能成为一种可实现的政治理想”。这些政治条件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了希望,即多角度和多模式的专注有助于公众在需要和人类能力的问题上做出决策。但能够保证这样的专注的并不仅是制度。在塑造关爱之人的德行和寻求确保不会滥用关爱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强化的动态关系。关爱将公民德行解读为一种不断自我检视的实践和倾向。特龙托对自由主义有些矛盾的评价,和她对自由主义哲学的缺陷的全面攻击相比,并不会显得稍为温和一些。此类攻击通常不会提出建设性的替代选项。特龙托并没有简单地将“关爱”添加到自由主义之中,仿佛关爱是另外一种被纳入理论中的调节性原则或事物那样。相反,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们能认真地考虑关爱,那么即使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会被改变”。自由主义思想,加上自由民主公民权的实践,都将会被改变。特龙托关注的不止是将一种新的公民伦理理论化,因为她将关爱的伦理实际应用于自由社会中。以下两段可以说明她的主张:
专注、责任、能力或反应力,没有必要将这些品质限制在我们直接关爱的对象身上,它们也可以影响我们作为公民的实践。它们将我们引向这样一种政治,其中心是对需要的公共讨论,以及对需要和利益的交叉点如实地进行评估。如果人们认为专注是公共价值的一部分,那么对社会(或世界)中一些群体的困境缺乏专注就会变成一个公共问题,它值得我们公开讨论。
总之,把对关爱的价值承诺囊括进对其他自由主义价值的承诺(诸如对人民权利、正当的法律程序、遵守法律、遵循商定好的政治程序的承诺)之中,可以使公民更具有思想、更关注他人的需要,从而成为更好的民主公民。
特龙托指出这种视角不仅会影响到资助决策,而且也会转变我们关于福利、医疗卫生、政治改革和公民教育的争论。
特龙托意识到关爱的伦理学(正如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一样)具有典型的、内在性问题。就像汉娜·阿伦特对奥古斯丁的批判一样,特龙托指出关爱的伦理会受到家长主义和狭隘主义(parochialism)的诱惑。照顾者(Caregivers)会将那些接受照顾的人当成幼儿来对待,并且“觉得他们自己有能力去评价接受关爱者的需要,而不是由那些接受者自己来进行评价”。而且,关爱的伦理可能促成一种偏袒,这种偏袒可能会变得狭隘,特别是在把关爱的模式理解为“母子关系的隐喻”时更是如此。特龙托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即把爱和正义联系起来。她的正义理论并没有放弃那些为人熟知的对普适性自由价值的承诺。我自己关于爱和正义的解读也和她的主张一致。但是,有时,我并不确定特龙托的构想究竟是怎样的。我发现她将关爱“连接”到正义理论的说法与她自己对关爱实践的洞察有所冲突。她竭力拒绝将关爱和正义彼此分离,也反对理论先于实践。但是她假设关爱只有在被纳入现存的正义理论后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在并不明确地坚持爱可以转化为(不是简单地移植)一种正义理论的前提下,她使爱和正义这两种价值之间隐含着一种分裂。我自己对爱和正义关系的理解寻求的是关爱的内在原因,它偏离了来自家长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诱惑。但是,特龙托强调,对需要和正义进行民主审议的做法,有助于抵御家长主义和狭隘主义。
最后,特龙托直率且明智地承认,即使是在民主的政治关爱伦理中,也仍然存在这些危险。她认为理论的确有助于改变我们看待政治世界的方式。关爱承认一种普世性的命令:“人应当关爱他人”。但它不是新的“社会德行的首要原则”。在特定条件下,一项关爱原则不能脱离开关爱实践。特龙托承认“不存在这样一种普世性的原则,它能确保他人和社会会主动投入到关爱之中,而这种关爱恰好可以免受家长主义、狭隘主义和特权的影响”。奥古斯丁主义者应该会认同这个观点。政治世界具有风险,脆弱而且不完美。正如人们滥用了“正义”的修辞一样,他们将会滥用“关爱”的修辞。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更多的是在实施操控和剥夺,而不是去解决操控和剥夺的问题。但是,这种现实并不意味着对于一种回应了非正义、有需要的人和阻碍人类繁荣的社会状况的政治实践而言,关爱是不必要的,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民主还可以进行下去。

本文作者 埃里克·格雷戈里
埃里克·格雷戈里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后又在耶鲁大学取得宗教研究博士学位;2001年起,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凭借本书,于2009年晋升为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宗教和哲学伦理、神学、政治理论、法律和宗教,以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他笔耕不辍,在《宗教伦理期刊》(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基督教伦理研究》(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奥古斯丁研究》( Augustinian Studies)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目前,他正在写作一本新书,暂定名为《陌生人的聚会:全球正义与政治神学》(The In-Gathering of Strangers: Glob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heology)。
▼

[美]埃里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著 李晋/马丽 译 出版: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复制淘口令打开淘宝购买:
(因疫情原因,发货将有延迟)
https://m.tb.cn/h.fujVLCz?tk=D9TU2NYzRSu
“当代奥古斯丁政治神学研究中的
重要著作”
奥古斯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是最早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理论的哲学家。本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格雷戈里分别以神学、女性主义和政治哲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对奥古斯丁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公民伦理的全新解读。通过分析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程序主义和以小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公民自由主义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及其与如何构想和施行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格雷戈里合理重构了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
通过广泛检视奥古斯丁的著述,以及不同立场的学者对这些著述的接受,格雷戈里确立了两个经典的主题:爱——及与爱有关的关怀、团结、同情等概念;罪——及与罪有关的残忍、邪恶和褊狭的利己。通过详实的论述,本书既拓展了当代奥古斯丁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想象,又丰富了自由主义者对奥古斯丁主义的认识。对于关注基督教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和宗教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人来说,格雷戈里的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全新的讨论。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在政治当中,“关爱”是否必要?——一种女性主义进路》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