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平原:城市要学会平衡“看得见的业绩”与“看不见的精神”

自2021年9月16日,被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以来,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关于潮州文化,关于城市文化的论述沿袭一贯的风格,妙语连连,金句不断:
小城的魅力,在于其平静、清幽、精致的生活方式。
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小巷深处,平常人家”。
有好作家的城市,真的是有福的。
……
自从1994年9月16日在《北京日报》刊发《“北京学”》以来,“我一直关注以北京为代表的都市建设、都市生活、都市文化以及都市书写”。尽管他也十分清楚,“当下中国学界之谈论都市,制约你思考的,除了国家大政方针以及自家的学术理想,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发展需要,以及开发商的利益诉求。”
印象中,这是我第五次与陈平原教授的正式访谈(见附录)。第一次是2008年,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潮变迁,更多是把他作为思想史研究学者,他提出“经过了30年,我们与世界思潮同步”;
第二次是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他当时是中文系主任,我们探讨的是“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访谈时既把他视为中文系负责人,也是作为文学研究者;
第三次是2011年,为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新京报》推出了“清华百年纪念特刊”,那时他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作为教育研究者,他提出大学“既有国际视野,也讲本土情怀”;
第四次是2012年,当时他还有个身份是“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围绕校友捐赠的话题,他认为“大学更应关注普通校友的‘小捐’”。
这一次,我想和他谈谈“城市/都市”,谈谈“都市记忆与文化想象”背后的城市众生相,谈谈“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背后的城市窘境与魅力。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陈平原: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出版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记忆北京》《想象都市》等近百部作品。
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评论人。

高明勇:您说“当初进入(都市文化)这个领域,本就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从文学研究转入到城市文化研究,这个跨度且不说研究难度,仅从研究群体的关注概率上看,相信也不会很高,我想知道您所说的这个问题意识的立足点是什么?
陈平原:我最初关注都市文化,其实是在延伸文学史的思考。也就是《想象都市》开篇所谈论的“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而言,约略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感时与忧国,以屈原、杜甫、鲁迅为代表,倾向于儒家理想,作品注重政治寄托,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第二,隐逸与超越,以陶潜、王维、沈从文为代表,欣赏道家观念,作品突出抒情与写意,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第三,现世与欲望,以柳永、张岱、老舍为代表,兼及诸子百家,突出民俗与趣味,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如此三分,只求大意,很难完全坐实,更不代表对具体作家的褒贬。如果暂时接受此三分天下的假设,你很容易发现,前两者所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第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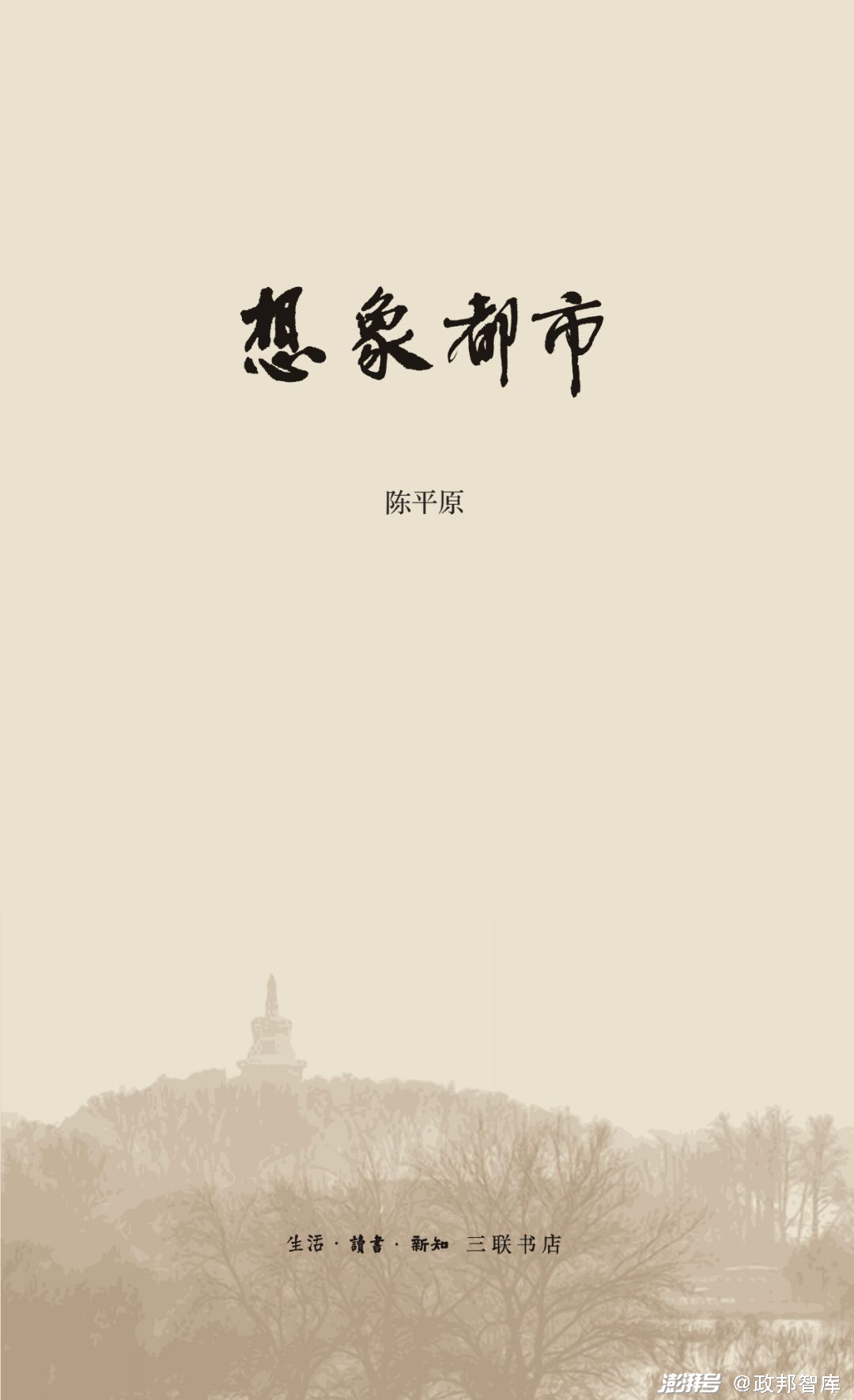
有朝一日,我们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那时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以及经典的确立与趣味的转移,我相信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这么思考问题,其实是受近年考古学突飞猛进以及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的刺激。了解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我的趣味与局限性:虽也关注“政治的城市”、“建筑的城市”、“经济的城市”,但立足点依然在“文学的城市”。以读书人(而非专门家)的状态,讲述与阐释我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目标是兼及学科建设与社会批评,可惜因精力过于分散,两边都没真正做好。
高明勇:如果从1994年发表的《“北京学”》开始,您关注城市文化也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回头看的话,您认为自己的研究能概括为“城市软实力”吗?
陈平原:“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创的概念,原指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国家形象等,主要是区别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以及军事等“硬实力”。这个概念被套用到城市上,必须做很多转化,比如“城市软实力”并不包括政治制度与外交策略,只局限在文化建设、科教实力、人文精神、城市风格等。我主要关注“文学的城市”(而非“经济的城市”),一定要分类,称其侧重“城市软实力”,当然也可以。不过,我自己写文章,不会用这个词。

高明勇:“城市软实力”该如何评判?能提升吗?
陈平原:“硬实力”不必发声,只有弱者才需要整天呐喊。为了提升所谓的“城市软实力”,学者们殚精竭虑,设计大类小类、名目繁多的各色指标,采用材料填报、入户调查以及网络投票等,其实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说自娱性质的“最幸福的城市”、“最怕老婆的城市”、“最具软实力的城市”等,即便各部委或专业学会颁发的金字招牌,也都只能“姑妄听之”。我曾在演讲中介绍美国评选“最有文化的城市”,某媒体想尝试做,我告知难度太大,因数据收集不易,更因牵涉官员政绩,担心浮夸与造假。

在收入《想象都市》的《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中,我曾提及:“不同于人均GDP,‘幸福感’很难测算,但普通民众脸上的笑容非常直观。上下班时刻,让电视镜头对准大街上匆匆走过的民众,看他们的表情是轻松愉快,还是冷漠麻木,或者忧心忡忡,就能大致明白这座城市的幸福感。”你会质疑,没有统计数字支撑的“描述”,怎么能相信呢?那我只好对你的善良报以微笑。
高明勇:通读您关于城市的作品,有一个印象,您似乎想在“茶余酒后的鉴赏”与“正儿八经的研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但又一直在反思,“做城市研究而不够专注,著述体例芜杂只是表象,关键是内心深处一直徘徊在书斋生活与社会关怀之间。之所以采用两套笔墨,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在与学界对话的专著之外,选择了杂感,也就选择了公民的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责任。”现在退休后,继续关注城市,还会有这种“纠结”吗?
陈平原:若是官员,退休前后发言的姿态及立场很可能天差地别;我不是官员,且现在仍然在岗,我的纠结主要不是“位置”,而是“兴趣”与“能力”。兴趣太广,精力分散,讨论“城与人”的关系,或描述“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那还勉强可以,若深入探究具体的城市规划与社会管理,则超出我的视野及能力了。
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读书人在体现社会关怀与尊重专业知识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能说、敢说,还得会说;要让人家听得懂,且愿意听下去,而不仅仅是表现你的勇敢或睿智。
高明勇:我看您很喜欢引用周作人的一句话:“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的野菜》)这句话很容易联想到苏轼的一句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以您为例,北京和潮州,哪个更容易让自己“心安”,为什么?或者说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心安处”?
陈平原:我1984年秋北上求学,此后便在北京安营扎寨了。相比故乡潮州,我在京生活的时间更长,且事业大都在此展开。你一定要问哪个更让我“心安”,毫无疑问,应该是奋斗、崛起以及收获掌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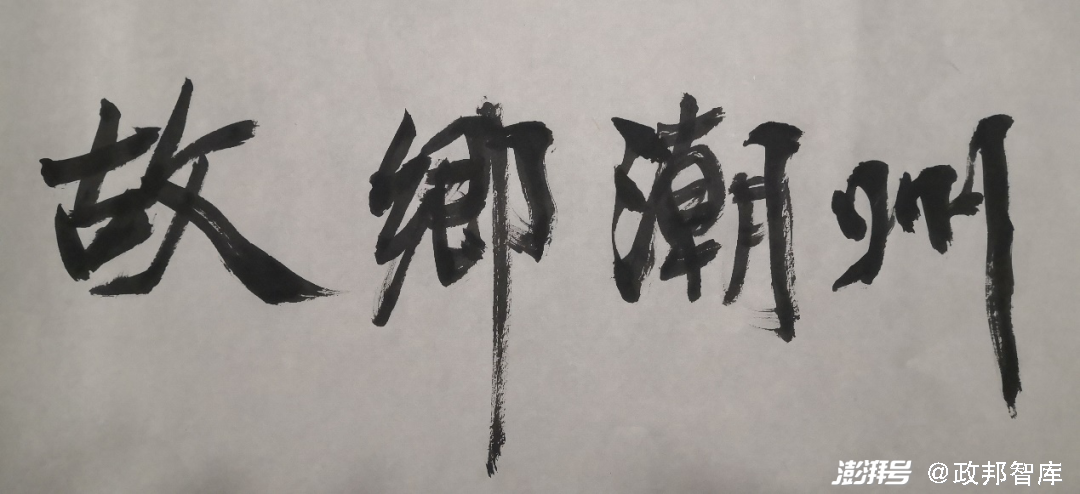
今年我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随笔集《故乡潮州》,其“后记”称:“为家乡潮州写一本书,这念头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这一选择,无关才学,很大程度是年龄及心境决定的。年轻时老想往外面走,急匆匆赶路,偶尔回头,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非乡土。到了某个点,亲情、乡土、学问这三条线交叉重叠,这才开始有点特殊感觉。”对我来说,这个时候谈论“故乡”,既是心境,也是学问。具体说来,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
高明勇:您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中谈到“北京学”研究的规划时说,“原来的计划是,退休以后,假如还住在北京,那时我才全力以赴。”现在您已经退休了,还住在北京,还会“全力以赴”吗?如果“全力以赴”,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和设想?
陈平原:从第一次在北大开设专题课“北京文化研究”,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变化题目,讲了一次“都市与文学”,感觉不太理想。因为,按目前的学科设置,这“北京学”横跨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建筑等,好像谁都可以插一脚,可又谁都不太把它当回事。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其中说到:“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学)念书,对脚下这座城市,理应有感情,也理应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

乘着还没退休,还有开课的权力与义务,下学期我约请了城环学院的唐晓峰、历史系的欧阳哲生以及中文系的季剑青,我们四人通力合作,为北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北京研究”专题课。若能成功,以后希望能变成常设课程。让每一个北大学生都有了解北京这座城市以及“北京学”进展的可能性,这比我个人撰写一部有关北京的专著更有意义。
高明勇:去年您被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否意味着继“北京学”之外再开创“潮州学”?如果开创“潮州学”,难处在哪?
陈平原:“潮州学”早就有了,不待我来“开创”。1993年12月,经饶宗颐先生倡议,由香港中文大学发起和主办,在港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潮州学研讨会。这里所说的“潮州”,是个历史概念,包含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以及汕尾、梅州两市的部分地区。为了避免纷争,今天学界更倾向于使用“潮学”的概念。我在暨大“潮人潮学”公众号的“开场白”中称:“注重溯源的,可叫‘潮州文化’;关注当下的,则是‘潮汕文化’;希望兼及古今,那就‘潮人潮学’。”

名称不太重要,关键是要有打得响、过得硬的研究成果。无论“北京学”还是“潮州学”/“潮学”,我都只是帮助敲边鼓,无力扛大旗或冲锋陷阵。有幸出任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规划了若干事项,其中最用心的是编纂《潮学集成》。有感于近年地方文化研究热潮汹涌,但学术水平不高,重复出版严重,我邀请了二十位对潮学有兴趣且学业专精的朋友,分语言、文学、历史、戏曲/音乐、华侨/海外潮人、教育、思想/宗教、美术/工艺、民俗/饮食、文献整理等十卷,站在学术史的高度,选编百年来的精彩文章,借此总结该领域的发展线索及现状,为年轻一辈确立标杆,也为后来者指示方向。
高明勇:我留意到您2002年时就提到过,“如果我当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专家,编写出几种适应不同层次读者需求的图文并茂的旅游手册。”转眼20年过去了,在国内有没有遇到过符合您的趣味或标准的“旅游手册”?会为潮州编写吗?
陈平原:设想的既可读又有文化品味的“旅游手册”,必须多方合力,而非纯粹的商业操作或政府行为。最近这些年,各地政府都很重视形象塑造,出版了不少印制精美的宣传册子。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正襟危坐,不太好读。经过层层审批,体现领导意志,承担太多功能(包含招商引资),这样的图书,很容易让普通读者(比如游客)敬而远之。
这是“供给方”的问题,至于“需求方”,也因网络发达,检索方便,变得更加挑剔了。实用性知识一查就有,精美图片也不稀奇;最为紧要的,反而是描摹世态人生,挖掘文化潜能,呈现精神境界,凸显文字魅力。这需要专家的学养与文人的笔墨,但又切忌“高大上”。便携、可读、实用、精致且有文化韵味,这样的“旅游手册”,不是很好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目前我没有为北京或潮州撰写旅游手册的计划。
高明勇:时过境迁,文旅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旅游局”也改成了“文化旅游局”,您今天想对文旅局长们说什么话?
陈平原:过去有句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主张反过来,应该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今天做不到,将来也必须如此。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众的丰衣足食以及幸福安康;而是否幸福,文化是个重要指标。
一个花钱大手大脚,一个赚钱锱铢必较,这天性不同的“文化”与“旅游”,很容易步调不一致的。当领导的,须学会平衡“看得见的业绩”与“看不见的精神”。一把手好办,因那都是你的业绩;分管的可就麻烦了,如何设计评价标准与激励机制,考验领导的智慧。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敢瞎出主意的。
高明勇:您关于“研究方法的北京”,是您“五方杂处”(旅游手册、乡邦文献、历史记忆、文学想象、研究方法)中的最后一种“面孔”,发表的时候是2002年,时隔二十年,关于都市的“研究方法”,是否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体系?
陈平原:这就说到我的痛处,二十年前一时夸口,至今没能实现。谈不上“相对成熟的体系”,只是深刻体会到,同样谈城市(即便仅涉及文化建设),专家、官员与文人,各有其立场、趣味与合理性。其中的张力,值得仔细玩味。既拒绝随风漂移,也警惕一叶障目,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局限性。这样才能管控好情绪,不至于像坐过山车,一会儿过分亢奋,一会儿极端沮丧。
接受采访时,常有人夸我在学问上“不断开拓疆域、引领风气”,我却真诚反省: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在很多领域都做出大的贡献。有的我真下了功夫,如小说史研究、学术史研究以及教育史研究,业绩还可以;有的却很不理想,比如城市研究。之所以还在坚持,大半是为了我的学生。我希望学生们不只是在老师的天地里腾挪趋避,所以预先开出若干可能的路径,他们凭自己的兴趣,有人走东,有人奔西,将来会比我走得更远。假如只是把自己的题目或阵地经营得特别精彩,学生们全都被笼罩在你的大旗底下,那不是一个好老师。
高明勇:您也专门提到“谁为城市代言”的问题,提出了官员、明星、老外、作家,以及民间自发代言五种情况,从文章来看,您应该是更欣赏作家和民间代言,但现实来看,不少城市还是选择明星的居多,希望关联记忆,快速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有什么具体建议吗?“代言问题”是否无解?
陈平原:请明星为城市代言,那明摆着是花钱打广告,我不喜欢。广告的功能是推销商品,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卖得出去,且短期内不被退货,那就是成功。城市的形象塑造,比推销商品要复杂得多,不可能这么直截了当的。极而言之,凡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都不是好的“城市代言”。
相反,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某个特定时刻,一个温馨动人的背影,一场不期而遇的欢聚,一首缠绵悱恻的民歌,都可能让城市迅速蹿红——说不定还名垂青史呢。这些,靠的是平日的文化养育,水到自然渠成,而不是花钱买来的。当然,还有我此前说过的,“有好作家的城市,真的是有福的”。
高明勇:就您的研究来看,之前关注较多的是北京、西安、开封等历史古城,那么对那些非著名城市,如何提升自身的“软实力”?
陈平原:其实我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三座历史名城,在《六城行——如何阅读/阐释城市》中,我借助某个特殊机缘,在“比较城市学”的视野中,阅读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台北、广州这六座中国最为重要的城市。而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中,我谈中小城市的改造方案,限于见闻,举的例子是甘肃的临夏市、山西的大同市以及广东的潮州市。当然,还是得承认,到目前为止,我没能力研究更多“非著名城市”。
有感于“最近二十年,随着经济实力提升,各种有形的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大剧院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容易被忽视的,是城市的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今日中国,东西南北以及特/大/中/小城市之互相抄袭(所谓‘千城一面’),很大程度是因其对自己城市定位失焦,把握不准,缺乏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 2019年年底,我向中央文史研究馆建议:“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各地政府文史研究馆参加,中央和地方文化旅游、教育研究、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协助,共同编写‘城市读本’。这将是贯通政府、学界、民众的机构编写的一套有精神、可阅读、能传播的‘城市读本’,目的是帮助各城市建立自己的形象、品格与精神。”建议案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若领导支持,我愿意投入。”口头发言时,现场反应极佳,但一个月后,新冠疫情爆发,议案理所当然地被搁置了。
人生苦短,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刚好大河在你脚下转弯,你跟不上,或不愿意跟,那就只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了。(完)
附录:高明勇对话陈平原先生系列访谈
1、《陈平原:经过了30年,我们与世界思潮同步》,2008年12月13日《新京报》,先后收入《京西答客问》陈平原著,凤凰出版社,2012年10月;《坐下来的中国》高明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
2、《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2010年10月9日《新京报》,先后收入《京西答客问》陈平原著,凤凰出版社,2012年10月;《陈平原研究资料》,王风,李浴洋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3、《既有国际视野,也讲本土情怀》, 2011年4月23日《新京报》“清华百年纪念特刊”,收入《京西答客问》陈平原著,凤凰出版社,2012年10月;
4、《对话陈平原:大学更应关注普通校友的“小捐”》,2012年5月27日《新京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