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听得见声音的世界:该流的眼泪流光了,剩下的只有苦尽甘来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编者按:
1957年,根据欧洲各国聋人组织倡议,世界聋人联合会将1958年9月28日定为第一个国际聋人节。从此,每年九月的第四个星期日,就是国际聋人日。
今年的国际聋人日(09/25)刚刚过去,是因为这些特殊的纪念日,才一次次提醒我们,从“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将目光移向那些特殊的聋哑人群体,看见他们的故事。
以下内容为李素琴以及其聋哑人儿子石头的真实故事。
文:范天玉
编辑:林子尧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李素琴说,他们家石头啊,本来是听得见声音的。
两岁零六个月,石头长得白白胖胖,由爷爷奶奶带着,爷爷奶奶在街道上开着家小商店,李素琴和爱人白天出去上班,爷爷奶奶就一面看店,一面看石头。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们总喜欢聚在石头家的商店门口谝闲传——这是陕甘一代的方言,指的是闲谈——看到石头就逗他,说让他跟着旁个锻炼的人扭屁股,石头也不恼,几步站起来,把背一挺,扭得欢得很。
石头喜欢人,按李素琴的说法,这或许也和街道有关。城市的边界步步逼近,街道就成了最后的村,石头的爷爷和奶奶都是村上人,少年时,爷爷住在村头,奶奶住在村尾,后来成了媒妁,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走过了整条街,奶奶就从村尾搬到了村头。由此,街上的人多多少少与都石头沾亲带故,不是姑姑伯伯,就是舅舅姨姨。石头半算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奶奶有时看店忙不过来,就招呼哪个远亲近邻看顾孩子,李素琴下班回家,总得找找孩子到了哪个叔叔伯伯怀里,石头会讨喜撒娇,每经过一双怀抱,总能要到些零食点心,到李素琴把他再抱回来时,小肚子总吃的滚滚的。
李素琴记得二岁半的石头同她说话,要“出门门”,要“带帽帽”,要“吃馍馍”。孩子小时没有任何问题的,她说了一遍,又重复了一遍,好像是怕有人不信,然而随后她又释然了。
“现在石头特别好。”李素琴最后这样说道,“我也很好。”

听障学校的老师
无声世界
石头是在两岁零六个月时,因病失去了听力。
这病究竟是什么,如今已不太好说。最大的可能是药物过敏,要么就是因为高烧,在李素琴的回忆中,石头刚脱离危险后,石头他爸就在找医生要病历,然而大夫和护士却都在推脱,说石头来了就在急诊,然后又推到抢救室,最后又转到了住院病房,几小时里周折了三次,哪里顾得上写病历。这之后,石头的病因就跟那份失落的病历一起石沉大海,再觅不着踪迹了。
李素琴不想追究谁的责任,谈起这事时,她要么说是命里的一劫,要么就只怪自己。按她的说法,石头起先只是腹泻,镇上的诊所给开了些药,但李素琴却没敢给孩子吃——那时村里有种说法,说这年纪的娃娃腹泻,是肚里有脏东西,不能立刻吃药止,得让他排空。李素琴信这个,于是便等,便熬,熬过两天,石头反复发起高烧,浑身发抖,她这才知道坏了事,急忙把孩子送去了市上的医院。到了医院,大夫给石头开消炎针,打下去没几分钟,石头就开始挣扎起来,护士看了,说“坏了”,是药物过敏,赶忙去喊医生,担架哐哐当当被急赶着推进来,又哐哐当当带着石头小小的、软乎乎的身子进了抢救室。
那一幕至今还刻在李素琴的脑子里——负责急救的医生把石头全身扒得精光,从肛门给石头上了药,小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六个月,是李素琴放在心尖上的宝贝,他无措地挥动着双手,好像挣扎着要抓住什么一样。李素琴说,石头开始时一把把攥医院的白床单,后来她才明白,石头是要抓着妈妈,她把手伸去,让石头握着,想同他说妈妈在,却是泣不成声。
这场大病之后,石头就变了,原本石头是个活泼的孩子,可住院那段时间,他却总是默不作声,呆呆地望着墙壁。这让李素琴总疑心孩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她同家里人说,“娃咋看着跟以前不一样”。家里人安慰她,“这么大病一场娃不得缓缓,这病大人都不一定受得住”。李素琴也就这么安慰自己,想着过一天、过两天,石头就好起来了,然而几天过去,石头却依然只是无生气地望着墙壁,偶尔露出困惑的神情来,好像整个世界在他眼中,都因这场大病变了模样。
李素琴等着、盼着,想尽办法让石头恢复精神,她把石头最爱的玩具搬到了病房,其中一件是辆玩具小卡车,按下按钮就会发出喇叭和音乐声,李素琴想,儿子过往最喜欢爬在家里商店的门边,看车来车往,或许他看到心爱的玩具,就能打起精神,跟妈妈说几句话了,然而石头却不知为何,对这一切都失却了兴趣。
李素琴越发不安起来,她替石头打理收拾着,一面心烦意乱,动作也不再像起先那样细发又慢条斯理,不经意间,她的手肘压到了那辆玩具小车,一声鸣笛猛然打破了病房里的寂静,她赶忙去看孩子,生怕这一声巨响惊扰了石头的睡梦。
然而没有,石头安静地睡着,仿佛那声巨响,就只回荡在李素琴的脑子里一样。
李素琴一低头,见自己手心上全是冷汗,心口一凉,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半厘希望
重度听力障碍。
这是医生给石头下的诊断。李素琴不愿接受,她带石头去更好的医院看,但最终得来的,仍是一句句冷冰冰的批语。李素琴的天塌了,她不再去上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同任何人说话,而石头他爸则待在另一个房间里,隔墙无言。仍被夫妻俩瞒在鼓里的石头奶奶照旧每日喊两个人吃饭,先喊了李素琴,听不到应答,又去喊石头他爸。喊过两天,终于是石头爸走出了房门。他把妻子从另一扇紧闭的房门中唤出来,而后郑重地把一家人聚在桌前,盖棺定论一般宣布了一张有一张病历单上医生对石头的最终诊断。
几日间的辗转周折与不甘地挣扎,好像就随着男主人的这一句话,终于尘埃落定。
愁云惨淡的一家几口迫不得已地商议起了石头的未来。在爷爷奶奶的眼中,“听力障碍”是个太温和又太过小心翼翼的说法了,那个年代,街道上的人只会把这喊做“聋子”、“哑巴”,或者更难听的,“残废”。在他们的记忆里,“聋子”和“哑巴”是成不了材的,那些让孙子当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作个“知识分子”的梦已破碎了,成了现实与记忆摩擦间留下的碎末残渣。最后,石头奶奶劝李素琴和丈夫,事已至此,只能当做是人生中历了一劫,孩子不能不管,干脆就彻底放给她和老头子带,至于李素琴和丈夫,不如再要一个,总算李素琴还年轻。那年计划生育政策已稍稍宽松,如果第一胎是非遗传性残疾——即像石头这样的伤病致残——可以酌情申请二胎。
可李素琴不想要二胎,那些念头像是在往她心口扎针,让那里淌出温热的血来。
然而日子总还要过下去。她又休息了一周,终于勉强打起精神,要去上班。彼时她还在长安大学工作,李素琴上过大专,是幼教出身,那时正在大学附中的后勤部门工作。学校的工作氛围比起公司总归是好上不少,她到了办公室,先看到的是堆在自己桌上的,同事们收集来打印好的资料,全是关于听力康复的。外面的声音多少让李素琴涨了一点信心,那些纸张似乎承载着些许的希望,但离李素琴似乎又都还太过遥远。这时,她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请她去吃一顿饭,见一位老师。
这场会面是姐姐特别安排的,另一位出席者是一位大学教师。据李素琴的回忆,三人聊了一阵,那老师笑着从耳朵里摘下一件东西来,比给李素琴看,一面说“小张,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李素琴凑过去看,见了个小小的耳塞状的机器趟在那位老师的手心,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副“耳道式助听器”。老师鼓舞她说“你看,这不是不妨碍我读书学知识吗”,李素琴这才知道,原来听力缺损可以通过器具弥补,只要康复得当,石头也有希望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工作。
回到家,她对着丈夫与公公婆婆宣布,要带石头去配助听器,后面的事很顺利,“短短一星期,就跟石头配上了”。
慈母情深

宽敞明亮的感觉统合室
带上助听器只是第一步,还有第二步,就是要训练,找康复机构。
这时李素琴已辞去了工作,全心全意带石头——孩子现在耳虽能听,却仍是口不能言,生活极其不便,必须有人看护——李素琴的丈夫和她商量,两人谁能挣钱养整个家,就在外面挣钱,另一个就在家带孩子,李素琴那时在长安大学的工资只几百块钱,远不如丈夫在外面挣得多,夫妻俩就此达成协议,李素琴辞去工作,过上了不比从前清闲的全职太太生活。
脱离了工作岗位后的李素琴所要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石头挑选一个合适的康复机构。二千年初的西安,听力康复相关的基础设施还极不完善,几天间李素琴逛遍了全市的特殊教育学校,最终选择了位于庙村的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的条件,按李素琴的话说,“只能算有上课的地方”,“有几间教室,每间教室里里有一块黑板,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教具都是老师自己做的,只是些粗糙的手工制品”,但她又补充道,这已是她在整个西安找到的最好的康复学校。
“负责任”,这是李素琴对陈老师的第一印象。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个月后,这位负责任的校长成了她的领导,而李素琴自己,则变成了在门的那一边接受巡查的人。
石头那时年龄小,要在陈老师那里上课康复,一去就是一整天,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分离这么长时间,是石头不曾经历的。于是,时常是李素琴一走,石头就开始坐在教室里嚎啕大哭,这一哭不要紧,往往会把嗓子哭哑、哭坏,课上不成了不说,还总发烧。陈老师无奈,只能打电话让李素琴先接孩子回家,等病养好了再来,一来二去,李素琴觉得不是办法,干脆跟陈老师商量,留在机构里陪石头。
那时机构的条件很差,老师们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开会和学习往往就在娃娃们午休处的旁边,李素琴安顿好机构里的孩子们,无事可做,就坐在一旁听陈老师讲课。这一年,西安还没有什么针对语训老师的专门培训,陈老师是唯一的专业人士,她自己编写教材,搜集其他省市的资料,口传给其他年轻的老师们听。听过一阵子,她渐渐摸出了门道,有一次陈老师给机构里的语训老师们考试,她大着胆子也去要了份卷子,做完后交了上去。隔天,陈老师找到她,同她说那场考试她拿了最高分,问她愿不愿意干脆给机构当语训老师,薪资就与其他老师等同,李素琴当然答应下来,从此转行成了一名听力语言康复教师。

宽敞明亮的感觉统合室
在康复中心里,李素琴是最受家长喜爱的那一个老师。大多数来这而的家长都知道,李素琴家也有一个“聋孩子”,因此总更愿意同她倾诉烦恼。
几处奔波
石头已能清晰读词了,但对李素琴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石头说长句时,总是磕磕绊绊,要只能康复到这种程度,显然还无法和听力正常的孩子们一起上学。这时她已有了技术,就自己测,给石头做评估,发觉是因为助听器的听力补偿不足,孩子只能听到碎片化的词语,而无法听到完整的句子。作为一名语训老师,近水楼台,李素琴自然知道要进一步提升石头的听力,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法,那就是手术植入人工耳蜗。
与助听器不同,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新玩意”。1995年,中国才开展了第一台多道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到李素琴那时,还尚不满十年时间。
第一个难关,是高昂的费用。24万8千元,李素琴清晰地记着这个数字,在零五年的西安,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都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幸运的是,李素琴家是拿得出这笔钱的。李素琴的丈夫在新时代的震荡中干脆选择了自己干个体,他本就从事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干脆趁着拆迁的浪潮干起了承包商,替周边拆迁的村干工程。这一来二去,居然也攒下不少积蓄。
李素琴同丈夫说了人工耳蜗的事儿,但丈夫心中却还有一丝犹疑。在他看来,儿子既然已成了现在这样,倒不如自己拼命工作替他攒下许多许多的钱,保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李素琴想,那样莫不是把儿子当成废物了吗?她不愿如此。

宽敞明亮的感觉统合室
隔天,丈夫同李素琴说,省里似乎有一个救助项目,如果能申请上,就能免费做。在西安,只有2到3个名额。24万8千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李素琴和丈夫商量了一整晚,干脆决定试试看。
在培训期间,李素琴自己给石头开小灶,一个月下来,石头的康复水平明显甩其他孩子一大截。出于吸引人才的目的,那里的老师找到机会单独与李素琴谈了话,将她聘到了该机构,工资是1000元,是当时语训老师中最高的。
石头最终没能申请到省里的名额,可李素琴却长久地留了下来,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名额申请结果公布的第二天,她和丈夫便双双放下工作,带着钱与石头上了北京。“我不放心西安的技术,”李素琴说,“伤口不长,就一点点,粗看是都看不出。那年西安同龄的孩子做的耳蜗,可以明显地看到耳后的疤痕”。
不上班的时候,她就带着石头去看书,石头看童书,她看语言康复方面的教材。李素琴说,自石头听力受损之后,她的时间就都花在了读书上,那时候用网络检索听力康复相关的资料还很不方便,她只是靠书。
“那几年我没有看过一分钟电视。”李素琴说,“也不出去玩。”
艰难困苦
在叙述往事的大多时候,李素琴都显得平静而克制,偶尔她会停顿一小会儿,似乎是在回忆当年的细节,痛苦很少浮在言辞的表面,反而都沉在水底,像是鹅卵石一样让岁月的流水冲刷,变成了光滑漂亮的形状。只一次,她忍不住落泪了,而那眼泪也是倏忽而逝的,就如流水上的浮光。
植入了耳蜗之后,石头的康复状况很好,这就意味着要不了多久,石头就可以去到“普校”上学了。“普校”与“普园”都是残障儿童家长通用的说法,指的是正常孩子们上的幼儿园和中小学,与特教学校和康复中心相对应。能去到普校,就说明孩子在功能上已与其他儿童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回普校,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就是胜利的号角。
李素琴清楚地记得,有天石头放学,让爷爷奶奶接回家,进屋时眼睛湿漉漉的,看到李素琴,就恨恨地盯着她,李素琴心里感到出了事,还没来得及问,石头就一把将耳蜗处理器扯了下来,用力摔在地上。

社会性区角-超市购物
“他对我吼,说为什么知道他听不见,还要把他生下来,要把他生成这个样子。”李素琴说着,第一次忍不住有些哽咽,她停了一会,努力地把苦痛都就着泪水吞咽下去,“还对我说,他一点都不想被生到这世上。我才知道,原来在学校,其他小孩就欺负我们家石头。”
石头带着的耳蜗,看上去就像是如今的蓝牙耳机,普校中的孩子没见过这件新奇的小东西,又看石头不让人碰,就聚在一起拿这事寻他开心,再加上石头毕竟听力有过损伤,说话的方式与大部分孩子都不同,语调难免有些生涩别扭,有调皮的小孩就给他起了外号,叫他“机器人”。石头到校和参加活动时,总有一群好事的孩子在走廊里奔走相告,喊着“小机器人来了”,到体育课和手工课要团队合作时,也不同他一起。
石头是他人的关爱里泡大的孩子,后来虽是因病失去的听力,却也没受过谁一天的冷眼,反倒是更招来了从前就疼他的叔叔伯伯们的关爱。在中心时,石头学话学得好,素来也受老师喜欢,更别说他性情大方开朗,在同伴中也受欢迎。普校中被人孤立与欺凌的经历,几乎是这个不过八岁的孩子第一次面对世界的恶意,让他惊慌失措,无从防备。
她心一横,干脆找到了石头的班主任,问她自己能不能去上一堂公开课,科普有关听力障碍的知识。这时她已算得上名师,说去科普,也算是有个由头,只是让家长上课,显然不太符合规定。然而,面对一个残疾孩子所受的欺凌,学校和老师最终还是选择了和她站在一起。
在此之后,石头的求学生涯越发地顺遂起来。小小的孩子在磕磕碰碰中日渐长大,熟悉了与好奇于他耳朵上小机关的人相处的秘诀,在李素琴的赏识教育下,他渐渐接受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挺直了腰杆。保有了开朗的性格,石头的话也说得越来越好,到初中时,已几乎无人能听出他曾有过听力语言问题。
接受访谈时,李素琴刚刚从郑州学习归来。据她所说,这次的学习是为了探究听障儿童是否能在进行康复的同时接受普园教育。“怎么进入普园,怎么适应普园,这都是问题。”李素琴说,“我是家长,对这个最清楚,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聋孩子。”
“主要是风险大。”她解释说,“娃娃们正是比较闹的年纪,现在做耳蜗的也比较多了,一个耳蜗20多万,有的是陶瓷的,不抗碰撞,万一在学校里小朋友打打闹闹,把这个弄碎了,经济损失还好说,碎片在脑袋附近,弄出什么事儿才可怕。学校也有学校的担心,现在很多家长入学都要私下签保证书,写如果孩子在校时出了什么事儿,学校概不负责。”
铁树逢春
九月开学,石头就该读大二了。他就读于本地一所高校,是名定向生,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工作也都有了着落,不需要李素琴再操心了。
孩子长大了,李素琴说,语气很感慨。过往冷暖自知的十几年,好像这会儿都远得像梦似的。那个小小的、摇着她的手说“要帽帽”的娃娃,如今窜成了一米八的大高个,性格宽厚开朗,爱打篮球,总能和周围人打成一片。说到这儿,她又提起一件事儿来,说前不久的暑假,石头头一次在外面试着打了份工,在学校里发传单。头二天,这个从没自己挣过钱的大小伙子觉得这份活很是新鲜,回家时总愿意和李素琴聊打工时的趣事。过几天,新鲜劲退了,西安盛夏里四十度的高温就开始显得磨人。石头回到家,热得说不出话,瘫在沙发上吹空调,李素琴打趣他说“知道挣钱不容易了”,一面笑着给他去跑菊花茶润嗓子,石头就向着她说自己“本来就生得黑胖黑胖,再一晒,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奶奶在一旁听了也笑,就跟他找来李素琴出去玩时买的女士草帽。石头把帽子戴到头上,样子不搭调,显出几分滑稽来,一家人就笑作一团。
“别看我现在总爱笑,我以前特别好哭,结婚前家里人就都埋汰我,说红红(李素琴小名)是水做的女娃子,”李素琴笑着说,“说来挺不好意思的,后来嫁给我老公,我一哭,还是得全家人就都来哄我,我也不是故意,平常和他拌个嘴,吵个架,我眼泪就忍不住啪里啪啪地就下来了”。
“这几年就不哭了,好像一辈子该流的眼泪都在年轻那一阵子流光了,现在只剩下好的,就像人们说的那个……” 李素琴接着补充道,“苦尽甘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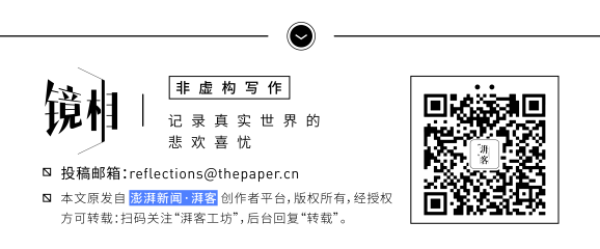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