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帕特里克·曼宁谈全球史、移民与民族国家

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1941-)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世界史专业安德鲁·W·梅隆(Andrew W. Mellon)讲席教授、荣休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6-2017)。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非洲经济史、人口史(非洲奴隶贸易)、法语区非洲社会文化史、全球移民史及科学史等。目前,他主要指导“历史信息合作与分析”(Collaborative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项目,并致力于世界史数据资源的创建与共享工作。他已译介至国内的代表作有《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世界历史上的移民》《历史上的大数据》(Big Data in History,待出),其他主要著作包括《非洲移民:透过文化看历史》(The African Diaspora: A History through Culture)、《世界历史的全球实践:全球的进步》(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Advances Worldwide)、《世界史:全球与地方的交互》(World History: Glob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等。2017年9月至10月间,曼宁教授应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邀请开设“全球史概论”系列讲座,一共六讲。在此期间,曼宁教授就全球史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专访。
您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历史开始,一直致力于非洲史的研究且坚持至今。非洲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您在这一领域耕耘如此之久?
曼宁:我非常有幸参加一个关于非洲的优秀的项目,该项目汇集了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教授。1963年我开始读研究生时,非洲史刚刚被确立为一个学科,但当时许多历史学家并不认为它能成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确实,最初关于非洲的书面文献似乎十分有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材料。所以,文献不足的问题其实只是出于想象。我们努力工作,以其他方式提出证据。一种是传统的访谈形式,另一种为文化史和人类学的研究等。我们尽量寻找不同的文献收集方式。当我毕业之时,研究非洲史已有一些时日。然后我继续学习了其他内容,但总感觉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另外,我发现很多关于非洲和非洲史方面观念错误的反讽之事,其中大多都是偏见和其他类型的信息错误。举例言之,一些曾经研究农业史的学者认为,非洲因土地贫瘠而无法支撑起先进农业的发展。但非洲现在的人口比那时多五倍,所以该观点可谓不攻自破。另外,也有人发现,一些专家所撰述的内容甚至都是错误的,这些都促使我进行回头研究。
那您肯定经常前往非洲?
曼宁:确实如此,但我并未逗留太长时间。在1966和1967年,为了撰写论文,我去过几次。但之后因个人事务及家庭原因,我一度中止了研究。后来,我又回到非洲研究领域。在最近十二年中,我每年都会去。当然,我在城市度过的时间远多于农村,也领略到了非洲西部众多不同国家的文化。
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您就一直潜心于全球史领域的研究,长达三十多年。您此前关注的焦点一直在达荷美的经济史研究,后来为何又转向全球史领域?
曼宁:最近有人问及相似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你所说,我对非洲史的最初研究关注于达荷美1880-1914年这一短暂时期的经济问题。当时我的研究关切为:法国征服并接管达荷美的事务中,有多少是殖民当局没有改变的?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有一个原本就组织良好的体系延续下来,而法国在理论上并未重塑该体系。我继续探索,于是有了更多发现。直至三十年后,我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时间跨度较大,涵盖1640年以后该地所有的奴隶贸易。在奴隶制度下,直至1960年,该地的很多黑人被运送出去,这种掠夺似乎给当地带来了极为沉痛的灾难。如今的观点则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有限的奴隶贸易是达荷美同世界交流互动的窗口,不会带来更多伤害。首先,早期很多人因奴隶制被运出只是阻止了更多社会冲突。
后来我又发现,到了非洲同世界交流的二十世纪,法国政府收取了大量税款,但这些钱并未花在当地,而是被送至其他地方。所以,繁重的税收制度对当地的损害远超奴隶贸易。我因此而沉迷于全球史,这就是我为什么研究该领域、该国家,特别是关于奴隶制和人口的问题。我开始研究奴隶贸易总体上对非洲人口有什么影响,并仍然致力于该问题的探究。我还在写另一本书,也是希望能澄清该问题。而且我发现,并非仅仅是从非洲到美洲的浪潮,也包括后来部分非洲人返回非洲故土,通过美国理念来重塑非洲。这些往来迁移的现象说明了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互联系——不仅与欧洲征服者,也包括美国人。
毫无疑问,全球史已经成为当前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潮流,但究竟什么是“全球史”似乎还有些众说纷纭。也有学者直接以What Is Global History为名出版了专著,较有影响者包括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2008)及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2016)。有人认为全球史是一种视野,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研究取向,抑或将之视为一门学科。您如何看待全球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歧?您对“全球史”又有哪些新的理解?
曼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讨论不会停止,并会一直持续下去。首先,我想评论一下这些书。有一个系列丛书以“什么是什么”为名,比如“什么是经济史”“什么是中国史”“什么是全球史”等,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就不仅是针对全球史了。但是,人们确实要问:“全球史是什么?它与其他历史有何不同?”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刚才的讨论,即关于我本人从非洲史向全球史“跨越”的问题。我于2009年写了一本名为《非洲移民:透过文化看历史》的书,之所以称“透过文化看历史”,是因为我们在早期并没有关于非洲的大量书面材料。但你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文化现象,从诸如歌曲、服装和建筑等相类的物质文化元素中找到证据。所以这本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书,包括那些被运到美国、欧洲、西亚和南亚的非洲人,均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非洲史就是研究全球史的一种不错方式。
关于全球史,首先,我们曾做过国别史的研究,但全球史并非国别史。我们可以从国别史的视角观察中国这样的大国,亦可观察我所来自的另一个大国——美国。人们还可以继续深入探究,甚或利用某个国家的历史。那是真实的历史,因为至少从十九世纪后期,也就是1870年代到1880年代以后,历史真正前进了一步:大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连化学博士也成了普遍现象,而欧洲的国别史、亚洲的国别史,最后包括非洲的国别史也繁荣兴起。但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远比国家的历史还要长,它不止是国家、政府、君主制和共和国。历史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而全球史即试图研究所有。
你们或许会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人们对全球史的质疑之一即是其研究内容太大,并试图包揽整个世界。其实,当前即有一些世界范围的现象,比如传播极为广泛的流行文化,或者诸如流感等疫病,人们似乎都不会理睬。但这里确实有一些全球性的故事。所以,全球史即是如此。但历史更为复杂,关于全球史的研究,我认为存在“规模”(scale)。我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没有广泛用于英语或其他语言,而我们开展规模分析,需要经历从“最小规模”到“最大规模”的梯度变化。生物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从事微生物研究时,我们观察到的是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组织,然后从研究个体、动物和植物到观察整个宇宙。我认为,并非仅我自己持这种观点。之所以说全球史试图研究所有事情,是因为历史发生于所有事情的不同层面。
那么再说国别史研究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国家造就一切,并想藉此解释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如愿以偿。但在某些情况下,看似是地方因素的影响却颇具全球色彩,诸如全球性的疫病等。所以我们要将全球史视为宏大的、世界性的领域,这就要求人们更为努力地探索。不过,我们可能必须要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书写方式,从而达到使人们理解的目的。因为我们绝不可能看到一切,我们或许只能得到历史上的一个剪影。
跨国史概念的出现要晚于全球史,您认为全球史与跨国史有何联系与区别?跨国史关注的核心问题与全球史有何不同?
曼宁:简单地回答,跨国史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国别史学家明白其中有跨国史的因素。一名美国史学家可能会觉得有必要研究一下加拿大,认为研究一些其他国家的信息有助于促进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而全球史学家的目标不是去解释一个国家,而是去解释世界或者世界的一大部分。所以就会有一些看似矛盾的情况:两个历史学家做的研究几乎相同,同样的文献,同样的问题,但一个是利用这些文献促进对一个国家的理解,而另一个是利用这些文献促进对全球情境的理解。历史被整理成不同类别的文献,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及文学史等,还有地区文献、国家文献和全球文献。跨国史学家研究国家文献,而全球史学家研究全球文献。
更复杂的是,人们之所以将“跨国”这个词叫作“跨国”,因为他们不想一下子跳到全球范围。我发现今天的美国,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贴上跨国史学家的标签,而不是全球史学家。这是因为成为一个跨国史学家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训练,你想做就能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有所创获。不过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发现停留在个人层面,而其他人也有过相同的发现。我的预测是接下来有一些国别史学家用跨国史的方式做研究,所以这一波跨国史浪潮将会增长,但紧接着会下降,而全球史将能够持续增长。未来十年全球史会发生什么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进行全球史的研究有时可能困难很大,因为范围太过宽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小的方面介入全球史,比如选择美国传教士,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促进了全球信息的交流互通,能否以他们作为全球史的微观缩影?
曼宁:当然可以。但是也应发现其中存在着危险。我想以移民史为例。人口迁移具有很长的历史,但一开始我们仅仅研究移民的一部分,譬如他们的迁入和定居,而这使移民史的研究越走越窄。尽管迁移是一种流动,大部分的历史局限在区域内部,即具有本地化的特征,和其他地区似乎没有联系。作为一名移民史学家,我研究的是非洲奴隶史。我确信这一历史和欧洲或中国的人口迁移处在同一时期。尽管后两者的人口迁移主体并非奴隶,但他们也经历了独为异客之愁。在进行移民史研究时,应该将这些不同的经历结合起来。奴隶迁移史的研究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接纳为移民史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特定领域会循环往复,就像一些古老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一样。
对于传教士而言,他们背井离乡,将福音和善言带给千里之外的人们。返回故乡后,他们仅将其事迹记录下来,或喜或悲,却不进行分析。因为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必要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和同时期其他事件联系起来。此外,有时你所使用的材料的语言也会阻碍你。当你发现某个特定的词汇被反复使用,你就会渐渐明白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当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你必须抓住这些信息,从背后发掘其意义。我并不是在劝阻你,事实上,我的一位博士生正在研究一名传教士。这名传教士生于荷兰,长在美国,后来前往日本,终其一生都在日本传教授课,并成为日本许多政要和大学领袖的老师。他在日本政治变革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遇到的移民问题都是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仍有许多在中国发生的和西方无关,而关于中国南北方之间、中国和东南亚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故事。无论如何,任何故事经过深入挖掘,都能够找到十分有趣的观点。这些问题是为了找到一些优秀的小型全球史研究项目,需要好好研究,阅读关于大项目的专著,反问自己这些研究者们是如何设定大问题的,看能不能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您关于全球史的研究中,黑人移民群体是您的重要关切。不可否认,移民群体的全球性流动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您能谈谈当前美国学界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状况吗?
曼宁:我们可以从《阴郁的指令:亚洲移民与全球化的边界》(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一书谈起。该书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亚当·基翁(Adam McKeown),我们关系很亲密。不幸的是,他最近因意外而突然离世,我们将参加他的追悼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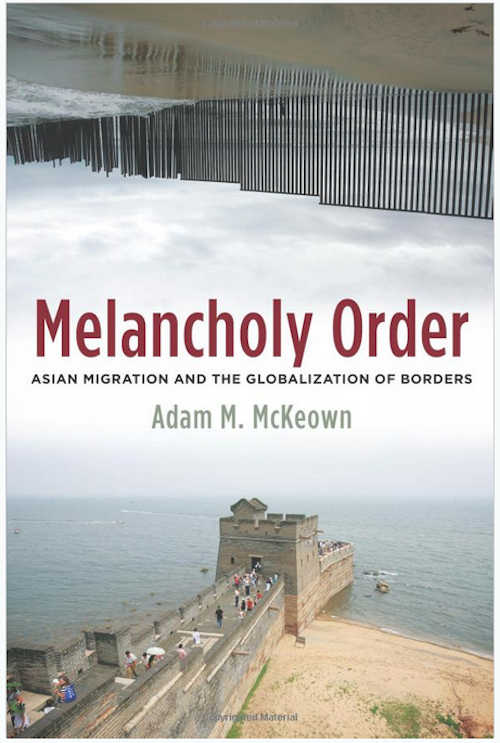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美国的华人移民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并非机械性地阻止中国移民,而是诉诸在中美双方政府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而这些机构均颇有影响力与民族特色。那些前往美国特别是加州的华人(多数为广东人),深谙管理机构会询问一些特别刁钻的问题。所以在到那儿之前,他们会率先到一些辅导机构学习,并且会捏造一些虚假的信息,以获得特定的身份认知。在他们做好准备后,就会前往接受询问。如果确有实力,他们就会通过考试并被美国接纳,反之就会被送回。因此,双方均知道其中有一些不实的信息,但这一系统却建立在公平的原则之上。这个故事讲的不只是移民,更是国家建设和美国政府治理的问题。这本书因此受到很多人追捧,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荷兰,有些学者们正编纂一系列关于亚洲移民的书籍,并试图呈现出一种探讨移民问题的新方式,这一新进项目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跨文化移民率等数据比较在过去的四五百年中,亚洲和欧洲及其他国家的移民情况。该系列的特色之一即是编纂者们将军人和水手纳入到移民群体中,而在原来的大部分情况下,因政府并不认同这一分类,所以这些人并没有被统计在内。如今这个问题已经划定清楚。还有一个例子,南美洲的学者们对非洲移民问题很感兴趣,他们也对亚洲移民兴趣浓厚。秘鲁总统就有亚洲血统,他的祖先是日本人而非秘鲁人,这也使得这一问题备受关注。
您在《世界历史上的移民》一书中一改过去按照“民族-国家”定义人类社群的模式,采取了根据“语言群”(language community)来划分的新取向,您为何有这样的学术关怀?
曼宁:是这样的,在受训成为一名非洲历史学家期间,我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洲语言的分布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联系问题。目前这项工作在非洲地区开展得非常顺利,但在过去,学者们不太关注语言的历史研究。这就好比中国有很多不同的语言,但我们在通用教材上似乎只能看到普通话,诸如蒙古语和其他土耳其语系的语言则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教材中(这里不包括那些地方教材)。如果你仔细梳理这些语言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关系,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语言群模式。研究语言能够很好地归置那些在地图上未被标明的群体,尤其是那些较小的、没有代表性的族群。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我曾梳理过全球印欧语系的传播情况。印欧语系是由欧洲的所有语言加上印度及伊朗的大部分语言组成,一开始只是东亚语言的细小分支,如今却分布甚广。在美国随处可见说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法语的人,整个非洲和欧洲都在说英语。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母语和第二语言。对我而言,英语是我的母语,也就是第一语言,是你们的第二或者第三语言。
你们来自中国的不同省份,因此会说诸如山东话、福建话与河南话等不同的方言。但当你们南下广州之时,出于交流之便,你们会说普通话,所以这些方言就变成了你们的第二语言。我认为从这个方向看待语言群和语言群的变化非常有趣。我再给你们讲一件事,我的住所对面有一环球小屋,那里有很多学生,其中便有一些非洲学生在学习中文。他们在济南参加了一个项目,一年中只学中文,包括听说读写各个部分,一年结束后则参加测试,如果能够通过就可以前往医学院学习。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就可以回到非洲,成为一名医生。当他们看书的时候,他们使用中文查询;当他们和其他同事交流之时,他们说的也是中国话。如果该项目取得成功,这将对非洲的所有职业都有显著意义。他们不仅会说中文,而且还要用中文工作。当然这需要别的语言辅助,毕竟非洲的语言环境非常复杂,因此必须要学习更多。总而言之,英语遍及世界,同时,中文、阿拉伯语等其他语言也都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点我认为十分有说服力。
近些年来全球各地均表现出极大的反全球化趋势,民族主义的膨胀似乎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民族国家的意识与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全球化到底是一种现实,抑或仅仅是一种梦想?
曼宁:我认为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人们察觉到了全球互动,甚至认为这在以前从未出现,于是问题丛生。其实相比以前,当下全球互动势头更甚。全球化时代也是疏于管制的时代,以前还对大范围合作有所限制和管理,不过当前的束缚则有所舒缓。另一方面,不平等现象亦在激增,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遍布全球,所以当前的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特点。
我正试图想象一幅不同的全球化画卷,其中是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我认为经济互动是一种全球化,但文化交往则是另一种。虽然每一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均不相同,但他们又交流频繁。有一次我乘出租车,虽然司机师傅年纪很大,不太可能是大学生,但他当时正在听英文歌曲!看,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文化全球化,外国音乐已经成为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嘻哈(Hip-Hop)或许可以是更好的例证。
除了致力于全球史研究外,我们得知您当前正在指导“历史信息合作与分析”项目,以建立起世界史研究数据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规模宏大且必将嘉惠学林的重要项目。您能谈谈这一项目的缘起、当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及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吗?
曼宁: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论全球史,但是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全球史的基本史实呢?事实上,目前我们在用国别史的史实来书写全球史,这其实算不上糟糕。试想国家一旦成立,这个国家的资料便开始形成。国家观念、教育、工业以及其他各种文献逐渐累积。不过我们现在认为世界是一个单元,而且这个单元早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所以,我们正试图为历史信息建立基本的共享平台,以此覆盖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区域,从而探究不同地域的相同问题,诸如人口、经济、社会环境、政府和文化等。这一工作十分棘手,因为它总会向不同方向发散,而我们只能向智者或是书籍求教,当然不会局限于文字层面。那么我们去哪儿找证据?除非掌握证据的人给我们。所以我们努力为手握证据的历史学家们建立网站,他们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证据,而我们的任务还在于进一步解释这些证据。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努力找到可以一以贯之的处理数据的方法,使档案数据互相联系。随后我们与信息科学的研究者一同合作,我们有优秀的信息学院并且和他们建立了常规合作。我们通过提高技术手段以对不同的数据组做进一步的取样、整合与研究。我们期望找到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世界在地方层次、区域层次甚至更大的层次上均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同时也期望可以梳理其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是人们始终不愿向我们提供数据,他们总是说:“我还在做,但还没有完成。”或者他们只是不愿让别人得到自己的数据。他们过去一直是作为个人来工作,从未将自己视作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有责任分享,他们也不愿提交自己的数据。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我的最新研究与城市科学这一新的视角有关。在互联网上提交问题和数据,任何对其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所以我们找到两组学生,一组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另一组来自于华盛顿,他们本科阶段的专业均是城市科学。我们给他们提供数据组,他们便会对其进行书写、编辑、核对以及整理,最终让这些数据可以更加容易地组合。我们在网站上提交材料,发给学生,学生整理后再发回。我们会记下学生的工号,这对他们来讲就变成了另外的课程、实习或是特殊的课外作业,我们也鼓励学生询问并完成工作的反馈。初步的工作尚未完成,并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急需条理清晰的历史信息,我们将会努力公开此类意愿并找到解决办法。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