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创造“世纪之交”:读周嘉宁《浪的景观》|新批评
原创 刘欣玥 文学报

无论是“地下上海”,还是电波里的“空中上海”,周嘉宁探入潜伏的城市人文地理脉络,最想突出的,仍是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有如热流在城市地层下方翻涌,时不时也能闯入公共空间展示自己。书中多次出现对于一代人“好运”思考。
从《密林中》一路写至《浪的景观》,周嘉宁终于抵达写作风格的成熟时刻:内在的专注,明亮的美学,清洁、克制而精确的汉语表达,对于青年时代精神世界的热爱与洞悉。
新批评
创造“世纪之交”:读周嘉宁《浪的景观》
文 / 刘欣玥
在21世纪快要走完第二个十年的时候,《鲤》做了一期“我去二〇〇〇年”的主题策划。受邀撰稿的“80后”作家、批评家与媒体人,共同回望那个人人急于快步奔向新世纪的90年代,讨论被匆忙略过的时代波动。求新求变的亢奋,全球化的近景,对未来的乐观预期,穿透新世纪前后一代人的青春,也参与塑造了当时还没有定型的世界想象与价值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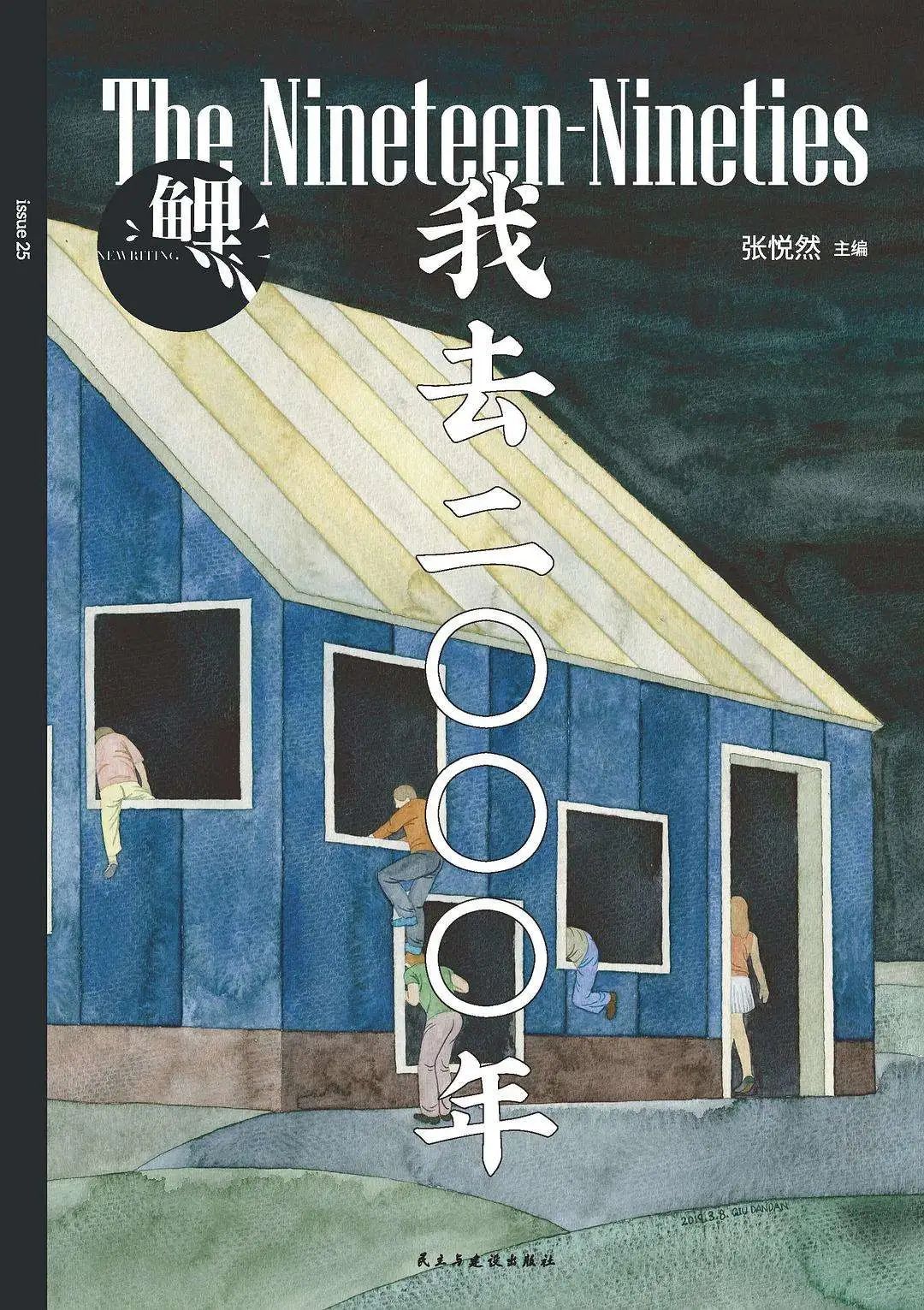
这一期里有周嘉宁的《风暴天》。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上海的台风回忆:高中的夏日,整座城市到处淹水的景象,让原本纪律严明的军训变成了一场无人管束的校园狂欢。短文的语调明快、轻松,但周嘉宁要讲的,其实是成长记忆里上海城市排水系统失调造成的影响。2000年以后,政府投入大笔财政预算,展开道路积水整治与城市下水系统升级工程,极端天气来袭时的乱糟糟场面,从此彻底说再见,和18岁以前胡闹的青春期一起留在了上个世纪。
台风意象曾多次出现在周嘉宁早期的作品中,《苹果玛台风》(2003)里有过典型的青春忧郁叙述,独自等台风来的女孩“感到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忧伤地潮湿着”。到了《风暴天》,室内的孤独个体变为集体流动的队伍,城市史和社会现实底色的引入,显然都为感性的青春心曲增加了发散的维度。对于这一点,周嘉宁自《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以来“走出自我”的写作调整,有更为充分的展开。《风暴天》的文末写道,“尔后,我们共同来到了干燥的下世纪。”

周嘉宁在近期思南读书会举办的
《浪的景观》新书分享会上
在一贯给人以多雨印象的上海,周嘉宁为什么会赋予其“干燥”的形容?“干燥”之感,是市政基建治理与改造升级的结果,更是感官体验在文学层面微妙的转喻。生活世界变得更加清洁宜居,如同雾障散去后,万物遵守的法则变得清晰。但标准化的过程,势必要整顿掉混乱与混沌感,也见证了诸多“另类之物”的昙花一现,而后消失。周嘉宁用几年的时间,将这种观察,写成一系列以21世纪前后十年为背景的小说,从上一本小说集《基本美》(2018),到最新小说集《浪的景观》里的“中篇三部曲”——《再见日食》(2019)、《浪的景观》(2020)和《明日派对》(2022)。《风暴天》可以视作这个系列的题跋,行文虽短,却具备了这些小说几乎所有的核心元素:对世纪之交的凝神思考,价值多元且宽容的时代氛围,年轻人的叛逆、合作与创造,秩序动摇时意外之美的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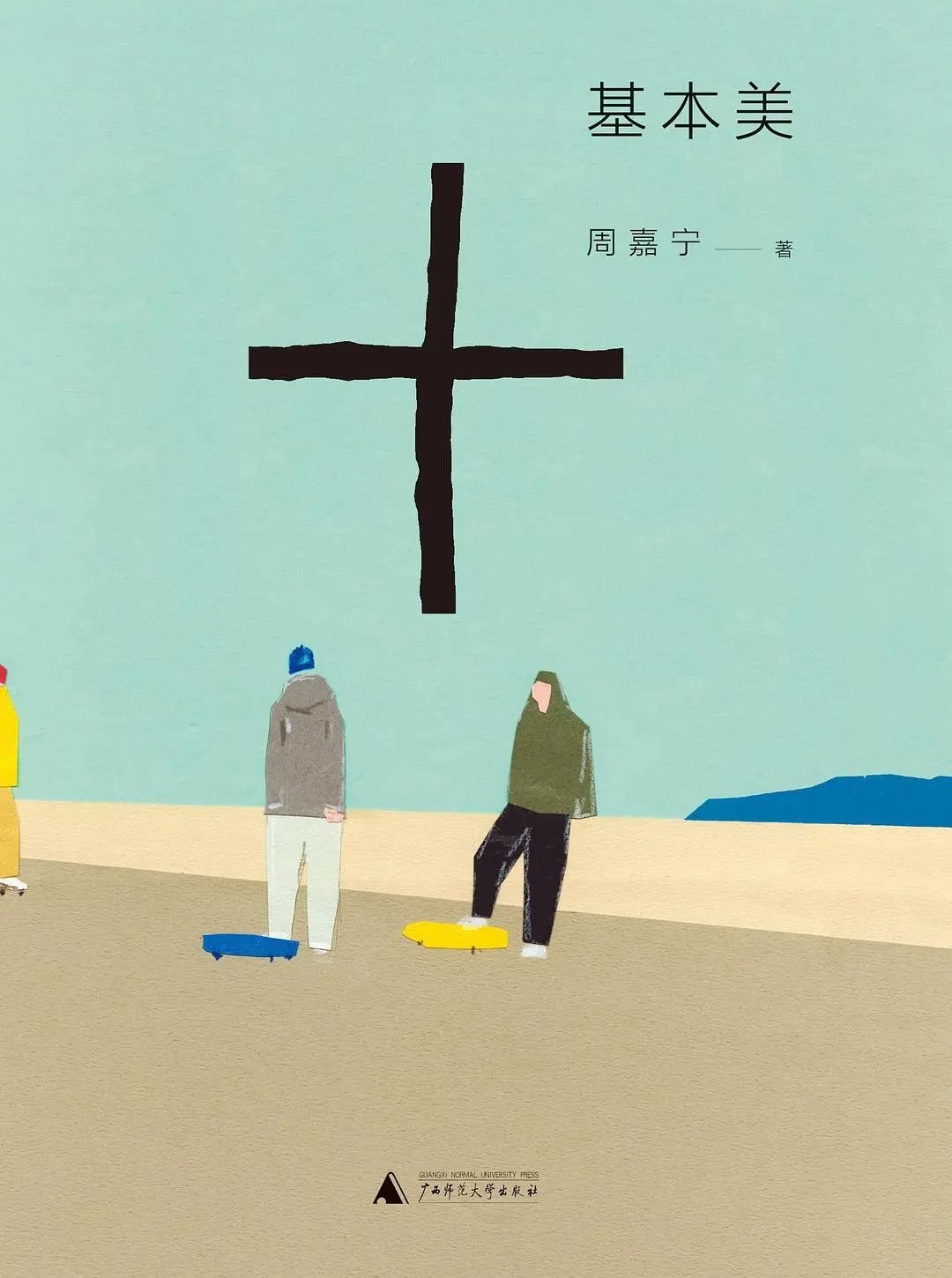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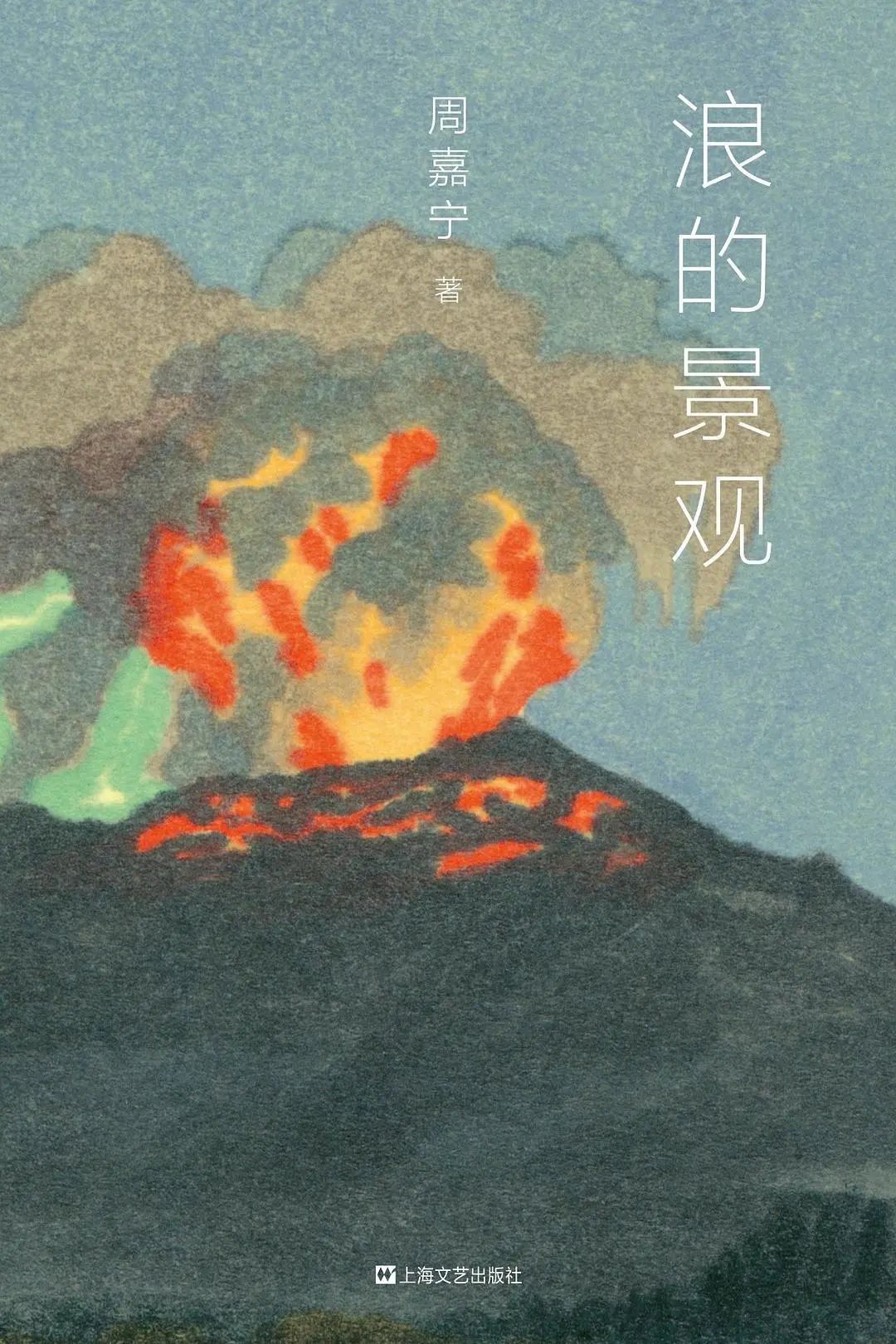
这样看来,“台风”是一则极佳隐喻——风停雨住后,世界趋于井然有序,周嘉宁想要用写作追摹的,却是规则尚未凝定时的遍地元气。释放出元气的,正是那些在城市快速变化中被抹去痕迹的事物,它们曾从裂隙里涌出,但在当时缺乏有效的文学觉察或文学表达。经过时间的沉潜与空间的考古,周嘉宁使用记忆、语言与虚构,让这些“另类之物”的细节与意义重新显影。借用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意象来说,那是时代的强风吹拂下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浪。在21世纪的弄潮儿眼前,再小的浪尖上都藏着未知的机遇,而每一个状似小人物的冲浪手,都是自己的历史书写者,无论他们此后是否被更大的浪所吞没。
同名作《浪的景观》讲述“非典”阴影下,从大专毕业后陷入无业状态的“我”和群青,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手了友人在迪美地下城的服装档口,成为上海最早的外贸服装个体户。如同一对携手闯关的拓荒者,两人熬过地下城兴起时艰苦阶段,直到交上好运,赚进第一桶金。地下城的审美与消费深受摇滚文化浸染,年轻人以衣着标榜叛逆与个性,“我”和群青在不知疲惫中度过了一段浪漫、惊险与财富齐飞的传奇岁月。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我”与群青的引路人,服装摊主老谢,他从华亭路、襄阳路,再到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的一路辗转顽抗,直到彻底退出行业的心碎历程。这段充满江湖气息的外贸服装贩售的变迁史,被周嘉宁写得鲜气淋漓。又是贩假,又是斗殴,愈发惨烈的金钱搏杀中,老谢这样富有情怀和才干的“外贸元老”相继出局,“我”与群青的小档口也最终被吞并。迪美地下城曾经作为小众时尚淘货乐园的精神已逝,只剩下一具供观光客打卡的消费景观外壳。故事的尾声柳暗花明,2007年前后恰逢淘宝网兴起,“我”与群青在结束实体销售生涯之后,告别彼此之前,还意外吃到了网络销售最初的一波红利。

《明日派对》同样采用了双主人公的结构,写了两个女孩在广播电台黄金年代里的友谊、奇遇与共同创造。故事从2001年轰动一时的罗大佑演唱会说起,“我”与王鹿相识于演唱会现场。两人同为一档电台节目的忠实听众,后来因为参赛获奖,以大学生的业余身份,在上海广播电台拥有了一档专业节目。她们建立起音乐上志同道合的小团体,通过电波传递20世纪西方摇滚乐的异质之声,也得到了素未谋面的听众的热情回响,甚至亲自采访了罗大佑。在举办名为“明日派对”的音乐现场演出后不久,两人的节目在汹汹来袭的电台商业改制中被关停。这段听觉共同体的存在时间尽管短暂,却记录下了同代人弥足珍贵的共鸣共振。

新旧世纪之交,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冲击广播电台这样的国营单位,为了效率和盈利,不得不割舍情怀,作出结构性的整顿与裁减。在《明日派对》和《浪的景观》里,无论是空间被一再挤压的小本经营实体服装销售,还是电台这种传统媒介形态的转轨,都置身在这个价值趋于单向的进程中。但与此同时,小说里也出现了方兴未艾的ebay、淘宝网,还有尚在胚胎阶段的豆瓣网的身影。今天的读者一定能会心一笑,像是看见了老友的童年照片。没有人能拒绝技术革新与资本竞逐,尽管告别总会伴随着叹惋,但那个时候,多的是继续奋勇迎上下一个新浪潮的人。
对与自己经历相近的城市文艺青年群体的造像,早已是“周嘉宁式的小说”的标识之一。她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偏离于主流规则,因为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结下友谊,也总能搭建青春乌托邦般的同温层与庇护所。《浪的景观》一书,则尤其突出地以空间化的方式,复现了一系列汇聚文艺青年的实体“据点”:《浪的景观》里的摇滚歌友会、外贸服装批发市场,《明日派对》里上海的“指挥部”与南京的“防风林”、电台节目、线上音乐论坛。《再见日食》的故事架设在更大的国际视野里,但位于北美中部的小城佩奥尼亚同样具有“飞地”气质。在那里举办的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为第三世界的年轻人提供了“身处世界进程之外”的避难所,在跨越语言、肤色、文化积习的碰撞中,摸索人生与艺术新大陆的入口。这些空间场所,都可以归入前述具有“混乱感”的事物之列,其所内蕴的青年创造力和文化传播能量却不容小觑。无论是对城市垂直空间的重新发现,还是年轻人在中国与世界版图上的跨境与流动,文艺青年的“空间创造”,都是《浪的景观》所着力刻画的。

小说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写空间。公路、街道、市场、公园、河流湖泊,调用大量真实的上海、北京、南京、台北等城市空间细节,阅读时仿佛也穿梭在实地、历史与想象的多重曝光的城市里。随着21世纪前后城市文艺青年交往史的路线重现,周嘉宁也重绘一个半隐失了的“地下上海”地图。“地下”在这里有双关之意,既是主流之外的小众文化角色,也是物质空间方位的地表以下——这些集群好像打游击一样,在隐蔽的城市夹层中开辟自己的活动场所。最典型的形态,莫过小说中出现的各式各样地下、半地下的防空洞。《浪的景观》中的迪美地下城、乐队演出live house,《明日派对》中的青年俱乐部,还有吸引了大批摇滚乐队的排练厅所在地,都是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防空洞,“墙上留着60年代的保卫标语,也贴着二十一世纪的唱片海报。”人防系统建设的遗留物、废弃的学农基地,都在各类文化青年集群的手中得到新一轮的空间赋权。

无论是“地下上海”,还是电波里的“空中上海”,周嘉宁探入潜伏的城市人文地理脉络,最想突出的,仍是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有如热流在城市地层下方翻涌,时不时也能闯入公共空间展示自己。书中多次出现对于一代人“好运”思考。“好运”如同偶然与奇遇的同义词,却只会在一个布满缝隙的社会频繁地随机掉落。用小说人物的话说,“难以想象,我们未经训练的声音和想法将被传播到如此坚固有序的城市里。”这在无意中接通了情境主义精神和1960年代以来围绕城市权力展开的行动。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明日派对》收束于“我”、王鹿与潇潇用充气艇在苏州河上划船的率性行动。在联防队不紧不慢的监视步伐和手电筒光照下,这个游戏般的冒犯/冒险游戏,也许只会给这三个年轻人自己制造出一段“犯规”的难忘记忆,却也在被城市规则板结化的空间区隔里,结结实实地划开裂痕,释放出解放城市空间的文学想象力。

周嘉宁的小说一向具有鲜明的城市性。作为生长于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一代,长大成人的过程,恰好踩上了城市跃迁的发展主义节奏。作家多次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上海是一座处处都在施工的“大工地”。《浪的景观》里也有无处不在的城市工地:夜色下挖了一半的越江隧道,深入浦东腹地的新的地铁站,机器噪音轰鸣,如同一头雾中巨兽。调查记者小象的感受是,“觉得前方阻断的淤泥被渐渐清除之后,通往的不是江的对岸,而是其他地方。”在隧道修了一半,还不知道要通向哪里的时候,人们被允许自行越界,拥抱歧路。无怪乎会产生通行无阻的空间畅想,“据说整个上海地下的区域与区域之间都是相互连通的,理论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想象与行动可以穿透混凝土、废气与泥泞,同样可以将个人联结于他人。小说里刻画的那个时期的人与城,都受到这种未知的放纵与滋养,处在如梦似幻的“现实中间状态”。借用作家偏爱的湖与岸的比喻来说,“对岸”的魅力,在于或许什么也没有,却仍然保有所有可能。

所以,面对那些后来消失在半途中的痕迹,周嘉宁使用了“景观”——这个郑重到显得理想化和浪漫化的词语——以示对于多元、平等的有机社会的敬重。语词的悖反,恰恰透露出对景观化的消费社会逻辑的质疑。不过,与其说周嘉宁要那些时代的冲浪手树碑立传,不如说恰恰相反。比起三篇小说主人公的犹豫底色,泉、群青、小象、张宙和潇潇等人,代表了一种坚定前行的姿态。面对集体生活的落幕,美好时光结束的感伤,他们更多时候是清醒的,也是坦然的。马里亚诺问,“你们还没有年轻够吗?”群青说,“不然呢,要造一座纪念碑吗?”借人物之口,同一个集体中不同声音形成张力。尽可以由衷赞美,但也处处警惕怀旧,拒绝再次掉入景观化陷阱,小心地避免落入自我感动和过分煽情。在某种意义上,周嘉宁专注“世纪之交”的出发点想来绝非怀旧和美化过去,而更接近于伯格森提出的“活的记忆”,“一种着眼于未来而对现在和过去所做的综合。”未来已至,让那些藏在年轻时代深处的“泉源时刻”重新浮出水面,是为了让现在继续在思考中往前走。就像那支在苏州河划船的小分队,最后在该靠岸地时候坚定地靠岸,岸上的生活也同样值得创造,“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
从《密林中》一路写至《浪的景观》,周嘉宁终于抵达写作风格的成熟时刻:内在的专注,明亮的美学,清洁、克制而精确的汉语表达,对于青年时代精神世界的热爱与洞悉。像尼采所说的,“最深邃的洞察只会源自爱。”使人惊喜的是,城市文艺青年常常被贬义为“狭隘自我”、“逃避现实”、“过分敏感”,周嘉宁的创作却能多年专注于此,耐心地向下掘地三尺,直到打通时代与城市变迁中潜在的文化脉络。这样的写作者的真诚在于,“21世纪初的考古”从未完全脱离“自我”的踪迹,而是以亲身经验读入这段历史,藉此反身更新自己深嵌其中的记忆与理解。小说对新世纪前后的每一次文学回收与精神反刍,都是对“城市文艺青年”更深层的历史经验的话语检索。

在“80后”内蕴诸多的身份所指之中,“文艺青年”招来的声音尽管褒贬不一,却从来都是独具时代症候性的一个群体。这个以文学艺术作为世界观乃至生活方式的集群,他们身上的指标性,还有大片尚未充分讨论的空间:西方流行文化工业、传统教育制度、以消费形式追求的个性化差异、互联网进入后初代网民的文化交往、bbs论坛时期的文学……周嘉宁的创作,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他们的生活史、心灵史与文化实践,从来都有机地内在于社会的剧烈重组,并且可以毫不逊色地对时代激荡作出有力的应答。
尽管作家并不打算要证明什么。在这一点上,《再见日食》描绘的那场日食,和男作家拓对于泉的思念、虚构与安放,最接近于周嘉宁目前的小说观念。在日食带外围看见的日食,隔着山的背面和湖的对岸听见的欢呼声,究竟算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日全食带的“阴影”之于阳光直射的地方,一如“地下”之于地面,当然,也一如小说虚构之于现实。新旧千年交替时,洞开过多少入口与出口,小说家并不想占据风景的解释权。她好像只是自在地逗留在虚构与现实的交叉地带,好像只是和旁人无异,看一看风景。
原标题:《创造“世纪之交”:读周嘉宁《浪的景观》|新批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