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文学经典中,认识自我是为了踏入未知世界前形成免疫保护|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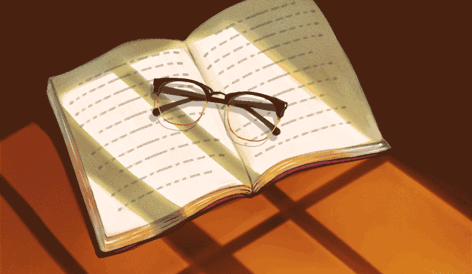
在高校里教文学课的作家张秋子,并没有学生当作专业读者,她坚持“新手友好”原则,循循善诱,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勘探文学带给心灵深处最隐秘的震动,使普通读者也能获得深入理解小说魅力的能力。常年接触本科新生的她,对文本细读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心得,许多难以亲近的文学名著在她和学生的共读下,更个人化也更沉浸式,远离了“标准答案”带来的严肃沉闷。近期,她将大学课堂部分讲解整理成《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推出,将这些解读分享给更多的青年读者。她在书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我希望这本讲稿能稍微打破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
许多读者都看过《变形记》,只记得里面活人变虫子的荒诞不经,但可能忘记了一个细节,它让这种荒诞里有了温度,有了一丝压实的感觉:虫子还是要盖被子的。
日常生活的至尊地位在小说中获得了一种永恒的保证——简· 爱永远在你翻开书的时候,讲述着她与庄园男主人的爱情纠葛;福尔摩斯永远在你翻开书的时候,带着华生勘察犯罪现场。小说中的人物永远在等候你,它们不会变,就像你周围的日常不会变一样。
我一直觉得,文学阅读是从感觉开始的,用我们的鸡皮疙瘩来阅读、用我们的寒颤来阅读,然后,再经由思维,最后达到自由——对文本解读的自由,对生活理解的自由。
今天夜读,从诺奖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短篇《旅客》解读出发,她延伸向文学史中“文学与自我”这一经典主题,“文学与自我的关系史,也是人类对自己认识不断深化并纠偏的历史。”
《旅客》:
文学与自我
在一堂文学课上,出现最多的词汇可能就是“我”。当聊起浪漫派或者象征派的诗歌,同学们会说,这些诗歌表达了诗人“自我”某些特殊的情感;当聊到惠特曼的关键意象时,同学们发现“有男人、有女人、有民主、有身体”,但最关键的还是“我”;当谈到对某部作品最本能的感受时,同学们仍然说的是“我喜欢、我困惑、我反感”。
“自我”,也许是文学中最深的核心。
很长时间以来,文学似乎都被视为对“个别”、“特殊”的呈现,普通人的生活总体上波澜不惊,所以总希望文学能够用其特别来擦亮庸常的生活,毕竟,平日里遇到堂吉诃德或者白痴班吉的机会不多。相应的,我们也愿意把文学视为对自我意识或者个性的表达。读者们相信,无论是看上去多么离奇古怪的写作,总难免有一丝作家个人情感、经历、思考的投射。但是,文学与个体的关系真的一向就是如此吗?“文学作为自我表达”、“文学塑造鲜明个性的人”,诸如此类的观念,从文学诞生之初就有了吗?

短篇《旅客》收录于
《怪诞故事集》
李怡楠 译
KEY·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

第九讲,我选的是近年的诺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旅客》。托卡尔丘克在成为作家之前做过心理医生,所以对人类的潜意识与梦境都很有兴趣,《旅客》就是典型之作。这篇小说被收录在《怪诞故事集》的开篇,打头阵。故事非常短,也很简单。它讲述了一次夜间航班上旁边一位旅客告诉“我”的经历,他说起童年时就有的一种恐惧经历,它往往在夜里发生,所以一到暮色降临他就会感到害怕,连姐姐讲的鬼故事都不及其恐怖。那到底是什么呢?他觉得“有个人”出没在他房间里,一个灰色的人影,满脸疲惫,脸上闪烁着小红点,那是燃烧着的烟头。每当这时,这个男孩就会哭喊着跑去父母那里求助。随着年岁渐大,他忘了这个人影。六十岁时,他疲惫地回到家,抽起了一根烟,走到窗前,发现玻璃上倒映出一张脸,他从小就无比熟悉的脸。那一刻,他感到轻松。
我为这篇很短的作品设置了几个导入性的问题:“这个灰色的人影”到底指什么?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孩子小时候会害怕他,但六十岁时再见到,就感到了“真正的轻松”?结尾那句“你所看到的人,并不会因你看到而存在,它存在着,是因为他在看着你”怎么理解?为什么故事讲述的场所设置在夜航航班上而非其他地方?这几个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我又提供了一些进阶问题:你觉得文学与自我的关系是什么?哪些作品在你看来是所谓反映自我的?哪些属于追寻自我的?你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吗?如果让你来比喻,你会把自我的存在形容成什么东西,或者用哪些形容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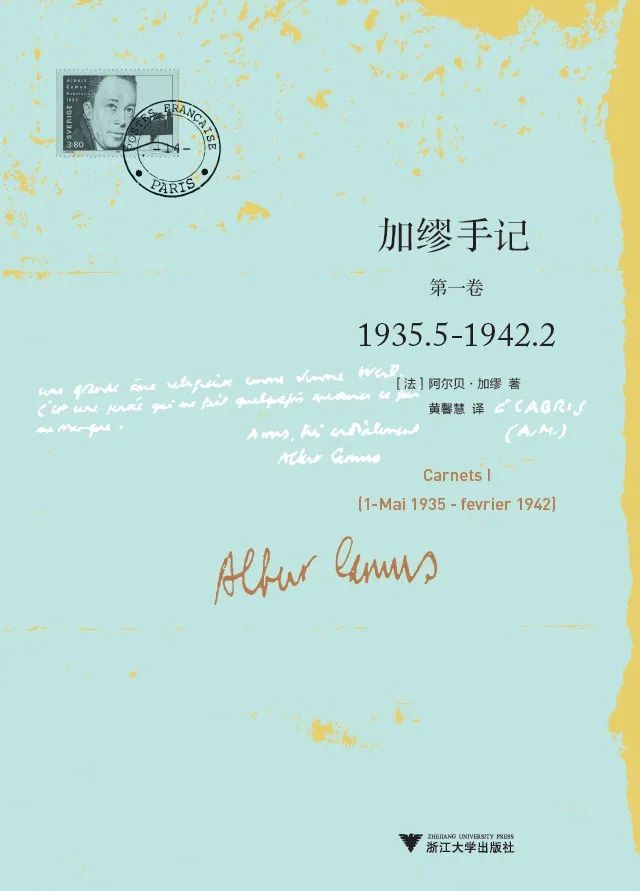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黄馨慧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最后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在课堂上特别喜欢问的,它涉及一个人怎么理解自己,怎么从万千词语和意象中打捞起几个来勾勒自己。加缪在第七本手记中,曾经写下了最喜欢的十个词,包括“世界、土地、沙漠、夏天、大海”等等,通过这些词,人们能够描绘出加缪典型的“地中海思想”那种中正、健康、力量与反抗的气息。你会用哪些词来形容自己呢?课堂上,有一个女孩说,希望把自己描述为“柔软的飘散的云”;有一个男生用“合金感(银亮色的钢制坚硬火车车轮)”来描述自己,因为“每次一听到或者想到火车车轮压过钢轨的声音,就有一种对遥远地方的想象”。于我个人而言,特别喜欢“坚硬”这个词,不是钻石的硬,而是野生岩石的硬,它大概代表了我对自己的一种期许。
回到文本。绝大多数同学都意识到,《旅客》中的那个灰色人影,其实就是“我”自己,但是,大家在解读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我注意到同学们的一种解读的偏好,一遇到无法逻辑自洽或者说不通的文本,就喜欢往灵异上靠,动不动就是鬼故事,因为鬼故事可以把一切反逻辑的地方都圆过来。所以,在鬼故事的思路下,《旅客》变成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灰色的人影其实是主人公去世之后的灵魂,灵魂回魂,想来看看生前的自己。

在第六讲,我们曾谈到过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并明确了小说无论多么想贴近现实,但始终都只是文字的虚构物。所以,它的故事逻辑可以是完全非现实的,可以完全不必套回到现实的逻辑中来。文学永远只是虚构,只是隐喻。
坦然接受小说的不合逻辑后,我们再往细部推进。
简而言之,我将《旅客》理解为人在面对自我时的惶惑与和解。小说设置了一个超现实的时间体验模式,一方面它让“已完成之我”回到幼年时,进行自我总结和审视,“带着一点不满”;另一方面又安排“未完成之我”向成人方向生长,最终与“已完成之我”齐平,最初的惶惑变成最后的和解。这有点像两条河,平行,但流向相反,但终点都是长大成人。这样一种来回逡巡的流动,让惶恐、泰然、惊惧、平静,种种不同时态的情感在“我”的主题之上纵横交错。
这多少有点像人们阅读蒙田时的感受,蒙田的随笔集用更为恢弘驳杂的方式展现出这种时光与生命的斑驳错杂之感——读者刚看到一个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子女的蒙田,不一会儿又看他自称精神百倍了。他并不是按照自己从年轻到衰老的历程来写作的,而是让不同时间段的自我跳跃在文字之间,就像他酷爱的那个比喻:阳光照到一碗水以后又反射到天花板上的图案,不停摇晃、不停跃动。

《旅客》中,讲述人小时候常常因为看到灰色影子而感到惊惧不已,这大概是一种象征:人的主体意识还很不完全,小说用其表现生命的懵懂与混沌意识。他觉得死亡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这时候,未来还没全部涌来,一切也都不可知,包含在未来维度的自我就像一个尚未明晰但显然可感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长成怎样的人,那个未来之我的形象就成了一种恐怖的诱惑,一种充满拒绝的靠近。到了长大衰老的时刻,人对自己的认知近乎完成——虽然不一定真的认清。托卡尔丘克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来描述人的成长,小说中的讲述人说到姐姐每晚用“兴奋又虚张声势的音调来吓唬他”,给他讲鬼故事,后来,“他应该在成年后感谢姐姐,正是那些故事给予了他对付普通恐怖事物的免疫力,也在某种意义上让他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这个讲鬼故事的细节正是对成长本身的隐喻。
许多作家都注意到少年成长中的惶惑与不安。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矿车》中,少年良平看到工人推矿车很好奇,就跟着去推,没想到被成年人玩笑式地利用了,他们让他无偿干活,把矿车越推越远,直到黄昏时分才发现已经离家太远了,良平“几乎要哭出来,然而哭又何济于事呢?”他一路飞奔回家,抱着母亲大哭,几乎“拳打脚踢”地折腾——透过这生动的一幕,芥川要说什么呢?他要说一种脆弱易折的孩子心性,一种受骗后的委屈,他只能向父母发泄,“拳打脚踢”也是一种无计可施的撒娇。

与托卡尔丘克神似的是,《矿车》中也有一个已完成之我的回视。小说结尾,芥川说,良平二十六岁那年,已经成家立业,不知怎么的,就会想起小时候那件事,“尘世的操劳使良平疲于奔命,他眼前浮现出一条道路,它和从前的那条一样,路上,竹林昏暗微明,坡道陂陀起伏,是一条细细长长、断断续续的道路……”当《旅客》中的两个自我重叠时,那种成长里的惶惑不安彻底败给了成年后的认命,一个恐怖的灰色影子原来就是自己;而当《矿车》中的良平长大后,一条跑不完的道路最终也抵达了终点——“带着妻女来到东京”——所以,两个作家有些相似,都是把成长的主题变为自我认识的主题,在时光的来回穿梭中,人的局限、能力、疲态、弱点、限度,也才能看得明了,也多少有点认命的意思了。
《旅客》的主题是自我,这个自我经由成长而得,最后又进入了认命的状态,显然它预设了这样一种结构:人的自我是不断找寻(以成长为例)而来的,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可是,荷马或者亚里士多德会这么想吗?甚至,他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奥德赛》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写人的漫游,但都是要塑造一个有着鲜明个性与自我意识的主角吗?或者,如果说文学或隐或显地在表现自我,那么《埃涅阿斯纪》在表达维吉尔的什么呢?福楼拜《圣安东尼的诱惑》中那个癫狂的安东尼又和他自己有必然关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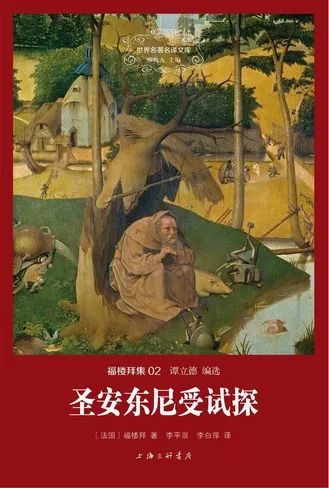
[法] 福楼拜 著|李平沤 李白萍 译|上海三联书店
这一讲,我简单呈现了文学与自我的关系。人们一般相信文学是对独特自我的表达,但其实自我这个观念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产物。古典时代的众多悲剧都表明,特定的行动与场景比人物更重要。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早期,许多作品虽然有一个明确的主人公,但目的不是塑造这个主人公独特的个性,而是借由他来传递更为普世的观念,作家们渴望“看尽寰宇”。在启蒙天秤的另一端,自我这个概念终于出现,一些作家选择将自我放在经验世界里理解,另一些则偏爱先验的自我,由此,催生出文学中“追寻自我”的主题。但是,对这一主题的不断强化,又使得人们落入了自我中心的幻觉中,把自我、个性看成了无上的存在,而忽略了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一些现代小说通过意识流或者科幻的手法,对被放大的自我进行了矫正。总体来看,文学与自我的关系史,也是人类对自己认识不断深化并纠偏的历史。
选自
《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
张秋子 / 著
新行思|上海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在文学经典中,认识自我是为了踏入未知世界前形成免疫保护|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