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他体内的“批评器官”仿佛时代喧嚣中一枚沉静而昂扬的音叉

《为经典辩护》是评论家凌越的新作,这是一部重读经典的的“娱思”之作,评论对象都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作品,如费吉斯《娜塔莎之舞》、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蒙森《罗马史》、阿玛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埃文斯《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等。书中还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马斯·曼、菲茨杰拉德、加缪、聂鲁达、布罗茨基、昆德拉等作家的评论。凌越写得认真而艰苦,经常为了写好一个人物而读近百万字的内容,就像威尔逊那样“为了写一篇评论而读了一架子书”。他体内的“批评器官”仿佛时代喧嚣中一枚沉静而昂扬的音叉。
凌越说:“书名‘为经典辩护’是我全部书评写作的一个核心思想。经典作品有时看起来不够时髦,甚至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时间的尘埃,但所有经典作品都有一股扑不灭的活力,英国作家伍尔夫曾准确地将这种活力比喻为大洋里‘深沉的潜流’。正是这股不易察觉的潜流,带动人类思潮向前运动,并将人类带往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未来。相对而言,我较少关注流行读物,这使我可以避免奥登所说的在批评劣作时容易流露出的虚荣心,而且它们在光鲜一阵子后就会消失,根本无须书评人额外付出‘埋葬的劳动’。”

《为经典辩护》
作者: 凌越
南京大学出版社
挑起双眉的旅行者
作品选读
在有关日内瓦那一章的开头,伊恩·弗莱明以他一贯挑剔刻薄的口吻,把威尼斯挖苦了一番:“威尼斯早就落入俗套了。我曾想写一篇关于威尼斯的幽默散文,但不写运河、贡多拉、教堂和广场。我将专注于描写火车站纯粹的建筑艺术、证券交易所的运作、威尼斯财政的乱象,以及自来水厂和发电厂的历史。······不过,除了胡诌这样一篇,威尼斯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谈。”老实说,在忍耐了弗莱明大半本对世界各地“横挑眉毛竖挑眼”之后,看到这里,按捺已久的抵触情绪似乎立刻爆发了。

伊恩·弗莱明
虽然我没去过威尼斯,但有关威尼斯的文字记忆可实在太多了,这位老兄竟敢说“威尼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谈”!我喜欢的两位诗人庞德和布罗茨基都很喜欢威尼斯,甚至最后都安葬于此,后者曾17次到访威尼斯,并写下厚厚一本水城赞美诗《水印》。我喜欢的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则在《美好时日的回忆——威尼斯随笔》一文中以缠绵的语言描述了他在威尼斯的游踪。更别说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名作《死于威尼斯》,把内心纠结、沉溺于畸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也放在了威尼斯。此外,威尼斯还激发了另外一些大作家——普鲁斯特、罗斯金、里尔克、拜伦、歌德、麦卡锡、蒙田、蒙塔莱——的灵感,“他们的言辞像运河的流水一样盘旋四周,就像贡多拉小舟过处,阳光照耀涟漪,揉碎万点微光”。(诺特博姆语)
我为威尼斯做这番辩护,是想说明真正的文学恰恰是从“没什么新鲜东西可写”的窘境出发的,庞德对此有过更好的总结——文学就是日常生活的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旅行文学”恰恰因为避开了“日常生活”而显出自身的先天不足。追求新奇感,往往是旅行者背起双肩包踏上旅程的最初动机,同时也暗示着人们困守一隅的生活方式是乏味的。新奇感驱使人们毅然出发,在厌倦感即将袭来之前从一座城市漫游到另一座城市,而旅行文学则是对这种漫游的记载——新奇的物件,迥异的生活方式,在眼前晃动随后飘过的芸芸众生。这种行走的方式,注定了典型的旅行文学是一种本质上“浮光掠影”的印象记。对此,伊恩弗莱明有清醒的认识,在结束了香港一澳门一东京一夏威夷一洛杉矶一拉斯维加斯一芝加哥一纽约的第一阶段环球旅行后,他总结道:“我花了三十天环游世界,而为旅程写下的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和一些肤浅的、偶尔缺乏尊重的评论。”

弗莱明笔下007的故事多次发生在威尼斯
图为电影《007:皇家赌场》剧照
追根究底,这是由一味追求新奇感带来的。新奇感似乎容易获得(踏上旅程就行),但也特别容易失去,典型的旅行注定是扁平的。旅者从那些风景和美食上掠过,从浅层的人文历史或貌似独特的生活方式上掠过,只要他稍做停留,厌倦感即刻像鬼影般尾随而至。每本旅行文学里都充斥着太多人物,但他们的职业往往很单调-餐厅或酒吧侍者,出租车司机,空乘,更多的则是街头匆匆而过的路人,或者和作者怀揣同样期待的观光客。但这些人物在游记里都是匆匆过客,只留下一个侧影、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神秘的表情,很偶然地被记在书中,成为一种点缀,成为旅行文学为何扁平化的一个证明。这里涉及旅行文学和一般文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前者对人物命运缺乏持久的关注,更别说带有同情和理解的关注了。旅行文学的核心始终是新奇感,其中出现的人物则是对这种新奇感本身的点缀;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通常更关心人本身的个性和命运,而美丽的风光不过是一种背景。
悖论的是,如果旅者终于克服了厌倦感,从崭新的路径进入文字,他也就开始离开了旅行文学,转而投身到不带定语的“文学”门下。以西西里为小说背景的皮兰德娄,以印度为小说背景的吉卜林,谁会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旅行文学”呢?年轻的加缪以华丽性感的语言描写贾米拉的风景,也写过去往布拉格的旅程,可由于他的文字和风景、韵律、哲学有着美妙的联姻,人们也不会说《婚礼集》是一部“旅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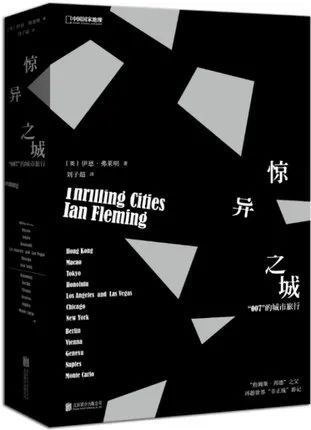
《惊异之城》伊恩·弗莱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旅行文学”好像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标准套路——一个主人公(当然是作者自己);飘忽不定的旅程;所到之处对于风景和当地人的观察;更深一点的旅行文学也会对所到之处的历史人文来一番探究。只要溢出了这个范畴,就会被胃口极大的“文学”纳入囊中,而这些文字恰恰是一个陌生的地名和一段不确定的旅程回馈给世间的最好的东西。如此说来,旅行文学注定是不成多的“庄稼”,因为一旦成熟,就会被“文学”本身收割。
伊恩·弗莱明的《惊异之城》当然可以归为典型的旅行文学行列,但也有它自身的特点。作为007的创造者,在由《星期日泰晤士报》提议并资助的这次环球旅行中,弗莱明体现出某种对于“惊险刺激”的格外趣味。自然,对于《星期日泰晤士报》,只要点明伊恩。弗莱明是超级畅销书邦德系列小说的作者,这个投入“巨资”的游记专栏也就成功了一半。事实也的确如此。平心而论,这本游记在如同热带植物般快速繁殖的旅行文学中不算特别出色,但它依然因为作者本身的特殊而凸显出来,并且在多年后被译成中文,加入中文世界“旅行文学”的崛起之中。
读者显然有一种期待:这位以写作紧张刺激的间谍小说闻名的作者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一种不同的旅行感受呢?虽然整本书语调多少有些傲慢,按照著名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在序言中的说法,他“对一切都挑起一对高傲的眉毛”,但是整本游记里对于赌博各种门道的津津乐道,对于富于传奇色彩的香历史与现状的介绍等,都显示出这位做慢的作者对于读者内在的体贴——他知道媒体需要怎样的稿件,也明白读者想要看到什么。

旅行中的弗莱明
在书的开头,弗莱明坦承自己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抽劣的观光客,“甚至经常鼓吹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门口提供轮滑鞋。我也受不了在政府大楼吃午饭,对访问诊所和移民安置点更是毫无兴趣”。这些无疑都暗示出弗莱明不是按常理出牌的旅行者,同时也是他内容独特的游记的变相广告。可是读完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苛刻的语调,像“香港夜晚的街道是我走过的街道中最迷人的”这样朴实的句子在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看得出,他的确喜欢香港),在大多数篇幅里,弗莱明都在想方设法地贬损观察物,这甚至成为他这本游记最突出的语言风格,当然其中也混杂着幽默,但当这种嘲弄更多地指向他人时,离刻薄也就不远了。我随意从书中选取几句:“就在我观察他时,一个穿着黑色绸裙、年纪可能在50-100岁之间任何一个岁数的女人离开最近的那张桌子,走到他身边。”“毫无疑问,巴林拥有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国际机场。就算在监狱里我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洗手设施。慢腾腾的风扇挂在一塌糊涂的棚屋墙上,连苍蝇都懒得动一动。”“假如这群老年人穿着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衣服,他们就会消失,成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但是在夏威夷,成千上万六七十岁的老人穿成各种奇怪的样子,这更让我感到压抑。”
《惊异之城》对于各种赌博方式以及赌场中的各色人等,都有细致传神的描述,对于闻名世界的黑帮也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同时,弗莱明本人超级畅销书作家的身份,以及《星期日泰晤士报》本身的影响力,使他得以采访各地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在澳门,他拜访了黄金大王罗保博士;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他采访了《花花公子》总部和知名的犯罪新闻记者;在日内瓦,他到卓别林家做客。这些都保证了《惊异之城》在追逐新奇感方面有其过人之处。我想这既是弗莱明自己的兴趣所在,也吻合媒体对于稿件的要求。对媒体而言,内容本身的特异性(独家或新奇)永远优于文字风格。换句话说,只要内容足够夯实,文字做到清晰流畅就够了。
显然,《惊异之城》幽默贬损兼备、有时又非常生动的文风,早就超过了媒体对文字的一般要求,也就是说,弗莱明提供给《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游记是十足的优秀稿件——从媒体的视角而言。问题是,和上文谈到的旅行文学过多的人物一样,过于扎实的内容,也使得整个文本过于拥挤。没错,这正是媒体报道的特点。媒体对于“事实”本身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它不能忍受作者陷入玄思——哪怕发一会呆也不可以。如此,留给文字自身表现的空间就愈发逼仄,而文学自然就被挤出报章那过于紧凑的版面了。

弗莱明(左)与第一任007扮演者肖恩·康纳利
作为纯文学热爱者,我对《惊异之城》可能有些苛求了,拿托马斯·曼的小说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散文与《惊异之城》相比多少有些怪异。我虽然对各种赌博毫无兴趣,但并不妨碍更多的人对赌博持有盎然的热情,而且弗莱明完全可以反驳说——我本来就没打算写传世之作,它就是有关旅行的一些浮光掠影的记录而已。就像推理小说的作者也没想要和托尔斯泰去竞争,他们想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劳伦斯·布洛克或者雷蒙·钱德勒,以及销量和版税。换言之,我根本就不是《惊异之城》的目标读者,喜欢这本书的人肯定大有人在,就像更多的人喜欢邦德小说以及《哈利·波特》或斯蒂芬·金一样。但只要进入文字领域,某种比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并不建立在销量和版税的基础上。作为类型文学,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和旅行文学都有其广阔的市场,内部也有高下之分,有些类型小说就是更吸引人,卖得更好,而有些可能会无人问津。但总体而言,类型文学的套路性限制了它可能到达的高度。它对读者过分的体恤,它用刺激和新奇这两个有效辔头牵引读者的自觉意识,都使它不可能像经典文学那样更多聚焦于人性和语言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旅行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只是通俗文学市场上的主力军,但并不肩负精英文化的传承。
《惊异之城》里还有一个引起我特别留意的地方,即每座城市的游记后面附上的所谓“前线情报”——有关这座城市的实用信息,例如最好最舒适或性价比较高的酒店和餐厅推荐。这些说明文和别的旅行手册上此类推荐并无多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时间。《惊异之城》首版于1963年,当年的读者完全可以手持《惊异之城》按图索骥去寻找那些漂亮的酒店和餐厅,可是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平实的说明文并不让人意外地沾染上某种特有的伤感气质:九龙半岛上极有殖民风情,房价只有100港币的半岛酒店今在何方?而苏丝黄曾下榻过的六国酒店又在哪里?位于汉堡阿尔斯特胡拱廊的河畔夜总会可还有很多漂亮女孩出没?纽约靠近时代广场的Seven Arts Collee Gallery酒吧就算还在,金斯堡、凯鲁亚特、柯索等垮掉派作家一定不会再来造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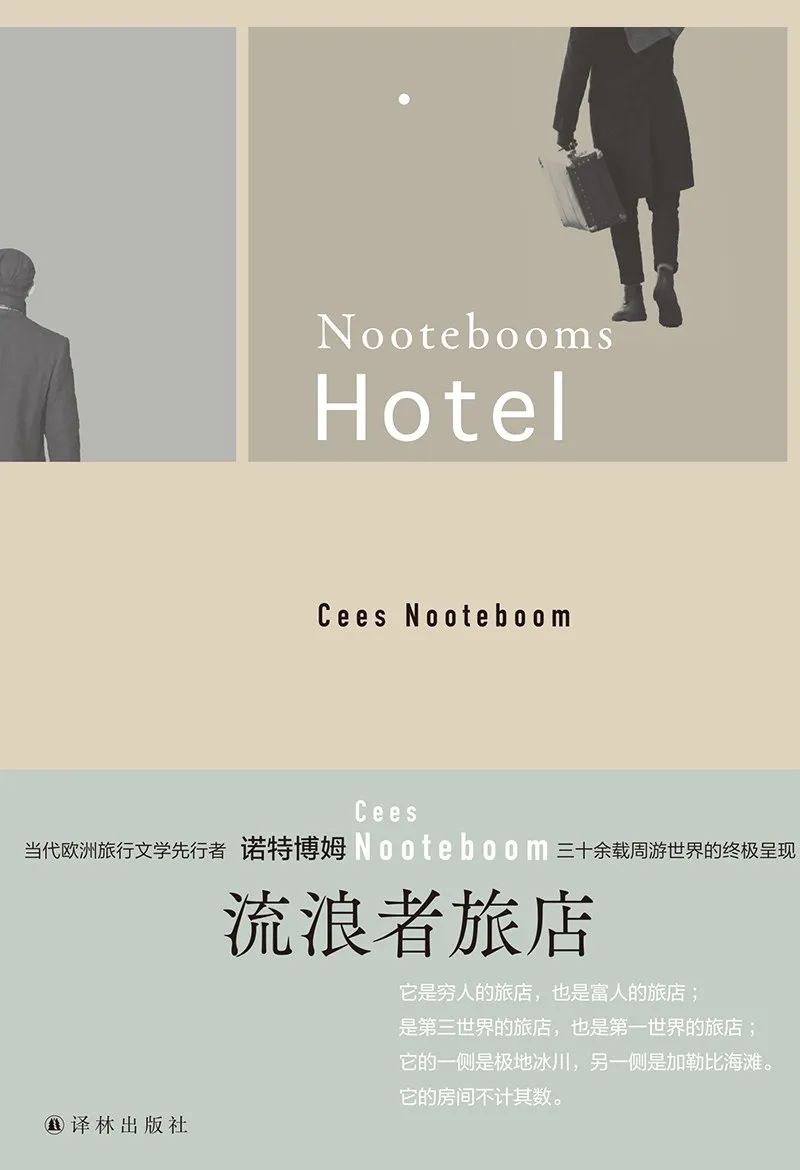
诺特博姆《流浪者旅店》|译林出版社
以前看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的《流浪者旅店》,里面写到他1998年去威尼斯旅行时特地带上1906年版的旅游指南和1954年版的意大利导游手册,曾留下很深的印象,如今看《惊异之城》里这些如废墟般的“前线情报”,多少可以领会诺特博姆的用意了。一种沧海桑田般的感受会自动从这些不同年代的导游手册中升腾起来,所有的开销都变得更加昂贵,而曾经美丽的去处也早已踪影全无,令人徒增喟叹。
最后说一句,在所有我看过的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旅行文学中,《流浪者旅店》肯定名列最佳之选。诺特博姆在介绍行程、描写途中见闻的同时,难得地保持了一种优雅的文体和语调。与此同时,他对于生死之类大问题的思考,因为置于流徙的背景中而显得格外耀眼。如此说来,旅行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也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原标题:《他体内的“批评器官”仿佛时代喧嚣中一枚沉静而昂扬的音叉 | 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