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亲身参与疫情公益送药的不完全社会观察
一、这是一个性别问题吗
幸运地转阴后,我把手里常备药品清点好准备送给需要的人。因为出生在医生家庭,一直有备药习惯,100片装的布洛芬曾经只要几块钱,没想到如今稀缺至此。所以药物互助公益平台刚推出,我就去注册了。
因为平台推出得十分仓促,很快我就发现,隐私保护方面做得不够完善,送药人电话地址身份证全部实名得清清楚楚,取药人找上门来倒是可以连电话甚至姓什么都不给一个。为了避免骚扰,我小心地把定位设置在了隔壁小区,尽可能隐藏了个人信息。实操中我还发现,一些应该有的安全提示这个平台也没有,比如双方请尽量选择无接触取药(隐私保护不说,哪怕是出于减少传播风险的考虑,这也是必要的),比如最好提供药品使用说明规避用药风险(我会发药品说明书给对方,用药剂量和禁忌都会给出,万一对方拿退烧药下酒或者是不能吃布洛芬的人群,出了什么事,我这边已经事先告知尽了义务,责任追不到我身上)。

不论男女,只要确实是高烧急需,我都会给药,而且不止给四粒。最终我给出了一百多粒药,虽然样本小了点,但令我吃惊却实打实的观察结果是:求药的女性普遍更有礼貌和素质更高,沟通过程更愉快。无论是事后答谢还是追着给我塞礼物的,无一例外全都是女性。
我以为上海已经是中国男性家务参与率比较高的地方了,没想到求药的人里女性还是主要的家庭照料者角色,电话打过来时问及病患情况,最后还是得换成女性接听才能把需求讲清楚。
我运气大概还不错,没碰到新闻里会踹门骂人去死的男性求药者这种极端案例。但是没礼貌的确实都是男性,比如有些男性求助者在我送出药后就没任何下文了,还要我主动问药有没有丢,才告知“收到药了谢谢”。女性求助者则全部都没有这种情况。我遇到最糟心的例子,是有人根本没生病,他通过这个平台找过来,想免费囤药。
当然,男性求药者里也有不错的人。比如有一个突然留言说谢谢我,但自己退烧成功不要药了,不想占用资源,请我留给其他需要的人。这么有道德的高素质男性同胞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已经达到遇到的女性求助者的平均素质水平了。
等等,这真的是一个性别问题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我试着和同样参与过送药的朋友讨论这件事,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2020年初我给武汉的医护对接过物资,今年上半年在上海我是小区团购发起人和最大的团长,也算是有一定的公益参与经验。这次送药,我最初是想送给家附近需要的邻居,他们在我当团长的时候给过我不少帮助,使用平台送药给的都是附近的人,我本来认为问题不大。
明明都是在同一片区域,居住人群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上半年上海封控期间当团长时(虽然团长无疑以女性占多数),感受到的性别差异没有送药平台这次这么明显呢?或者换句话说,封控时期小区里明明遇到了不少人品和素质都很不错、也很热心的男性邻居出手相助,为什么这次全部消失了呢?
二、性别分化:一些可能的原因
无法获取更多数据的情况下,只能基于一些朴素的观察和粗浅的判断进行讨论。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可以分享一下。
说到底,送药和小区当团长,都是公益互助,但运作机制是有很大不同的。
和送药平台可匿名的设计不一样,当团长期间的小区,每个人其实都等于是半实名状态的。当时有阿姨买的惠民菜被送错到另一户,团长们安慰阿姨别着急时,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放心吧阿姨,大家都是有门牌号的人,跑不掉。”——团购群里一般入群都会改名成所在门洞单元楼号户名,物资被拿错也能很快找到人,因此所有人都尽量表现出了礼貌和友好,不讲道理的人全小区都会知道他或她住在哪里,并避免打交道。后来六月解封后,邻居们在路上碰到,都还会以门户号来相称呼:“啊你好啊702,还记得我吗我是和你一起搬过菜的201啊!”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邻里监督机制。参与团购的过程中如果有心术不正的人,一旦被邻居发现,至少在小区刚刚因为缺少物资而自发形成团购的过程里,他或她的信用会迅速被透支,从而失去当团长的资格。因此早期的小区团购能组织起来,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大家必须相信发起人是一个没有私心、为了公众利益在做事的人,这样才会迅速聚拢起来,把钱和采买权放心地交出去。
而送药平台是没有这样一层监督机制的。即使遇到了骗子,或者是不讲道理的人,也很难通过平台投诉或报警来维权——而有些时候警方的监督效力,可能还不如封控时期能干预居民团购事务的一些小区居委干部。
“监督”以外,第二个关键词是“筛选”。
能够参与到团购活动,或主动帮助女性团长跑腿卖力的男性,本身等于是被筛选出来的人群,比如是家务参与很多或者要帮忙照顾小孩的男性,有需求要和妈妈们一起团购买奶粉尿布。他们本身就是交流沟通能力比较好、有同理心的男性。我所在小区第一次团购成功的参与男性里就有一个奶爸,太太是基层干部去当大白,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团购物资做消杀时他甚至带上了小孩,“因为孩子自己想来,留在家里没人看也不放心。”于是给孩子戴上了面罩和做了很细心的防护。而担心快递传播病毒而反对团购的人,是不会加入到这类活动里的。
因此在当团长初期,只要能在小区里从零起步、成功发动起人来,是非常容易能遇到好人的时期,也很容易形成多赢的局面。我个人当时虽然完全不缺物资但也要去做这样的事,就是出于当年我在武汉封控期间的观察:小区的邻居质量将直接决定封控生活的质量——但好邻居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筛选寻找出来的。
筛选出可信的邻居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己能放心的互助网络,远远比个体单打独斗对抗各种不确定性,要靠谱得多。比如说,如果我因为阳了要进方舱,至少我知道哪些邻居会可能同意帮我照顾我的猫。如果我的猫要被不合理地无害化处理,我知道小区哪些养了猫狗的邻居会站出来帮我说话。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我的这个实践目的基本已经达到,成功认识了一些非常不错的邻居,收获了一些友情,其中女性占八成以上(毕竟干得好的团长和活跃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这个占比并不奇怪)。不过,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团长”公益行为,本身只是物资紧缺情况下解决需求的一种权宜之计,等后期物资宽裕一点后,这个模式就很难持续下去了。我从未认为自己参与公益仅仅是为了行善,对我来说,去努力做这些事情收到的实际回报是,当发生龃龉和误解时,会有邻居支持和理解,当缺什么东西时,只要开口,就会得到热情回应。我幸运地靠着很多陌生人的善意和信任撑过了两个月。封控结束后,团购的大群就地解散,但这可能是多年来一直习惯各扫门前雪的上海人的邻里关系最好的时期了。
相比之下,送药的公益行为里要筛选掉不靠谱的人,就要困难和麻烦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也会变多。如果填写了送药人信息,等于被动地等待自己被别人筛选。自己在明,对方在暗,考虑到女性是这类送药活动里占相当大数量的人群(很简单,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来说布洛芬就是常备药),这实际上劝退了非常多在意个人安全和隐私的女性。
平台本身带有筛选性,最好的例子大概是,二手交易平台上女性被骚扰的概率会惊人得大。所以顾忌这件事的一部分送药人会直接选择不注册平台,转而在发布信息里挑选求助人。实际询问了一些参与者后,发现大家筛选的标准各种各样:比如不看没写清个人病情的求助者(你都来求助了难道还差这两句话吗),不理会填写了多种数量药物需求的人(只要四粒布洛芬就能成功退烧,要这么多药品恐怕是囤药或倒卖药品者吧)。这实际上等于是倒逼用户为了安全,去选择以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方式来助人(比如我就没有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实在没时间每天浏览那么多信息),也很容易造成重复送药等浪费(有些人不动声色地收取了不止一个人送出的药,来得如此轻易,自然不会珍惜)。
求药踹邻居门这种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公愤——送药的当事人妹子,算是非常罕见的、标准意义上的完美受害人了(这个词简直和真空里的球形鸡一样一般只存在于理论中呢):她动机无私,事发选择报警,不但完整保留了视频证据,维权的微博文字为自己辩护时也注重条理,明显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但她还是要花上篇幅,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送药给男性,并被训“你懂不懂法律”。
为什么过程如此简单、是非曲直如此明晰的一件事,竟然能直接击穿和毁掉互助送药这种还没完全成熟的公益行为机制呢——我认为,问题就正好出现在“筛选”和“监督”这两块上:有暴力倾向的男性没有被筛选掉,也没有一个公正的监督机制来保护好心的人。
这也许能解释送药参与者遭遇的性别分化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没有更好的隐私保护,在筛选和监督方面提供足够的支持力度,恐怕活动参与者观察到的结果,都会有些大同小异。
三、可以脱离性别来讨论吗
可以脱离性别、中立客观地来讨论这件事吗?我的一些男性朋友这样说。女性朋友也有人这样说,觉得“这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曾经试图这样思考。
但是,实践的过程中,能“中立客观”、“脱离性别”地以个体身份参加公益的,恐怕只可能是男性。女性可以伪装成男性,在网上使用男性头像名称和性别(很多避免骚扰的女性就是这样做的),我一直很喜欢以中性的身份和名字出现在网络上,注册平台信息时我会模糊性别,我写作的风格一直倾向于中性(这次除外)。女性的生活里,假装自己是一个男性并不少见,就像假装阳台上有男人的衣服,门口摆了男人的鞋子。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直到露出女性身份。即使什么都没做,女性都会成为了一些人眼中的靶子、猎物和软柿子,或者被视为有某种义务或被赋予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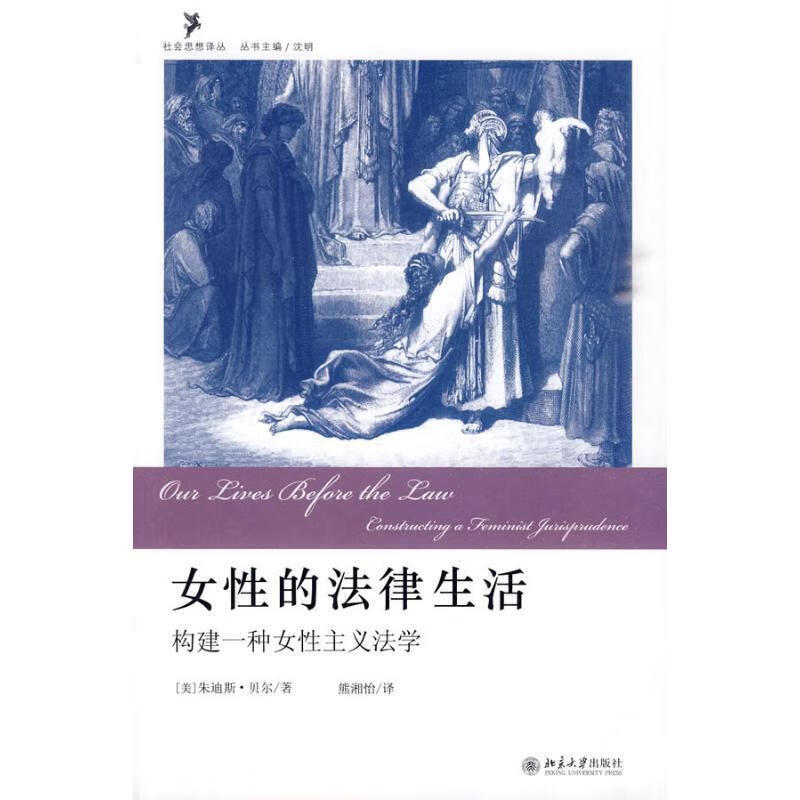
法学学者朱迪斯·贝尔曾经在书里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她有一天独自散步的时候身后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哭的孩子,身边人陆续出现,开始指责她不负责任,直到孩子的真正母亲出现,向公众道歉。没有人关心贝尔本身的感受;她什么都没做,和她也没有任何关系,突然被指责仅仅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照顾好孩子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属于她。我有同样的经历:坐着,什么都没做,突然有陌生人向我走过来请求我让座。哪怕我腿上放着十几斤的书包,旁边男性没带包、低头在玩手机,我也并没有坐在老弱病残座位上。我会被视为是可以提供座位的合适人选的原因,仅仅因为是女性,人们会觉得我更容易答应请求。一个女性,想要假装这不是性别问题,恐怕这才是不切实际的。
能脱离性别、中立客观地看待这件事吗?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预设和陷阱。
要客观地承认,也许这会是我招致批评最多的一篇文章:毕竟,只有一百多粒药物送出样本的我无法提供更多的数据和规避偏差,没有办法保持更多的中立,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带任何感情在客观理性讨论这个现象的、中性的人,因为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我会更倾向于优先考虑女性(更安全、效率更高、收益更大)。
我看到那位完美受害者的女孩说,“我是一名医学生,所以赠药方面没有特地去关注性别”。她和曾经的我一模一样,这次她是我写作的动力。我有一种幸运的超能力,就是每次去看医生,医生都会很喜欢我,侃侃而谈,就像看到娘家人一样松弛。这是因为我的家人全部都是医生。我会投身在这几年的这些互助活动里的机缘也正是如此,这不但是一种自助自救,也是我获取疫情相关信息来预判和保护自己家人朋友的一种方式。毕竟我哥在两年前就是急诊科一线,现在仍然留在岗位上高烧着,父母早就退休但这次人手不足,我爸打了第四针直接上了一线,妈妈待命中。我从小是被当成医生接班人培养,但是被父母认为更适合做医生的我,反而最后是家里唯一一个逃离学医安排的人,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
因此我也非常敬佩做了医学生的这个女孩。但我并不同意,这是一件参与时可以不去关注性别的事情。我以为,恰好因为是女性,成为医生时才更应该注重性别。医学行业里最厌女的领域之一,恰好就是妇科这种和女性最相关的科室,教科书里充满了各种男性传统偏见的女性的身体知识(熟悉医学史的话会知道这算是长期的遗毒了),甚至很多妇科医生本身就非常厌女。朱迪斯·贝尔是我喜欢的法学学者,她说:所有的女性主义法学家恐怕都会同意,法律如果有性别,那一定是男性。这句话换成医学,也是成立的。美国的法学院里现在挤满了女生,中国的医学院里也不缺少女性,很多行业,我们都不再缺少女性的参与了,但是区别可能仅仅是,从此变成了一个更多女性从事的男性行业。
真正的善良,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高贵品质,人们通常容易低估它的难度——我也许确实做过点好事,但我绝对不敢轻易地奢谈自己是善良之人。很多人的所谓善良,更可能只是因为他或她没有条件和能力去作恶。
哲学上有一个专业的讲法叫做“道德运气”,简单说,我能完成一些善举,可能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善良多经得起考验,而更可能只是因为我足够幸运(这篇文章的很多地方,我都在特意强调和解释这件事),得以成功免于一些复杂的道德难题和拷问,没有遭遇社会新闻里各种极端情况,比如我不需要去担心扶老人会不会被讹诈,向人伸出援手的同时是否让自己置于险境。否则,当我忘记为自己武装上獠牙和尖刺时,我的善良只会被嘲笑是愚蠢和好收割。这确实令人难过。
但是,也正因为善良是如此的宝贵,在仓促地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还是想说,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子贡赎人”、“子路受牛”的故事,简单说,孔子这样的圣贤也同意和推崇,做了好事的人,是应该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收获答谢礼物的(无论是国家的补偿金还是接受救助者送出的牛),孔子说,因为这样才能倡导更多的鲁国人去救落水的人。能在这些公益活动设计里更多地考虑保护好那些本应受到夸奖的人,无论性别,这本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