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一个经济学家的忧患意识与……警世之声
昨天给学生上经典名著课的时候,讲到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自然要介绍他所奉行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关于人要善待自然与人类同胞,要重视自己的道德实践,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个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同时要宁静而达观,自足、劳作、保持内心的宁静。但是,在今天这种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充满竞争与不无忧虑的生活语境中,我不知道学生会如何理解和是否认同这种价值观,特别是关于自足和保持内心的宁静;甚至不敢想象一个学人文学科、有思想、有才华的学生假如受斯多葛学派思想的影响,将如何面对来自生活的真实挑战。据说斯多葛派(Stoicism)近年在美国比较流行,甚至有“斯多葛主义周”(Stoic Week)的活动,有些人愿意据此而自我修行,力图做一个坚忍、坚定、宠辱不惊、不轻易动感情的人。听起来有点像流行于某些文化群落的人生“鸡汤”运动,学习经典名著或古代哲学的学生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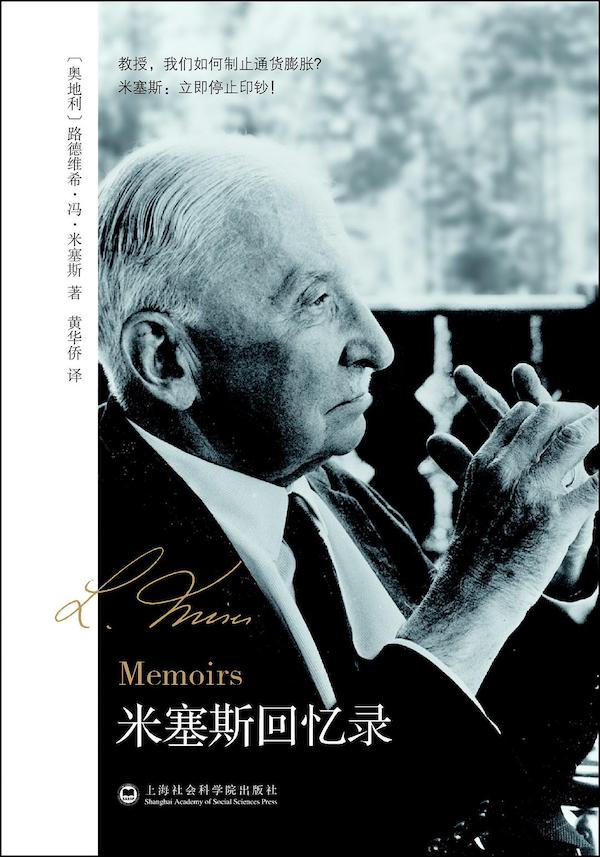
(Memoirs,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黄华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9月)
,翻了几页就遇上了Stoicism。许尔斯曼(Guido Hülsman)在该书“前言”中说,米塞斯在书中对各种人物的美德和过失的描述,反映了一种斯多葛式的价值体系——“崇尚善意、苦干和专长甚于一切,同时,鄙薄贪婪、自负和肤浅。”他还说米塞斯在这本回忆录中不谈个人事务和情感,只聚焦于公共形象的做法,“大概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谦卑态度,以及公私分明的斯多葛式的作风”。读完这本米塞斯回忆录,我想,如果从斯多葛精神的角度来看,或许美国基督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1934年写的那段非常著名、流传甚广的《宁静祷文》(“The Serenity Prayer”,美国在二战中曾印刷了无数单张发给作战军队),相当贴合米塞斯的思想与学术生涯:“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并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也赐我对你公义的信心,不与这个罪孽的世界同流……”因敏感和睿智而对助长极权暴政发展的思想与现实趋势了然于心,但以一己之力无法抵御,只能在悲观失望中仍然坚守着思想的岗位与人格的尊严,这是米塞斯的思想自传中分量很重的内容。
接受无法改变的,争取所能改变的,但无论如何要仍然相信公义存在,任何时候不与罪孽同流合污,这样的斯多葛精神或许会让我们的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受到感染。印在该书“目录”之前的这段话(出自书中的82页)就是米塞斯的斯多葛精神的最好体现:在无法避免的趋势或灾难面前,做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在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诗。……甚至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因此,我决定写一本讨论社会主义的著作。”这本书就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有王建民等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曾任维也纳大学法律教员(“编外讲师”)和经济学“助理教授”,在维也纳商业委员会工作了将近30年。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在大学之外开办了独立的经济学私人研讨会(1920-1934年),在那里他对哈耶克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卡尔·门格尔之后继续推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发展,后来这个学派在美国开枝散叶。尤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按照哈耶克在该书“导言”中的说法,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是直到他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始终是学术界的圈外人——我的理解是,从身份上他是学术体制之外的,在影响上是业界主流之外的。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他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分支的纯粹专家,如果是的话,他应该不难在讲德语的大学中占据教授席位。
米塞斯在体制化的学术圈难以立足,除了思想倾向之外,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和对学术圈中的骗子、庸才的蔑视,也是重要原因。米塞斯对经济学的精深研究使人们希望听到他对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但是却往往难以理解和遵从他的建议。然而米塞斯一直凭着学术良知和一己之力发出声音,尽量制止或缓和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米塞斯于1940年移居纽约。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到达美国后就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在他去世五年之后的1978年,他妻子玛吉特同时出版了该书的德文和英文版。哈耶克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史上,能够与米塞斯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穆勒,并且认为他的思想和研究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发展的整全解释(global interpretation),我相信这是对一位二十世纪学人和思想者的最高赞誉。
米塞斯在这本篇幅不长的回忆录中,不断谈到他亲历的、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笼罩着奥地利与欧洲的令人悲观失望的发展形势,所涉及的人和事以及他的忧患意识,今天看来都是回荡在伤痕累累的历史坑道中的警世之声。
从思想发展来看,小德意志的“历史主义”是黑暗降临的先声。米塞斯很早就发现德国历史学派并不是真正探讨科学问题,“它关注的是为普鲁士的政策和普鲁士的威权政府(authoritative government) 歌功颂德并且提供辩护。德国的大学是国家机构,大学教师是政府公务员。教授们很清楚他们身为普鲁士国王仆从的地位。即使他们真的运用他们名义上的独立自主批评政府措施,这种批评也不会超出我们通常可以在行政官员圈子内部听到的那些牢骚和不满”。(12页)从学派到大学,溃烂从所谓的知识精英开始,米塞斯作为学界中人太了解那些溃烂的景象了:大学教职大都被那些智力平庸的人占据,他们只会从一堆官方报告之中拼凑起一篇历史学论文;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说谎成性和蓄意欺骗,尽力为当权者提供服务,像维尔纳·桑巴特那样旗帜鲜明地表露其思想的奴性,他把希特勒视为上天眷命的载体,是一切权力的核心(15页);曾经环绕大学的光辉不复存在了,教学水平的普遍低下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一种与文化和科学格格不入的精神统治着法学院和人文学院的教职员工”(116页);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愿意盲从而且要坚持提出反对意见的,以及属于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的学者都无法在奥地利各大学获得正式教职,米塞斯自己的遭遇也是这样,“大学教职已经对我关上了大门,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任何人只要不属于三个党派(基督教社会党、德国国家党和社会民主党)之一,就没有希望获得教职”(86页);“教育体制下滑到如此田地,以至于现在已经无法教给年轻人什么东西了。大部分法学博士、社会科学博士和哲学博士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思考,而且刻意回避严肃著作”(118页)。米塞斯在德国大学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与这些人相处久了,我就开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平庸的蠢人已经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分子。他们在大学里讲授的那些领域是政治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知识阶层和人民大众一样,把他们奉为科学大使。遇上这样的一些老师,你能指望年轻人怎样呢?”(130页)

对“人民”,米塞斯的观察同样非常深刻,他认为邪恶的政治之所以能够存在,与人民大众缺乏足够的智识、没有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紧密相关,而在这里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81页)。这里说的是反智主义与愚民术对人民的欺骗性统治,无疑早已为二十世纪的历史所证实。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1900年的时候,德语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不是国家主义者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历史的黑暗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一切都属于国家(16页)。他也并不讳言刚进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也是国家主义者,但是在学习社会调查的课程中,由于看到现实中的国家主义如何干预生活以及带来的危害,很快就转变过来。
有的时候,米塞斯又表现出对统治者与平民大众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表述,他认为“政治决策并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而是取决于公众舆论,也就是平民大众。多数意见决定未来走势。任何政府体制都是如此。即使是专制的君主和独裁者,也必须按照公众舆论的要求进行统治”(78页)。这句话的语境似乎是为了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往往无力改变错误的政治决策,但是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真实关系来说,这是我们在大学一年级的马列理论课程中就讨论过的问题——恩格斯在解释普鲁士专制政府为何能够存在的时候说过:“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68页)后来才知道,早在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迈斯特就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应该说,米塞斯关于人民的两种表述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正是因为人民缺乏智识,所以只能接受那样的统治;而他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则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他在批判小德意志的历史主义者在权力问题上的粗暴立场的时候说,在他们眼里的权力只是意味着刺刀和大炮,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幻想、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休谟的至理名言——民意是统治的基础”(8页)。这是对民主政治的正面理解,也是对赤裸裸的枪杆子统治术的批判。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曾经告诉米塞斯说,“我听到人们议论俄罗斯民众的情绪,议论那些煽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潮。我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这些说法让人如坠云里雾里。相反,决定性的因素是那些身居要职的政治家们的意志和他们敲定的计划”(9页)。
这可以说是对民众舆情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判断,当然充满了对民众的蔑视之情,但可怕的是这往往是实情,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民众舆情太容易被风吹得烟消云散了。而米塞斯接着引用的奥地利警官朔贝尔在1915年写给上级的报告中的那段话就更为形象:“谁会领导这场革命?当然不会是托洛茨基先生,他只会坐在中央咖啡馆里看报纸。”(9页)虽然这位警官看来对托洛茨基并不十分了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托洛茨基正在呼吁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办的报纸被查封,本人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可不是一个只会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的文人,但是在这里面所包含的对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国家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行动能力的判断倒是比较准确的。
韦森教授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认为,这本思想回忆录的翻译出版对我们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理清当下的思想观念,看清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还有更具体的问题是:“在当前中国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米塞斯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是否又在中国要验证?”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在经济问题之上,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洞察现实的忧患目光,和他以决绝的道德勇气发出的警世之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