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彭国翔: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改善身心——从儒家的功夫论谈起

按:近期彭国翔老师出版了新著《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我们就这本书对彭国翔老师进行了采访。本书是彭老师二十多年来对“功夫论”思考的总汇。所谓“功夫论”是儒家对如何实现理想人格的种种方法。如彭老师所言,儒家有“宗教性”的传统,儒家的“宗教性”不是一神教的宗教模式,而是即凡俗而神圣,在“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之下,思考如何能够实现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关系的圆满,借由成仁成圣,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值得注意的是,彭老师对功夫论的思考,不限于中国文化内部,而是建置在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野之上,在中西之间穿梭往来,尤为珍贵,可供借镜。本书的编辑成书工作,是在上海封城,万物静默之际完成的;而本次采访则是在岁末年终,疫情肆虐之下进行的。在这一人类的特殊时期,思考如何成人,读者与作者共同经历一场身心修炼。
本次访谈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孙绪谦完成,下文简称“学人”。
一、功夫实践的最高境界是“彻悟”
学人:您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儒家“功夫论”的意涵?
彭国翔:“功夫论”就是“论功夫”,即关于“功夫”的各种思考所形成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这里的“论”字,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理论”、“论说”,当然也可以叫“哲学”。因此,“功夫论”也就是关于功夫实践和方法的理论、论说和哲学。而“功夫”这个词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实践”和“方法”的意思。“实践”和“方法”总是关联于“目的”。换句话说,“功夫”总是指向一个最终要追求的“目的”,“目的”不同,自然也对“功夫”的实践和方法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的目的是成为一个儒家的君子人格,那么,你关于功夫的思考,或者说你的“功夫论”,便自然围绕如何成为一个“君子”这一目的。如果用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自身的话语,目的是“本体”,实践和方法是“功夫”。同样,如果你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像佛陀那样的存在,或者说成为道家经典中描述的“真人”、“至人”和“神人”,那么,你的功夫论便自然会体现出佛教或道家道教的色彩。
我之所以用“功夫论”这个名词,一来是内在于中国传统自身的话语,使用传统自身的语汇;二来是希望避免像“哲学”这样的现代词汇对中国传统中关于功夫实践的各种思考所可能造成的狭隘化或过度泛化。当然,我曾经做过澄清的工作,指出中文里的“哲学”,不必是英文“philosophy”的直接对应;而英文里的“philosophy”,涵义其实也比一般的理解远为丰富。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一书里有详细的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考,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哲学方法论》
作者: 彭国翔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0-11-1
儒家的“功夫论”自然是儒家对于功夫实践和方法的思考。而“儒家”当然首先是指古往今来儒家传统中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于“功夫”的思考所得。由于不同的思想和精神性的传统对于功夫实践各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儒家的“功夫论”自然也意味着具有儒家特色而有别于佛教、道家道教、犹太教、耶教(Christianity)、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其他思想和精神性传统对于功夫实践和方法的思考。简单地说,儒家的功夫论是围绕如何成为儒家的君子人格这一最终追求和目的,或者用儒家自己的话来说,是围绕如何“成人”这一核心问题意识所形成的各种系统性的思考。
学人:除了您所介绍的受到阿道(Pierre Hadot)、纽思浜(Martha C. Nussbaum)等对西方古代哲学研究的启发之外,您自身是否有这种“功夫”的修炼,又有什么感触与启发?
彭国翔:我在《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一书的前言中提到,我学生时代曾有静坐的功夫实践,后来时作时辍,如今已经到了若有若无的地步。不过,正如我自己的研究所显示的,功夫实践不必只有静坐这一种方式。而且,在儒家看来,静坐甚至并不构成根本的功夫实践方式。日常生活中的时时处处,都可以成为功夫实践的道场,借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行住坐卧,皆是禅定”。这一不脱离日常生活的功夫实践的特质,正是儒家功夫论的特点之一。从我对《论语》“乡党”篇的考察可以看到,孔子向世人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非但不脱离日常生活、反而把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都自觉当成功夫实践的道场和机会的场景。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我思考儒家传统功夫论多年所获得的最大感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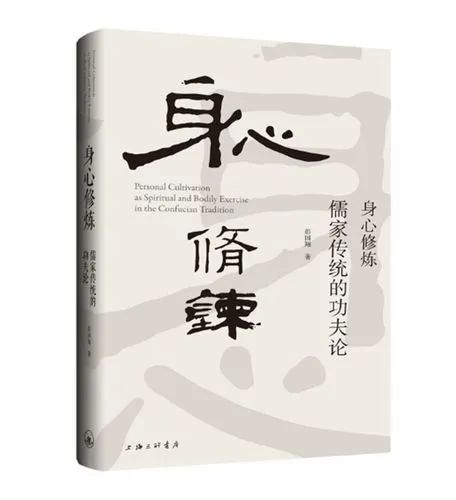
《身心修炼 : 儒家传统的功夫论》
作者: 彭国翔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2-8
当然,把功夫实践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本身就是功夫实践达到相当程度和境界之后才能体现出的特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开始需要“念兹在兹”的高度的自觉。正如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只有经过长期的磨练之后,才能自然而然,最终达到阳明学的翘楚王龙溪所说的“忘”的状态。
用王龙溪的话来说,功夫实践的最高境界是“彻悟”,就是“大彻大悟”中的那个“彻悟”,是随时随地处在功夫实践的状态,也就是《论语》“乡党”篇中所描绘的孔子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的状态。不过,除了“彻悟”,王龙溪说还有“解悟”和“证悟”两种功夫实践的方法。“证悟”是指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去体会自己内在的心性本体。刚才说的“静坐”,儒家意义上的静坐,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证悟”的功夫实践。至于说“解悟”,就是通过读书,通过理解书中所讲的道理,来体会自己内在的心性本体。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尤其是阅读那些饱含智慧和哲理的古今中外的伟大经典,只要用心体会,特别是和自己人生与社会的种种经验相印证,就能获得觉解,产生智慧。王龙溪虽然也说,单凭读书获得的“解悟”如果不能完全内化,就不免只是一时的感兴,他用了一个比喻叫“门外之宝,非己家珍”,意思就是还没有真正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但是,他毕竟也承认读书本身可以构成一种功夫。
事实上,如果说就像古人所说的,读书可以变化气质,那么,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功夫。所谓“变化气质”,就是指通过功夫实践来改变自身,使我们越变越好,越来越接近“君子”的人格。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最可行也最易行的功夫实践。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如果一个人饱读诗书,这个人的气质自然就会不庸俗而优美。这就是读书作为一种功夫实践使我们的身心得到修炼、获得改善的经验例证。
对于把读书作为一种功夫实践的方法,尤其是身心修炼、变化气质的方法,儒家传统里面谈的最多的是朱子。对于朱子来说,真正的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客观的知识,而正是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在他看来,如果你读了儒家的经典之后,仍然和读了之前的你一样,自身的气质没有得到变化,那么,你就等于没有读过那些经典著作。所以说,正因为读书切实可行,朱子把读书作为一种身心修炼以最终成就圣贤人格的功夫实践,就有其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特别值得提倡。

牟宗三
我记得,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经批评朱子,他说“朱子之学是学人之学的正宗,非圣人之学的正宗”。这句话并不是没有它的道理,这和牟先生对于朱子哲学思想的整体判断有关。他称朱子为“别子为宗”的说法,不免受到一些推崇朱子的学者的质疑。但这既不意味着对朱子的不敬,也不是没有它的理据。朱子心理为二的基本立场,的确无形中会使得“理”成为一个外在的被认知的客观对象,如此一来,“心”是不是一定要按照“理”去进行道德实践,便没有必然的保证。当时陆象山对朱子的批评以及后来王阳明最初按照朱子的方法进行功夫实践,最终却难以契合,反而走上了与陆象山一致的道路,都是这一问题的反映。所以,牟宗三先生对朱子思想的整体判断,并不是没有其相当的理据。但是,有一点我想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在把读书作为身心修炼的方法,以追求圣贤人格的实现为目标这一点上,牟先生所谓“朱子之学是学人之学的正宗,非圣人之学的正宗”这句话,对朱子来说是不够公平的。因为至少就朱子的主观用心来说,他最终要追求的,并不是像学人之学那样去追求客观的知识,而无疑是以成就圣贤人格为目的的圣人之学。
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要强调读书完全可以作为身心修炼、变化气质的功夫实践。只要我们能够长期不断地阅读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并不断和我们的人生、社会阅历相互印证,不断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久而久之,一定可以获得身心的转化。这就是今天人人可行的功夫实践。如果不读书,不仔细研读那些古今中外一流学者呕心沥血的经典著作,在还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情况之下,就妄谈“笃行”,自以为不必读书、钻研就可以“悟道”,很容易走火入魔,使得儒学标签化、口号化,变成一种“师心自用”甚至“猖狂恣肆”的粉饰。这一点,可以说就是我最大的感触和启发。
学人:如您所说,儒家功夫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您用“善”“信”“美”“大”“圣”“神”等描绘概括儒家理想人格的不同维度,请问您理解中的这种“理想人格”是什么样的?
彭国翔:“善”“信”“美”“大”“圣”“神”是孟子的词汇,是他对儒家理想人格不同层次和境界的一个描述,也是对功夫实践道路上不断进阶的形容。以往历代的注家在解释《孟子》文本中关于“善”“信”“美”“大”“圣”“神”的那段话时,似乎大都没有关联于儒家理想人格不同的层次和境界以及功夫实践的不同进阶来加以讨论。我在考察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时,因为对这段话已有较长时间的思考,就把这段特别值得思考的话提出来加以分析。我可以把书中关于这一段的分析在这里跟你复述一下。
孟子“可欲之谓善”和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及“为仁由己”的观念遥相呼应,意在指出“仁”和“善”的价值追求与实现不受外部条件的制约,只要一念发动求仁向善,所谓“可欲”,便已经处在成就“仁”与“善”的途中了。而一念“欲”善,注意这里的“欲”是动词,是“想要”、“追求”的意思,内在的“仁义”便已然启动发用,成为真实不虚的自我意识。“有诸己之谓信”,则表明“善”的价值已经不再是外在于自己的抽象观念,而成为植根于自身的价值自觉。这和孟子提倡的“自得之学”,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正相符合;与孔子的“为己之学”以及《中庸》里“诚”的观念,无疑也是一脉相承。而“充实之谓美”,则是“有诸己”的更进一步,表明以“仁义”为内容的“善”在自身得到了完全与充分地实现。这在孟子看来,可以说是一种“美”。至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则意味着“善”的价值彰显和实现不再是一种局限于自身的行为,而必定要对身外的世界产生影响。既然是“光辉”,对周遭的照耀之功,就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与《中庸》的“修道之谓教”,在义理内涵上同样彼此呼应。如此“己立”(“充实”)而“立人”(“有光辉”)的教化之功,自然非崇高而伟大(“大”)不足以形容。不过,对孟子来说,儒家理想人格的成就并未至此而止。其终极的境界只有在“圣”与“神”这两个观念中才达至最后的圆满。如果说“圣”的涵义不仅在于理想人格充分实现了“四端之心”并发挥了“浩然之气”,更在于这种理想人格化除了那种崇高伟大的庄严之相而不再显得与众不同。那么,“神”的意思就在于:在“己立立人”和“己达达人”的作用过程中,“圣人”的化育之功不着痕迹,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所谓“不可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在我看来,《孟子》里面这段完整的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描述和形容的就是一个通过功夫实践的步步提升,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最终达至儒家所追求的一个理想人格的过程。儒家理想人格的丰富内涵和不同层次,可以说在“善”“信”“美”“大”“圣”“神”这几个概念中得到了完整的描述。当然,这样一种理解,是我多年的思考和体会所得。如果孟子泉下有知,能够肯定我的理解和诠释,对我来说,那将是最大的鼓舞。
二、儒学,可以说自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宗教性的传统”
学人:您经常提到,将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哲学)作为参照,在比较中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请问与西方文明类似的“身心修炼”相比,中国的功夫论的特点在哪里,它们又有何不同?
彭国翔:在西方古代的哲学传统中,就像我书中提到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中,他们更多地是将作为生活方式的不断思考的人生称为“精神修炼”,而不是“身心修炼”。如果说“精神”和“心”相对应的话,那么,“精神修炼”和“身心修炼”相比较来说,关键在于前者少了一个“身”的向度。这当然不是说古希腊和罗马人不重视身体,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稍微有所了解,就知道古希腊和罗马人是特别重视身体的。那么,为什么古希腊和罗马的那样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思考被称为“精神修炼”,而不是“身心修炼”呢?这主要是因为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柏拉图主义基本上对身体持较为轻视的态度。比如,柏拉图就认为,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人们净化灵魂,而灵魂的净化也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肉体不过是灵魂的监狱和枷锁。另外,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不免会将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柴米油盐的琐碎,作为哲学思考活动的妨碍,从而总有一种希望摆脱日常生活干扰的倾向。
而与此相较的话,中国传统“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其特点之一就是并不轻视身体,不仅中国本土的道教传统非常重视身体的修炼,儒家“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也同样不轻视身体的方面。比如,在儒家看来,首先我们很难在身心两个方面一刀两断,形成一种二元的认识。或者说,对于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来说,你很难清楚地在“身”和“心”之间划下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身”和“心”是相互渗透、彼此交关的关系。所以,一个人的修炼,或者说功夫实践,一定是“身”和“心”两个方面同时关联的。这一点,也是我在书中特别指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不仅不把日常生活当作功夫实践的妨碍,反而恰恰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衣、食、住、行、言,都当作功夫实践的契机,前面已经提到,就像《论语》“乡党”篇所描绘的孔子那样。后世禅宗讲的“行住坐卧,皆是禅定;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也同样是这样一种把功夫实践日常生活化、同时也把日常生活功夫实践化的态度。
当然,西方并不是只有“精神修炼”,而同样也有其“身心修炼”,即兼顾身和心两个方面的功夫实践。不过,西方的“身心修炼”更多地表现在他们的宗教传统中,像犹太教、耶教和伊斯兰教等。然而,虽然也兼顾身和心两个方面,但由于他们对于人的整体理解,尤其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理解,和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儒家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导致了他们即使也有“身心修炼”的功夫,仍然和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差异。对此,我在书中也有交代。比如说,我在讨论儒家式的静坐功夫时,就和西方的传统大致做了一些比较。只不过由于我的探究对象是儒家,并不是西方传统本身,所以对西方的传统就无法也不需要做过于深细的考察。对西方传统中的“身心修炼”如果有特别兴趣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很值得专门加以研究的。好像这一方面我们中国学界研究的人并不多,我倒是很希望多一些在这方面能够登堂入室的中国学者。
总的来说,儒家传统身心修炼功夫的特点,我概括为三点:一是身心交关;二是不脱离日常生活;三是让道德意志、情感和法则,也就是我们的“良知”,始终做主,在功夫实践中起到“定盘针”的作用。
学人:“身心修炼”的功夫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儒学”。王汎森有观点认为,“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也是一种思想”。当儒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践行者的思想世界与日常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彭国翔:儒学从其产生之时起,一开始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如果说“生活也是一种思想”,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说“思想也是一种生活”呢?事实上,没有人的生活能够离开思想,我们很难在“生活”和“思想”之间一刀两断。试想一下,即便是最没有知识和文化的人,只要他们有意识活动,多多少少也总是在想事情吧。当然,如果不是所有的意识活动都能够叫做“思想”,我们只能把有条理、成系统的意识活动称为思想,那么,所有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特别是那些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人,恐怕他们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由他们的思想构成的。换句话说,正是每天从早到晚几乎不断的思考活动,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把“思想”和“生活”割裂,认为“生活”可以脱离“思想”、“思想”不是“生活”的想法,特别是那种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与“思想”无关的所谓“生活”的说法,是肤浅而禁不起推敲的。试想一下,不要说那些以“思想”为毕生“志业”的学人,即便是以谈论“思想”为“职业”的知识从业员,假如过着没有“思想”的“生活”,岂不成了“行尸走肉”?
所以说,当儒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践行者的思想、精神世界与其日常行为之间,当然应当表现为一体的关系。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儒学践行者的思想、精神世界及其日常行为之间,应当是“知行合一”的关系。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有这样几点我们要注意。
首先,把儒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个人成为儒学的践行者,是一项很高的要求。或者说,这得是身心修炼的功夫达至相当程度之后才能做到的。尤其在一个“国学”流行、儒学成为时髦的风气之中,所谓把儒学作为生活方式、做儒学的践行者,往往流于口头禅、赶时髦。比如说,是不是穿上唐装汉服,屋里摆几件中式家具,挂几幅中式字画,书架上放上“四书五经”、《传习录》,平素焚香饮茶,就算是过上了儒学的生活、践行了儒学呢?我想恐怕是算不上的。前面已经提到孔子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话,如果“笃行”最能代表“生活方式”和“践行”的话,那“笃行”之前一定要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工作要做。这就和以读书、思考为核心的知识、理性活动密不可分。这一点,往往是我们在强调“生活”和“践行”时容易忽略的。
儒学是一个极为重视“学”的传统,孔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我们知道,“忠信”是儒学中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孔子这里用来自我界定的,是“好学”而不是“忠信”,足见他对于“学”的重视。虽然儒家的“学”不只是为了追求客观的知识,而是为了追求“智慧”和“觉悟”,所以过去理学家把“学”解为“觉”,但是,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很容易走火入魔,流于浅薄和狂热。所以说,把“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儒学,就像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哲人那样,过一种“精神修炼”的生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换句话说,要想把任何一种学说变成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要想成为任何一种学说的真正的践行者,都必须对那种学说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过程,达到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和孟子所说的“深造自得”的地步,才能谈得上。否则的话,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成为一件与实际如何生活、实际践行什么价值无关的幌子。古往今来之所以“伪君子”屡见不鲜,正是因为真正把儒学当作生活方式、真正践行儒学的价值,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把儒学这样一种精神性的思想和学说作为生活方式,在生活中践行这种思想和学说,并不意味着现实当中就能够完全地实现“知行合一”。或者说,不要说儒家追求的最高的理想人格,即“圣贤”,即便尚未达到“圣贤”的“君子”,也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的。换句话说,即使真诚而且尽力把儒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去做儒学价值的践行者,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完全实现儒学的那些核心价值。
我这样讲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拿圣人、君子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用放大镜、显微镜去看别人。我曾经说,不要说朱子、王阳明不是圣人,就连孔子也不是圣人。孔子自己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意思是“圣”和“仁”这两样,他是不敢当的。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孔子,自己都不接受圣人的名号,我们也不应当把他当作一个圣人。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有一个作为文化符号的圣人孔子。事实上,当我们说圣人孔子时,我们主要是在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说,我们有两个孔子:一个是作为文化符号的圣人孔子,另一个是作为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的孔子。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现实当中有血有肉的人谁也成不了圣人,还要那个作为文化符号的圣人孔子又有什么意义呢?要我说,意义是有的。这就涉及我要讲的另一方面的意思了。
我们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拿圣人、君子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是,圣人、君子的人格,对于我们将其作为一种始终追求和不断对照的典范,却是很有意义的。只有始终高悬这样一种典范,以为不断改善自己的标准,自己才能不断进步,使自己不断变好。如果没有一个典范,我们不断完善自身的标准又在哪里呢?打个比方说,圣人、君子人格就好比是衡量方圆的“规矩”和“尺子”,这把规矩和尺子的用处不是要去比量别人,而是要用来不断衡量自己,意识到自己和那把规矩和尺子之间,永远有距离。这种距离感对我们自己来说,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圣人和君子人格遥遥无期,最终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是要让我们始终意识到,自己只要存在一天,就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明日之我永远有可能比今日之我要更好。这是我要说的关于“即使真诚而且尽力把儒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去做儒学价值的践行者,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完全实现儒学的那些核心价值”这句话的第二层意思。前一个意思是针对别人,这一个意思是针对自己。
总的来说,“知”与“行”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难以消解的永远的距离,对于看待我们自己的身心修炼来说,是一种永恒的动力,它推动着我们不断要试图去缩小那其间的差距;对于看待别人的身心修炼来说,则是一种推行“恕道”的理由和依据,因为正是那种差距的永恒性,使得我们不应当用圣人的标准去对别人求全责备。
学人:您的多篇文章,是从宗教学的视角下,来审视儒家。您将儒学定义为一种“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传统,这种宗教性的传统是什么样的特征?近代以来,在西方耶教国家及日本神道教的刺激下,才有立教以救国的声浪,您认为这种“宗教性传统”的历史起源又是何时?
彭国翔:是的。我从宗教学以及比较宗教教学的角度观察儒学,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这本书里。这本书的初版是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了一个增订版,增加了三章近十万字的内容。对于儒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宗教性和精神性”的传统,这种作为一种宗教性和精神性的儒学传统具有怎样的特征,我在那本书里有较为详细和充分的说明。我想我不用在这里重复其中的内容,并且,过于简略的说明的话,也许会将其中的丰富性化约掉。所以,你如果想了解我的具体和完整的看法,不妨去看一下我在书中的论述。另外,该书的英文版2023年春天也会上市,对于英语世界进一步了解作为一种宗教性和精神性的儒学传统来说,该书应该说也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虽然在我那本书里新增补的关于民国时期“五教”的两章中不无涉及,但并不是我主要的问题意识,就让我在这里尝试回答一下吧。当然,你的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在这样或那样的语境中或多或少提出过。当你说“在西方耶教国家及日本神道教的刺激下,才有立教以救国的声浪”时,其实你已经预设了某种关于“宗教”的理解,虽然也许是不自觉的,那大概就是以耶教为基础的一神教的宗教模式。而如果你说的“立教以救国”中的“立教”指的是清末民初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的建立孔教运动,那么,他们所要把儒学建立成的那种“教”,正是以耶教的模式为样板的。但是,这里问题就来了。
以耶教或者说以一神教为模式的“宗教”,恰恰不是我所谓的“宗教性与精神性”中的那个“宗教”。康有为、陈焕章要以一神教的模式把儒学建立为宗教,并不能简单地以荒谬而论,予以一笔抹杀。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有此想法,基于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中国社会当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我常说,任何一种文明就好比一个房子,尽管风格可以各种各样,但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这些不同的功能项,却是都必须具备的。这些功能项是使得一个文明能够成为一个完整而不残缺的文明所必须的基本单元。宗教正是人类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能项。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越来越趋向于一个类似现代西方的社会,宗教这一功能项也必须随着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而有所确立。由于宗教的功能主要是“正人心、齐风俗”,而这一功能在传统中国社会正是儒家的擅场,因此,康有为、陈焕章希望比照一神教的模式把儒学建立为一种宗教,就是当时社会变迁大势之下的自然结果,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事实上,如今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所以有“孔教会”一类的儒教组织,也可以说是在当地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为了使儒学更为明确地成为那样一种功能项的诉求和努力吧。
不过,宗教的模式未必只能有一神教一种,康有为和陈焕章的时代,西方的宗教学理论在比较宗教学方面尚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随着比较宗教学的发展,比如到了W. C. Smith的时代,他和其他一些不局限于一神教传统的宗教学者,就已经具备了全球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宗教观也不再仅仅建立在一神教的模式之上了。例如,W. C. Smith由于意识到了“宗教”这个名词已经长期被耶教独占,他甚至主张放弃用“religion”来界定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如果康有为、陈焕章能够对此有所了解的话,我想他们建立儒教的主张,也许就未必再非要以一神教为模式不可了。
一神教的模式因为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即教会,最大的好处是利于传教。但是,一旦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就有它难以避免的问题。等级森严造成的威权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丑闻,或多或少都与那种严密的组织化有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个人与超越的上帝可以直接建立联系,不需要通过教会组织,以及晚近很多不去教会的信仰人士用“spirituality”代替“religion”,也都是对那种高度组织化的教会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回应。就此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历来没有“孔教会”那样的组织,尽管不利于传播,但却恰好避免了严密组织化的教会带来的各种负面问题。

所以,要回答你问的儒学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在历史上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对如何理解宗教做出明确的界定。如果对宗教的理解以一神教的模式为基础,那儒学作为宗教性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出现。康有为、陈焕章的建立“孔教”并未成功,新中国成立迄今的法定五大宗教,也没有“儒教”。不过,如果说对宗教的理解并不限于一神教的模式,而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可以给人们的身心带来终极性转化的理论和实践,人格化的上帝和组织化的教会都不是必要的条件,那么,通过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以“变化气质”并最终成就理想人格的儒学,可以说自其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宗教性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已经较为流行的“五教”的观念,就是把儒学作为一种和佛教、道教、耶教以及回教并列的一种“宗教”。事实上,如果我们充分顾及到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传统所具有的不同模式,比如除了起源于西亚的一神教模式之外,还有起源于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以及起源于东亚的儒家和道教,“宗教”的定义便不应当再以一神教的模式为依据了。这一点,在西方宗教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早已经被专业的宗教学学者所接受了。这个问题,我在《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和讨论。
学人:在“身”与“心”,有情感维度作为桥梁以连接。“情”在理学中,也是一个经常常见术语,从“性”“情”的体用关系方面多加讨论。近年来,西方学界也有情感研究的趋向。请问“情”在身心修炼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彭国翔:你之所以这样问,应该是对我的“身心修炼”中的“心”字的理解有所窄化所致。我使用的“身心修炼”中的“心”字,并不是理学传统中“心”“性”“情”三分那样的概念架构中的与“情”不同的“心”。简单地说,“身心修炼”中的“身”,是指我们“身体”的部分,用英文说就是physical/bodily的方面;而“心”则是包括知、情、意在内的“认知”、“情感”和“精神”的方面,用英文说就是包括cognitive/mental/emotional/spiritual的方面。或者说,“身心修炼”里的“心”字,基本上包含了中文里“心”字所能包含的所有涵义,它已经包括了你所说的情感(feeling/emotion)的方面在内。事实上,如今英文里之所以多用“heart-mind”而不是过去常用的“mind”来翻译中国哲学里面的“心”字,就是充分认识到中文里的“心”更多地与情感的向度有关,不单纯是更多地与“脑”有关的那样一个理性认知意义上的概念。我们知道,如果侧重的是认知方面的“心”的活动,英文里对应的更多的是“mind”,而不是“heart”。“heart”更多地与人的情感活动有关。汉语里面“伤心”、“痛心”等等用语,突显的也是“心”的情感的向度。
这样的话,“身心修炼”自然包含“情”的内容。“身心修炼”中“修心”的部分,自然包括情感、情绪的修养与磨练。事实上,儒学功夫实践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正是对于我们七情六欲的调节。你看《中庸》里面讲的,宋明理学里面讲的,很多都是关于如何调节我们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如何让我们情感和情绪的表达和流露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不欠缺,避免“过”和“不及”,正是儒家功夫实践的重要内容。
你提到近来西方学界对于情感的重视,是的,的确如此。记得我当初还在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吧,有一次我们开了一个关于身体观方面的研讨会。我在那个会上特别介绍了西方哲学界21世纪以来关于情感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后来,在我的“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那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我也对这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比如说,我专门提到了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生前两本很有贡献的书:一本是他的专著《真实面对我们的情感》(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一本是他邀请分析哲学传统中若干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分头撰写而编成的《情的思考:当代哲学家论情感》(Thinking About Feelings: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on Emotions)。虽然“情”的方面在西方哲学传统一开始就被关注和提出来加以讨论,但理性主义传统毕竟占据主流,所以像所罗门那样的专业哲学家在21世纪再次强调情感的重要,在西方哲学中就格外有意义。比如他在《真实面对我们的情感》一书导论开头所说:“我们不像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那样仅仅是理性的动物,我们也拥有情感。我们通过我们的情感来生活,是我们的情感给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对什么感兴趣,我们为什么而着迷,我们爱什么人,什么东西让我们生气,什么东西令我们厌倦,所有这些东西定义了我们,赋予我们品格,构成了我们之所以为我们。”
当然,与此相比较的话,我们说中国哲学传统一直以来相对更加重视情感的因素,是一个不错的观察和判断。这一点,西方学者在研读中国哲学的古典时,也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专门以“情”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合情合理”始终是中国文化同时侧重的两个方面。我记得林语堂先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讲究“合情合理”。钱穆先生好像也有类似的说法。的确如他们所说,对于情感与理性两个方面的兼顾,不仅是中国哲学传统的高度自觉,同时也早已深入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了一种“心灵的积习”。我记得清人张潮在其《幽梦影》中有这样一句话:“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这当然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情感的重视。
我那篇“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就是以牟宗三先生这位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哲学中最富理性精神的一位哲人为例,讲“情感”的问题。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觉得与这里我们讨论的内容恰好密切相关。我是这样写的:情感与理性是任何人都具备且彼此不可化约的两个方面,不会“此消彼长”。即便被认为是最为理性的哲学家,情感的方面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与其理性一样,较之常人往往更强。如果说“大智之人,必有深情”,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判断。并且,情感的力量在决定人的行为时,常常比理性更为强大。在儒家看来,人的终极实在如“仁”“恻隐之心”,历来也恰恰不仅是道德理性,同时也是道德情感。这段话里说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同时也就是“道德心灵”,完全可以用一个“心”字加以概括。
也正因如此,儒家传统“身心修炼”的功夫论中包含了丰富的调节情感、情绪的内容。对于今天日益受到情感、情绪问题困扰的现代人来说,这一部分内容正是极为有益的观念和实践的资源,值得我们好好汲取。
三、知识化并不一定是“负面的”
学人:自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仍积极推动修身,但相应的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是,其目的是从儒家理想人格的自我养成,转移到现代的国民培育。传统儒家维度的功夫论以及一系列的修身方法,与培养现代公民有何关联,是否可以实现一种“现代转换”?
彭国翔:从儒家传统的“修身”到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当然可以说有一种“现代的转化”。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主要侧重于权利意识,更多地是着眼于公共领域。而就道德来说,也更多地着眼于所谓的“公德”。比较来看,儒家理想人格的养成,似乎更多地侧重自我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个人的“私德”。这大概是一般的看法。像英文里把儒家的“修身”或者说功夫实践翻译成“self-cultivation”,多少也是这种看法的反映。
不过,我想说的是,“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更多地是一个现代的观念。这种划分当然有其意义,有利于澄清很多问题。即便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关键在于,传统的儒学并不认为“身心修炼”可以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孤立的自我行为。换句话说,“身心修炼”一定是一个要在自我与他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之中来进行的过程;甚至不只是自我与他人之间,还在于自我与整个天地万物之间。你知道,儒家有一个“万物一体”的观念,就是指出一个人的“身心修炼”不仅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还要发生在人与动物、植物乃至看似没有生命的像瓦石那样的无机物之间。这样来看的话,儒家功夫论的各种实践,又很难局限于“私领域”“私德”的范围之内去理解。换句话说,只要是“身心修炼”,一定必然同时涉及“私领域”和“公领域”、“私德”和“公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所谓“私德”很好而“公德”很差的人。在我看来,真正的“德”,一定是要在“公”与“私”两个领域同时有所表现的。
当然,“公德”有时和所谓的“文明”(civility)有关,而“文明”有时又难免与风俗、习惯有关。比如说,以前在公共场合抽烟似乎不太会被认为是不讲“公德”,但如今一定会被认为是“公德”有亏。但如果一个人是由于风俗、习惯而没有意识到公共场合抽烟会给别人带来不适,这个人又是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只要告知这个人公共场所抽烟会给别人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那么,我想这个人一定会改掉这种看似缺乏“公德”的行为。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在“公德”方面似乎做得很好,彬彬有礼,但这个人“私德”很差,我们恐怕很难说这个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个人所谓的“公德”,大概多半是缺乏内在真实性的表面文章而已。孔子指出只有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的“礼”才不是“虚文”,意义正在于此。
所以,我想说的是,儒学的“修身”或者说“身心修炼”,原本就是从自我到家、国、天下一以贯之的,并不局限于自我的“私领域”,这和儒家把“自我”本来理解为天地万物中的一个关系性的结点是一致的。虽然随着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诸多巨大变化,“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人们越来越具备那种和君主制下的“子民”意识截然不同的“公民”意识,你所谓的“现代转换”的问题的确会出现。但是,由于儒家的“身心修炼”原本不以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为前提,所以,实现这一现代转化,对于那些真正能够于儒学传统深造自得的人,并不会构成一个问题。晚清以来,最先、最快地接受各种现代意识的人,恰恰都是那些儒学传统内部的精英人士。你提到的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个例子。而那些真正保守、拒斥现代的人士,反而大都是于儒学传统未能“登堂入室”的人。
学人: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传统儒学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儒学与现代学科分类存在一定的缝隙,单一的文学、史学、哲学,或西方高校流行的东亚研究、宗教学等学科分野不能准确地概括儒学的意涵;另一方面儒学也面临着被“知识化”的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方面的困境?
彭国翔:你说的那种困境,的确存在。在现代的知识分系统之下,从任何单一的某个学科的视角去看待儒学,总不免“盲人摸象”,不太容易对儒学有整全的认识。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只是儒学面对的,世界上任何精神性传统,比如佛教、耶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据说以前欧阳竟无先生说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意思就是说佛教的思想不能仅仅归于宗教或者哲学的单一学科之下,因为佛教思想中同时具有宗教和哲学的内容,所以他在那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说了“佛法亦宗教亦哲学”的话。他的这一说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儒学以及其它的精神性传统。
不过,这个问题也并不只是困境。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用现代知识的分类系统去观察儒学,特别是从文、史、哲等某一种人文学科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儒学,就好比一束聚焦的光照射到儒学之上,可以最大限度地照亮儒学的某一个方面。这比以往笼统的、没有现代学科意识的观察,能够使儒学的某一方面被更为清楚地观察到。如果不同的学科之光在各自照亮儒学的某一方面的同时,能够彼此配合,而不是只以为自己看到的儒学才是儒学,别的学科之光照耀下的那些方面就不是儒学的固有内容,这样的话,不同的学科之光彼此配合,一起再来观察儒学,恐怕就会比传统意义上对于儒学的理解,更为深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现代的知识和学科分类注重“分”,那么,只要在“分”了之后再将不同学科观察之下各自的所见“合”起来,对于像儒学这样的传统,比起以往没有经过了“分”的笼统的“合”,其了解就会更为深入。在这个意义上,你说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困境,就未尝不能够避免,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得以避免。
至于你说的儒学被“知识化”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这里我想说两点:首先,所谓“知识化”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传统,儒学的终极追求当然是身心的转化、气质的变化,是成为君子那样有智慧的理想人格,所以,像朱子那样被认为是儒学传统里最为注重知识的人物,在其“读书法”里第一句话说的,反倒是“读书是学者第二事”。这就表明,朱子也不把单纯的知识获取作为最终的追求。但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知识本身也是君子人格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对于作为圣人的孔子,过去的形容是“仁且智”。这里的“智”,就内在地包含知识的内容。换句话说,儒家的理想人格必然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这一面,儒家的理想的人格就会如同鸟儿缺了一只翅膀一样。
其次,你说的儒学“知识化”如果是指忘记了儒学的终极追求是通过“身心修炼”以成就理想人格,对儒学的学习变成了单纯的积累知识,甚至把这些知识作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那么,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知识化绝不是随着现代的知识分类系统进入中国、随着现代的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才产生的现象。可以说,把儒学作为一种谋求功名利禄的知识和工具,在历史上是从来就有的。尤其是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很多从小读圣贤书的人,都只是把儒学作为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利禄的知识工具。你看南宋那些迫害朱子的官僚集团中的人物,不正是和朱子一样饱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的吗?所以说,儒学异化为“知识”,或者说你说的那种负面意义上的“知识化”的问题,自古便有,不必是现代知识和学科分类系统之下的产物。
此外,在现代的知识和学科分类之下,或者说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之中 ,儒学也不是只能作为知识来被教师讲授和被学生接纳的。只要教师不把它只是作为知识来讲授,学生不把它只是当作知识来吸收,而是把它当作身心修炼、变化气质的精神资粮,即便在现代的知识和学科分类系统中、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中,儒学也不只是知识,而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深入人心、发挥作用。所以说,对于儒学来说,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它。你把它当作知识,那它就是知识;你把它当作一种转化身心的精神价值,那它就不只是知识。这和它是否在现代的知识和学科分类以及教育体制之中被讲授和被学习,并无必然的关联。
试想,哪怕是在修道院里天天念圣经、在佛寺里天天念佛经,你不把那些经里讲的东西切实作为转化自己身心的精神资粮,尽管你把它们念得滚瓜烂熟甚至倒背如流,它们仍然也只是外在于你的知识。而即便在现代的大学里面,如果你能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切实转化身心、变化气质,那即使教师是把它作为知识来讲授的,对你来说,它也不再只是知识了。这样来看的话,你所说的“知识化”的问题,同样也不是不可化解的困境。
学人:您经常提到“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研究态度与写作方法,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与研究方向吗?
彭国翔:“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是余英时先生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我想,对于真正知道学术为何物、应当如何做学术的学者来说,都会对这句话心领神会。事实上,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所应当具备的基本自觉。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余先生笔下的这句话时,立刻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因此,后来我在讨论研究态度和方法时,便经常援引这句话,希望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更年轻的学子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道理,踏上学术研究的正途,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
为什么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很简单,学术工作是一项海内外很多学者一起从事的“共业”。即便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能会有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在进行研究。因此,你只有充分了解该题目迄今为止已经在哪些学者手上被做过,做到了何种程度,你才能进一步决定要不要继续做这个题目。如果一个研究课题早已被其他学者充分地研究过了,已经毫无剩义,而你并不知道,那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研究,不仅是白白浪费时间精力,更为关键的是,它对学术是没有贡献可言的。打个比方,大家一起在山中采矿,在已经被别人发掘过甚至发掘多次的地方,以及在别人尚未发掘过的地方,你在哪里更能找到矿产呢?所以说,“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既是要充分尊重既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要避免重复、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学术能够真正有所贡献。
我目前是有一些研究计划和方向,比如说,我要在先秦(包括汉代)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这三个领域继续耕耘,完成一些我早有计划但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此外,在儒学传统之外,对于佛教和玄学,我也积攒了一些题目。假以时日,我也希望能写出来。当然,我在其他场合也说过,我的一些研究与我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很多是由于我在世界各地的高校和学术机构阅读到一些新的文献,以及在和世界各地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交流的过程中,随缘激发产生的。这类的研究,虽然与我自己既有的研究之间不能完全毫无连续性,但也的确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所谓随缘而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从事学术工作其实常常和福尔摩斯侦破案件以及在以往不曾身临其境的大自然中探险一样,会让你的心力乃至体力不断经受挑战;同时,你在侦破了一桩桩案件和经历了一处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后,也会获得心智乃至身体上的愉悦。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身心修炼的过程吧。也正因如此,学术工作才未必总是枯燥乏味,而完全可以是充满了好奇与乐趣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