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变老的哲学”与……“向死而生”的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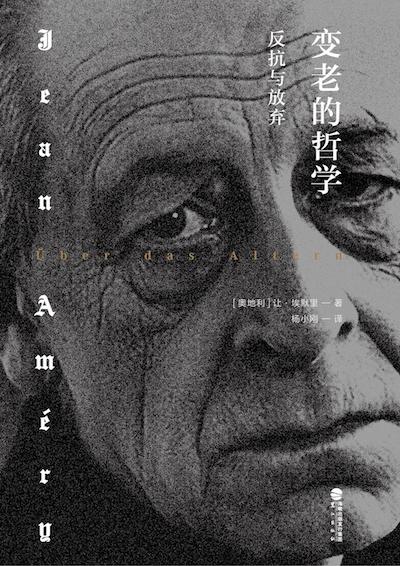
关于生与死之间的关系及其真实意义,我一直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趋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 death)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说“人固有一死”,更重要的是说人只有积极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才能获得生之存在的意义,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更准确说,“趋向死亡的存在”的意义就是“向死而生”。
奥地利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让·埃默里的哲学散文集《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4月)的主题也是生与死,但是焦点落在“变老之人”,或许也可以说是对“向死而生”的一种更有身体感性和对过程更敏感的另类解读。虽然“阿多诺看重让·埃默里对死亡经验的描述,这成为他批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死亡的观点的一个例子”(见译者为本书写的“代序”),但是在我看来埃默里的“变老的哲学”还是可以看作是对海德格尔生死观的一种诠释。本书的英语译者约翰·D·巴娄说:“让·埃默里写作《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是为了打破变老之人对死亡的妥协,并敦促读者去寻找属于他们自己作为个体去反抗和接受的方式。”那么,何谓“对死亡的妥协”?何谓“作为个体去反抗和接受的方式”?埃默里在书中时而化身为普鲁斯特、波伏娃、萨特等人,更多的是让自己出场,以充满复杂经验的“变老之人”的过程细节揭示人是如何无奈地与死亡妥协,又是如何不甘于这种妥协,因而要在死亡降临前作最后的“反抗”。
在这里,我想到的更多是在现实语境中作为个体的“反抗”的意义与可能性。“意义”是价值观的产物,死亡面前的“反抗”往往就是通过对一种价值的坚守而呈现出生命的意义。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内部发行,译者雷延中)的结尾处写道,那孩子已经永远地游到河里去了,“我”的内心如何被强烈震撼∶“我现在只能说一点—— 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一个7岁小男孩以他主动面向死亡的选择否定了他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成年人世界的贪婪与残忍),这就是他作为个体的反抗及其意义。那么,不要问什么是“作为个体去反抗和接受的方式”,只需要追问的是这个世界上是否还存在我们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如果有,这就是“向死而生”的时刻。亚历山大·科耶夫吸收了海德格尔的生存—死亡观,承认“人的理想只有通过终有一死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实现”,进而认为基督教的理想王国只能在此世、在地上的国家中实现。(科耶夫《黑格尔导读》,227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从哲学出发的死亡思考,很自然就进入到政治学、社会学和神学等领域,“变老的哲学”最终应该成为“向死而生”的政治学,妥协应该转变为反抗。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死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人才能体现自由的本性,并且更能体验生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变老之人”渐被社会抛弃,不仅是一种人生感受,也是今天社会的无情现实。别的不说,光看今天从许多商业机构到公共服务窗口无处不是把扫描二维码、下载APP作为入门条件,就让许多老人望而生畏,高科技泛滥的非人性一面暴露无遗。当然,能够被社会抛弃的“变老之人”只是属于普罗大众之列,权贵中的“变老之人”不仅不会被抛弃,而且日益位高权重。正如埃默里说的,“社会的顶层和支柱正是上了年纪的人,甚至是年纪很大的人,以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的那一代人?总统与总理,影响广泛的大学教师、管理委员会主席、学院成员,在这些职位上的人都正当年纪。……发号施令的人而言日子总会越变越长……”(97—98页)这是年龄政治学应该研究的课题,而且埃默里说的五十、六十岁现象还应该扩展到七十甚至八十岁。“年龄政治学”要研究的当然不仅仅是年龄的身体问题,“老人政治”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关键词是权力固化、思想保守、家族利益等。“变老”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可以很接地气,是很符合“不被西方学术牵着走”的学术抱负的重大课题。说到底,“变老之人”不能一概而论,有家族政治中的老爷子、沦为乞丐的曾经抗日的老国军、数着社保金过日子的老工人。虽然诗人布罗茨基说过,疾病与死亡是独裁者与老百姓唯一共同的特点,但是对待同样疾病的治疗却有天渊之别,身后哀与荣的方式更是绝不相同。面对“变老”,有一种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抵抗是“变真”,即所谓“两头真”(据说这是杨老记者提出的概念)中的一头,其要义是“觉醒”、“真理”和“敢说话”。当然,客观来看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变真”的前提不一定是“变老”,但一定是已经不在权力中心圈内。这可以说是超越了“年龄政治学”的课题,也是“变老”的哲学辨证法之一例。但是无论如何,说真话、真实地面对世界,当然在什么时候都不晚,他们“变真”的意义就在于在最后时刻否定了他们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变老之人”成为“变真之人”,后来的年轻人就会少了一点误入歧途的风险。
关于“变老”的感受,埃默里在书前所引出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那段话极为真实和残酷:“我以前的日子过得像一名画师……他先从一道缺口瞥见了湖水,接着湖泊整个儿地呈现在他眼前,他举起画笔。可此时夜色已经降落,他再也画不成了,而且白天也不会回来。”我也喜欢在旅行中画风景写生,对于在夜色悄然降临之时“再也画不成”的感受尤为真切。在暮色低沉的时候苍茫四顾,或许会很自然地追忆过去的自我,于是埃默里提出了这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我们把哪一个自我从过去带入老年?十岁时我们坐在教室里,二十岁时我们亲吻姑娘,三十岁时我们嫉妒职场上的同事,四十岁时我们发现,我们还爱着女人。每一次我们都是一个自我。变老时我们要拥抱哪一个?在这一个里明知或者仅仅是想象着,它比任何一个之后和之前的自我都更接近我们?”(75页)埃默里不会想到的是,这个问题会刺痛“我们”——我想象的是有过共同经历的一代人——十八岁我们上山下乡,三十八岁我们唱着《血染的风采》,四十八岁时我们重读奥威尔和哈耶克,五十八岁时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的确,“每一次我们都是一个自我。变老时我们要拥抱哪一个?”无论我们如何选择,我相信所有的选择都会与曾经有过的时代紧密相关,都会与我们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紧密相关。尽管其中有些是属于乌托邦,但是如果从来没有过属于乌托邦的黎明和青春,成长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权力与财富垄断了天空与大地的日子里追忆自我,“……别了,过眼的烟云。那个五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心里说实话有些难过,就像每次有一堆火熄灭了那样。我重读着巴枯宁、蒲鲁东的篇章,复诵着莎士比亚的诗句(‘反抗是一只疯狗的狂吠’),径自重蹈陈规,回到平常的小日子里去了”。法国著名剧作家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他的回忆录《乌托邦的年代》(戎容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写的这几句话让人眼热,不是因为过去的自我其实难以带入老年,而是由于目睹火堆熄灭、黑夜沉沉、反抗成了一只只能在心中狂吠的疯狗。埃默里更加不会想到的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变老时我们要拥抱哪一个?”而是那些曾经在空旷的广场上漫步的“变老之人”无论如何不愿接受变老时仍然无法摆脱的梦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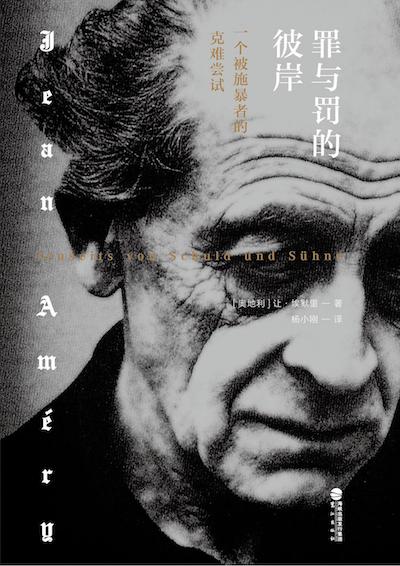
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被逮捕,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并遭受酷刑,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惨痛经历使他写了一本专著《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因而关于身体的真实感受在“变老的哲学”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而且他力图挑战公共语言的约束与无能。“作为变老之人,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陌生了,但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自己的身体,那变成纯粹质料的迟钝堆积的身体。”(185页)于是便有了“辛苦的腿,不听使唤的心脏,造反的胃,你们这些敌人让我疼痛……我是我的腿、我的心脏、我的胃,是我所有活着的却仅仅迟缓地更新自己的细胞,却又同时不是它们,我越接近它们并因此越变成自己,我就越对自己变得陌生,这些想法让我眩晕”。(64页)这些想法当然会让人眩晕,但是总的看起来,埃默里的身体观更多还是出自自我的身体感受,比较忽略了哲学史上的历史悠久的灵魂与身体之战,同时也忽略了围绕对身体的控制在当代政治中的尖锐对立与斗争。福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代政治学其实就是生物政治学,国家围绕着对身体的监控所展开的政治与技术斗争是这种政治学的核心。以这样的政治学视角看待正在老去的身体,可以激发更有想象力的“老去的哲学”。
该书最后一章题为“与死共生”,正好回应前面所说的海德格尔和科耶夫的思想。埃默里对“变老”与“死亡”的态度是颇为现实而又不无悲观的。“变老是一处变得荒凉的生命区域,不给人一丝一毫合理的慰藉。人们不该给自己任何幻想。变老时我们失去了世界,变成对纯粹时间的内感官。……在我们越过生命巅峰之后,社会禁止我们再做自我的筹划,文化成了我们不再理解的文化负担,它反而要求我们明白,我们已是精神的废铁,走在时代的下坡路上。在变老时我们终将与死共生,这是难以置信的苛求。我们忍受着无以复加的羞辱,不是带着谦恭,就是作为被羞辱之人。”(185页)话说得够狠的,“精神的废铁”、“走在时代的下坡路上”,这都是一种羞辱。但是他最终还是引用了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句说:“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日子在缩减、干枯,这时他终于有了说出真相的欲望”。(185—186页)这又很像是前面说的老人们的“变真”,当然埃默里的涵义更为宽广,包含有对尊严的肯定与呵护。这似乎很难看作是全书的结论,但可以肯定是来自埃默里内心无法熄灭的生命火焰,所以他仍然要“燃烧”和“咆哮”。
但是,在日暮时燃烧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咆哮?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得到表述。在我看来,可以从赫尔岑那里得到帮助,因为我们曾经与俄罗斯同受煎熬。赫尔岑说,文学、艺术与历史使我们看清楚了这个荒唐的环境、侮辱人的风习和畸形的权力社会,我们对这种生活既不可能适应,也不愿意和它搏斗而被毁灭。这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说话:要离开还太早;因为看来在死魂灵的背后,也还有活的灵魂”。(《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5月)是的,要离开还太早,“宙斯送来生命之火,余焰还在慢慢地燃烧”。过去我更多把这句诗看作是思想史的写照,现在更回到了生命本身的祭坛上理解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