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孙末楠的Fokways与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研究
诸如步济时、甘博,初创时期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师,不少是有着教会背景和身份的外籍尤其是美籍教师。在许仕廉执掌社会学系后,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师渐渐以有着留美背景的华人为主。无论是许仕廉还是吴文藻,这些留学归来的才俊,在走出去的同时,也经常聘请欧美一流的学者来华或长期或短期地任教、讲学。这样,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对同期国外研究的动向、思想、学派等都有着及时、广泛且不乏深入的了解。这使得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学水准、研究层次、创新精神在同期的中国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也才有了当下社会学史津津乐道的“燕京学派”。
因为步济时和甘博的关系,燕大社会学系创立初期的师生对1914年美国的春田调查(Springfield Survey)并不陌生。1918年9月起,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当时还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甘博和步济时受春田调查的影响,开展了对北京的调查,其成果即至今都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北京社会调查》。1932年秋冬,许仕廉迎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来燕大讲学。派克将其以研究美国都市为主的人文区位学系统介绍到了中国。在相当意义上,人文区位学是反抗改良式社会调查的产物,研究的是人类的社区和人与人的关系。竞争、互助、共生(关系)等,是人文区位学的关键词。在强调实地观察、访谈的同时,人文区位学也有着历史的视野。
1935年10月,功能主义大师阿尔弗莱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时译为拉得克里夫·布朗,当时的学人多称其为布朗)来燕大讲学一个半月,系统地介绍了其偏重于初民社会研究的功能论与比较社会学。1936年秋,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莱斯利·怀特(Leslie Alvin White, 1900-1975)在燕大社会学系讲授了人类学及方法论,德国的经济学家魏特夫(K.A.Wittogel,1896-1988)也于此时受聘,在燕大指导研究。1948年,派克的女婿、时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的罗伯特·瑞德斐(Robert Redfield,1897-1958)前来燕大、清华,主讲其关于乡土社会等方面的研究。
与这些来燕大现身说法的名家不同,孙末楠是一个并未出场却对包括燕大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界、民俗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美国学者。
孙末楠其人
孙末楠,又音译为撒木讷、萨姆纳等,186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在瑞士日内瓦、德国哥廷根和英国牛津游学三年后,孙末楠于1866年回到耶鲁大学任教至终老,主要从事政治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研工作,包括币制和财政、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等,其间,孙末楠曾于1869-1872年离职,做了三年牧师。孙末楠长于辞令,读大学时,每次辩论赛他都是获胜者。在教学上,他勇于创新,是最早将《纽约时报》作为课堂教学资料的教授之一,深得学生和同事好评,并被不少教授效仿。

孙末楠
1876年,他在耶鲁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是在美国教授社会学的第一人。因率先使用持进化论观点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著作《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作为教材,孙末楠在耶鲁大学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事端最终得以平息,却使孙末楠几欲离开耶鲁。孙末楠博学多才,精通英、法、德、古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多种语言。在45岁之后,他还学会了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罗斯和波兰等多国语言。
广泛阅读的孙末楠,勤于笔记。他常专门雇请一位书记员,帮助抄录读书笔记。在临终前,孙末楠写满割记的读书卡片,有52箱约16万张之多。就他做读书卡片的方法和对这些资料的珍惜,吴景超曾经写道:
他所以能驾驭这许多事实,便是因为他平日做倒记之勤。他是用卡片做割记的,每张卡片,长八寸半,宽四寸半。卡片的颜色,有好几种:从书上抄下来的文章,用白卡片;书目用红卡片;他自己的观察与论断,用绿卡片;文章的纲目,用黄卡片。在他死的时候,留下来的卡片,共有五十二箱,每箱约有三千张。这是他最珍贵的宝贝。有一次他的邻居失火,他怕延烧到他的房子,于是把这一箱一箱的卡片,从三层楼上的书房里,搬到楼下的后院中。这次把他累坏了,火熄之后,只得雇人来搬回原处。
正因为这样,其著述中资料的博洽和事实的充分,深得好评。
孙末楠,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通行的译名。然而,对他出版于1906年的Folkwas一书,学界有多个译名。孙本文、游嘉德、赵承信将之翻译为“民俗学“,在另外的著述中,孙本文、吴景超也曾将其翻译为“民俗论”,吴文藻、黄迪等翻译成“民风论”,李安宅、杨堃译为“民风”,罗致平译为“俗道论”。为行文方便,后文叙述中采用较为常见的译名《民俗学》或直接用英文原名。因为该书,在20世纪首尾,孙末楠曾两度与中国学界结缘。前一次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主要以“孙末楠”的名字出现。后一次则是以民俗学家的身份,以“萨姆纳”的名字回归。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界影响深远,并被他者反复诠释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高丙中几乎花费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译介了孙末楠“注重生活和整体”的民俗观。
孙本文、吴景超的译介
在国内,最早介绍孙末楠学说的应该是孙本文。在1927年年初出版的《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中,有“孙楠William Sumner之民俗论”一节。“在该节不长的文字中,孙本文将作为书名的“Falklways”译为“民俗学”,将在同一“超机官”上三个层次的民俗分别译为民俗、俗型(mores)和制度(institutions)。而且,孙末楠民俗学说的核心观点都一一在列,诸如:“民俗在个人为习惯,在社会为风俗”;“社会的生活societal life全在造成民俗与应用民俗”;“社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cty即是一种研究民俗的学问”,等等。不仅如此,孙本文还认为,孙末楠的民俗学“实开近时文化学派分析文化之先河,无可疑也”。稍后,孙本文也曾将follways这个词直接翻译为“民俗”。
与孙本文一样,李安宅也是较早译介孙末楠学说的学者之一。李安宅,笔名任责。在一定意义上,兼通哲学、美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家李安宅,是燕京学派的游离者。1927年,在哈特(Homell Hart)梳理的对社会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名单中,孙末楠和他的Falkways位居前列。1928年,李安宅翻译了哈特的文章,将孙末楠音译为撒木讷,将“Folkways”翻译为“民风”,并简单介绍了民仪、制度和民族等概念。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分别如下:
Customs are widely accepted folkways; mores are customsplus a philosophy of welfae; institutions are mores plus structures.Peoples are ethnocentric; in-group mores differ from out-group.Charity interferes with survival of the ft.
风俗是广被接受的民风;民仪(mores)是加上公益理论的风俗;制度是加上了结构的民仪。民族是族化自中的(ethnocentric);内群的民仪与外群的不一样;慈善阻碍适者生存的演化。
自此,源自孙末楠的民风、民仪与制度,不仅是李安宅1929年在燕大社会学系完成的毕业论文《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的关键词,也是其整个学术写作中的核心词汇和文化观的核心知识源,并在相当意义上影响到了李安宅的学术生命。
1929年,在以孙本文等留美归国生为主体创办的东南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刊》的创刊号上,有三篇文章同时介绍孙末楠,分别是:吴景超《孙末楠传》、孙本文《孙末楠的学说及其对于社会学的贡献》和游嘉德《孙末楠与恺莱的社会学》。孙本文毕业于纽约大学,吴景超和游嘉德均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吴景超还另文介绍过孙末楠的研究方法,将孙末楠的民俗研究与英国人蒲斯(Charles Booth,1840-1916)研究伦敦东区贫穷人口所用的访谈法、汤姆士(W.I.Thomas,1863-1947)研究波兰农民使用的“传记法”(即现在所说的生命史、生活史)相提并论。因为孙末楠《民俗学》是在其16万张卡片建构的资料库之基础上写成,所以吴景超将之视为用“考据”的方法,研究相对简单的初民社会及其风俗。
1907年,孙末楠当选为1905年才成立的美国社会学会的会长。这让不少社会学教授多少有些意外。二十年之后,德高望重的密歇根大学顾勒(Charles H. Cooley,1864-1929)教授将孙末楠的《民俗学》一书视为美国社会学界“脚踏实地根据事实的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一本。是年,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顾勒对同行不无感慨也语重心长地说:
同别人一样,近来我常想到研究学问的方法,以及类似的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问问我们自己,美国社会学界中这些著作,我们认为最成功的是哪一本?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意见不会一致的。然而我曾仔细思量过,假如我们把空论的社会学抛开不算,只提出那脚踏实地根据事实的著作来投票,看看谁得的票最多,结果孙末楠的《民俗论》,Folkuays即使得不到过半数的票,也会得到最多的票。
在五十岁之前,孙末楠的注意力主要在经济学。此后,其注意力才更多地集中到社会学。然而,在1899年开始整理自己的读书笔记时,他才发现“民俗”至关重要:
起初他想写社会学的,后来觉得“民俗”一个观念,极其重要,所以把社会学放开,写他的《民俗论》。此书于1906年出版,共六百九十二页。在此书的序文中,最后一句是:“我们第二步工作,便是完成社会学。”
换言之,在孙末楠的社会学中,民俗、民俗学不但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且是社会学的基础与前提。
至于孙末楠在社会学界中的地位,在《孙末楠的学说及其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一文中,孙本文将之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等人相提并论。对于孙末楠的民俗论、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学系统三大学说,孙本文花费了大半篇幅梳理其民俗论。孙本文指出,孙末楠民俗论的中心思想是:民俗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要素;它支配着人类一切活动。
孙本文全景式地介绍了孙末楠的民俗论,包括:1.民俗的定义与产生;2.民俗的产生是不觉得的;3.民俗的起源是神秘的;4.民俗是一种社会势力;5.民俗与幸运的要素;6.作为重要民俗的德型(mores);7.德型是一种指导的势力;8.德型和社会选择;9.德型规定是非的界限;10.德型具有非文字的、保守的与变化的三种特性;11.德型和革命;12.德型是可以改变的,但却是渐变的;13.政治力量不易直接改变德型。
关于“德型”一词,根据孙末楠原书,孙本文特别加注说明:mores是拉丁文,“意即风俗,不过这类风俗是关系安宁幸福而有相传神秘的权力,所以是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权”。最后,孙本文将孙末楠对于社会学的特殊贡献归结为三点:注重调适的历程、注重民俗对于人生的影响、注重归纳的研究方法而非理论先行。就民俗在孙末楠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孙本文基于阅读体验,认同他人对于《民俗学》是“第一部科学的社会学著作”的评价。关于“注重民俗对人生的影响”,孙本文写道:
民俗是民众的风俗;是一切行为的标准;他是范围人类种种方面的活动。举凡人类所谓是非善恶的标准,都受民俗的支配。人类不能一刻离民俗,犹之不能一刻离空气。所以民俗的研究,为社会学上极重要的部分。孙末楠对于民俗,加以一种极详细的分析。这是他第二种特殊贡献。
在对孙末楠和他的弟子恺莱(Albert G. Keller,1874-1956)合力完成的《社会的科学》的评说中,游嘉德在陈述其专书的基本观念、资料与方法的同时,也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诸如,孙末楠太受斯宾塞与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1832-1917)进化论的影响,所引用的来自初民社会的资料参差不齐,其客观性值得商榷,显得比较随意,等等。然而,游嘉德也反复指出,孙末楠和恺莱前后差不多耗时三十年完成的这部巨著,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是“人类适应他的环境,即研究习俗礼教制度等的演化”。换言之,在孙末楠及其弟子等追随者搭建的社会学大厦中,民俗始终都是重头。事实上,《民俗学》一书,取材之丰富、内容之广博、分析之生动深刻,“不啻将整个社会隐含在内”。
就其对美国社会学的演进而言,由孙末楠发扬光大的folkways这个学术词汇,还派生出了美国社会学另外一位重要的奠基者——季亭史(F.H Giddings,1855-1931)的stateways(国纪)一词。正如后文将要再论及的那样,无论是folkways,还是stateways,通过诸多留美归来的学术传承者,这些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基本认知和演进,对燕大社会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
此外,孙末楠Folkways一书也明显对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俗的写作产生了影响。1917年,公理会传教士何乐益(Lewis Hodous,1872-1949)从福州协和神学院(Foochow UnionTheological School)院长任上回到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与绝大多数传教士以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民俗的写作以folklore命名不同,何乐益1929年关于中国民俗,尤其是岁时节日和信仰、敬拜的写作,是用folkways命名的。他将folkways解释为:中国人使其生活和自然更替(changing moods of nature)维持和谐的方法(methods);社会群体(social group)为使他们自己适应自然律动(the breathing of nature)而生的情感反应(theemotional responses)。显然,这些意涵与戴尼斯、韦大列(G.A.Vitale,1872-1918)、翟孟生等西方学者更多指向民间文学的folklore相去甚远。尽管在其专著中,何乐益并未提及孙末楠。

1931年,燕京大学
派克的力荐
孙末楠《民俗学》一书是人文区位学的理论渊源之一。作为人文区位学的大师,派克于1932年的到来,再次引起了中国学界对孙末楠的关注。不仅如此,派克本人还亲自撰文介绍、阐释孙末楠的社会观。只不过在翻译该文时,孙末楠的名字被音译为“撒木讷”,Folkways也被译成了“民风”。派克对孙末楠社会观的介绍主要依据的还是Fokways这本书。派克阐释了孙末楠在该书中使用的“我群”“敌对的合作”“生存竞争”“互助”“共生(关系)”等关键词与理念。如同前引的顾勒教授和孙本文对该书的肯定一样,派克开宗明义地写道:
撒氏在1899年根据讲学材料起始写社会学教本,但在中途见有自述对于民仪(Mores)见解的必要,于是放下写教本的工作,写了一本《民风》。撒氏自认为《民风》为“我最后的著作”,当是美国作家对于社会学最有独到的贡献的著作。
在《论社会之性质与社会之概念》一文中,派克直白地说清了孙末楠以民俗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学与他的人文区位学之间的关系。派克认为,在《民俗学》中,孙末楠升华了生存竞争与文化关系的理论,强调人的竞争既是为了基本的生存,也是为了在群体中的位置,而且是群体性的。故群体有“我群”(we-group)、“他群”(others-group)之别。人口在空间的分布,便是由这种竞争-合作的方式所配置,且人类在大小社区内的安排,亦非偶然。进而,派克认为孙氏这种理论正契合人文区位学的区位结构论。
在继承孙末楠《民俗学》认知的基础之上,派克认为传统、习俗和文化是一个“有机体”。他关于文化的定义,显然是“民俗化”的,甚至完全可以将“文化”二字换成“民俗”。派克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同于印度、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的有机体、复合体-文明体:
文化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生长在这里面。我们的语言、习惯、情绪和意见都是不知不觉地在这里面养成的。在相当程度之下,它是一种出于各个人的习惯及本能的传习,它表示在各个人的共同及团体生活中,保持着某种独立生存和显示着一种个性。这种个性虽经历种种时间中的变端,仍能持久地遗传于后代的各个人。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习俗,和文化是一个有机体。
在燕大讲学期间,派克对孙末楠《民俗学》的推崇,给当时“洗耳恭听”的黄迪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记述道:
他来华后,第一天走进课室,所带来与我们相见的,便是孙末楠的《民风论》一书,而最后一课仍是诵读该书,对我们叮嘱言别。凡常到其办公室去的学生无不知道:《民风论》之于派克是不可须臾离的。至其平时在口头上、文字上对孙末楠思想的推崇佩服,扼要解释之处,比之季亭史与柯莱对孙末楠的好评,更为过火,更为精细。派克在燕京大学为社会学原理一课所编的讲义,亦显然以孙末楠的学说为中心。
派克的力荐和燕大师生对他基于孙末楠学说创立的人文区位学的理解,使得其中国同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孙末楠。不仅是前引的黄迪《派克与孙末楠》一文,1934年,吴景超再次撰文介绍孙末楠的治学方法。同年,黄迪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以《民俗学》一书为主要材料,专写孙末楠的社会学。在根据恺莱的文章再次介绍孙末楠的治学方法时,吴景超提到孙末楠的言必有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使用,还提到了《民俗学》这本书:“我们读过他那本民俗论的人,看到事实之后,还是事实,最后才来一两句结论,便没有不相信他所说的。他所以能驾驭这许多事实,便是因为他平日做割记之勤。”同时,吴景超也强调了孙末楠对史学方法的看重。
德型:黄迪的深研
1934年,黄迪的硕士毕业论文《孙末楠的社会学》,在燕大通过了答辩。在该文中,黄迪将custom翻译为“风俗”,将folkways翻译为“民风”。有鉴于孙末楠“社会的生活是造成民风和应用民风,社会的科学可以认为是研究民风的科学”的总体认知”,黄迪将民风、德型和制度并列在“社会秩序”一章之下。在“民风”一节中,黄迪对孙末楠《民俗学》一书中散见的关于“民俗”的描述性定义进行翻译之后”,总结道:
人生第一件事是生活,所谓生活就是满足需要。在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行为中间,是种种心理上的兴趣,因兴趣乃行为直接的动机。人类在满足需要的动作上,背后有兴趣(需要的化身)为其鞭策,面前有本能为其向导,而两旁则有快乐与痛苦的情感为其权衡。如像初生的动物,人类满足需要的步骤,总是先动作而后思想,所以结果往往是尝试而失败。但在这尝试与失败(或成功)的方法中,依快乐与痛苦的经验的教训,许多较好的满足需要的方法,便一一选择出来。人是生于团体中,满足需要是大家的事。各人的需要既相同,处境又一样,即使不相为谋,而结果,彼此满足需要的方法,也常会不谋而合,何况大家是相谋相济地分工合作。每个人可因其他各人的经验而得益。于是由互相刺激,互相交换,互相贡献,互相甄别等的作用,那些被选择的满足需要的方法,便为大家所一律采用,一律奉行。这时候它们就不只是一个人的习惯,它们已是许多人的习惯,这所谓许多人的习惯,便是民风。
在随后对于孙末楠初民社会民俗起源推测的功利性定义的辨析中,黄迪也指出了孙末楠四散的论述,同样强调竞争、暴力、强权与霸道、鬼怪、个体的社会性等之于民俗的重要性。 根据孙末楠对民俗的描述,黄迪进一步归纳总结出了孙末楠所阐释的民俗的特征:
(1)社会空间上的普遍性,它是所有社会制度、上层建筑的基石。
(2)在时间连续性上的传统性。
(3)对于个体与群体而言,身不由己、先天习得的无意识性。
(4)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域民俗的彼此关联、互相交织和牵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即民俗的一贯性。
(5)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势力,民俗的控制性。
此外,孙末楠也注意到了民俗的过程性,注意到了街车、电话等新的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的出现会促生新的民俗,注意到了民俗不同于有行政力量、司法等支撑的法律的控制力,而是具有柔性特征。
在孙末楠的民俗学体系中,德型(mores)是一个能够与民俗相提并论的重要概念,它来自民俗,却是一种特殊的民俗,甚或是一种高阶的民俗。因为权利与义务观念、社会福利的观念,最先与“怕鬼及来世观念相连着发展”,这一领域的民俗也就最先上升为德型,即德型是“关于社会福利的哲学及伦理结论”。孙末楠写道:
当民风中“真实”和“正当”的要素,发展为福利信条时,民风便升到另一层级。这时,它们便会产生种种推论,发展为新的形式,并伸张其影响人们和社会的积极势力。我们遂称之为德型。德型是那些民风,含有关于社会福利的哲学及伦理结论,而这种结论既为那些民风所启发,又随之而长成。
德型包括这些重要范畴:道德、禁忌、仪式、贞洁、检点、谦和、得体等社会准则,时髦、虚饰、嗜好,身份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及与这些现象同时存在的观念、信念、欲望、理想等。常识和直觉强化了德型的神圣性,从而使之对传承享有者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对于一个群体更具有持久性,犹如社会秩序甚或社会历程的磐石。对孙末楠而言,德型坚如磐石的僵硬性、保守性和顽固性一发展到极端,就会阻碍社会的演化,即当德型不能随着生活情势(life conditions)而变通时,革命或改良的爆发就有着某种必然性。
然而,孙末楠不看好革命,甚至也不看好改良,因为革命可能建设不足,破坏有余,而改良则完全可能是不顺应德型本身的演化而投机取巧。为此,他写道:
在高级文化的社会中,倘若生活情势改变了,而德型还是照样顽固,就会发生危机,这危机便由革命或改良来解决。在革命中,德型是总崩溃。在革命爆发后的那个时期,可以说没有德型。旧的已经破坏,新的尚未成立,社会生活仪式,大为扰乱,旧有禁忌不再发生作用。新禁忌不能随便创制或公布,须经过长时间,才能建立而为大家公认。
这导致断崖式的革命通常是短命的,而且常常为守旧势力“复辟”,或回归“过去”。在孙末楠看来,相较革命与改良,随着社会演化的德型,其变化的最佳方式是“混化”(Syneretism):不同文化在“友善”的接触过程中,通过日积月累的相互影响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同化。换言之,对社会的演化和德型的演化,孙末楠有一种为情势所趋的“自然而然”的理想演化观,有着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
重要的德型又会演进为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换言之,所有的制度都源自德型,更远的渊源则是民风。在孙末楠看来,财产、婚姻和宗教都是最基本的制度。由民风、德型加以观念(概念)和结构(间架)演化而来的制度,是理性的发明、计划的产物。因此,相对而言,在“自然”的德型中,信仰、情操、无意识、非自主等因素,在明定的制度那里则被理性、功利实际、有意识和自主所取代,且以武力和权力作为后盾。最终,作为一套或一串东西,民风、德型和制度就合成了一个社会的超级系统的总体,并表现为该民族独立的精神、特殊的品格或个性,这即孙末楠所言的“民族性”(ethos)。对此,黄迪有着清晰的梳理和总结。
但是,在孙末楠的表述体系中,德型又经常与民俗混用,很难分清。孙末楠曾经这样定义民俗:
民俗是满足一切兴趣正当的方法,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并存在于事实之中。它们弥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打猎、求偶、装扮、治病、敬神、待人接物、生子、出征、与会,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事情中,都有一种正确的方法。
同时,孙末楠也曾将德型定义为:
它们是一个社会中通行的,借以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做事方法,以及种种信仰、观念、规律和良好生活标准。这标准附属于那些方法中,并与之有来源关系。
难能可贵的是,在孙末楠众多关于民俗的比喻性描述中,黄迪机敏地捕捉到了孙末楠将德型视为空气的比喻。孙末楠写道:
The mores come down to us from the past.Each individual isborn into them as he is born into the atmosphere,and he does notreflect on them,or criticise them any more than a baby analyzes theamosphere before he begins to breathe it.
黄迪的翻译如下:
德型是从过去传下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之呱呱坠地,而生于其中,如同他生于空气中一样。他之不把德型作为思想对象,或批评它们,也正如他在未呼吸之前,不去分析空气一样。
两年后,黄迪还曾这样翻译过这段话:
德型是过去的时代传下给我们的。每个人生于其中,如像生在空气中一样。他不会以德型为思考或批评的对象,正如一个婴儿在没有开始呼吸之前,不会分析空气一样。每个人在还不能够对德型加以推理的时候,都已经接受它们的影响,且为它们所造成。
稍晚,在对文化的系统诠释中,黄迪再次引用孙末楠的《民俗学》时,遵从老师吴文藻,将Mores翻译为德仪,并如同李安宅一样强调文化的民风、德仪和制度三者之间的演进关系。黄迪写道:
他以为无论古代或现代,只要是在一般民众生活的范围内,主要部分的文化总是先成为“民风”(Folkways),其次进为“德仪”(Mores),最后发展为“制度”(Institutions)。
其所谓民风就是指社会的风俗——满足社会需要的方法和产品。民风的重要程度不同,有的民风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所系,不容任何人违反或破坏。此种为强有力的情操和信念所维护的民风,便已成为德仪,德仪中又有比较重要的——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的,其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更为理性所认识和特设的机关所执行,由是便成为制度。所以在这个观点之下,一社会的文化可以视为许多制度、德仪及民风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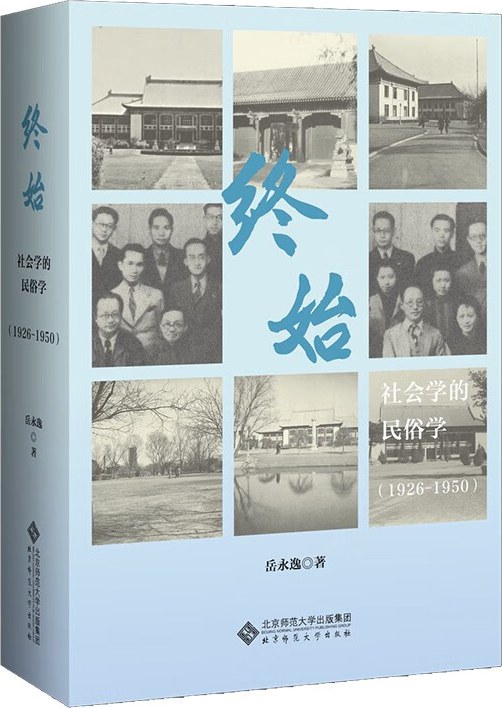
(本文摘自岳永逸著《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