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民族志学者必须让异质事物给人熟悉感,同时又要保持其特异性
【编者按】
为什么两位研究兴趣不同的人类学家要写一本《民族志阅读指南》呢?因为通常没有人教读者如何阅读民族志,告诉他们人类学家是如何写作的,因此,帕洛玛·盖伊·布拉斯科和胡安·瓦德尔希望传递一种开放式对话的感觉,在提供分析文本技巧的同时,引导人们一探人类学知识的特质,并培养出读者自己的人类学想象力。本文摘编自该书《叙述即时经验》一章,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1974年,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和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回到菲律宾。四年前,他们曾在那里对居住在森林里的耕种者兼猎头族伊隆戈人(Ilongot)进行田野调查。他们的伊隆戈朋友非常喜欢听这对夫妇在20世纪60年代末录制的猎头歌曲磁带。然而:
我刚播放磁带没多久,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之一、也是那盘旧录音带的坚决维护者,莫森(Insan),突然厉声要求我关掉它。我按他的要求做的时候,没有人向我解释——我发现自己困惑、烦恼、不知所措甚至生气……那天晚些时候,客人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以及我们认为是真正的朋友和“亲人”的人。我发现我一整天都带着愤怒的受伤感——因此我要求他们对他的唐突命令做出解释……我看见莫森的眼睛是红的。然后,罗纳托的伊隆戈“兄弟”图克保(Tukbaw)打破了脆弱的沉默,说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他告诉我们,当人们知道永远不会有另一次猎头庆祝活动时,听以前的录音就会很伤人。用他的话说:“这首歌牵动着我们,拉扯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想起了死去的叔叔。”又说:“如果我接受了上帝,就不会这样了,但我心里还是一个伊隆戈人;我一听到这首歌就会心痛,因为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这群不经世事的小伙子,而再也不会有机会带他们完成猎头。”然后,图克保的妻子瓦加特(Wagat)通过她的眼睛告诉我,我所有的问题都让她感到痛苦,她说:“别说了,这还不够吗?我只是一个女人,心里都无法忍受这种感觉了!”(M. Rosaldo,1980:33)
“愤怒的受伤感”、“心会痛”、“无法忍受”……罗萨尔多的描述,以及她的整本书,都围绕着我们每个人最直接的情绪和感受。不难想象,这两位人类学家面对他们的朋友/报道人时尴尬的样子,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的位置以及他们做了什么激怒了那些他们认为是“亲人”的人。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莫森、瓦加特、图克保他们的痛苦。不太容易理解的是这些伊隆戈人为猎头活动消亡而感到的遗憾。的确,这一小段话浓缩了人类学翻译和理解的核心——熟悉与陌生之间的冲突,这种张力被文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描述为一个悖论。他告诉我们,民族志学者“必须让异质事物给人熟悉感,同时又要保持其特异性”(1986:52);他“必须弄懂异质事物”(同上),同时又不损害它的陌生感。根据克拉潘扎诺的说法,要达到这一目的,人类学家既要通过民族志描述强调报道人与我们是多么不同,还要提供解释或分析,使自己和读者都能理解这些行为。举个例子,在上面这段节选后的几页中,罗萨尔多向我们展示了伊隆戈人对于猎头活动消亡的悲伤,并借助人类学中“人”、“自我”和“社会”的概念来解释这种悲伤。
罗萨尔多的叙述和克拉潘扎诺的见解指出了熟悉感在民族志写作中所起的中心而模糊的作用。熟悉感的概念包含了亲近和理解:它既代表个人关系的亲近,也代表对某事或某人的彻底了解。在人类学中,这种联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因为我们在那里。但是,尽管熟悉和亲近是所有民族志学知识的基础,它们并不意味着完全透明、完全理解我们试图理解并为他人解释的人。因此,罗萨尔多也谈到了她无法理解她的“亲人”的情感和动机,以及这种不解如何促使她更深入地挖掘和质疑自己关于伊隆戈人和人类学的假设,以及“了解他人”的真正含义。事实上,就像克拉潘扎诺指出的那样,人类学中关于亲近关系的叙述强调的往往不仅仅是作者/读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还有我们了解和代表他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在书中结语部分,罗萨尔多告诉我们“解读从来不能真正‘进入’当地人的‘大脑’”(1980:233)。
尽管有各种这样的预警和保留意见,仍然可以说,对熟悉感和亲密关系的描述是民族志写作的支柱。民族志学者经常像上面罗萨尔多那样,描写他们自己与一群人亲密互动的经历,以及这种亲密带来的深入了解。有些时候,作者本人并没有出现在叙述中,即便如此,她描绘日常生活细节的方式仍然能清楚地展示她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这种亲密关系被视为可以验证民族志学的描述和解释。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详细讨论,民族志作为一种文体和一种认识论,所依赖的是这样的假设:“身临其境”(Geertz,1988)使得人类学家能够将自己的经验和回忆转化为对特定社会世界的分析性描述。
在这一章中,我们把熟悉和亲密(民族志学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以及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归入即时性这个概念,也就是直接、即时的特点或状态,与某事或某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联系。熟悉和亲密意味着在他人的陪伴下感到自在、享受欢乐、有同理心、能够理解,而即时性还包含着不安、困惑、烦恼、怨恨、无知和冲突。所以,当罗萨尔多向我们表露她的困惑时(“他们在说什么?我再一次感到痛心,我对他们所说的话的肤浅理解,与他们最简单的语句所承载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她所叙述的就是即时感受。
即时的叙述在民族志写作中随处可见,包括如上文的作者自我叙述和作者将自己从文本中移除的其他叙述,对日常生活、周期性仪式和一次性事件的描述,日记或田野笔记,与报道人或报道人之间的谈话记录,以及生平事迹。尽管文体手法五花八门,导向的理论观点也各种各样,但这些叙述都关注人类存在的本质,并密切注意社会生活描述的细节。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所讨论的,在这些不同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探索人类关系中特殊、偶然的东西与普遍、共有的东西之间,以及一次性事件与社会文化生活模式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讨论并且将在第五章中继续强调的,这种关注是人类学的核心主题之一,正是这些主题将人类学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怀疑、认识和表现世界的模式。
的确,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民族志写作中对即时经验的叙述,是建立在对生活世界进行有人类学意义的描述的意愿之上的。此外,这些叙述被定位在人类学辩论的特定领域以及更广泛的学科历史之中。虽然克拉潘扎诺认为这些描述为民族志学者进行解释和抽象提供了出发点,但我们认为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不优先于对方或发生在对方之前。也就是说,通过对即时经验的描述,作者既试图传达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感受,又试图解决关于文化和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来自于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所关心的问题,也来自于人类学的发展轨迹。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体验是由他们的学科知识所塑造的。若昂·德·皮纳–卡布拉尔(João de Pina-Cabral)认为,民族志学者将他在田野中所观察到的“与他所积累的学科知识相比较,而不是与他联系最密切的社会群体的世界观相比较”(1992:6)。
只要对即时经验的叙述是由人类学问题和研究方法所产生和形成的,它们就不是“即时的”,而是经由这些以及其他问题所“调和”的。可以说,因为这些叙述是由学科所建构的,而且实际上完全是为了阐明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观点,它们将读者与它们声称要描述的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我们甚至有理由将这些叙述视为烟幕,它将作者和读者都与经验分隔开来。这些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是作者的经历和回忆、她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以及她自己的学科定位之间的交汇点。当然,读者也会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回忆,以及人类学的直觉、立场和观点来看待这些叙述。
下面我们将从辨别两种最普遍的叙述即时经验的方式开始,关注这两种叙述在特定的民族志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作者叙述即时经验的方式如何体现她对人类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的理解,也就是说,即时经验是如何被特定作者关于人类学知识本质的观点所调和的。有些民族志学者利用即时的叙述来支持关于社会和文化的实证主义和/或规范性解释,而另一些学者则专注于民族志解释的局部性和暂时性。本章最后,我们将探讨即时经验在构建人类学论证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详细检视民族志描述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层次与交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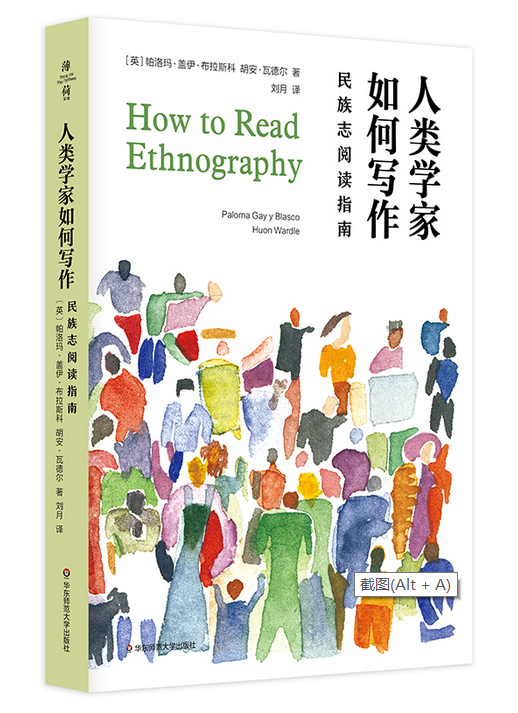
《人类学家如何写作:民族志阅读指南》,[英]帕洛玛·盖伊·布拉斯科、胡安·瓦德尔著,刘月译,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