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女儿:拮据的东亚家庭,母亲的礼物我等了二十年丨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丨散步厅
指导老师丨雷伟
编辑丨柳逸

本文配图均来自台剧《俗女养成记》
旅行的路上,我收到妈妈给我发来的信息,是几张鸡块薯条和表妹的照片,她正跟着小姨一家自驾去上海玩。妈妈说她们正在外滩吃点心,休息一下。 “我给你妹妹买了礼物。”
“「大拇指」是什么呀。”聊天框里正在输入。
对面发来消息,“给你也买了一个玩具。”
发来的短短一行字突然让我有些无所适从,紧接着而来的是紧张,不可思议。我删掉了对话框里还没有发送的信息。
“是妹妹要给我买的吗。”
“我和你小姨给你们两个都买了一份。”
我盯着手机屏幕,思绪已经飘向远方。我料想过很多种妈妈会回复的消息,她可能会说这是什么样的玩具;可能会说是妹妹自己喜欢,也想给我买一份;可能是随手在微信里面拍的一张失焦的16:9的照片,而事实却是我从来没有料想到的那一种。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仔细回想,我确定这是我第一次从母亲那里收到“正经”的礼物。记忆像一个柔软的白面团,不断地在时间里被揉捏和重塑,褶皱被融合吞噬,直到被新的痕迹取代;童年沉重迫切的幻想就这样,在母女俩各自的旅行途中轻飘飘然地发生在了电子屏幕里,就像在揉好的面粉团里面扯出来一根头发丝,划出一道锋利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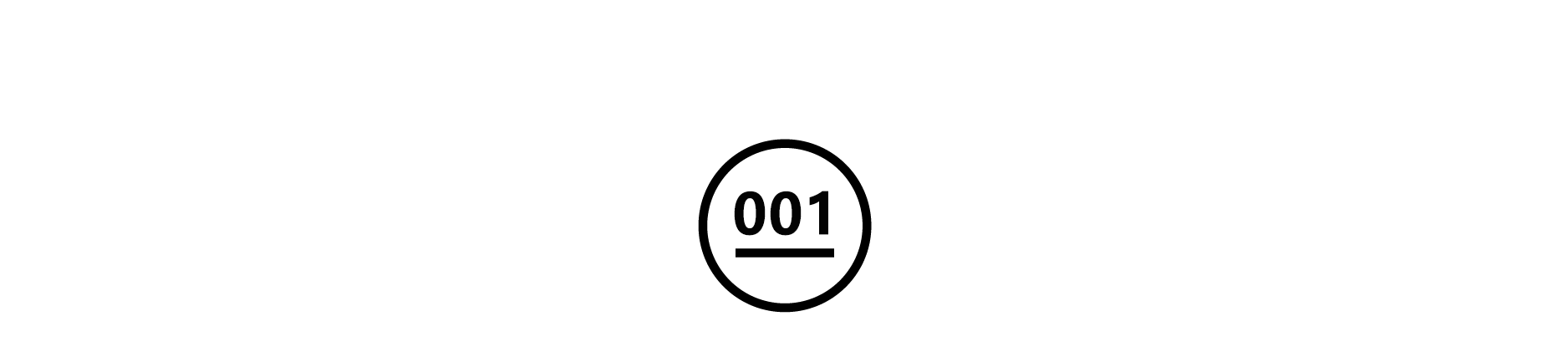
车窗外白雪皑皑,大巴车开在公路上,公路两边是连续的电线杆,我抬头盯上了那些接连不断的平行黑色电线,思绪飘回到了小学生用来写周记的蜗牛笔记本。
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老师在一个晴朗的周日午后宣布下一周学校里要举行作文比赛,那一周的周记会变成命题作文,并且成为小学生们能否参赛的评判标准。我记得很清楚——作文的标题是《礼物》,我凭借那一篇周记赢得了代表我们班参加比赛的资格。老师在课上念了我的作文,给我评语是“有很多细节,情感丰富,充满了感染力”。但事实却是,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礼物,我知道那是自己胡扯的。但是孩子们的周记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别把那些小学生在周记里写的东西都信以为真,我宁可相信孩子们更多时候是通过想象和世界发生交流,而不是感知力。我只是凭借着超凡的想象力拿到了参赛资格,我给我强烈的幻想补充了足够多的细节,希望自己的人生真的经历过收到礼物的那一天。

事情过去很久,我想那篇周记的灵感最初就来自于三年级六一儿童节前的某一天,妈妈带着我上市场的经历。也许妈妈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兴许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只有我清楚地记得,明天是儿童节,去学校里但是不用上课。早十年前那个时候,小区楼下的小商品市场上还很热闹,有很多卖儿童服装的小商贩在露天摆摊。市场上各色的商品在母亲的眼睛里面是按照逻辑摆放好的,她看不见那些印着卡通图案的氢气球,也看不见露天衣架下面挂着的时兴雪纺衬衫;她牵着我的手,寻思着怎么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于一个即将意识到自己是女人的孩子来说,挂在露天衣架上的衣服就成了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天色已晚,我的眼睛落在了一件淡黄色棉质连衣裙上面,荷叶摆,泡泡袖。我一眼就看中了它,无论被妈妈牵到哪里我都会朝那个方向瞥去。但妈妈能熟练地应对这样的暗示,她只装不知道,直到我开口。
“妈妈,我想去看看裙子。”小小年纪我已经学会了避重就轻、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欲望。
妈妈这时候就会皱起眉头,往童装摊位走去。
然后就是我假装在衣架前面兜圈子,迂回地走到早就选中的裙子面前,再看一眼妈妈。母亲像是审判似的摸了摸那条裙子,这时候的孩子往往最胆战心惊。她抬头问老板多少钱。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套路戏码,母亲应该陪我演过很多次。

具体是什么价格呢?我也忘记了,反正老板说的不是一个能让母亲满意的数字。然后母亲这边就会出价,她说这样的料子就应该值这样的价格,也许是出自她年轻时在纺织厂工作留下的经验;然而这套经验在买衣服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套科学又固执的衡量标准。
老板不同意,为自己觉得不值。母亲也会开始她的表演,转过头来对我说不买了,走。小时候的我分不清这到底是是对老板的威胁还是对我的通牒,我只是害怕事情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毕竟母亲给自己买衣服的时候也上演过一走了之什么也没买到的情节,我不确定这样的威胁是否有用,但也确实发生过痛心疾首的服装店老板在顾客跨出店门的那一刻把他们喊回来的情况。
但明天是儿童节,并且我想要穿新裙子的。母亲拉着我往家里走,我不是那种会在买卖现场撒泼打滚的孩子,我回到家里,才会发起一场需要软磨硬泡的恶战。“明天是儿童节,你就当是给我的儿童节礼物嘛。”这是我最后祈求的筹码。好吧,母亲并不多少情愿地又带我下了楼,以一个折衷的价格买下了那件裙子。类似的周旋发生过很多次,一般都以母亲的妥协告终,但那些似乎从来都不是礼物,是被勉强满足的、需要借口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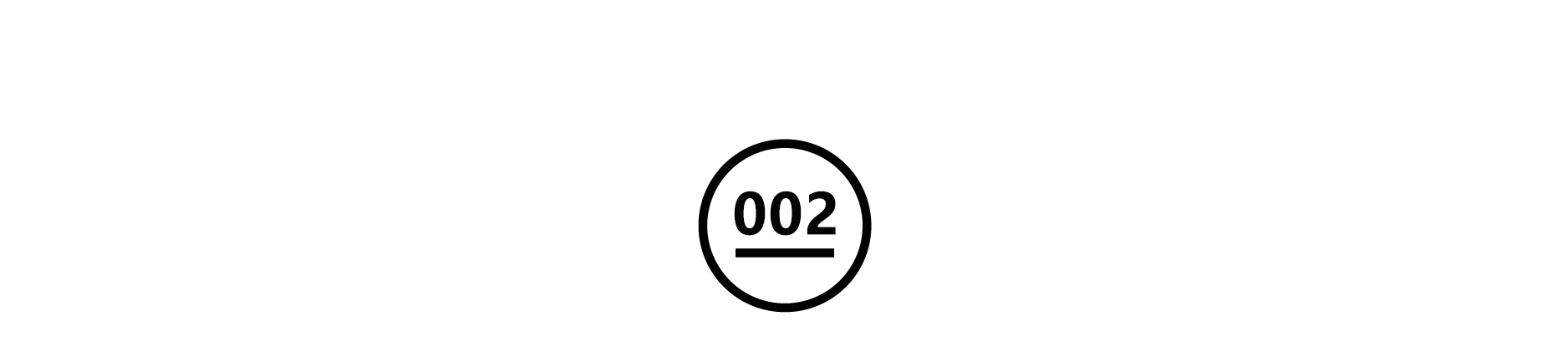
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我身上,家人之间的诉求表达在我的家庭里似乎从来不是直接的。父亲需要更换新的皮鞋的时候,他会把我叫过去,让我蹲下来看他旧皮鞋上的磨损痕迹,然而年幼的我并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爸爸会说自己工作太辛苦了,去外面谈生意也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爷爷每个月总有一段时间需要在晚饭结束之后“报菜名”,讲述菜市场上又有什么蔬菜涨价了。
然而这些场景里,母亲无一例外地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一言不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场景似乎还有些幽默。父亲需要放下身段在孩子面前讲述自己的“功劳”来换取一双两百元的皮鞋,难道蔬菜不涨价妈妈就会拒绝给爷爷发生活费了吗?不是的,都不需要,只是因为生活太拮据了,所有的开支都需一场理由充分的答辩和谈判。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管理家庭的财务开支不是她可以行使的权力,而只是她的劳动、一种义务,她并不会从中受益。母亲把这一任务扛了起来,把家庭的每一分钱利用好是她的责任,这份工作不仅不会给她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反而给她制造了更多的焦虑和愧疚,她也因此把自己的物欲降到最低。我猜想,面对这样一个对自己都节俭到近乎苛刻的女人,所有家庭成员在提起各自的需求时不作一番铺陈,会感到格外过意不去吧。

小学的时候,我去好朋友家里一起玩台式电脑上的双人小游戏,她领我走进她的房间,介绍每一样陈设的来源。“这个存钱罐是我爸爸出差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礼物。”这一句话包含了太多未知之物,让我有些发懵。那个存钱罐很新奇,把硬币放在上面,一只陶瓷的猫手就会伸出来把硬币揽进去。从此以后,那些能收到父母出差带回来礼物的孩子就成了让我嫉妒的对象,这可能也让我以为出差和礼物之间似乎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礼物,是因为我的母亲父亲从不出差。
记忆会在一次次的回想里被重塑成我们想要的模样,比如在那篇名为《礼物》的周记里,我把那条淡黄色的连衣裙包装成了一个惊喜,在我醒来的时候出现在了我的床头柜上;把母亲对我强烈暗示的熟视无睹变成了她对我想要的东西的处处留心。可能我的内心是想写她出差回来,正好赶上了儿童节,给我买了一条牌子货连衣裙。但那时候,我从来不知道需要出差的是什么样的职业,父母出差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穿着高跟鞋打着领带需要出差的女人男人,他们似乎只出现在电视剧里面,他们的工作好像就是去出差,出差就能赚钱。
那次作文比赛,我没有取得什么瞩目的成绩,也记不清现场的命题是什么了,只记得自己满头大汗地想象着,但这一次胡编的发挥并不如意,太过贫瘠的经历支撑不起动人心魄的想象。
父母年轻的时候一穷二白,我想他们也不曾收到过礼物。过分的节俭是贫穷给母亲留下的恶习,钱是用来过生活的,那些飘在空中的彩色气球和蕾丝边的无袖衬衫未免显得太过骄奢淫逸。

母亲愿意跟着小姨一家出去玩我是很开心的,其实日子很早就好过起来了,父母找到了赚钱的办法,只是贫穷的日子太过深刻,母亲年纪大了,像一块硬石膏,要花很多时间去磨平从前的划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早些年母亲从来不要求出去旅行,她总是会嫌路途太长、她还有晕车的毛病,何况她还要守着家里小小的作坊。直到最近,母亲才像上瘾一样开始憧憬远方,想离开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这块小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知道,母亲从前并不对那些未知的地方和旅途感到恐惧,也不是嫌弃车马劳累,而是想省下一个人的旅费。那些迟迟没有被满足的欲望会在某个人生节点突然爆发,是我的那篇胡诌的《礼物》,是母亲对旅行突如其来的渴望。如今,母亲可以熟练地在旅程出发半个钟头前在嘴里含上一片晕车药,并且承认那个小小的家庭作坊离开她几天也不会陷入混乱和无序。在那之前,她的生活就是她的两个孩子和维持生活本身,自那之后,母亲的世界里面有了她自己。
窗外的黑色电线在这时候消失了,车上的旅客睡得很沉。我打开微信,对话停留在“我给你买了礼物”,妈妈没有说更多了,我还不知道礼物是什么呢。此刻我幼稚地幻想自己是一个十二三岁,在家里等着母亲下班回家,给自己带神秘礼物的小女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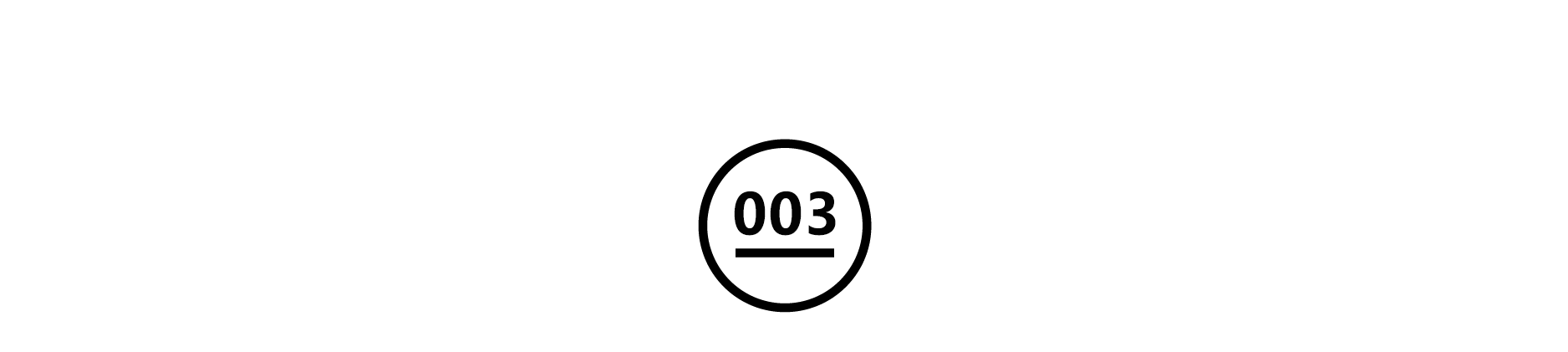
母亲一车人比我们先回到家里,妈妈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她买的两个“玩具”——原来是两个泡泡玛特的盲盒,她说她特地叮嘱妹妹不要拆我的,等我回来拆。母亲说她是在外滩边上的商店买的,这些小玩偶都要七十几块一个呢。这让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她花了一百五十块钱买了“毫无用处”的小摆件。按照她那个兴奋的样子,看来我不得不以同样的兴奋和惊喜来回应她了。盲盒里拆出了粉红色玩偶和宝可梦精灵,她不停地说真是太可爱了,不过她还是觉得我会更喜欢粉红色的那一个,那个是她给我挑的,真是太可爱了。
妈妈甚至还学会了“惊喜”那一套,可不是我自吹自擂,这可能是跟我学的吧。我很早就开始在母亲生日时给她送礼物,但是依照母亲节俭的性格来看,收到那些花哨不实用的东西对她而言反而是一种负担,她会心疼钱花在了不应该的地方,于是我总是事先询问她的意见,买的礼物往往也是妈妈手头上正在用的化妆品,她说她用完了就可以用我买的。但去年,我决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

我自以为是地用外卖软件下单了一大捧玫瑰花,算准了母亲下班回来的时间,就选在那个时候送上门。我的内心十分忐忑,不知道她会对这样只能存留几天的礼物作何感想,她会责备我吗?晚上七点半,我打开朋友圈,那个红色的小圆点旁边居然显示了妈妈的头像。“受到人生中第一束玫瑰花,有点小激动。”妈妈配了两张自己手捧玫瑰花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藏青色的圆领卫衣,她说过年轻姑娘就喜欢穿这些,她也赶赶时髦;她面色红润,应该是开了一瓶红酒;玫瑰花上面有我写的贺卡。
这是母亲为数不多的朋友圈,再往前翻阅,还有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姐姐的驾照。母亲并不擅长“现代科技”,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没有自己的手机,按键手机时代,她给奶奶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黑手机,她说能用父亲的手机联系到她的两个孩子。她也因此错过了智能手机时代,她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我小姨淘汰下来的iphone5,小姨以一种强硬的语气让她收下,“哪有人到现在还不用手机的!”母亲这才开始被推进了电子时代浪潮。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用手机打字、用微信发消息,很多必备的技能是在两个女儿不耐烦的教导下学会的;她看到别人发的朋友圈,总是羡慕他们的文采飞扬、生活丰富,而自己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上了大学之后知道了如何形容母亲——母亲就是“数字难民”。她生日那一天,她在视频通话里告诉我,那天的朋友圈是她让姐姐帮忙拍的照片,她自己写的,有很多人给她点赞。“谢谢大家的点赞”,母亲也留下了朋友圈的第一条评论,是给自己的。
母亲叮嘱我把那两个玩偶放在我的书架上,正好可以和我原来自己买的那些放在一起,放在更显眼的位置——哦,原来你一直都知道啊。
亲眼看着我把它们妥当安置之后,母亲要和我讲述她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她掏出了手机,仍然在用密码解锁,我问她为什么不用面容解锁,她说自己不信任这个技术。但是无论输入多少次密码,母亲对那十个数字按键仍然感到陌生,需要一个一个找到她需要的数字,按得很慢,我耐心地等待。她说自己最喜欢的是上海水族馆,她打开手机相册,一整面都是蓝色海水,和奇形怪状的鱼的照片。我走了神,并没有仔细听她在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兴奋的脸,忘掉了淡黄色的连衣裙,觉得这一刻比什么都要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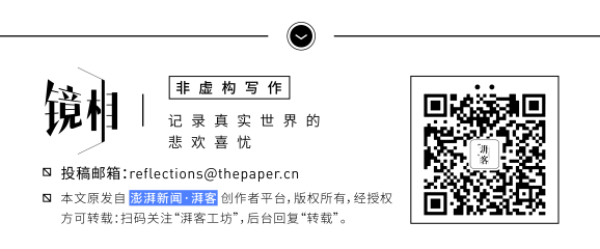
目前镜相栏目除定期发布的主题征稿活动外,也长期接受非虚构作品投稿。关于稿件,可以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有群像意义的个体故事,或反映社会现象和症候的作品等。总之,我们希望所有值得讲述的好故事都得到应有的记录。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