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炼油厂三代人走过的“大江大河”|镜相
本文由镜相 X 上海大学文学院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写 | 郑沁辰
指导老师 | 吕永林
编辑 | 吴筱慧
东海边,矗立着一片三万余亩的钢铁森林。各色炼油塔罐织着错杂的管道爬架,在不同塔层里炼着航空煤油、汽油、柴油……最高的烟囱红白相间,像海上的灯塔。这些鳞次栉比的炼油设备,从高处看,像这片大地上丰收的庄稼。
白天,烟囱向天造云;夜晚,塔罐缀满明亮的白色灯盏,辉映成一片恢弘的水晶城。那是我至今所见的任何一座特大都市都不能比拟的夜景,在东海之上接住一片银河,昼夜不息。
再向内去,好像有一座小城挨着,居民楼、菜场、公园、文化宫、医院、学校……这是镇海炼化的生活区。一条河贯穿而过。人们靠海、沿河,活成一条小船。国企改制前,这里住着一个小社会。连着厂区、生活区,炼化人都叫它:炼油厂。
我和我的祖辈、父辈就从炼油厂走出来。有人说,刻在石化人基因里的是一种“轮回”,像一张网,兜住了每个人。炼化人和炼油厂共同织着这张网,将炼油厂的历史印记与炼化人的生长痕迹一道织进几十年的纹理。

晨曦中的镇海炼化(图源网络)

“先生产,后生活”
1974年底,爷爷奶奶带着三个儿子和全部家当,从温州坐着卡车来到镇海。卡车在盘山路和泥巴石子路间穿梭。半路上发动机过热,车趴在了路边。司机用铁桶从农田里打来水降温,才又徐徐上路了。这桶水,舀来了炼油厂的第一把火。
1975年,镇海炼化在一片芦苇丛和棉花地的滩涂上打下第一根桩。除了爷爷奶奶的温州化工厂,同来的还有各地石化企业的工人:兰州炼化、湖南长林化工厂、衢州化工厂……每厂调三四十人,在海涂上组起一个大的新家。从那时起,炼化人开始织着一种没有血缘却血脉相通的亲情。
从蜿蜒的小土路走,经过小卖部、几个粪缸和摞着的农家肥,一户户的黑瓦青墙房,就是第一批工人落脚的俞范村和后施村。爷爷奶奶家租在村大队一间老会计室。第一年冬天下大雪,房里下小雪,大家连夜赶制棉被棉鞋。
第二批工人住在海涂,叫“七千平”。“七千平”由红砖砌起,盖上棚子,就算临时家属房了,足绵延七千平米。工人们自己挖井,有时候靠“天落水”。第一个临时的“厂子弟学校”就搭在那,竹编的顶,裸露的红砖墙和地面,架子是毛竹筒。

镇海炼化生活区一角
奶奶工作的设计院最早也在那里,是营房样的尖顶屋子。不仅如此,炼油厂的其他临时办公点,也纷纷就着棉场留下的旧工棚运转起来。在这样的“凑合”中,炼油厂的第一代开始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厂岁月。
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支持他们的首先是理想与热血。奶奶毕业于浙大建筑系,早年大学生分配难,只能“随便塞塞”,奶奶就被“塞”到了温州化工厂。温化撑不下奶奶的理想,“学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在温化一点也没用到,很失望。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奶奶语气平缓又如数家珍,“到了炼油厂以后,的确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设计了好几栋房子。”设计院方案竞赛,选中了奶奶的那套,我小时候就住在奶奶设计的房子里,每间都有朝南的窗。我问奶奶,算是在炼油厂实现理想了吗?奶奶笑答:“我的梦想还要高,不可能实现的。但就这样为止了。”
建新厂,也是第一批工人们理想中的一部分,“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有盼头。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就靠自己的一腔热血,带着老厂作风和石化精神,心很齐,关系也很亲密。”
有年元旦前夕,工人们组织了一场颇具仪式感的活动:零点起,大家不沾枕头,都相约着上厂里干活去了。那代人是带着心中的保尔·柯察金来的,他们都想成为自己平凡生命中的英雄。“那时候一心为了把炼油厂搞起来,不是幸福在物质上,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苦中有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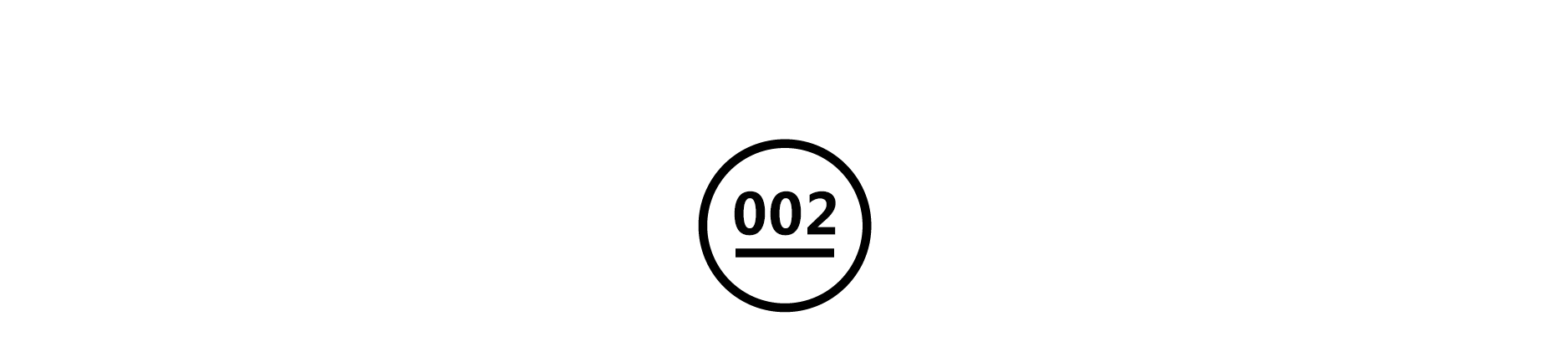
“调回家,总是好”
支持他们的另一副骨架,是团聚与回家。早年祖辈一代的夫妻,由于工作分配,多是分隔两地。爷爷奶奶曾分居两地十年,炼油厂这次面向全国的召唤,让两人看到了团聚的曙光。
“调到一起觉得很安逸,生活好像从此再也没有顾虑了。父母都在宁波,等于回家了”,奶奶这样说。同样如此的,还有外公外婆。
外公在省水电局,跟着建设走,宁波奉化、台州天台县、武义牛头山,就这样在浙江各地飘游。夫妻一年聚一回,开销又大。
1982年,38岁的外公抓住炼油厂新建变电站的档口,辗转调至地方上的五乡泵站,虽不在总厂,“跟‘老百姓’比起来,条件是很好的了。”1984年,外公到了总厂电气车间,成为炼油厂筹建鄞县白渡泵站的储备人员。
外婆是按职工家属调来的。来之前,外婆在慈溪公社办的塑料厂工作,“那时候业务都靠自己,动不动发不出工资。路道粗的人有,路道不粗就没有,我们经常失业。”外婆辞职去了炼油厂,慈溪的人们认为,外婆是去了“城里”,能穿上漂亮的工作服,过上更好的日子。

外婆家的窗口
外婆初来乍到,没有正式工作,就被安排在机动组,同来的还有十几个职工家属。外婆形容机动组的工作“像打游击,像救火兵”。在机动组几个月,外婆种过花、拔过草、冷却过设备、植过树。偌大的厂区,外婆不认路,也不会骑车,就坐在别人后座,跟着任务分配,今天去几号油库,明天又是几号……
“我那时候经常坐在铁路边上讲大道,一批从一个地方来的家属,凑起来聊得很开心,听着火车隆隆来了……”他们就这样盼着,等着,不止团聚,还翘首于那份属于“炼油厂双职工”的“荣光”,刻进他们命运中新的高位。后来,外婆分到了厂技校门卫的工作,一直干到退休。那时,从技校毕业的厂子弟,都将四平八稳地进入炼油厂工作。
那是外婆一生最开心的日子,工作稳定离家近,三五同事没事聚拢,一起盼着要领工资、发工作服了。看着周围的三职工,四职工,外婆想自己以后也会有的,“每天想着什么时候女儿读出技校就能分配工作了,一天天过得很快。没有心思,又自由。来了炼油厂,就像吃了定心丸。”
“炼油厂是老家,父母姐妹都在,调回来就是要回家,夫妻团圆。那时候不管什么单位,调回家,总是好。”外公回想起来,还有喜悦的滋味。
那些年,厂里的生产生活蒸蒸日上:工人们搬进了崭新厂区和家属楼;棉田上被征了地的农民,都成了炼油厂的后勤职工,有的供应果蔬副食,有的当了食堂师傅;职工家属也被安顿到各个岗位。炼油厂总领着包括生产和生活在内的各个子公司。

2023年 拆除的老文化宫
生活区也渐有一个小城的样貌,从幼儿园到技校、集电视台和活动场于一身的文化宫、用菜卡就能买到实惠菜品的菜场、厂里的影院、百货商店……生活区的福利分房按着职称和工龄分配;双职工和带孩子的单职工,不花一分钱,就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每年深秋起,厂里的生产余热给人们免费供应南方少有的特殊标准——暖气。北边有片海涂,厂里用来自种西瓜、蔬菜、养鱼,分给职工。
在外婆的记忆中,炼油厂最兴旺的时候,烫头只用券,房子不要钱,饭菜一直有,子女有归宿。外公记得有一年,厂里给每位工人发了一笔666元的奖金,一举轰动全市。人们说孙玉宝是一位“很厉害”的厂长,凝聚着万众一心,把收益最大地返给职工,他是带着“大庆精神”来的。在他们言语的流光中,孙厂长像一条海岸线,托起东海上的朝阳,照着彼时灿烂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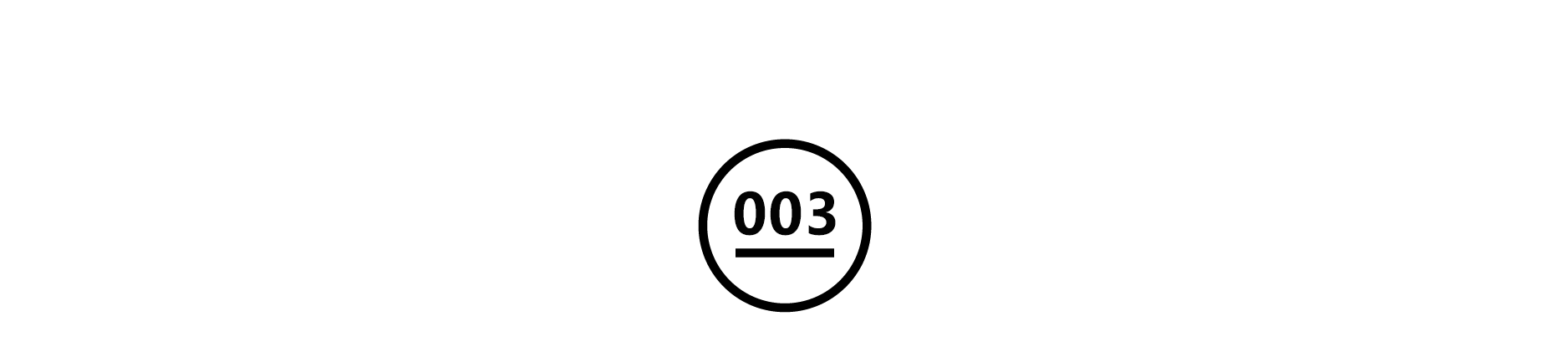
被按下了的那股“劲”
有人说,石化人的职业生涯不是写在自己身上,而是在父辈的基因里。我的父辈一代,或多或少也是如此;而属于第二代人的“首个家园”,也冥冥中被炼油厂所选择。一张由血缘“传承”的炼化网,开始向下织开来。
八十年代,随着炼油厂创业初期的成功,第二代厂子弟们不仅生活在那片宽宏地允许所有炼化人不用为“过日子”而操心的天地;也在这曾经承载过第一代人理想的地方,成了舞台的下一代主角。
从技校入学到离开炼油厂,这十余年,爸爸找到了他人生中“最闪亮的日子”。爸爸是炼油厂高中技校名列前茅的尖子生,“那时候有找回自己的感觉。所有专业课像有天赋一样,不需要花力气,听老师讲完,就能学以致用了。”毕业时,爸爸以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进入炼油厂,成为一名仪表工。

镇海炼化大门
爸爸的仪表维护工作,是胆大心细的活,他经历过各种现场:高温高压、石油刺鼻,目睹班组同事在身旁中毒倒下。冬天,西北风呼呼吹,爸爸穿着工作棉袄,爬到炼油塔上排除故障;遇上细高的“火炬塔”,好几十米,人就在半空和塔一起晃。
爸爸曾和同事们检修完毕爬下半程,旁边炉子的气体瞬间爆炸,响声震彻厂区,炸飞的炉砖簌簌地往安全帽上落。即便如此,爸爸近乎日夜“镇守”在他的岗位以防任何突发状况。
炼油厂每每开发出新装置,会让老师傅带着年轻人去学习。爸爸工作第二年就参加了最先进装置的培训。他进步很快,不久便成了岗长,带了好几个徒弟,“后来厂里又有新的装置出来,那时候我就成了‘老师傅’,带着年轻人去,虽然我也只有三十岁。”
跟爸爸相比,妈妈的核心词则是“稳”。但过分的平稳,从这代开始,正悄然滋生出裂痕。
和大部分炼化父母一样,外公外婆也希望子女技校毕业后得个炼油厂的稳定工作。但妈妈曾想找一条特立独行的路。
“当时所有人都在考技校,但我想考高中,我觉得应该走走别人没走的路”。小时候,妈妈就不断萌生与众不同的想法。她说,她要抓坏人,外婆嗔怪道:“公安局都是男人做的,你一个女人家杀气腾腾的干什么。”
不出所料,妈妈不想当工人的想法,也在中考前被父母熄灭了。在他们心中,炼油厂稳稳的庇护,象征永远安定的生活;而不随大势的选择,意味着要面对风浪更大的世界,让人“心不定”。
妈妈上了技校,学的是钳工,到头来还是做了“男人的活”:每天技术操练、敲榔头、打磨、锯锯子。“钳工是男的干的活,女的进去要开后门,因为出来不用倒班。”从此,妈妈唯一的盼头就是毕业后在厂里上白班的日子。
1991年,19岁的妈妈进了炼油厂机修车间。说是钳工,女的上了岗,就是记笔记、擦桌子类的工作,“有时候去现场,也就是给人跑跑腿、打打下手,弄点柴油、搬搬设备。有些仪器设备拿不动,人家就不用你拿了。”
妈妈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隐在所有的自行车和工作服中。外婆回忆起大家骑车上班时的场景,“淡蓝的工作服,连声音都没有,看过去像海浪一样的一片,让我在里面找你妈妈,我找不到。”
有时候,妈妈觉得一天时间很漫长,因为没事做,连天也聊完了,于是,她就盼着下班换下工作服,穿好看的衣服,看看电影、逛逛街;直到我出生,妈妈的一天里又有了新的盼头……这段过分平淡的生活中始终埋着的,是妈妈从来都被按下了的那股劲。

厂子弟的后代不再是厂子弟
1992年,市场经济的风吹向全国,大批国有企业陆续加入上市大潮。两年后,镇海炼化也上市香港,成为股份制公司,企业的重心渐渐更集中向生产。也就是那段时间起,人们感到炼油厂在悄然变化。
当爸爸和很多人一样,还拿着厂里稳定收入的时候,早年肄业离开炼油厂的朋友已赶上了深圳卖电脑的风口,他的随身包里总有厚厚的百元钞票。外面的世界带着无穷的机遇和宝库,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将炼油厂从曾经那个万众瞩目的“神坛”卷了下来。像一个被从外敲破了壳的鸡蛋,一些刺和光,都透过裂缝,刺着第二代炼化人。
伯伯是处里第二个走出炼油厂的。
他在厂环保处的气象站里,边工作边念完了同济大学的环境工程。大学毕业时正逢炼油二期工程建成,原油加工能力跃居杭州湾地区首位,开始开拓国外市场。于是,伯伯加入了炼油厂800万吨改造水污染治理的国家项目。污水处理项目交流结束前,法方代表将一把家族制的小刀送给伯伯,“他说,‘我要送给我在技术上交流最合拍的人’”。几十年过去,这把刀伯伯一直带在身边,刀柄是一只华丽的长靴,或许,这早成为一种远行的伏笔。
1999年,辞职的时候,伯伯敲了二三十个章,每一个都仿佛敲下万众瞩目的决心。那时,厂里的原油加工能力已上升到1600万吨,伯伯看到日益加重的污染,又想起童年时那条清澈见底的河。同时,他也不愿在那些退休后的第一代职工身上,一眼望见自己的未来。“总想往更高更远的地方跑。一是为了孩子,一是还想在更高的舞台做出更多项目。那时候改造的一阵风过了,或许在炼油厂,已经到头了。”
2000年,我出生,正逢蓝印户口制度,退休的爷爷奶奶已在上海买房落户。和很多第二代炼化人一样,因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爸爸不希望我继续成为厂子弟。2005年,爸爸打头阵来了上海。
妈妈埋着的那股劲,也是在那时破壳的。“以前的想法都被爸妈掩盖了,这次我想自己跨出这一步。”妈妈自学拿到电大文凭,又考出了会计证,她相信自己并不是父母口中鄙夷的那个“成绩差,又粗心,离开炼油厂就无处可去”的人。“想感受不同的生活状态,想看更广阔的东西。”

夜晚的镇海炼化
如今,在更大的东海畔,伯伯不断攻下新的污水领域,而炼油厂,是曾经那片给足他底气的大海。同样在上海找到自己生活轨道的妈妈,也说炼油厂是“曾经的自己”——但她更喜欢“现在的自己”。爸爸创过业,也辗转不同公司上过班,虽然似乎没有炼油厂的日子那般左右逢源,但回想起来,爸爸仍觉得要不断向上走。他有了更丰富的阅历和变化,“或许当人生走到最后,我就比一辈子在炼油厂的人能讲的故事更多一些。回忆起来,好像‘经历了一些事情’,不管是有没有意义,但这些是永远忘不掉的。”
原来属于第一代人的保尔·柯察金始终不曾离开过。数十年间,那个实现过第一代人的炼油厂,在第二代炼化人心中,渐渐成了撑不下奶奶理想的“第二个温化”。
炼油厂的第二代,是和镇海炼化一起生长的一代。从早年骑自行车就能很快穿越厂区,到后来坐班车都要用上一段时间,他们见证了镇海炼化发展最迅猛的三十年。但大船终归载不动理想与志向沉甸甸的小船,小船要向自己选择的更广阔的未来家园出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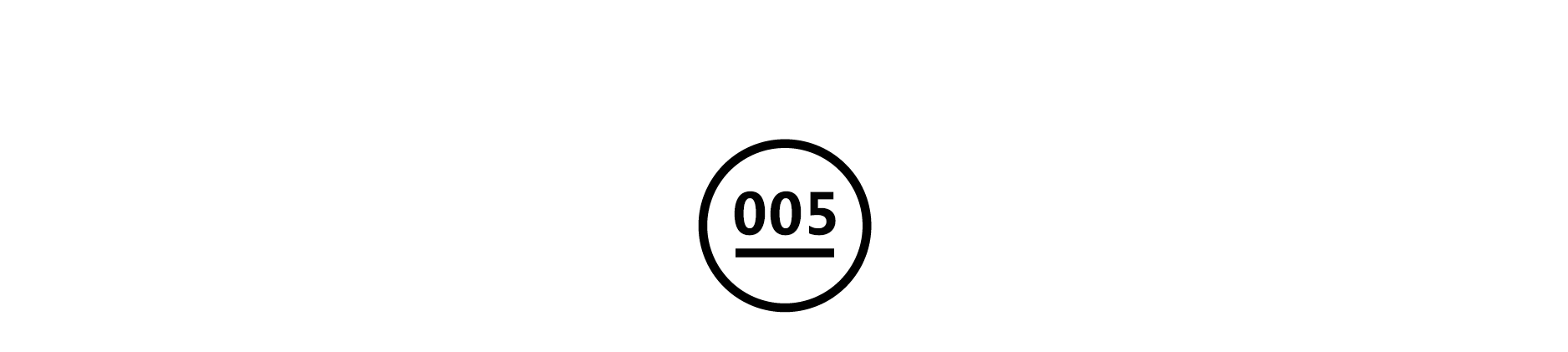
00后眼中的“炼油厂”
2000年,我出生在镇海,正是父母计划离开的前几年。
每天傍晚五点是我最喜欢的时刻。“一片海水”从厂区大门涌出,有说有笑弯进各自的单元楼,又被归还成很多条小溪。锅碗瓢盆开始碰撞,各层楼道的声控灯一串串明灭,像慢速的鞭炮欢庆每个黄昏的节日。
对炼油厂的第三代来说,生活区是与我们相关的所有。文化宫的哈哈镜和“黑水潭”,是我和同伴的“探险地”;公园里有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足够巍峨的小草坡;有游泳池和体育场门口夏天盖着棉被的移动冰棍摊;有一家小牛奶店,店铺虽小,却永远有我们爱喝的牛奶;还有炼油厂医院,作为曾经的常客,连护士都知道我是那个吊针只能扎脚背的小孩……

搬迁后的牛奶店
小时候,大人们最让我讶异的一项能力,是“识人”。路上随见的人,几乎都能脱口而出对方的名字、车间;有时遇到爷爷辈的人,还能叫出是某人的爸爸、妈妈。
2006年一个晴朗的下午,在石化幼儿园过完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跟着妈妈坐火车离开了炼油厂,去往更大的一片海。就在那年前后,国企改革深入炼油厂。许多职能处和子公司陆续分离出镇海炼化,交由社会或个人负责。变化是寸缕滋生的,但对往后逢年过节才落回炼油厂的我而言,一切如天翻地覆,像一部掉出太多帧的电影。
曾经让我讶异的“识人术”和“点头礼”消失了,生活区有了太多陌生面孔和方言,又一批人陆续带着自己的“小生意”来了;炼油厂在宁波和庄市造了新房,职工依然优惠,他们说,生活区环境不好,得肺癌的人多,于是年轻人都搬了出去,剩下老人与和他们一样老的房,其余则租给新的外来客;电影院大部分时间都上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挂锁,二楼大厅有时给社区老人打针;文化宫的联欢会、体育场的运动会也相继隐匿;离退休中心成了社区服务中心,从一科室的40人到一办公室的4人……不久前回到炼油厂,车子驶出生活区的一刻,父母叹道:“还好当初走了,否则一辈子窝在这个地方要窝死了……”
我始终觉得炼油厂进入了它的下行时代,而长辈们告诉我从未如此,镇海炼化始终是中国石化一面耀眼的旗。在他们的回忆中,自己永远是炼化人。每代人对炼油厂的留恋同中有异,或是归属、安心,或是氛围、人情,是“厂子弟”这个概念,是曾经那个炼化集体和他们青春的镌刻处,是炼油厂织出的每一种家园。
奶奶说那时的炼油厂,“好像个大熔炉,里面是我的安身之处,大家都感到很温暖,很有凝聚力”;外婆说,“以前天塌下来好像有炼油厂顶着,后来慢慢各家管各家”;外公说,改制前的炼油厂对职工,都像“一家里的子女,每个人都要关心到”;伯伯说,不变的是炼化情结,是在任何时候接触到石化企业都感到的亲切;爸爸说,炼油厂是多少个午夜梦回的地方,曾经从进入后施村开始就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上海,缩进了自己的房子;堂姐说,即便现在生活习惯和物质追求已经偏向上海,但情感上的追求还是偏向炼油厂时的感觉。
如今,镇海炼化已成为国内最大炼化一体化企业。有太多人离开,也有不少人坚守,还有更多人不断想进来,伯伯形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十多年后,我又看到那片厂区灯火,我仍认为那是我至今所见的任何一座特大都市都不能比拟的辉煌夜景,包括上海。我才惊觉,设备上的每盏灯,都是一个人。那是祖辈贡献的全部青春,是父辈韶华所有的闪亮,是我们记忆深处恒为一种支点的光。
(本文头图来自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其他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实习生王悦颖、吴争对文本亦有贡献)
欢迎继续关注本期“小行星计划”专题:

海报设计:周寰
目前镜相栏目除定期发布的主题征稿活动外,也长期接受投稿。关于稿件,可以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义的个体故事,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症候的非虚构作品等。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