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董成龙评《美国秩序的根基》︱个人自由合成政治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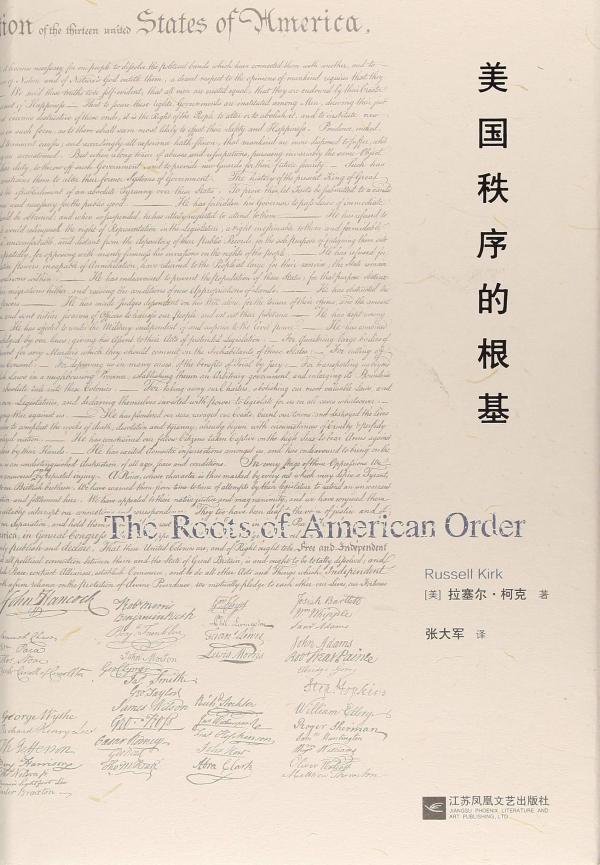
某种巨大的盼望照亮了他的行程。
——薇依(Simone Weil)
人们的幸福之源在于恢复和改善灵魂的秩序与共和国的秩序,不在让灵性和社会沙漠化的毁灭性举动。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一
电影《海上钢琴师》(1998)的主人公别名“1900”,因为他出生那年正好是这个世纪的转折点。言下之意,这部影片要讲述1900年之后的故事,那么,1900年有什么特别?据麦金德所说,大航海时代结束了——经过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不断敞开,而历经数百年的大开发,现在的世界各地都各有其主,世界开始封闭了(《历史的地理枢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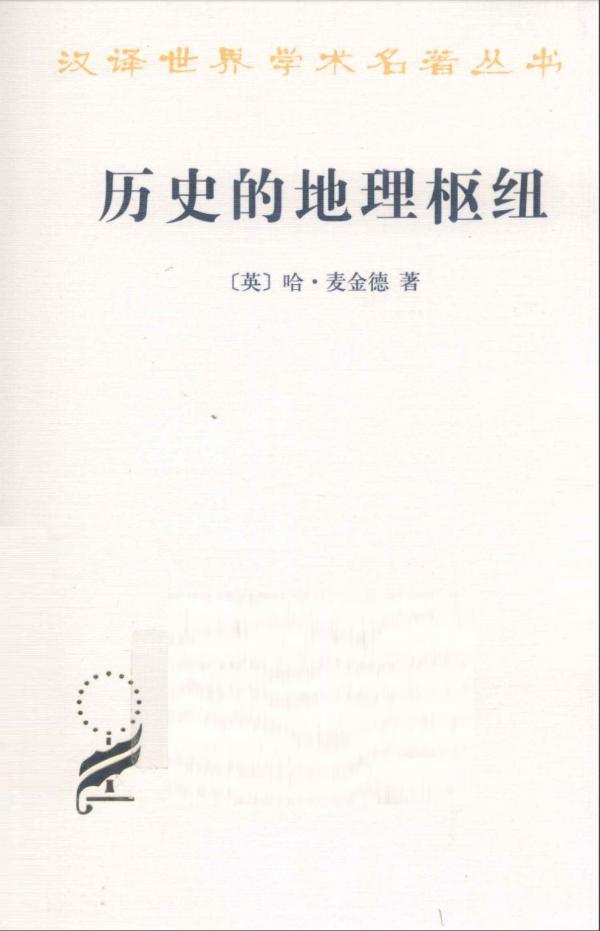
这部影片开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到雾霭蒙蒙处高呼“America ! America !”随即映入眼帘的便是法国人送给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自由女神像——一船的异乡人到达美国。这段高呼很容易让人想到《埃涅阿斯纪》中的场景——埃涅阿斯一行历经坎坷,终于抵达意大利,友人发现意大利就在眼前,高呼“意大利,意大利”!
犹太人为摆脱埃及暴政,遂有“长征”建国的《出埃及记》。特洛伊被毁后,埃涅阿斯带领众人“长征”建国,遂有罗马的“出埃及记”——《埃涅阿斯纪》。美利坚则上演了第三次出埃及,并在国玺上刻有《埃涅阿斯纪》中的“新的伟大事序”(Novus Ordo Seclorum)。承受苦难,漂洋过海,旧秩序承载了“新美国”(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46-49页,以下如未注明皆为该书页码),往日所有的苦难都成为铺就日后辉煌的坚强基石。
历史首先是过去事,它并不顺理成章地等于传统。当“历史”在“当代”变体重现,它才不再是那个死去的往事,而真正成为“活的”,从而变成作为当下基石的“传统”。如果某一段人或事只是历史而不能成为传统,那对后来人而言,这段历史跟没有一样(黑格尔判定中国历史悠久又没有历史,参见《历史哲学讲演录》)。
所以,拉塞尔·柯克的这种“旧”与“新”的表达并非文学修辞,而是他的考察重点。谈到中世纪时,柯克显然就反对启蒙意识形态给中世纪贴上的“黑暗”标签,从他的章节名称就可以看出,第六章的标题是“中世纪之光”,原来中世纪不是现代的阻挡者,反倒是照亮了后者开拓前行的路。在柯克看来,纵然是美国的国父们可能也过多强调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资源,而忽略了中世纪顶峰时期与现代美国的内在连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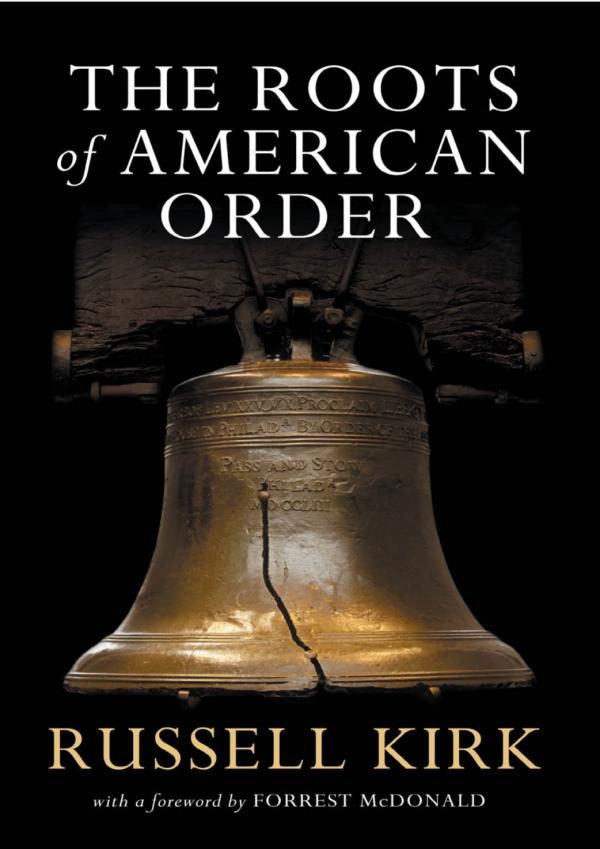
美国人确立独特的政治秩序两百多年,“之前的道德准则仍旧有效”,在所有大国中,似乎只有英国做到了(398页)。关于连续性,十七世纪的英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典范。杀死查理一世的英国人,转而又告别克伦威尔,决心迎回查理一世的儿子作为王室后裔继承王位。政治成熟可见一斑。
所以,拉塞尔·柯克在讲述中世纪时把重点放在英国。他别有深意地举了一个关于1066年诺曼征服历史地位的认定问题——要知道,波考克就曾抓住这个问题撰写《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对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者而言,认定哪一个时刻为英国的立国时刻,是否承认英格兰的在地秩序被诺曼征服打断,涉及到英国秩序的连续性判定。关于英国历史的这段叙事,背后的史观也会影响美国历史的叙事,所以,柯克直指杰斐逊“将诺曼征服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理想化,错误地认为英格兰历史上曾因诺曼人的统治失去自由”(185页),他看重秩序,深知理解诺曼征服背后是关于政治秩序连续性的判定,不容有失。
拉塞尔·柯克的中世纪叙述就是讨论英国如何处理诺曼征服前后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还有王-法关系问题(王在法下还是王在法上)。中世纪的英国种下了现代代议制的种子(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代议制联通了个人自由和政治帝国,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府统治技艺的唯一巨变。
现代的代议制政府要归功于英格兰树立的榜样。如果没有代议制政府,现代的大国最好的归宿要么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架构,要么就再次解体为城邦国家和州。(200页)
说到罗马,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将“霸欲”(libido dominandi)视作罗马帝国强大的奥秘,但奥古斯丁却恰恰认为这种认知忽略了灵魂秩序(吴飞:《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的困境是尘世之城的困境,源于“灵魂秩序的匮乏”,集中体现为罗马帝国的衰落。由此,国家是必要的,却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它在诸种恶中并非最邪恶的——它之为恶在于霸欲,或曰统治的热望;它之必要在于,如果没有国家那就是无政府状态,“会迅速毁灭掉整个民族”,所以国家是和平的保卫者(166-169页)。于是,柯克指出,基督徒不会反对现世政权,反而会服从现政权,因为他们要把“凯撒的归给凯撒”(当然,前提是国家不干涉个人信仰,“基督的归基督”);这种讲法正是美国政教关系的实际形态。
拉塞尔·柯克认可托克维尔的判断,“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于基督教”,基督教的灵魂净化成了美国人的“习俗”,规范其思想和行为;虽然没有国教,却并不等于没有社会共识——这一点成为了美国思维的底色,从而保障了多元主义时代下的核心价值取向(178-179页)。这种影响不仅在于个人德性的内在要求,还在于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和限制世俗权力的公共主张,从而为处理自由与权威的关系提供了约束。
二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诸国逐渐在美洲建立殖民地。荷兰就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英国取而代之后,将其命为新约克(New York,查理二世任命弟弟为约克公爵,后来将王位传给他,即光荣革命之前的詹姆斯二世),也便是现在纽约城的前身了。
所以,谈论美国历史,首先想到的是告别英帝国殖民地身份的“美洲革命”或“独立战争”,柯克却写作一本《美国秩序的根基》,开篇就谈“秩序”问题。秩序与革命是政权的要命问题,二者恰恰代表了美洲革命与法国革命各自的特色,柏克就指出“法国国民议会强于破坏拙于建设”(《反思法国大革命》,张雅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196页)。拉塞尔·柯克要谈秩序的基础,而不想“陷入美国历史上的秩序与失序之争”(444页),“活生生的秩序之树便是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社会”(471页),他就要追溯奠定这“活生生秩序”的活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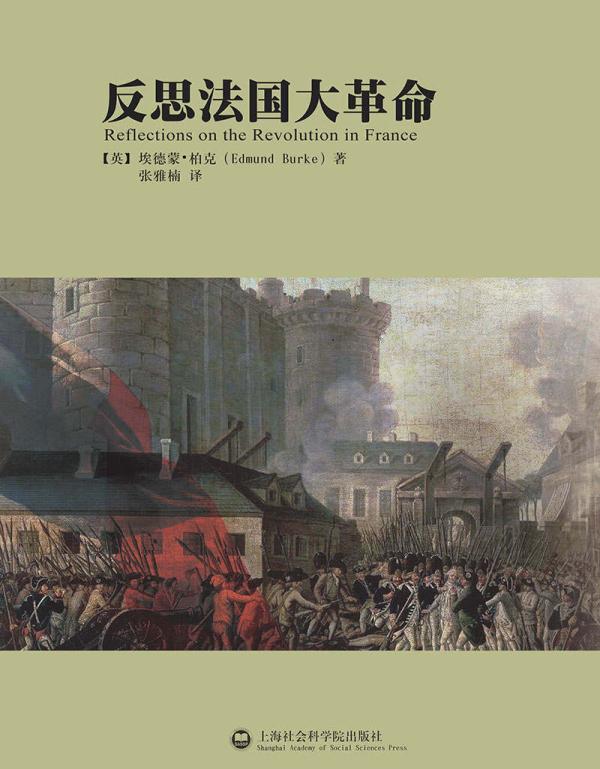
关于美洲革命,柯克否定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1775年殖民地人民的经济负担并不重,而且如果只是为了避免每磅茶叶三便士的税而作战,也并不划算。更有意思的在于,波士顿茶党觉得,茶叶税的降低使走私失去赖以存在的经济效益,所以他们恰恰希望提高茶叶价格,而非降低。看起来,以经济决定论解释1776年这场革命,很难囊括动机各异的革命者;需要引入经济因素之外的要素来考察这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命题是,英帝国君主和议会是否可以不通过殖民地代表机构的同意就向美国人征税(399页)。茶叶税所引发的革命,背后是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思考,如果茶叶税可以任由英国议会安排,那么殖民地的权力和命运最终会全部交由英国裁决。现在,美洲殖民地政治觉醒,坚持“无代表,不纳税”,将经济贡献与政治权利绑定。
支持这场“革命”的一个“保守”资源则是光荣革命,就像英格兰辉格党人反对詹姆斯二世一样,现在的美洲人以辉格党人自居,反对他们心目中的詹姆斯二世——乔治三世。所以,1776年革命的逻辑是:乔治三世要发起革命,“推翻古老的自治体系”,而美洲人则针对这场革命发起革命,恢复旧制度(399页)。既然这场革命与要开拓创新的法国大革命(1789)不同,它是回望过去,扎实地基,倒是更容易停下来,而不像法国大革命那般“不断革命”,不断“向前进”。当时,普鲁士人根茨(Friedrich Gentz)就意识到美法革命不同,法国革命接过了美洲革命提供的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原则,却引向了灾难(《美法革命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这篇美法革命比较的文章发表在1800年的柏林《历史杂志》(Historical Journal),而约翰·昆西·亚当斯(第二任总统之子,后来出任第六任美国总统)正是当时的美国驻普鲁士大使,他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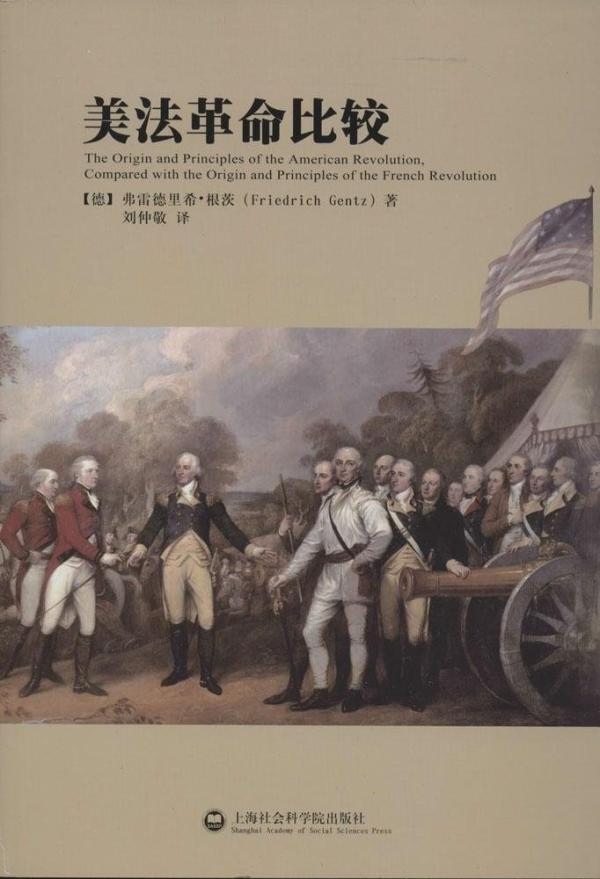
根茨曾经将《革命在法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译成德文(柏克此书译成“革命在法国”比“法国大革命”更妥帖——一如托克维尔的论著译成“民主在美国”优于“美国的民主”,但引用时仍采用现行中译本),显然受到了柏克的若干影响。法国革命以人民之名,用抽象人权摧毁了具体的社会秩序(柏克就批评“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革命喜欢没收充公的行为,很难想象下一场充公行为会假借怎样的名称”(《反思法国大革命》,183页)。法国革命值得省察的重要因由在于它提供了必须重视的反向可能,柏克就指出:
法国的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远离你们的灵药或是瘟疫时是如此。哪怕它是一剂灵药,我们也不需要它。我们知道它提供的毫无必要的医术。如果它是瘟疫,那么也一定是需要做好最充足的准备以应付其危害的那种瘟疫。(《反思法国大革命》,104页)
显然,柏克认定,要清除君主专制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剂疫苗,然而在现实运作中,这剂疫苗本身成为了新的瘟疫。后见者观之,岂不正要长叹“嫦娥应悔偷灵药”?
古老共和国的立法者……要处理的是人类事务,因此他们不得不去研习人类的本性。他们要面对的是公民,因此他们需要学习公民在生活情境中的交流习惯所带来的影响……令立法者羞愧的是,连山野村夫都了解应该如何区分使用自己的羊、马或牛,不会将它们抽象化或同等化为无区别的“动物”,而是给予每一种不同的动物恰当的食物、关照和劳作;而他,自己同类的管理者、安排者何保护者,却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形而上学家,只认识人类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对自己的跟随者们一无所知……当代的立法者不仅没有古代共和国立法者的才干心智——因此也就没有对人类道德状况和习性的准确把握与关切,而且还将他们发现的君主制下自然形成的粗糙等级全部捣毁,将一切都齐列于同一水平线上。(《反思法国大革命》,220-221页)
均质化的设想十分可怕,“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孟子·滕文公上》)。当然,美国革命中也出现了迫害和残暴,但这与法国革命的普遍迫害形成根本差异。柯克特意提到根茨所说:“美国从未像法国那样:对所有权利以及最基本的人类规则的玷污会成为立法的普遍准绳以及对系统性暴政的无条件的背书。”(404页)
柯克不醉心于“山巅之城”的神学表述,躲避“人间天国”的迷狂引领,没有将神引入人世间,从而以神之名划分绝对的敌我,造成无谓的牺牲;而是把神力转化为人力,把神义转化为人义,一切都在人力的勇猛精进和自我矫正(审慎)之间完成。
柯克的同时代人阿伦特也曾比较美法革命,意在思想史谱系中把握“革命”与“秩序”和人的根本处境。《论革命》言辞优美,征引罗伯斯庇尔的一句话发人深省:“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将逝去,不留一抹烟痕,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自由立国的时刻。”柏克也有同样的反思:“摧毁古老的思想和人生规则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从它们坍塌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失去了帮助我们自治的罗盘,同时也不再了解我们应该驶向哪一个港口。”无怪乎柯克的博士论文(学问起点)是研究柏克,1953年,他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当年出版博士论文《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其命意当然是挑战保守主义没有谱系的观念,提供自柏克以来的保守主义谱系,但更重要的不是增添一个意识形态的“主义”,而是经由此路思考政治秩序的连续性——一个政治共同体如何才能绵延不绝。

三
拉塞尔·柯克谈到了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罗马传统、中世纪传统和现代欧洲传统,从标题设置上看,《美国秩序的根基》全书十二章,直到最后两章才直接谈美国秩序问题;可见正是这些传统铸就了美国秩序的根基,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帝国,就在于他的通-统之道,“从旧世界引入的道德秩序已经在新世界扎下根”(444页)。
秩序的根基可蜿蜒曲折地追溯到希伯来人对上帝之下的有目的的道德生活的认知。它们涵括了古希腊人在哲学和政治上的自我意识;罗马人的法治和社会组织经验涵育了这些根基;它们与基督教对人之责任、希望和救赎的理解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从中世纪的习俗、学问和英勇精神中吸取生命的养料;它们紧紧地抓住十六世纪酝酿的宗教情绪;它们源自英格兰千辛万苦争来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殖民时期美国一百五十年的共同体经验强化了这些根基;它们得益于十八世纪的辩论;它们借着《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展露峥嵘;它们经过美国内战的严酷考验后又全面恢复生机。(474页)
所谓通-统之道,不仅是“三统”,而是有多个统绪,可谓“大熔炉”(资中筠:《美国的强盛之道》)。通-统之道,就是努力实现各种矛盾方面的共和,至少包括地理形态上的共和(超越欧洲地缘政治纷争)、人文形态上的共和(民德与民治,参阅任军锋,《民德与民治》)和国家形态上的共和(分权与制衡)。所以,托克维尔看到的美国人,虽然汲汲于个人利禄,“却没有先入个人和公共无政府状态”(449页),奠基于欧洲千年历程的美国秩序,突出表现为社会的开放度和公共的安全感。
正因如此,柯克对1960年代美国爆发的文化革命心有余悸,事后追溯,他很害怕美国就此与她短暂却深厚的传统一刀两断,从此成了无根的浮萍。柯克在全书首尾都征引过的薇依就曾指出,古希腊诸神的性不受时间和伦理的限制,人的性虽然不受时间限制,却受伦理限制,动物的性虽然不受伦理限制,却受时间限制(发情期),可见通过性事,我们看到了神-人-兽的界限(薇依:《柏拉图对话中的神》)。1960年代美国的文化革命伴随着性解放运动,无怪乎同为保守主义阵营的雅法(Harry Jaffa)也曾写过《鸡奸与学院》(“Sodomy and the Academy”,1984),指斥性解放背后的文化革命。

因为美国的通-统之道,以参照过去的方式迈向新时代,没有造成时代的断裂。在拉塞尔·柯克看来,美洲革命奉行“审慎”原则的另一佐证是,他们使用了“政府”而非“国家”。“政府”是有届次的,而要创制“国家”就意味着推翻整个生活秩序。显然,美洲革命的革命者是要在既定秩序内做改变——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推翻国王,却没有另立新国(415-416页)。
因为对英国政府权力的不信任,美洲革命者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将推翻与建立翻开来——既然英国政府可以践踏美洲人的自由权利,那么,在美洲大地上建立起的政治权威,怎会不重蹈覆辙?直到美利坚邦联的松散弊端逐渐显现,人们才意识到要建立一个能够捍卫个人自由的强大政权。所以,1776年是独立(所以没有使用“国家”一词),更像是一场针对英国议会的“反议会革命”,直到1787年才真正建国(标志是制宪,以确立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建国)。
“新生的美国怎样才能在维持一种有力秩序的同时保障个人自由和某种程度的民主?”(422页)拉塞尔·柯克的这一层关心,是诞生于自由主义土壤之上的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柏克就说:“要建立一个自由政府,即合成自由与强制者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需要苦思冥想和超凡智慧。”(转引自郭定平:《关于柏克的政治哲学》)柏克对现代西方的三次奠基性革命(革命的“原型”)都有深入探讨,他欣赏光荣革命的保守,也看到了法国革命背后的民主势不可挡,更看到了美洲革命为欧洲政治注入了新希望。
柯克在全书结尾特意安排了“大事年表”,能够折射出他深谙美国秩序通-统之道。
此年表除包括本书提到的重要事件外,还增加了某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其他日子。其目的是以“线性时间”的方式罗列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和罗马在相同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508页)
这个年表以公元前2850年的埃及古王国开始,终结于1865年林肯被杀和1866年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出版《美利坚共和国》(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其中特意介绍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大卫成为以色列王,荷马创作《荷马史诗》,迦太基创建,罗马创建,柏拉图出生,等等等等。比较下来,反倒关于美洲和美国的篇幅很少,与全书的谋篇布局一样。
作为年表结尾的林肯和《美利坚共和国》各有深意。林肯是为了捍卫秩序,不得已而作战(雅法就指出,“于是,战争来了”[then, the war came]表明林肯作战的被动性)。林肯去世数月后,布朗森出版了论著《美利坚共和国》,他指出每个有生命力的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天命,美利坚的天命就是“协调自由与法律”(469-470页):
希腊和罗马的诸共和国在维护国家的同时却对个人自由造成伤害;现代的共和国要么同样如此,要么在主张个人自由时对国家造成伤害。美利坚共和国在创建时就领有这样的天命:实现两者的自由,并同时造福两者。
在全书尾声,拉塞尔·柯克深情回忆了薇依生前最后一项工作《需要根基》(L’Enracinement,The Need for Roots)。该书在薇依身后1949年出版,首先是薇依对欧洲人在二十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生存经验,更是对二十世纪欧洲文明的反思。她指出:“灵魂的第一需要是秩序。”反过来看,若没有秩序会怎样?一切的自由将会被他者的自由而消解,终结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却仍要诉诸私力救济,何其危险与悲哀。
冷战之后,美国研究更加成为重头戏。美国历史的研究路向是穷根追底,追溯到早期美洲史,即美国之前的美洲大陆在地史研究(美国的在地史前史)。与这种地缘的史前史研究不同,拉塞尔·柯克引向了秩序的史前史研究——他是在提示我们,直面美国、理解美国的捷径,恰恰不是对当代美国国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也不是美洲在地史的研究,反倒是绕道欧洲(当然还有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和亚洲),曲径通幽才能抓住美国的根底。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