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拉美文学中,小说是现实,非虚构又在编织家族史的梦网
近期,哥伦比亚作家英格里德·罗哈斯·孔特雷拉斯的长篇小说《移动云朵的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这是一部充满魔法的小说。在小说中,外公拉法埃尔是赫赫有名的巫医,他的天赋包括但不限于和亡灵对话、预知未来、治病救人……母亲,不守规则、不畏传统的的奇女子。她不仅有继承巫术的雄心,还能和鬼神交谈,能分身两地。我,在芝加哥上大学,安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一次车祸失忆让我通灵的能力觉醒,被去世的外公托梦召唤…… 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位亲戚都梦到了外公,这是一场共享的梦,我们决定回到哥伦比亚,挖掘被隐藏的家族历史。

[哥伦比亚]英格里德·罗哈斯·孔特雷拉斯 著|张竝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在哥伦比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巫医的世界里,有无数魔幻的传说和生活日常,《移动云朵的人》里,初读最令人惊艳的就是这个部分。
巴卡塔王国偷情的妻子,被严惩惨死之后化身潟湖精灵,就漂浮在水中央,宣讲预言。引男人入水,凡是被引诱入水者,都会发现脚下并无立足之地,旋涡便将他吞噬。
若有人进入女巫所在的森林,女巫会变成黑头美洲鹫在树上死盯着他,女巫施法,人就会无法走出森林,无论如何奔跑,都只能困在原地。
外公开诊所治病,在梦中浮现草药的位置,便可在醒来出发采药,治病救人。
母亲的分身在哥伦比亚全境满地跑。
在全家快被淹死的时刻,母亲默默施法停了暴雨。
姨妈能见到将死之人整张脸上笼罩的幽灵面纱。
正如作者所言,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他们的现实主义,这些远在拉丁美洲、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在英格里德真实的家族故事中蕴藏的还有拉丁美洲被殖民的历史和拉丁美洲动荡的社会现实。
《移动云朵的人》写到了大毒枭埃斯科瓦尔,游击队的屠杀和勒索,殖民主义对原生文化的扭曲,以及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之后种族身份的不明不白,这些都与作者家族的遭遇息息相关,生活在哥伦比亚,就难免是战争的牺牲品。
写下这些故事,就是要揭示殖民者给哥伦比亚造成的伤痛。

▲ 孔特雷拉斯(郭天容 绘)
孔特雷拉斯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出生长大,现居加州。她的第一部小说《醉树之果》曾获得加州图书奖首部小说银奖。孔特雷拉斯任圣玛丽学院的客座作家,多篇随笔和短篇小说刊登于《纽约时报》等杂志。
如有评论所言,在《移动云朵的人》中,孔特雷拉斯使用极为精致的哲学笔调,围绕家族历史,将殖民史、个人叙事,和魔法纺成了一张网。读者能感受到它们轻柔的转动,仿佛行星围绕太阳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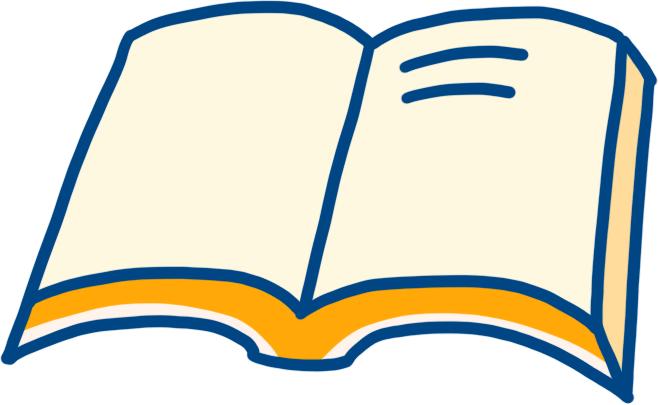
译作选读

他们说让我暂时性失忆的那场事故,其实就是我继承的遗产。既无片瓦,亦无寸土,更无只字,唯余数周的遗忘。
我妈也有过暂时性失忆,只是她当年八岁,而我二十三岁。她掉入了一口枯井,而我则骑着单车撞上了敞开的车门。她在哥伦比亚奥卡尼亚地表之下三十英尺的黑暗之中差点流血而亡,而我则安然无恙,起身离去,于芝加哥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四处徜徉。她有八个月之久不知自己是谁,而我则有八个星期不记得自己是谁。
他们说遗忘症犹如一扇门,让我们拥有了本该拥有的天赋,只是我妈的父亲,也就是我外公,忘了传承给我们。
外公是个巫医。他的天赋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同死人说话、预知未来、治病救人、呼云唤日。我们是棕色人种,梅斯蒂索人。欧洲男人抵达大陆,强暴土著女人,那就是我们的起源:既非土著,亦非西班牙人,而是一道伤口。我们把这种天赋叫作秘密。在桑坦德山区,秘密由父传子,子又传子,子再传子。但外公说,他的儿子没一个有种,能成为真正的巫医,唯有我妈可以承受这种天赋。她意志坚定,天不怕地不怕,在外公眼里我妈比男人还男人,他喜欢把我妈叫作山里的兽。但我妈是个女人,这种事情是万万要不得的。据说一个女人要是掌握了秘密,倒霉事就会接踵而至。
可是,那年我妈才八岁,刚掉入过井里,还在养伤。等她记忆一恢复,事情也就这么成了。她虽意识不清,却重掌了见鬼魂听阴声的能力。
家里人说我妈能掌握秘密是命——既然外公教不了她,那秘密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四十多年后,我出了事故,丢失了记忆,家里人都很兴奋。姨妈们边喝酒边唠嗑,喜气洋洋:“又来啦!蛇咬尾巴啦!”
然后,他们就眼巴巴地瞅着,看这秘密究竟会如何在我身上显现出来。

这是一个发生在西班牙语语境下的故事,我妈和姨妈们都用vos称呼彼此,vos即古称“汝”,但她们用tú来称呼我,tú意为“你”,休闲随意,温柔亲切。她们用的是奥卡尼亚的讲话方式,我的先辈就来自那里,那儿的语言听起来就像殖民时期的化石。用西语来讲的话,我们的故事先徐后疾,讲的时候还会一直咯咯地笑。
我们娘俩犹如彼此的传声筒,想想都觉得可怕,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遗忘症。但这事就像挠痒痒,不挠不行,可一挠就破,一挠就烫。而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反复试探。
姨妈们要我说说,活着却没有记忆究竟是什么滋味。我设法告诉她们这种生活极具超现实感,像是在看电影。姨妈们冲我翻白眼(不过她们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好像我就是一档糟糕的电视节目,她们边看边评论,毫无顾虑。“这小妮子不知道在说啥,是不?”她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做了什么样的梦。
对我们娘俩来说,遗忘症发作的时候,只要醒着,全是困扰,而我们的梦却已触礁搁浅。我妈的梦有先后顺序,她在梦里是个鬼魂。我在梦里没有身子,当我这么大声地告诉姨妈们的时候,这才意识到: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鬼魂。
西语里针对亡者行走有个词,叫作desandar,行走之不能,越走越无力,直至行走本身不复可行。认为鬼魂有特殊的行走方式,是我们从入侵大陆的定居者身上传承而来的观念,而我们内在固有的则是“间隙感”这个概念,认为我们恰好处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而真实和非真实又时常合而为一,彼此相同。因此,对我们而言,生者也会以鬼魂的步态行走。
我父母都是桑坦德的土著人,当地的土著人都会梦见次日即将猎获的野兽。晨曦初现,他们便会动身前往,寻觅梦中所见。
梦,于我们而言实属重要。
我们娘俩的遗忘症相隔四十三年,我们都梦见了驱逐。

我妈是村里的鬼。她困居于村内,村民所讲的语言,她虽不懂,却能理解。村民们膜拜她的尸体——她的尸身未曾腐烂,芬芳馥郁,堪称奇迹。
我时常出没于海平线,海浪有时会从那儿退却,抛弃陆地,暴露海床。有时,陆地出现小故障,海洋会倏然而回,仿佛从不曾离去。于是,海浪战栗不已,咳吐出熔岩和烟雾,海岛诞生。
外公治病时,会让梦引领自己,去往药草的所在之处。等从睡梦中醒来,他便会徒步寻觅,直到景色与梦境相符,而后在那个地方采集草药。我妈困于梦中之村,她是村里的鬼,时常操持与生者的沟通,一旦恢复记忆,回到了梦醒的生活之中,她便懂得如何与亡者交流。我在梦中观察陆地的诞生,醒时,我会用心研究我正在成为的这个自我如何创造了自身。
既然我的生命呼应了我妈的生命,而我妈的生命又呼应了外公的生命,那我便不禁犹疑,我们所有人是否都在踏着同样的鬼魂的步态,重复并毁灭着彼此的生命?
姨妈们打断了我的思绪。她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我没在听。她们又问我,失忆之后的梦本质上是否算预言。我回答之前思索良久,她们惊恐而又期待地盯着我。她们知道掌握秘密是一种祝福,但也是一种负担。她们见识过,对权力的痴迷常常伴随着秘密,醉心于权力会颠覆生命,会导致酗酒、抑郁和自残。但无论如何,她们的眼中都似乎充溢着期许,我从她们的凝视中读出了渴望,渴望我是这秘密的最后一个接受者。我很享受那白驹过隙般短暂的一刻,如果我对那些有求于我、想听取我建议的人说“没错,我就是像我妈那样的人”,又会怎么样呢?最后,我还是摇了摇头:“我没法像我妈那样看见鬼魂,我听不见亡者,未来原本就藏得好好的,我也看不见未来。”
姨妈们慢悠悠地点了点头。她们垂下了目光:“好吧。”她们拍了拍我的手,我让她们失望了。我本有机会接纳秘密,可我不知为何把它挥霍掉了。
她们一直在等待答案,此刻她们得到了回答,于是将目光转回到我妈身上,想要听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充斥着死亡、鬼魂和复仇的故事,但她们却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我妈,说:“不管怎么样,正常更好。还是要过日子的。你会发现自己忘得有多快,比巫师放屁还要快呢!”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

原标题:《在拉美文学中,小说是现实,非虚构又在编织家族史的梦网》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