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肖琦评《水下巴黎》︱巴黎的世纪大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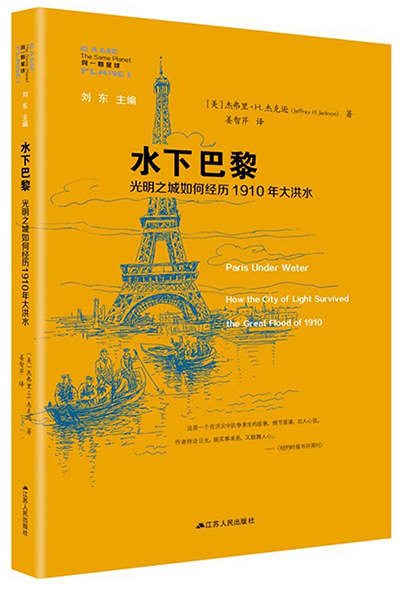
洪水围困光明之城
历史上能持续发展繁荣的大城市往往都受到大自然的眷顾,较少有自然灾害的危险,罗马、伦敦、巴黎莫不是如此。对徐志摩笔下“到过就不会再稀罕天堂”的巴黎城而言,千百年来,唯一持续的困扰大概是塞纳河的水患。塞纳河是巴黎城的母亲河,它从史前时期就开始哺育着两岸的居民,经年累月地为巴黎人提供食物、水、军事防御与航运水道,最终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同时,塞纳河的洪水也像一颗定时炸弹,让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的巴黎人感到惶恐不安。而其中最晚近的一次,给巴黎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10年的世纪大洪水。在那次洪水中,巴黎及其周边有两万四千户家庭受灾,造成近一万四千人流离失所,受伤住院者达五万五千人之多。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为四亿法郎(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亿美元),社会投入救济和援助资金五千多万法郎。杰弗里·杰克逊在《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经历1910年大洪水》写道,在同时经历过1910年大洪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看来,“大洪水对巴黎造成的破坏要比德国的炸弹还要严重。与德国人比起来,大洪水是更可怕的敌人”。

事实上,为了应对洪水的破坏,巴黎人曾经求助于城市的主保神——圣女热纳维耶芙(Sainte Geneviève),曾经坚持不懈地改造塞纳河,疏浚河道,修筑堤坝。尤其是在奥斯曼改造时期(1853-1870),巴黎的地下管道设施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在塞纳河附近的地下,人们设计了更大的排污通道,铺设轨道,轨道上可以行驶机动车,清洁工可以乘车在里面通行。整个系统集废水与雨水处理为一体,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地下世界。不久前上映的《碟中谍6》就在巴黎的地下世界中大量取景。据说在巴黎,如果不小心把钥匙掉进了下水道,完全可以根据地漏位置,把东西找回来。巴黎人对他们的这套系统十分引以为豪,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下水道博物馆——巴黎下水道博物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892年开馆,向世人展示他们改造自然和改造城市的伟大成就。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钢铁、电力、汽车工业的发展,科学与技术成了进步的代名词。为1889年世博会建造的艾菲尔铁塔被设计为科学模式胜利的象征。铁塔二层的巨大柱壁上刻有拉瓦锡、巴斯德等法国科学家的名字。塔身共有一千七百九十二级阶梯,1792正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的时间。进步、科学与共和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三个关键词。
然而,巴黎人对他们的科学技术与工程系统的自信却在1910年的世纪大洪水到来之际显得盲目。1910年1月中旬,塞纳河的水已经开始上涨,习惯了冬天雨雪纷飞的巴黎市民乐观地以为,即使河水已经超过了正常水位,城市的下水系统仍然会保护他们远离洪水的危害。1月21日,大洪水终于到来。由于水位急剧上升,建在塞纳河上的水文观测站无法测量和共享数据,水文观测系统开始崩溃;为钟表提供动力的压缩空气服务系统被上涨的河水淹没,许多钟表的时间都定格在1月21日晚上的十点五十三分;洪水不仅在巴黎市区翻涌奔腾,也渗入到地下。洪水开始从地下流进大楼里,从水分完全饱和的泥土里汨汨冒出;地铁停运,道路坍塌、扭曲变形,到24日,城市交通整体瘫痪;物资紧缺,污水垃圾泛出阵阵恶臭。夜间,因为供气管道坏损,工作人员不便在受淹的城市中点燃和熄灭街边汽灯的火苗,曾经的光明之城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黑暗。这些都是杰克逊在《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经历1910年大洪水》的第一部分中为我们描绘出的大洪水来临时的场景。
“民主制度已将巴黎置于危险之下”
汹涌肆虐的洪水挑战着巴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政府总统、部长、国民议会、巴黎市议会、巴黎警察局、市政工作人员、社会团体、民间救援组织、国际社会、军队、普通市民等都出现在救灾工作的行列中。救灾工作不仅仅涉及政府层面的指挥调动,还关乎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衔接,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协调,巴黎与郊区省份之间的统筹等问题。杰克逊在该书第二部分“水下巴黎”中着重记录的法国政府与社会关于巴黎是否需要实行军事戒严以应对洪水的讨论,将全书对于救灾的描述引向深入。
法国军队在巴黎城外长期驻扎一支守备部队,这支军队在洪水爆发伊始,就应救灾实际总指挥巴黎警察局长路易·雷平和其他市领导的请求,进入巴黎城,协助地方政府安慰和救援受灾人员。为了协调军队,部队的指挥官达尔斯坦将洪水泛滥地区分成五个区,每个区都派遣一名高级军官负责指挥。军队不仅承担了道路工程,救灾救援的工作,还与警察一起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全。但是许多市民依然不愿意配合军方的救援,他们只愿意接受紧缺物质的援助,不愿意离开家撤离到安全地带。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就会被抢劫一空。实际上,巴黎多地已经发生了偷盗、抢劫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市议会议员路易·杜赛在1月28日市议会预算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呼吁对巴黎实行戒严,将城市交给军方管理,改变令出多头、各部门职权交叉的局面,以使政府的救灾工作更为有序与高效。杜赛的发言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对第三共和国的保守派人士来说,由军方来控制城市非常契合他们的政治信仰与理念。包括《法兰西行动》在内的极右翼力量借此攻击民主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能,“民主制度已经将巴黎市置于危险之下,使政府机构充斥着腐败、无知的公务人员”。 他们强烈赞成军事戒严,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在右翼记者、作家雷翁·都德(Léon Daudet)看来,“由于他们掠夺了光荣的法兰西,破坏了它的自然保护能力,过度使用了它的土地,因此民主注定了要死亡……在他们的规划中,灾难和毁灭将不断积聚”,他甚至认为“巴黎洪水的教训就是:共和国必须打倒”。
激进共和派与社会党人完全读懂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对军事戒严的抵制亦同捍卫民选政府与共和体制联系在一起。共和国总理社会党创始人白里安强调,洪水爆发以来,巴黎市民一直非常镇定、沉着地应对,一点儿都不需要极端的抗洪措施,不需要军事戒严这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对许多曾经支持巴黎公社的左派人士而言,军事管制使他们想起1871年公社起义被军方镇压的“血腥的一周”。此外,在1906年刚刚获得平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军方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法国人对军方的不信任感。最终,大洪水期间,巴黎城并未实行军事戒严,而巴黎人民也亲眼目睹了法国军方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恪尽职守与忘我牺牲。在全巴黎,全法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九个漫长的风雨交加的昼夜过后,1月29日,太阳升起,巴黎人抬头看见了久违的、湛蓝的晴空。

救灾神话与乌托邦精神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感知到自身的渺小。然而,自然灾害本身可能并不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对所处的地球别无选择。更重要的是在灾害过后,深入地反思与总结,以便在下一次灾害到来时能做出更好的应对。而对大洪水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水下巴黎》一书最后的第三部分,也是笔者认为该书最为出彩的部分。
杰克逊将灾害后法国社会对大洪水的反思,放到他所熟悉的第三共和国诸政治力量之博弈的背景下展开。
在天主教一方,1月30日,巴黎红衣大主教阿麦特主持了两场弥撒,为城市的获救感恩上帝。他号召信徒救助受难者,也希望借此恢复法国对天主教的信仰。历史上,法兰西一直被认为是天主教的长女。然而第三共和国初期,最主要的斗争就是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保守派与共和派人之间展开,天主教因之与保王党人和极端右翼势力在传统联系、道德秩序上的亲近,在反对共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纪初,共和派中的激进共和党执政,该派坚决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于1905年通过《政教分离法》,规定政府在宗教事务中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从而在法律层面将宗教排除出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最终确立了世俗的共和国体制。
1910年大洪水发生后,天主教人士抓住机会,提醒巴黎人民,上帝常常用他的自然之力,惩罚人类的罪恶,而这次大洪水,可能就是上帝对于法国政教分离的惩罚。应该说天主教对大洪水的解释符合他们一贯对自然灾害的解释,黑死病是天谴,大洪水是惩罚,社会道德的堕落导致上帝发怒,人们只有通过虔诚的忏悔和信仰来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庇佑。
对另一部分科学的信徒而言,大洪水则引发了他们对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信任危机。巴黎《晨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受的教育是要相信科学,科学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最美丽的城市不受变幻莫测的河流的伤害?该报的编辑甚至直接将1910年称作“工程师的1870年”,这是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失败,是法国技术上的惨败。人们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逐步确立起来的对科学的信仰,在这次失败中遭到了沉重的一击。历史的天平是否要重新将科学摇摆不定的信徒们推回宗教的怀抱?还是在科学与信仰之间找到重新的平衡?
官方层面的反思充满了神话的意味。白里安总理在2月初就任命了一个由法国内阁成员、科学院院士、海军部长阿尔弗雷德·皮卡尔为首的调查小组,对大洪水的成因和产生的后果进行调查。皮卡尔小组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调研任务,给出了一整套大洪水的原因和今后防洪工作的详细规划。最为重要的是,该报告从官方的角度,着重构建出在洪灾中,政府与城市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神话——尽管杰克逊在书中也列出如左翼政治活动家阿道夫·威利特的更为平民主义的不同观点,后者认为所有艰苦的工作既不是他们的主保神圣热纳维耶芙做的,也不是共和国做的,而是巴黎市民自己完成的。
虽然杰克逊承认,皮卡尔报告的官方结论对团结一致的强调具有明显的目的导向性,即着眼于城市的恢复,在灾后重建中继续讲述着关于工程力量战胜自然、巴黎人民的精神力量战胜灾难的故事,但是他仍然对这种团结的神话叙事十分热衷。杰克逊甚至引用了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对1995年芝加哥遭受热浪袭击的研究来表明团结的重要性。后者在研究结论中指出,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与社区中其他人的亲疏关系所决定的。在1995年芝加哥热浪中,那些邻里关系好、人口稠密、家庭成员和朋友多的社区,在热浪中幸存下来的人就多得多。同样,巴黎人在社会阶层甚至城市人口分布的地理区位上虽然形成了坚固的“壁垒”,然而在灾难面前,他们还是能够实现跨越阶层的相互帮助和团结一致。
杰克逊最终将这种凝聚力上升为人类应对社会和自然灾害时的一种普遍模式。即在灾害发生之后,人类会出现一种令人兴奋的乌托邦精神。受灾人员会团结起来,以无私、利他的精神,把人力、物力等资源汇集起来,减轻受害者的苦难。当然这种模式也有它作用的条件,杰克逊引用埃里克森对西弗吉尼亚水牛湾洪水的研究结论说,在受灾人数远远大于没受灾人数的地方,这种乌托邦精神就不会存在。因为受灾人员自顾尚且不暇,遑论去顾及他人。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很容易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3年的非典,1998年的南方洪灾与这种令人兴奋的乌托邦精神联系起来,屏幕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救灾故事无不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然而,对这种社会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解释过分强调,往往会掩盖一些事实层面的问题,包括社会不同群体展开自救的能力、工程技术的储备、基础设施的质量、救灾应急动员机制等,这些才是在灾害的各个阶段发挥实质性作用,最大程度地减少无谓的人力和财产损失的决定性因素。
杰克逊在书中大量运用了一手档案资料,这得益于他在巴黎市各档案馆的长期浸淫。他对巴黎地区社会文化史的熟稔掌握亦使得读者得以追随阿波利奈尔的脚步亲历大洪水中的社会万象,得以深入到洪水背后探究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作为罗德学院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杰克逊不无遗憾地指出,在1910年,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将洪灾的原因归结于环境问题。多数法国人认为大洪水是个意外事件,是工程技术未能控制住洪水,而不是人们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了这次灾难。对科学技术崇拜的深度反思还要等到四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环保运动的兴起,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环境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被重新定义。今天,在最集中展现了人类文明成果——科学技术对自然之控制的城市中,城市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引发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而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加入城市环境史的整体叙事中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