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书荒”年代的上海读书记忆:为买到一本名著通宵排队
在“书荒”的年代里,一本本名著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一本好书是可以让人回味无穷、受用一生的。有人说,与书结缘、有书相伴,人生不会寂寞。在书籍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审视自己,还能与各路名人名家沟通灵魂。
艰难岁月里与名著相伴
每个星期四的早上,上海五里桥街道的老年读书会都会准时进行,大家聚集到一起,每次讨论一个主题,每次都由一位读书会的成员来讲解。
上海市民吴畏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她说自己学生时代为了应付考试,读的多是一些专业书,很少有机会去看文学作品。等到快毕业时,“文革”却开始了,那个时候,想要读到中外名著就非常困难了。有一次,吴畏偶尔经过学校图书馆,意外地发现图书馆底楼的角落里堆了一堆书,她如获至宝,就在书堆当中一本一本地翻看。
后来吴畏跟随丈夫来到了上海,在一个医务室里当医生,在那里她又碰上了读到名著的机会。吴畏是一个很和气的医生,服务态度又好,所以很多病人都喜欢她。在她服务的病人中有一位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干部,负责打扫图书馆的卫生。他为了表示对吴畏的友好,每次来看病的时候总会悄悄地塞一本书给她,在这位干部的悄悄“输送”下,吴畏看了很多名著,像《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都是在那一时期看完的。
不过,从小酷爱读书的沈嘉禄就没那么幸运了。20世纪60年代,他要用饿肚子的代价去换取精神食粮。资深媒体人沈嘉禄回忆说,那时候社会上没有什么书可读,精神生活十分贫瘠。后来,他了解到学校图书馆的大量藏书都堆放在了库房里,对此他无比憧憬,班里几个比较调皮捣蛋的同学跟他说,他们能把书拿出来借给他,但代价是一本书借给他一天需要付1角钱。沈嘉禄说,当时两个大饼、一根油条也是1角钱,于是他就只好把吃早饭的钱省下来给了那几位同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巴尔扎克的十几本小说都看完了。
沈嘉禄就这样在精神饥渴的年代里艰难地读着一本本来之不易的名著,终于有一天,他在表哥那里挖到了宝。回想起那次的经历,沈嘉禄仍然觉得又好笑又脸红,他说:“表哥的一位同学来看望他,给他带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鲁迅诗歌集》。当时我看到后也非常激动,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表哥答应把书借给我,让我带回去抄。当时我比较着急,眼看着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我就把诗歌集里内容比较多的几页撕了下来,放在家里慢慢地抄,结果被表哥发现了,因为这事,我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看书时,只要是沈嘉禄觉得精彩的部分就会把它们都抄下来。在沈嘉禄的抄书生涯当中,有海涅、莱蒙托夫的诗,有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的小说,他最疯狂的举动就是把整本手记本的《茶花女》抄了下来。一本《茶花女》大概有20万字,而手记本也有5万字,当沈嘉禄看了几页手抄本后非常激动,想跟同学多借几天,却被拒绝了。没有办法,沈嘉禄只得赶时间,为此他还大着胆子把手抄本带进了课堂,当他抄到最后一页,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时,门被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冲了进来……这些事情如今看来很不可思议,却是沈嘉禄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后来随着藏书积累到一定程度,他索性办了一个“私人图书馆”。后来沈嘉禄发现,同学借去的书时常有去无回,为此他专门还刻了个图章,上面刻了一个字—
“还”,把这个字印在书上,提醒同学按时归还。
想尽办法找书看
借书不还可能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事情,曾经是沈嘉禄同事又是朋友的胡展奋就坦然承认当年自己是个“雅贼”。回忆起那时候“偷书”的经历,胡展奋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很多人偷了我的书,我也偷了不少人的书,比如说我的书被他卡住了,那么我只能卡住他的书,再拿他的书去和别人做交换。我觉得我们当时的读书人都是‘雅贼’,没有读书人敢说自己的书本本来历都是清清白白的,总有一本是暧昧的。”
生于50年代的胡展奋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少年时代,大量的名著都是在一位小伙伴家的亭子间里读完的。那时候,他住在江宁路五福里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有个邻居叫陈巍,他俩天天在一起玩,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陈巍看到胡展奋成天躲在阁楼昏黄的灯光下看书时,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告诉胡展奋,说他父亲的书比他的多得多了。陈巍的父母亲都是做老师的,家里接待外人也比较谨慎,但出于小伙伴之间的友情,他向胡展奋打开了他家的书橱。在那个“书荒”的年代里,胡展奋在小伙伴家如饥似渴地读着那些外面极难看到的名著。
当时,想要借到一本名著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为了能得到一本好书,会想尽各种办法。市民杜金海回想起自己当年读名著的情景也感触颇多,她一位同学的父亲早年在印制厂工作,“文革”期间被抄家,大部分的书都被抄走了。然而,放在厨房一个角落的书却幸好没有被发现,杜金海为了能读这些书,就给她的同学织毛衣,以此来联络感情。那时候,有些书借给别人看还要偷偷摸摸的,杜金海的同学为了防止被别人察觉到什么,不仅把书包裹起来,还在上面覆盖上《毛泽东选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杜金海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简 · 爱》《呼啸山庄》等世界名著。
资深媒体人秦来来回忆起那段“偷偷摸摸”读名著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因为私底下交流各种名著而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如今,回首那段岁月,秦来来把名著阅读总结为三个阶段,他说:“‘文革’之前我们到处借书读;‘文革’当中我们觅书读;‘文革’以后我们可以买书读。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有些书是不能公开的,借书就像搞地下工作,当时流传的手抄本,就是由某个人创作的,别人若觉得好,就抄写下来,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流传出去了,当时比较有名的有《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三下江南》。”

在很难找到原著来读的时候,那就只好自己动手去抄手抄本。在上海音像资料馆工作的石左虎很早就掌握了四国语言,业余时间还翻译了几本外国著作,当年他初学英语的时候居然想动手抄英汉词典。那时,石左虎还是初中生,他几乎跑遍了上海市内的所有新华书店,却找不到一本英汉词典。后来,石左虎的老师听说了他的经历,便悄悄地把英汉词典赠给了他。
与书结缘的美好经历
那时不仅家里珍藏着几本名著的人很吃香,就连看名著看得多的章丽琼也因为哥哥、姐姐总有办法弄来几本书而使得她变成了小姐妹里的红人。章丽琼的一帮小姐妹天天围着她,让她讲故事,于是章丽琼就把《悲惨世界》《红与黑》《安娜 · 卡列尼娜》《复活》中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章丽琼不仅因为读名著而拥有了很多朋友,而且还为她带来了甜蜜的爱情。她的丈夫当年知道她爱读书,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找来各种她想要看的书。章丽琼的丈夫原先是她的中学语文老师,当他得知章丽琼最崇拜的是斯巴达克斯,特别想看小说《斯巴达克斯》后,就千方百计地借到这本书,以家访的名义把书带给了她,回想起这段往事,章丽琼至今仍感到十分有意思。
曾经是“振兴中华读书会”主要参与者之一的陈振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陈振民还居住在老式的里弄房子里,躲在阴凉的地方看书是他童年暑假里最美好的事。白天,随着太阳的移动,屋内的阴处也在移动,于是陈振民就不断地跟着太阳转移位置读书。到了傍晚,陈振民就在滚烫的地上洒上水,然后就是一把躺椅、一杯水、一把蒲扇、一本书的休闲时光了。陈振民曾任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副主任,他记得,儿时“少年之家”图书馆也是他吸取养分的好地方,那里有几千册的藏书,《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吕梁英雄传》《草原烽火》等,都是在那里读到的。
可是到了“文革”开始后,这些名著对陈振民他们这代人关上了大门。那时,陈振民只有14岁,无所事事的他总喜欢和同学到学校里溜溜转转,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门口贴着封条的地下室,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揭开了封条走了进去,却意外地发现了难以计数的好书。他们像搜索宝贝似的在书堆里翻寻,陈振民当时就带走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还有很多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比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时常回荡在他的脑海里,让他受益无穷——“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成为他这一生的座右铭。
陈振民的父亲当时在出版行业工作,所以家里也有很多藏书,但在那个非常时期,那些书很可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为了免去后顾之忧,父亲让陈振民去废品回收站把书卖掉,当时,陈振民是含着眼泪把这些书带到长春路上的废品回收站的。他记得,有一位中年人就站在那里,看当他到陈振民的书后,当即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下,那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出于对书的爱护,陈振民就答应了他。
五里桥老年读书会成员陈晶龙老人是读书活动的积极分子,年轻时曾经两次被评为“振兴中华读书会”的先进个人。说起读名著的经历,陈晶龙说:“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候我们还是青年,有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作为我们的榜样是很好的。到1959年,国家刚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我响应国家的号召,到上海一个铁路建设工地去支援工作,那时是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我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在铁路工地工作时也是冷天,那时候我觉得保尔能挺过来,我也可以,是保尔的精神鼓励了我。”陈晶龙老人前年生了一场大病,在困难的时刻,又是这本书给了老人巨大的信念,支撑他与病魔作斗争,他觉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他的一生。
对于杜金海来说,也有一本名著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成为他心中最大的精神支柱,那就是《简 · 爱》。回忆起那时的艰苦岁月,杜金海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在生活上碰到的坎坷还是蛮多的,但每当我碰到坎坷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到简 · 爱,她在寄人篱下的环境里还能顽强地生活,所以我一直用这个故事鼓舞自己。”
那些疯狂买书的记忆
“文革”的结束使思想被禁锢了将近十年的人们一下子升腾起了对读书的渴望。38年前,张建平走进上海译文出版社报到,38年后,他恋恋不舍地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张建平记得,改革开放不久,文化部决定恢复外国文学的出版工作,当时在全国只有两家出版社能够出版外国文学著作,一家是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家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得到文化部的指示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外国文学名著《斯巴达克斯》。让出版社全体员工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一上市,就立马遭到了疯抢。经历了“书荒”年代的人们一听说有文学名著要上市,总会在新华书店门前排起长队,有时甚至要排通宵。
那时,就连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的张建平想要买到一本《斯巴达克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天,张建平和几个朋友相约来到淮海中路的新华书店买书,可没过多久,店员就把大门关上了,原来是加印的《斯巴达克斯》到货了。于是,被关在里面的读者幸运降临,每人都可以购买一本《斯巴达克斯》,等买到书以后,店员让张建平等从后门悄悄出去。当时,张建平还想再买一本《斯巴达克斯》,于是他也只得加入长长的排队买书的队伍之中。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年里,新华书店的门口经常排着见首不见尾的长队,那时,秦来来就曾经为了买到名著天还没亮就去排队,由于当时供给每个新华书店的图书数量有限,这对读者来说更加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感觉。秦来来记得那天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就连豫园派出所民警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这样的场面,秦来来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的读书活动的一个高潮啊。”人们争先恐后地买书、看书,用阅读来充实自己,这一不可再复制的场景在当时来说,却是再普通不过。
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精选了35本中外经典小说,一版再版,总共发行了150万册。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购书的读者最多的一天就有1.6万人,有的人买起书来不是一本一本地买,而是一叠一叠地买,而张建平也成了这套书出版发行的见证者。
他介绍说,这35本中外经典小说叫“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直到现在这套书在网上的旧书店里还卖得挺火。当时,这套书的名气很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书荒”。那时候由于大家都在抢购这些中外名著,使得市场上的供应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甚至连印刷的纸张都成了紧俏物品,用“洛阳纸贵”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为过。由于当时出的书少,看的人多,因此,爱书人中间还自发形成了一个换书市场。
沈嘉禄介绍说:“上海人蛮聪明的,他会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共享,书店门口会自发地形成一个交换市场,大家拿着自己看过的书,在那里交换。我有一本书,交换之后就可能看了五六本书了,我觉得这一幕非常温馨,上海人读书读到这个程度,应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

从十年“文革”里走来的那一代青年人,当他们走到改革开放的门口就像走出茫茫沙漠一样,把书店当成了生命的绿洲。那时候,如果谁有在新华书店工作的亲戚朋友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秦来来儿时就有一个小伙伴的母亲是延安路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因此他就经常托小伙伴的母亲买书。
阅读使人终身受益
20世纪8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上海拍摄了一条新闻,记录的是那些年的每个清晨,上海图书馆还没开门时,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的情景。因为到新华书店买书不易,再加上买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上海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也就成了很多爱读名著的人们热衷去的地方。
当时在徐汇女中旁边的校办工厂工作的胡展奋就在身边找到了这样一个读名著的好地方。工厂负责人知道胡展奋喜欢看书,就让他中午去图书馆休息,当时“文革”刚结束,来图书馆的人还不多,于是胡展奋就自得其乐地看了很多好书。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当年是在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复旦的图书馆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文学的宝库。金光耀在考入复旦前,并没有看过什么文学名著,进入大学后,在研读大量专业书的同时,他还没日没夜地看了很多文学名著。回想起那段经历,金光耀说:“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和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知识饥渴是联系在一起的。”
1981年,孙嘉明从黄山茶林场回到上海,同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他的读书欲望也是在大学校园和书店里得到满足的。那时候,他经常去福州路买书,收集书籍成为他的一大爱好。经过了30多年的积累,孙嘉明拥有了自己丰富的藏书,最近他正在整理这些书,打算把它们全部捐献出来,送给有需要的老师和同学。孙嘉明教授是这样说的:“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地点在美国,接触的也是英文,而且这些书分量很重,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带去美国。我想把这些很有价值的书分享给我的同事、同行,让它们在合适的人手里,再一次焕发出它们的生命力。”

在一批批的中外名著重新走进人们的读书生活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用于收藏的精装本世界名著—“外国文学名著珍藏本”。这套书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它不仅满足了人们阅读和收藏的需要,更成为当时赠送给朋友的最佳礼品。
千里姻缘一书牵
当年,“文学墙”的出现是一个新生事物,文学青年可以在这个园地谈名著、聊文学,因为到这里来的大部分是青年人,所以还有一部分人也在这里找到了爱情。胡展奋有一位朋友很喜欢诗歌,有一次,他把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抄下来,贴在了“文学墙”上,有一位女孩子看到后就堵住了他,向他要济慈的诗来读,这样一来二去的,很自然地就有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七八十年代上海兴起的这股读书热的确影响到正在谈婚论嫁的男女青年们。那时候的年轻人结婚讲究的是“三十六条腿”,而从小就爱读名著的卢其芬对丈夫的要求居然是要有一张书桌和一盏台灯。她渴望结婚后能在书桌旁安安静静地看书,而她的爱人也实现了她的梦想。沈嘉禄和他的太太也是在一套名著的牵引下开始走上爱情道路的,《战争与和平》成了他们之间永恒的信物。陈振民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他把一部名著里的故事讲给一个女孩子听而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就是那一本本的文学名著给了那个年代的人一份精神上的富足和希望,支撑了许多年轻人的日日夜夜,为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点上了一盏明亮的灯。
选自上海音像资料馆编:《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
(本文题图:剧照 | 《大江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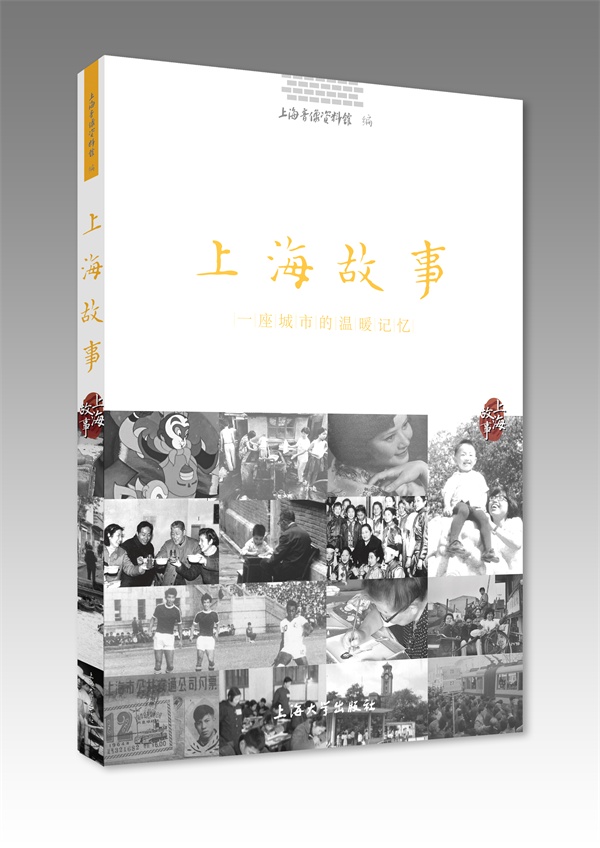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