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愤怒激发了……一个诗人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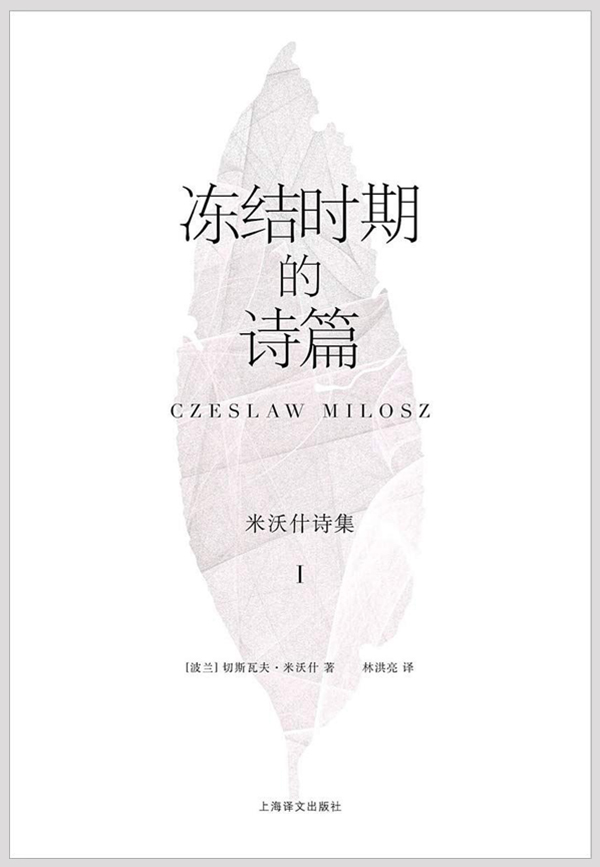
前几天当我正在读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冻结时期的诗篇:米沃什诗集Ⅰ》(林洪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的时候,传来新西兰发生恐怖枪击案的消息。震惊之余,猛然体会到什么是“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出自授予米沃什诺奖的颁奖词)。所谓的“赤裸状态”,就是一种难以逃避、无所依凭的状态,伴随着无法言述的悲剧感与痛苦,无法用概念、逻辑或善与恶来简单定义。米沃什在该书的“前言”说自己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恐怖现实,我也只能暂时中断在他诗歌中的遨游,转而思考新西兰恐袭案所引发的议题。
过去人们相信,恐怖主义总是与意识形态的信念有某种紧密联系,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经从相反的角度说的那样:在任何意识形态的下面,你都能发现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现代史叙事中,亦有启发;9·11以后各种穆斯林恐怖分子恐袭案中的“人肉炸弹”等极端方式,也强化了行为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恐袭例子说明与意识形态信念的联系并非那么确定、那么清晰,换言之,要确定和消除恐袭行为的个人动机变得更为困难。比如,这次新西兰恐袭的凶手自称在年轻时候是共产主义者,然后又变为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最后是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可见简单地挂上某一意识形态的标签是靠不住的。又比如,这个凶手的确有理由被称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他又自称对他影响最大是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 )——一个美国黑人女政治活动家,以保守主义和极端观点而冒尖。实际上在他的宣言文本“大置换”(The Great Repalcement)中充满了不无思考的观点糅合和或许是故弄玄虚的概念拼贴,再加上充分利用影像拍摄与即时发布的传播技术,使整个恐袭行为不再是单一的枪击事件,而同时更具有通过社交网络和游戏门户向主流媒体挑衅的传播性质。而为了抵御凶手的这一传播意图,网络平台的删帖也成为一种双面刃,反而使舆情更加撕裂。不排除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与枪击同步的文化恐袭策略,或者可以说这也是恐怖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也不能因为这个文本思想内容的芜杂、拼贴和肤浅而忽视了作为恐袭个案研究的价值。
关于移民问题,大概谁也无法否认的是西方国家的移民福利政策早已带来很多负面的社会问题;而且历年来在处理这些问题甚至是罪案的过程中,在反种族主义口号的影响和干扰下,法治的价值观与权威蒙受耻辱。更不用说在这个枪手的弹夹上用英语和其他几种语言所写的那些发生在现实中的恐袭事件和历史上反抗伊斯兰的战争,不能否认的是一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绵延的纠缠不清的悲情。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丝毫不能为凶手的罪责开脱,但是必须反思,这次新西兰恐袭案最令人忧虑的是极端种族主义和报复主义危机的蔓延。无可否认,这次新西兰枪击案的确反映了极端种族主义发展的危险势头,但是也要分辨的是,这种白人至上主义与关注白人人口变化等问题的右翼团体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如果就连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早在五十年代末就说过虽然法国向所有种族敞开,但前提是有色人种只能占少数;否则法国就不再是法国,“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白种人的,继承了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的欧洲民族”。(出自Alain Peyrefitte撰写的、1994年出版的传记《这是戴高乐》,也有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有怀疑)这样的话,那么在今天讨论和正视这个问题就不能说都是白人至上主义作祟。更要看到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面临不同族群的人口增减变化、难民危机与移民冲突、在多元文化口号下的共同价值观危机等严重问题,而且在现实冲突中有越来越多的历史事件、文化元素被召唤出来,充当动员与传播的象征符号,因此长期以来在“政治正确”与“政治禁忌”的影响下难以展开平等、自由的公共讨论的局面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应该看到,一方面是主流媒体的顾忌、自我约束和固化在政治正确的苍白话语中,另一方面是极端主义思潮通过各种鲜活的、有效的手段实施的传播影响,结果必然出现思想和舆情的乱象。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他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原书名: Identity and Violence,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中指出,驱使着暴行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可解脱的仇恨,还有人们的思想混乱:“确实,概念混乱,而不仅仅是恶意,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们周围发生的骚乱与残暴承担责任。”(见该书“引言”)。他的用意当然不是要求舆论一致,而是希望从思想观念挖出极端主义思想的病灶,引导人们走出单一的和固化的身份观念误区。

谈到移民问题,社会学家鲍曼曾经在他题为《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的文章中集中探讨了“移民恐慌”的时代症状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危机都是根源于一个事实——当世界性困境已经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事实上却仍然缺乏世界主义意识、理念或态度,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产生尖锐冲突。(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38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我相信这是实情,也可以从当代世界史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证实。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困境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战争状况?遗憾的是鲍曼最后只能从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声明中找到答案——“我们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对话文化的发展,从而重建社会组织。……和平将是持久的,只要我们用对话这一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如何在相遇与协商的论争中打一场完美的胜仗。”(同上,45页)这固然是很美好的可能性,但是,把这种理想与呼吁放在产生“移民恐慌”的充满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现实语境中,恐怕只是一句空话。又比如,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上述著作中正确地指出了冲突与暴力都受单一身份的幻象影响,分析人们如何自愿地或被迫地仅仅根据宗教立场或文化认同来划分世界和选择行动,而忽略了本来还具有的多种身份——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文学、科学、音乐、道德或政治立场,从而否定了合理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和本应共享的人性。对于这种“单一身份”论,我们实在并不陌生,不就是那种时刻不能忘记的以所谓的“阶级”划分敌我的洗脑大法吗?但是,森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是提出理性与自由选择优先于身份,强调要以自觉意识到身份的多元性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来消除冲突与暴力的基础;他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这一理念,世界就能够消除暴力、迈向和平。事实上,这也是我在阅读了一些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后产生的最大困惑:在无疑是正确的愿景、呼吁与在现实中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改造方案或重建方案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然,或许这本来就不是哲学、伦理学所能承担的任务。话说回来,我们也必须承认,哲学思考仍然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尤其是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上帮助我们思考现实中的敏感议题。例如,在《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依高·普里莫拉兹编,周展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一书中,依高·普里莫拉兹在他的文章里援引了汉娜·阿伦特关于集权主义的理论,说明在集权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体制化的恐怖主义”,它是“企图全面控制社会的手段”(48页)。该书第三部分以“国家作为恐怖主义者”为论题,依高·普里莫拉兹在他的文章里指出:“国家恐怖主义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许多事务弄得相当复杂,其中充斥着秘密、欺诈和伪善。当涉及恐怖主义时——不管是国家机构直接实施还是通过代理进行——国家会偷偷摸摸地干,却对外宣称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并声称它所遵从的价值和原则本身就排除了恐怖主义的可能性”(167页)。更具体的分析是托米斯·卡皮坦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以色列政府通过使用“恐怖主义”修辞来掩盖自己的国家恐怖主义,并且以这种修辞来抹煞恐怖主义的历史起因和转移对现实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的关注(238-254页)。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例子说明“恐怖主义”修辞与国家恐怖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可能的恐怖主义与现实的国家恐怖主义和道德灾难之间,选择是痛苦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回到米沃什的诗歌。他说“我经历了二十世纪恐怖的一幕又一幕——那是现实,而且我无法逃避到某些法国象征主义者所追求的‘纯诗’的境界中去。虽然有些诗歌仍保有一定价值,比如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华沙、在犹太人居住区熊熊燃烧时写的《菲里奥广场》,但我们对暴虐的愤慨少有得当的艺术性文字来表现”。诗人承认在现实的暴虐与恐怖面前,诗歌的无奈与无助;但是即便如此,“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由此而言,米沃什强调诗歌具有传达精神反抗的作用,认为“诗歌一直以来都是我参与时代的一种方式”。(同上)虽然有“精神反抗”之语,但是作为诗人,他更是常常难以自拔地坠入到总是在内心盘旋的风景、痛苦和敏感之中,他敏感于风景的所有细节、光线中的任何变化、预感中的所有灾难。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什么是单一的、纯粹的,无论是阳光还是阴影,是和平还是战争,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有复杂性。当他平静地说, “而在街上,一辆 / 坦克驶过,还有一辆有轨电车 / 在叮叮当当作响,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华沙,一九四一,41页)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一幅真实图景却是那么复杂与沉重。
《菲奥里广场》为什么被视为米沃什的重要代表作?米沃什自己说,他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华沙,在犹太人居住区熊熊燃烧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歌。他是华沙犹太区惨案的目击者与见证人,这首诗的性质准确来说就是见证文学中的著名诗篇。而作为见证者,米沃什的使命是以一己之力抵御整个民族的冷漠与失忆,以对现实的见证和对记忆的追寻抵御“人性事物的消失”。在华沙,当犹太区遭受暴行的时候,他被周围人们的冷漠与麻木所刺痛,由此而想到了罗马的菲奥里广场,想到那个为了追寻真理而被作为邪恶的异端分子烧死的布鲁诺,深深地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冷漠与失忆感到痛苦和愤怒。“正是在这座广场上,/ 他们烧死了乔丹诺·布鲁诺。/ 刽子手点起了被观众紧紧 / 围住的火刑的柴堆。/ 在火焰熄灭的那一刻,/ 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 一筐筐橄榄和柠檬,/ 又扛在商贩们的肩头上。”(41 页)这不正是鲁迅笔下的那些看客吗?“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傍晚,/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在欢快的乐曲的声响中,/ 我想起了菲奥里广场。/ 欢快跳跃的旋律淹没了 / 犹太区围墙内的枪炮声。/ …… 愉快的人们放声大笑,/ 在这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有的人读出了道德的含义;当华沙或罗马的人们 / 走过殉难者们的火刑堆时,/ 还在讨价还价、嬉笑、求爱。/ 而另一些人则读出了 / 人性事物的消失。/ 读出了人们忘性的增长,/ 在火焰熄灭之前。(42 页)但那时候我只是想到 / 垂死者的孤独,/ 想到乔丹诺当时 / 如何爬上他的火堆,/ 他无法在人类的语言中 / 找到这样的一个词句:当他在告别人类之前,/ 留给活着的人类。// 他们已跑去喝酒了,/ 或者在叫卖他们的白海星。/ 一筐筐橄榄和柠檬,/ 他们谈笑风生地扛着它们。/ 但他离他们已经很远了,/ 仿佛过去了好几个世纪。/ 当他在火堆上升天时,/ 他们仅仅停留了一会儿。// 那些死去的孤独者,/ 已被世界所忘记。/ 他们的语言让我们感到陌生,/ 就像是来自古老星球的语言。/ 直到一切都变成了神话,/ 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在一个新的菲奥里广场上,/ 愤怒激发了一个诗人的话语。// 华沙,一九四三”。(43 页)现实见证者与历史追忆者的身份交织在一起,杀戮与谈笑重叠在一起,孤独是孤独者的命运,遗忘的发生竟然就“在火焰熄灭之前”,犹在耳边的语言一下子变得极为遥远、古老和陌生,所有这些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就这样,“愤怒激发了一个诗人的话语”;就这样,在米沃什写下这些诗句多少年之后,愤怒同样激发着无数阅读者的话语。有时候,看起来是愤怒的情绪使他的诗句变得异常直率和粗粝,不再讲究诗意:“在你周围有一帮阿谀奉承的小丑,/ 你一意孤行,把善恶是非全颠倒。// 虽然大家在你面前屈膝卑躬,/ 夸你多么英明,多么高尚 / ……你切莫心安理得,诗人记得很清。/ 即使你杀了这个,另一个又会出现,/ 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记录在案。/ 冬日的早晨,压弯的树枝 / 和一条绞索对你最为合适。”(《你侮辱了……》,114页)甚至有点寒光闪烁在诗句间。
米沃什的组诗《世界(天真的诗)》中有一节题为《找到》,是父亲在回应儿子在恐惧中的呼唤:“我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无谓的恐惧!/ 黑夜即将过去,白天很快就会来临。/ 你听,放牧人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条形红带上的星星正在变白。// 路是直的。我们正在树林边上。/下面村子里,钟声已经敲响。/ 公鸡在篱笆上欢唱黎明的到来,/ ……这里依然很暗。雾像条涨水的河,/ 笼罩着一丛丛黑色的越橘树。/ 但黎明已踩着高跷涉水而来,/ 太阳的火球正在隆隆地升起。”(57 页)这既是两代人之间的呼唤与安慰,也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搏斗与交替;在这里,在这时候,所有的恐惧其实都是无谓的——也就是不必要的,这种关于恐惧的态度可以使人想起那句名言(“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一般的歌颂黎明如何驱走黑暗不同,米沃什在这里要歌颂的是对黎明的盼望与信念是如何战胜恐惧。这里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声音,比如艾青的《黎明的通知》:“为了我的祈愿 / 诗人啊,你起来吧 //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 / 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 ……”但是,米沃什的“找到”没有艾青的“通知”那么浪漫和高调,也没有那种敏感于政治的转变,甚至带有一点沉郁与忧伤的气息——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实的“黎明的通知”;他只是希望“找回我们失去的一切;/ 星星和玫瑰,夕阳和黎明”。(57页)
《可怜的诗人》再次提到了那个“愤怒的诗人”,他“眨巴着眼睛,充满着恶意,/ 手里掂量着一支钢笔,/ 我正思谋着复仇。/ 我拿起了笔,它长出枝叶,覆盖着花朵,/ 但那树的气味却肆无忌惮,因为那里,/ 在真实的大地上,/ 这样的树不能生长。那树的气味,/
对受苦的人类是一种侮辱。”(62页)这里必须停下来,必须询问:在真实的大地上,树的生长和它的气味为何是“对受苦的人类是一种侮辱”?为什么“这样的树不能生长”?近日读到一位中国诗人的新作《你不可以这样开花》,仿佛是对大半个世纪前的波兰诗人的最好回应:“海棠和梨树突然开花了 / 看见满树缤纷 / 顿时我崩溃了 /……这样纯洁 不染纤尘 / 这样简单 安静 / 而且真实 / 你让我蹲在树下抱头 / 你让世界蒙羞 // 不可以 在这样疯狂的春天 / …… 一个震惊世界的枪手 / 而且 他的爱震慑了我 / 唐诗宋词里找不到 / 那是谁的中国 // ……在高高扬起的鞭子下 / 在准备施刑的凶手的注视下 / 在已经被淡忘的今日 / 16年前一个逝去的名字 / 你 竟一如既往地开花了”。是眼前盛开的鲜花与心中无限的悲伤,使这位中国诗人在飘落的花瓣中只能抱头坐下,恨不得让自己化为泥土,“这样就没有人能打扰我 / 悄悄地嚎啕大哭”。(艾晓明《你不可以这样开花》)
米沃什继续谈到绝望与希望,猛然间就像抽向我们心坎的鞭子,令我们疼痛:“然而给予我的却是否定一切的希望,/ 因为自从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有大火和大屠杀,/ 看到的只有欺压、侮辱和吹牛者的可笑的羞耻。”(62 页)这种绝望的痛苦在《在华沙》中变得更为悲怆:“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这里每一步脚都能踢到 / 未被掩埋的亲人的尸骨。/ 我听到声音,看到了微笑,/ 但我却无法写作”,最后诗人只能“不断重复着两个被拯救下来的词:/ 真理和正义”。(81页)那么,诗人和诗歌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救不了国家,救不了人民的 / 诗歌是什么?/ 和官方的欺骗同流合污,/ 变成快被割断喉咙的酒鬼的歌曲;/ 变成天真少女们的闲暇读物。// 我期望人间的好诗,但我无能为力,/ 我发现了它高尚的目的,但太晚了。/ 它的目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拯救。”(《献词》,83页)这里的拯救,只能是诗人的自我拯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