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静波︱日本的近代,为何至今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一
在日本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三谷太一郎教授,在他八十一岁高龄的2017年,推出了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以下简称“本书”),在日本的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内立即在今年6月由社会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译本。
论述日本近代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日本的近代,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它的内蕴是那么斑驳复杂,它衍生的结果又是那么歧异多变,以至于很难对其进行一目了然的、穿透式的审察,导引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因而出现了各个领域内如此之多的微观的、具象的个案研究、实证研究,乃至像三谷教授这一类宏观的大著。不仅日本人自己非常关切这一话题,近邻的东亚诸国乃至遥远的欧美,世界范围内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论著和无数的论文问世。
本文想围绕三谷教授的这部著作,或者借着这部著作的问题史意识,讨论两个或许是老生常谈却仍未获得明解的问题:一、为什么通常意义上的“近代化”,在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至二十世纪初期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除了本源地欧美之外,全世界只有日本实现了?二、为何日本的近代化导致了极为强烈的帝国主义化?帝国主义是日本近代内生机制的必然结果吗?
二
三谷对近代的理解和解释,是基于英国政治社会学家白芝浩(W. Bagehot,1826-1877)的理论,即一个称得上近代国家的基本政治运作方式是“基于众议的统治”(governance by discussion,日文的表述是“議論による統治”,中译本为“基于讨论的统治”),以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为蓝本,而近代之前的统治方式则是“基于习惯的统治”,这里的习惯主要是传统、惯例的做法,相对而言,是一种保守的、专制的方式。日本在近代之前的天皇及幕府的统治,基本上是后一种形态。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在经历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革命之后,政治上已演进到了以“立宪”为基本特征的“基于众议的统治”,这是欧洲(后来又加上北美)近代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欧洲资本主义的进程,就是以“基于众议的统治”为基轴,在不断发展的近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通过“贸易”和“殖民地拓展”这两翼来展开的,并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西方近代文明。这一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无疑已在世界上确立了优势地位,并通过海路不断向全世界扩展。
这一扩展在日本的结果,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两次进入日本领域,并在1854年1月强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尔后日本又在1858年被迫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这一开场,与中国的情形基本相似,只是中国差不多每一次都要以战争的方式进行抵抗,而日本则放弃了与西方的武力对抗。至于大院君时代的朝鲜,则是坚决抵抗西方势力的进入,并在一开始获得了成功。
面对西方的“近代”,上自幕府,下至各地的藩主和民间有识之士,都在认真地思考如何应对。幕府果断废除了持续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开始与外部世界交往,在非常有限的财力下,1860年派遣“咸临丸”前往美国,1862年派遣商船“千岁丸”来到中国上海。从两边获得的情报,使日本人清晰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剧变,西方的新文明正在灿烂地崛起,而传统的东方大国满清帝国则在无奈地衰落。
日本朝野都在苦思冥想如何在这急剧变化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当政的幕府以及一批民间的有识之士(如福泽谕吉等)已在与西方的交往中,逐渐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并试图迈开有限的步伐来汲取西方的先进元素,但地方上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等则表现出了与西方的强烈的对抗意识,并在1862年和1863年主动挑起了袭击英国人的“生麦事件”和在关门海峡炮击美国商船的事件,结果都在翌年分别遭到了英国人和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的猛烈反击,被打得一败涂地,由此彻底放弃了“攘夷”的姿态,改而主动向西方学习(萨摩藩就在1863年的“萨英战争”中被击败后,偷偷地瞒着幕府向英国派遣了十九名留学生)。后来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成立,统治者虽有更迭,而其基本方针,实际上是沿承了幕府已经开辟的路线,只是在具体的做法上更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还是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即为什么在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至二十世纪初期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除了本源地欧美之外,全世界只有日本实现了近代化?我的理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及以后的几十年里,面对西方文明以武力为背景的强势冲击,差不多只有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而在东亚的中国和朝鲜,则囿于深重的历史因袭,碍于沉重的祖宗之法,不愿意看到西方文明在当时相对于东方传统的先进性。魏源看到了洋人在“技”上或许胜于中国一筹,但目的还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头脑比较开通的如冯桂芬,也仍然主张要“以中国伦常之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1页),并未想到要对中国的传统进行变革和改造。相比较而言,福泽谕吉则在1868年就提出了“文明开化”这个词(《西洋事情》外编),并在《文明论之概略》(1875年)中明确认为:“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洲诸国,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福沢諭吉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59年,16页)进而指出:“现今世界各国,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同前,19页)这一认识,不久就成了日本朝野的主流意识。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识,是基于多次的实地考察(福泽谕吉曾在1860-1867年三度访问美欧,明治政府的“岩仓使节团”在1871-1873年对欧美进行了两年多的深入考察)之后形成的,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则完全没有这样深入的直接接触。因此,日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以欧美为楷模,全面实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用三谷教授在书中的描述,就是在具体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进上,通过改革地租等方式来最大程度上获得国家的财源,而避免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以免受制于外部的势力,即在最初的近三十年中,走了一条“自立的”资本主义道路,即几乎所有近代化行为的发动者,都是日本人自己。
那么,在政治运作上,又如何将“基于习惯的统治”转换成“基于众议的统治”呢?三谷教授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认为一个时代的变革或转换,既与前代有割裂的地方,也有沿承的部分,在幕府时期的统治方式上,实际已存在了“众议”的方式,即将军的决断,都要在幕府内部的上级官吏会议上进行比较充分的议论之后做出,无形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机制,只是在明治以后,将其演变成制度性的议会及宪政形式,在经过了启蒙思想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的朝野都普遍乐意接受这一“基于众议的统治”的形式,从而在制度上达成了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而中国的传统政治中,这种“众议”的元素则一直非常弱,虽然推展了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但在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上则拒绝了西方的“近代”,因而无法达成“基于众议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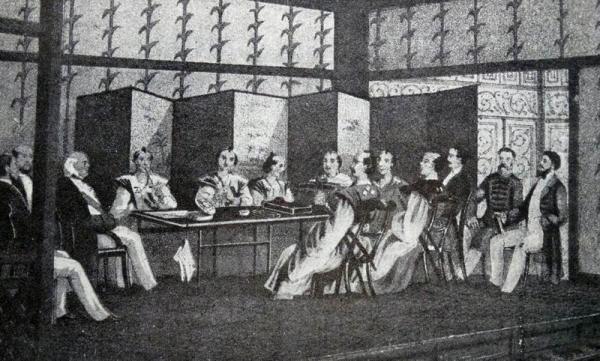
三
那么,日本在达成了西方基准的近代化之后,为何最终走向了三谷教授称之为“殖民帝国”的道路呢?三谷教授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期间,开始从自立的资本主义转变成国际资本主义,其重要的标志有两个,一是1894年开始,日本陆续与西方列强修改了此前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关税自主权,政府在财源上有了新的增长;二是开始在国际上发行外债,外国资本开始进入日本,日本在经济上与全球连在了一起。
但是,日本没有仿效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即以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来迫使贸易对象国让渡出更多的利益,而是走上了“殖民帝国”的道路,“日本的殖民帝国的构想,较之对经济利益的关心,更多的是以对军事安全保障的关心为出发点”(本书161页)。三谷此话的潜台词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从这一逻辑出发,山县有朋首相1890年在议会的演讲中提出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自然就获得了正当性,当时日本设想的利益线,是在朝鲜半岛(因而后来策动了企图占有朝鲜半岛的甲午战争),到了1920年代末,则把“利益线”演变为“生命线”,那时生命线的范围则是在中国的“满蒙”了(因而在后来策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其实,1890年前后,日本是有一批人主张对中国等实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而非走“殖民帝国”之路的,军部出身的荒尾精等,以他们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经历,主张通过贸易的方式在中国获取日本的国家利益,因而费尽千辛万苦,筹资在上海办了一个“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日本对华的贸易人才,并编纂了厚厚两大卷的《清国通商综览》。日本当局也试图在1879年底借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琉球问题之际,向中国提出过签署享有与欧美国家同等优惠待遇的贸易条约,但遭到了当时中国的拒绝。后来日本的执政者意识到,如果没有与欧美国家同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背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恐怕不易实施,索性选择“殖民帝国”道路,其利益的获得,应该远胜于所谓的“自由贸易”,虽然后者的成本会比较高。
事实上,老牌的英国法国等,差不多同时实行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殖民帝国”两条路线,以武力扩张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也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内生性之一,也决定了日本的近代一开始就伴生着帝国主义的内质。明治伊始,就急切地把虾夷之地(1869年定名为北海道)正式归入日本的版图,1879年又用武力的方式强行“处分”琉球,使之成为日本的一个县,一直到后来的甲午战争,试图占有原先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朝鲜半岛,并最终占有了中国的台湾,继而又不惜与俄国大动干戈,来确保它在朝鲜和在南满的优势地位,占有了萨哈林半岛的南部,再进而吞并朝鲜,在它本土的周边,建立起了象征着帝国主义得以成立的殖民地。而三谷教授对这些“殖民帝国”行为的解释,是因为日本要确保自身的军事安全保障,从而轻轻抹去了日本在以武力为背景的“殖民帝国”路线的实施中,对被殖民、被占领地区的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
四
在1920年代末凯末尔(M. Kemal,1881-1938)赢得了政权并对土耳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仿效西方的改革、奠定了土耳其作为一个近代国家基础之前,全世界恐怕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完成了从前近代向近代国家的转型。之所以获得了大致的成功,第一是日本人的行动理念从根本上来说是现实主义者(三谷教授用了“功能主义”一词),它虽然也拥有两千来年的文明史,但它的主要文明资源几乎都是来自海外(农耕和金属文明、儒教和佛教),因而自身并无太沉重的历史因袭,早期与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使得它很快就服膺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因而产生了比较坚定的变革自身的内在动因,并且涌现出了一批比较明智的领袖,朝野互动,在大约三十年的时期内,在重要的领域中大致完成了向近代的转换。或许,日本传统政治中存在的“众议”元素,也是作为近代国家最重要标志的宪政能够在日本成立的基础之一。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的时代,近代的成立是否意味着一定会走向帝国主义?三谷教授的著作中回避了这一问题。我认为,近代的日本之所以蜕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先后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乃至德国,都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武力扩张行为,以武力为背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美国虽然避免了殖民地形式,却是建立了明确的势力范围(东亚、中美洲和菲律宾等),仿效西方完成了近代进程的日本,自然也沿承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内生性。
另一个可以从日本自身去探寻。依照三谷教授的解释,明治的领袖们意识到西方的近代背后有一个精神性的功能元素——基督教,于是决定将天皇定格为“现人神”的天皇制来取代基督教。我觉得,明治领袖们用来取代基督教的应该不是天皇制(天皇制古已有之),而是炮制了一个将天皇祖先神格化的“国家神道”,然后以国家神道在精神上将全体国民凝聚起来,将日本推举到“神国”和“皇国”的境界,把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鼓胀起来,将“国权”(国家利权)作为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三谷教授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的《教育敕语》,实际上是向青少年灌输“国家神道”的工具,弱化个体的合理性,强化集团的正当性,从而在实质上大大削弱了“基于众议的统治”,强化了统治的独裁性。这实际上是对近代西方思想的一个违逆,是有悖近代的基本原理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战前的日本近代与西方的近代之间是有相当睽隔的。在一个没有充分民主的政体内,很容易滋生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并且很容易借着国家的名义向外推行武力扩张,最极端的阶段,就是军国主义。对这一点,三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触及,但是他提炼出的两个关键词“基于众议的统治”和“殖民帝国”,倒是概括出了日本近代的本质,只是到了1930年代前后,前者日趋弱化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