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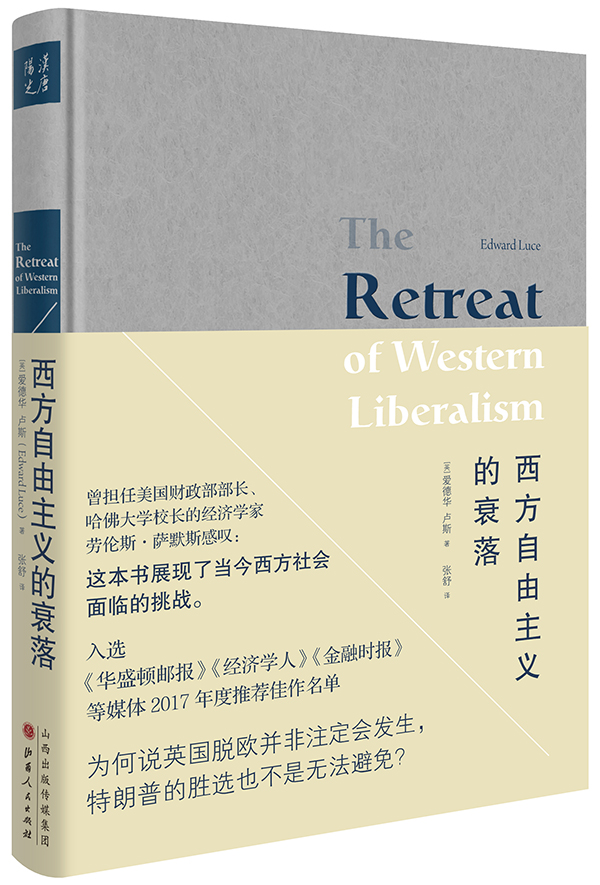
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原作名: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原书出版于2017年;张舒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从书名上看是一个既有社会政治发展和思想史脉络的宏观视野又有对西方各国状况与趋势的深入剖析的大题目,似乎是一部煌煌巨著才能胜任的论题。但本书只有10万字左右,作者估计阅读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作者在“前言”中承认“这个主题毫无疑问地超出了我认知的深度”,在最后的“致谢”中表示“一个作者胆敢处理这样一个涉及如此多国家,深入、广泛且历史错综复杂的主题——而且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交稿,看上去有些荒谬”。但他并不认为应该为这种大胆的尝试道歉。在我看来这正是该书充满思想激情的魅力所在——它是在敏锐观察与危机意识的强力催化中产生的思想急就章,是在深深的政治恐惧与希望中发出的警言。更使我另有所思的是,作者在“致谢”中说:“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居民(现居美国),曾经在另外四个民主国家生活的居民,以及经常出入更多民主国家的旅行者,我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怀有热情……我也是小女儿咪咪的父亲。当我想到她的未来时,我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希望与日俱增。每个人都有资格为他们的孩子成长所处的社会感到担忧。当我想到自己年过八旬的父母时,更是五味杂陈。我知道他们整个一生对这个世界未来的担心就从未减少过。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无力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肯定能够阻止我们的社会陷入新的黑暗时代。”(192—193页)值得思考的是,作者为什么要那么强调个人经历中的“民主国家”?什么是对社会的政治前途所怀有的热情?为什么在想到下一代未来的时候会感到恐惧和希望与日俱增?什么是父辈们从未停止过忧虑?在作者看来,我们即便不考虑自己,难道不应该为孩子一代的未来有可能陷入的“新的黑暗时代”而忧心并奋力阻止那样的时代到来吗?把“我们的政治前途” 的危机感与既为人子亦为人父的责任感联系起来,并且坚信“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15页),我感到在这里有一种催迫读者倾听的力量。无论深浅、对错,就因为这份危机感和责任感,作者真心期待读者的参与,因此祈求与读者立下阅读协议。如果读者在阅读时心不在焉,我甚至想象作者会脱口说出亚瑟·佛莱克(Arthur Fleck)的那句台词:“You don't listen, do you?”(你没有听我说,是不是?)
爱德华·卢斯是英国新闻记者,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特区的首席美国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此前曾任《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和新德里南亚分社社长。他于199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学位(简称PPE),卢斯知道作为大学精英的PPE学生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关于西方思想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自负,有着近乎信仰的进步论思想。1995年他进入英国《金融时报》,最初在菲律宾从事新闻报道,此后曾在华盛顿特区担任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讲演撰稿人。他在担任《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期间曾经与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参议员唐·里格尔(Don Riegle)等公职人员以及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商业领袖以及教师、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科学家进行过访谈。他的工作经历为他的全球视野和思考西方危机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前一本书《是时候开始思考了:美国与衰落的幽灵》(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and the Spectre of Decline,2012;另外一个版本的副标题是“蜕变时代的美国”——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中论述了席卷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和民众的不满,对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衰退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将这一图景和分析扩展到了西方世界。在该书中,“作者爱德华·卢斯立足于对历史上一些相关重大事件的回顾,以自由主义的困境作为切入点,宏观纵览,针砭时弊,展现了当下西方社会的种种复杂境况。在卢斯看来,西方世界面临的危机由来已久,并非仅仅在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也不会快速消失——这种危机是结构性的,很可能持续下去。而问题的解决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尤其需要有意识地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见该书推荐语)《经济学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敏锐而又适时的调查成果。卢斯是精明的观察家,通过快速的叙述节奏以及对数据的展示,带领读者进行了一场充满见解的旅程,穿越了以往未被重视的地带”。这是对该书比较恰当的描述。该书出版以来得到不少好评,入选《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媒体2017年度推荐佳作名单以及被亚马逊网站评为2017年度百部最佳图书之一。

全书以作者当年和同学一起驱车去柏林投入那股推倒柏林墙的洪流开始讲述。“在冷战时代核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想要一睹这个时代符合自然法则的消亡,这种诱惑难以抵挡。”那些挥舞着凿子和铁镐的年轻人在这场历史性的狂欢中建立友谊、分享香槟,“还有什么能比陌生人的香槟更适合庆祝这个新时代呢?”(2页)那几位牛津大学的PPE学生被乐观情绪所感染,自以为掌握着开启当下时刻历史意义的钥匙。这是与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中的终结》中表达的“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相同的感受,但是在30年后作者说“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似乎都已成为陈年旧事”,历史发展的必然论难以立足。作者在书中一再申明“没有什么是预先设定的”、“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思想的双面刃,西方自由主义无论是胜利或衰落都不是必然的,为此应该学会的是怀疑、思考,让理智在这个过程中经受考验。在这样的理性思考中,该书分为四个论述主题,第一章“核聚变”解释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它对西方经济的激进影响,严重的问题是西方中产阶级收入的下行压力;第二章“核反应”解读了由此引发的西方政治的衰落;第三章“放射尘”探讨了美国和西方霸权衰落的可能后果;最后一章“半衰期”探索了如何应对的问题,“除非踉踉跄跄的西方国家弄清楚冲击它们的到底是什么,否则它们根本没有机会从内部拯救自由主义”。(14页)以核爆过程为标题是对危机、冲击与挽救的形象表述,颇有一种警世的用意。作者在“前言”将结束的时候说,“西方的危机是真实的、结构性的,很可能会持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有些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要很清楚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此外,还需要有意识地努力从陌生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承认西方对真理或德行没有垄断权”。(15页)这种自我反思的分析精神贯穿全书。在卢斯看来,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与在世界范围中的经济增长背景下的西方中产阶级经济收入的明显停滞以及穷人生活经济的衰退有密切联系,简单说来就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带来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本表征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自由民主思想对社会的凝聚力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典型事件就是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这是一种经济与政治的内嵌式关联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也不陌生,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这种关联绝对化,以为只要经济不出问题,政治的实然就可以视作应然。卢斯认为要解救西方自由主义危机的关键在于认清并消除导致大面积不满的因素,例如他提到要实行普遍的医疗保健、实施人道主义移民法、坚决简化税制、启动各种“马歇尔计划”对中产阶级进行再培训等等,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堕入仅仅以经济解救政治的肤浅或功利的谬见之中。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危机是政治性的,因此解决方案必须远远超越经济层面。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总是适合20世纪纷繁复杂的情况。但我相信,保护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免遭任意噩运的伤害,是对我们文明价值的最终考验”。(183页)他认为校园和媒体都应保持言论自由,“应该重新设想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最重要的是,必须打破金钱对立法过程的钳制”。(184页)
卢斯对于互联网时代的趋势有一段相当深刻的分析:“奥威尔设想了一种未来,其中监视一切的专政统治会扑灭自由思想并且取缔人类的亲密关系。但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比起《一九八四》,更接近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恐惧是老大哥会一直看着你。赫胥黎的恐惧是我们会沉溺于在电视上观看老大哥,其他什么都不在乎了。如果人们不去阅读,就不需要禁书了。”(131页)他接着谈到普京,“相比于奥威尔,弗拉基米尔·普京是赫胥黎更好的弟子。20世纪80年代,当他在德累斯顿担任克格勃特工时,当地大多数人可以通过他们的发射机接收来自西方的电视节目。这些是政治上最平静的东德地区。他们才不会被西德的新闻所吸引——他们迷上的是《豪门恩怨》、《海滩护卫队》和《王朝》”;“空想家们相信革命会在Twitter上传播。普京主义者认为,他们更乐意消化西方的娱乐节目,不会在意其他事情。俄罗斯人不会去读异见人士的博客,而是去迷恋小猫咪和唇语。”(132页)在信息越是自由的地方,人们越是不在乎某些事情,这似乎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实。
有评论者注意到卢斯对达沃斯精英们的自尊心怀有深刻而正确的谴责(英国《文学评论》),在书中卢斯的确是通过分析达沃斯论坛表达了对西方政治、经济精英们的不信任,例如他认为“每年一月份,达沃斯论坛上的发声听起来并不太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用诸如市场弹性、全球治理、多方利益合作以及数字化广场等流行术语来表达,以为这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针对每一种风险,达沃斯提供了千篇一律的解决办法。大部分抑扬顿挫的措辞听起来无伤大雅,但是这种词汇与密切关注公众舆论的世界观背道而驰。”(67页)但是卢斯对达沃斯的判断也有严重看走眼的时候,在这里他似乎还是容易被“抑扬顿挫的措辞”及其背后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果说在十年前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她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中译本前言”说的关于“你们”将如何、“我们”将如何寄希望于“你们”的那番话还情有可原的话,卢斯在2017年对达沃斯的判断可真是有问题。
当然,无论如何他还没有失去他最为忧虑的问题意识:“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在全球力量的巨大转变中存留下来,是本书关注的问题。答案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而我们迄今为止做出的回应却在加速这一转变。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正是西方未能接受它所面临的现实的一个具体写照。”(26页)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书中许多篇幅过于偏重了对特朗普当选前后的批评,以致关于西方自由主义危机的问题意识时有失焦之感。在关于该书的评论中,好像还没看到在西方评论界有人会认为卢斯是危言耸听。在卢斯和像他这样对西方自身的变化有敏锐认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看来,对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危机产生恐惧无疑是件好事,尤其是在意识到一种强行输出的残酷的可替代选择已经出现,而且发现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出现某些趋同倾向也不再是天方夜谈的时候。有评论者更为直接地点出了卢斯的忧虑中的关键问题:“西方自由主义将国际领导权拱手相让已迫在眉睫,而接手者中并不乏专制国家。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加以补救,迎接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未来?”但是同时也要对恐惧有可能被夸大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两种应该并存的观点,前者使人警醒,后者使人不要失去信心,应该针对精英阶层的内部问题以及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展开矫正与调整。卢斯和他的朋友门显然在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什么是我们的社会不想变成的模样?只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说,“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必须特别留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智慧箴言:‘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尤其是自由派精英们,未来必须要抵挡住自己继续过舒适生活的诱惑,并且想象时不时地在Facebook上发表抗议,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对特朗普来说,如果你不反对他,你可能就会和他站在一起”。(189 页)在最后,他还是没有忘记对未来的差异性表达忧虑:“有人曾经说过,情色和色情的区别在于灯光。非自由民主与专制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同样朦胧的界限。当我们看到它时,就会知道它们的差异。”(190页)问题只是,在他看来的“朦胧”实际上常常是非常清晰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