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想让散文重新得到认可,而且回到日常生活
【编者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册“有趣的小书”,是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1985年到1990年切磋学问、品谈文章的记录。“三人谈”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打通了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曾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漫说文化》则收录了“漫说文化”丛书各集的序言及三位学者各自的回忆文章,阐明了他们编撰“漫说文化”丛书对“散文”的独特理解。
近日,这两册书合刊为一的增订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三位学者2018年10月重聚燕园,于落花时节再度“三人谈”,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也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本文摘自这一长篇讨论中陈平原教授谈“漫说文化”丛书的一段,由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小书》,因为当初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以后,钱锺书写了书评,有好多批评,但有一句话,说“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以前此类小而可贵的书不少,今天的书越写越厚。有些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多情况下不完全是专业论述,而是舍不得割舍,学不会剪裁,罗列一大堆材料。所以我才会感慨,小书和短文是配套的,以前的小书今天变成了大书,以前的短文或小品,今天变成了长文或大品。
关于散文的问题,等一下有兴趣再谈。我下面谈几个跟这套书有直接关系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鲁迅当年为杂文争地位的时候说,如果文学殿堂那么威严,非要符合文学概论不可,我就不当作家,我就不进去了。原因是,诸位必须了解,传统中国“文”是核心文类,文以载道的“文”是核心文类,到了晚清以后,特别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文”从中心退到边缘,变成很不重要了。当年朱自清《背影》出版的时候,在序里面说很抱歉,我不会写诗,不会写戏剧,不会写小说,我只能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当然属于杂文学,不是纯文学。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对“文”的感觉是它从以前整个文坛的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个过程中,这一百年中,“文”还一直在挣扎,而这套书某种意义上是基于我们这个概念,觉得“文”必须重新提倡,而且“文”有可能重新回到文坛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如果看一下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章文,第二章小说,第三章诗歌,第四章戏剧,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章排在最后。今天讲近现代或当代文学,“文”也都不太重要。当初我们有一个想让“文”重新得到认可,重新回到文坛的关键位置,而且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设想。
当初之所以分专题编散文,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史的质疑。这个思路,我后来有进一步的拓展,最近十几年我写了好几本书,包括《假如没有文学史》,更包括《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史》,讨论的是文学教育的问题。文学教育以文集、选本还是以文学史为中心,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力图纠正1904年引进文学史以后,整个中文系以及所有的文学教育以文学史作为中心的这个教学框架。我说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大批没有品味,但记得一大堆名词和人名的学生们,离开这个文学史,已经没办法再自己阅读和欣赏了。我希望恢复回到文章、直面文本、独自阅读的状态,而文学史只是作为一个帮助你了解的背景而已。我曾说过这么一个教训:夏老师讲古代文学,我是教现代文学的,曾经有一学期她到德国教书,我替她讲古代文学,考试题目是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答卷里面80%的学生举的是范进中举,为什么?因为中学课本有。后来我发现,读大学以后好多重要作品没再读,为什么?没时间,因为忙着读文学史。可以这么说,我们教给同学一大堆作家和作品名称,同时告诉他什么叫作主义、流派、风格,但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去好好读作品。所以我才会说,宁肯编选本让学生们自己读,多少还有收益,比起你背一大堆名词有用得多。
第三,为什么选这十个题目?某种意义上,这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包括《神神鬼鬼》,子平补充说跟老钱当年的《周作人传》有关系,我补充的是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八十年代我们重新发现地方文化、民俗、宗教等等,八十年代我们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诸位肯定记得,成仿吾当年批判鲁迅,说鲁迅落后,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所以鲁迅写了一本《三闲集》。“有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批评的对象。包括周作人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国人缺乏丰腴的、温润的、从容的生活感觉。外在的是因为战争问题,生活水平下降等等,没有那个能力,但也跟心态有关系。这就说到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狭隘论述。而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人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谈文化的时候,都明白散文的特点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某种侧影。谈中国文化,不一定在儒释道的大文章,不一定在教科书,不一定在文化史,也可以是在散文的点点滴滴中,见到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而且,用这些接地气的、生活化的、零碎的、感性的材料来弥补过于宏大的叙事和过于僵硬的概念,是有意义的。这是当初的一个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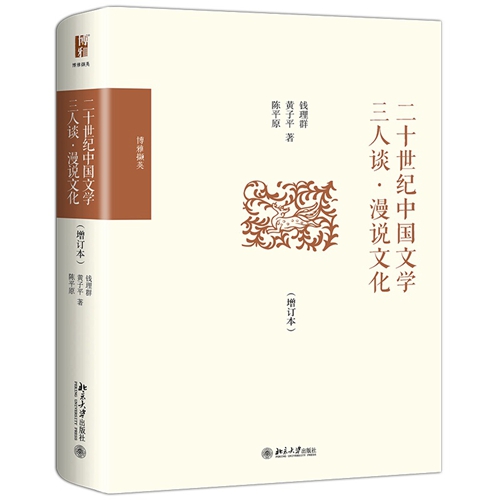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