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潘光哲谈晚清的世界知识及传播

在近代东亚的士人,面对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先生,今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新书《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他认为:“仔细考查中国近代史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史,即可发现,既存的知识状况与研究视野,既是后继者开展知识生产之旅起步前行的基点,却也可能是妨碍其放眼四顾的无形眼翳。”
应该怎样理解您著作中提出的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与“知识仓库”之说以及您在其背后所设置的问题意识?
潘光哲:大清帝国和东亚世界在十九世纪遭受的挑战与引发变化,前所未有,怎么理解这段历史的后续效应?拙著可以说是对这个历史问题的一种回答方式。
如本书导论之始,举引了两位十九世纪东亚世界的卓异之士:佐久间象山和康有为,如何假借俄罗斯彼得大帝的例证,取为楷模,替自己的国族构思图存求强方案。佐久间与康有为对彼得大帝的理解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位在具体的时空背景里堪称第一流的思想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凭借(基础?依据?)之上,开展他们为因应世变而构思想象的观念旅程?我的诠释是,就在当时,凡是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之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或是寰宇情势,或为新兴学问,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

康有为
然而,身为史学工作者,不能离事而言理。拙著则以具体的个案,阐释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如何被创造生产,从而对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洪流,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为描摹其间历程,我创制了一种譬喻之说,主张他们犹如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外邦奇技妙器,或是令人惊异不置,或是令人叹为观止,或是令人掩卷深思,或是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观奇揽胜者的心怀意念,进而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我的诠释,力求立足于逼近历史本身,而不是以现下吾辈可以任意撷取的空泛概念,骋思悬想,自做文章。毕竟,那等做法,其实与误置时空的概念游戏,距离并不遥远。研讨近代中国历史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现象的时候,当然会进行“概念化”的工作。即如本书以“知识仓库”作为开展统合诠释诸若魏源、徐继畬等人进行纂辑《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籍的意义,也是笔者个人操作“概念化”的成果。笔者更进一步地述论,“知识仓库”提供的“思想资源”,对近代中国追求“世界知识”的历程,提供何等思想动力。可是,本文对这些历史现象的“概念化”,是尝试尽可能地回归史料基础,从而藉以逼近历史原来样态进行操作的结果;而不是用现在已然知晓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来“指导”个人对这些历史现象的解释。即如“导论”具体论证,康有为以彼得大帝为楷模的言说,其实袭取删改自徐景罗翻译的《俄史辑译》,固然既是“凿空”之论,也是在说明晚清知识人确实可以借着“知识仓库”,从而追求“世界知识”的历程。
透过“知识仓库”及其影响所至的研究,识其渊源,晓其本末,无疑也可提醒我们,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各式言说,本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相互纠缠的产物;一旦“历史化”,溯其本末,当可显示它们在历史/生活世界里的意义和地位,其实未必“理所当然”,更绝对不是“天经地义”;对挑战现实的意识形态霸权,自必启发无限。
您在书中认为,晚清的报刊是国人获取“世界知识”的重要途径,这些报刊的默认读者是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吗?您又是怎样看待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世界知识”对知识精英乃至政治势力的影响力?
潘光哲:即如本书“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一章,以《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及其刊布的各式各样的译稿)为对象的讨论,确实可以想见,报刊对创造制作晚清中国的“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确实影响深远。
从历史的脉络里观察,晚清改革派士人群体都重视现代报刊的意义与作用,如郑观应即将“日报”看成是“泰西民政之枢纽”,举证历历地论说西方各国“报馆”具有深刻的政治效果——“是非众着,隐暗胥彰”。康有为亦将报馆看成是足供“见闻日辟,可通时务”的工具,所以应该奖励民间设立。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1896年意欲创办《时务报》的时候,则自我宣称,《时务报》要努力于“宜广译录,以资采择”,以发明“政学要理”与翻译“各国报章”。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一册首度出版与大众见面时,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便是梁启超的论说《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不无激情地表示,报刊应该“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
当然,媒体自身也是讯息/知识的“过滤器”,从《时务报》的选择题材来看,即使它借着异域之眼反观自身,亦屡屡表达它自己独特的观照。像是《时务报》不乏翻译外国关于中国内部动乱的报道;然而,对曾被视为“匪酋”的孙中山,当外国媒体报道他在伦敦遭受“劫难”的事迹之际,《时务报》给予更多更广泛的关注,刊登了许多关于孙中山这场遭遇的译稿,盖《时务报》主事者梁启超等,和孙中山早有往还。如此的关注,显然实非将孙中山与一般“匪乱”等同视之。《时务报》也借着外来的译稿,为正在炽热非常的维新变法运动张目,如从《伦敦东方报》译出《中国不能维新论》,指陈变法维新的可能路向:“中国欲求维新之道,必自裁撤都察院及翰林馆始。既撤,然后削总督之权,或径除总督名目,仅设巡抚已可矣……若不维新,则凡遇不论如何凌辱之者,亦惟有耐受而已”,文末虽有附语表示“以上二篇皆英报之说,因照译之,以见外人窥察我国之意。至其说之是否,阅者自能辨之,无待赘言”,凡此这般,各种好似“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示,政治意图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实际上也表明,当时的“世界知识”其实已经成了一些报刊论政论的某种论证资源。
又如,《时务报》译自上海《字林西报》的文稿,既声言道“中国宜亟开民智”,并提出具体方案曰:“应广布浅近有用之学,如各国政治形势之类,于考试时以之策士;而由国家编辑各种初学读本,散布民间。” 这等于是为当时甚嚣尘上的“开民智”运动,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入手方案。
以是,《时务报》的论说与译稿,在在引起读者的兴味。所以像是后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之一的高凤谦(梦旦),在《时务报》问世之际,还只是蛰伏于福州一隅,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士人,一旦读到了《时务报》之后,对它的丰富内容深有所感,同时也担心它可能招致言祸。所以他就致函汪康年等,殷殷劝说,《时务报》刊载的“《民权》一篇,及翻译美总统出身,欧洲党人倡民主各事,用意至为深远”,可是恐怕不免让“守旧之徒更得所借口,以惑上听”。就此一例,正清楚反映了《时务报》自是满怀用心地制作/传播“世界知识”,有心之士自可读出这些讯息的“弦外之音”(参照本书“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一章)。尤其是要知晓《时务报》与高凤谦这等读者群体之互动响应,笔者主要仰赖的史料是《汪康年师友书札》(这套史料“原汁原味”地展现《时务报》编者和读者之间的多重响应样态与具体场景,本书未多涉及,略有不足,读者如有兴味,另可参考: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修改增订本)。因此,即便近现代报章的不少读者来信,恐怕是编者编造的(如刘半农、钱玄同在《新青年》上演出的双簧戏),我们可以想见,《时务报》的读者确实满怀着兴奋之心,透过阅读讨论“世界知识”与它的编者进行往来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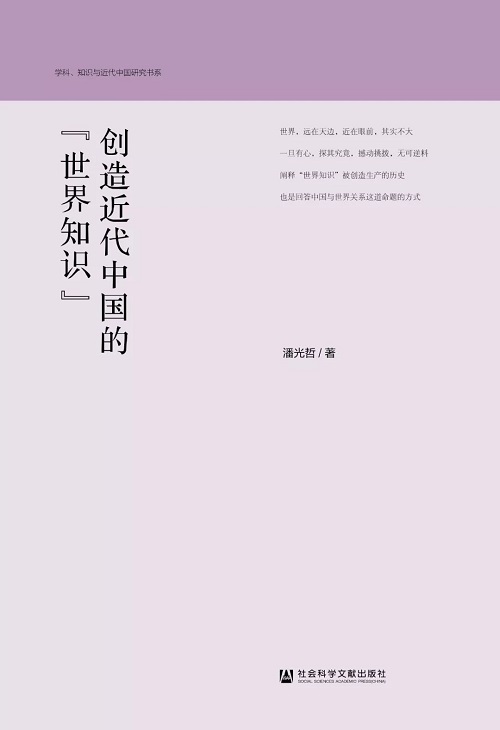
您在书中指出,很多当时流行的概念是以比附中国经典的形式出现,这些比附对时人理解西学既有帮助,应该也有很多误导,是这样吗?
潘光哲:约略言之,明清时代的“西学中源论”,流行一时,如本书提到的张自牧与他的主要撰述:《瀛海论》和《蠡测卮言》,即是个中名著。张自牧系统地从各个文化生活领域(如宗教、纪元方式、货币、文字、政治制度等)举出大量例证,相互对比,企图论说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虽然,他的中心意旨是呈现“华夏中心本位”世界观的具体象征,却具体展现“以中释西”的思惟方式(参见:潘光哲,《张自牧论著考释札记:附论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四期),自是对承受西学,多少提供动力。正如本书“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一章讨论的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泰西新史揽要》,本是广受好评的畅销著作,面对“政体抉择”的问题,仅只强调“国以民为本”,显示传统中国“民本论”的论述格局,依旧是思想市场的主流观念。即便如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以“共和”为其革命宗旨,他的解释是“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将传统三代作为政治乌托邦的想象,与现代共和国的实践,兼融并治。章士钊取宫崎滔天的自传《三十三年の夢》(1902年出版)“译录”为《孙逸仙》(1903年出版)一书,当时大受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参考本书“创造‘革命想象’的知识文本:以章士钊‘译录’的《孙逸仙》为中心”一章)。
这等在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曾经雄霸一时的思想现象,当然是走过一段“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漫长历程的产物。“跨语际实践”本是刘禾教授的创获,她认为,“由于中国现代的思想传统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所以,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研究会以翻译作为其出发点”,在她看来,“研究跨语际的实践见识,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由于主方语言(the host language)与客方语言(the guest language)的接触/冲突,因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因此,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改变’(transformed),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里被发明创造出来的”(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页35-37)。然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跨语际实践”的“语际”,未必是“中”与“西”/“古”和“今”的二元对立样态。诸如“共和”这等古老词汇,作为认识的对象,往往可以穿梭于古今中外之间,凝聚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各方论者,自由驰骋,依据他们的认识理解,将之建构为簇新的符号架构(a new symbolic framework,这是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表述),非“中”非“西”,不“古”不“今”,竟可生产出或者是和现实一致或者是逼近历史样态的意义,确实可为自身在具体的环境里倡论立说,或是开展行动找寻正当性。研究这等意义脉络的思想课题,如何它们被建构为簇新的符号架构而“古为今用”的历史过程,对我们思索类似的词汇和思潮,如何成为好似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用语,自是大有帮助。
这些“世界知识”,对东亚的中日朝三国是“同润共享”的,但各国对世界知识不同门类的反应是不同的,您能举例谈谈原因吗?在您所界定的知识仓库中,世界史地与国际法是怎样勾连起来的?我们感觉,世界史地当然对时人冲击很大,但也许可以宽松地理解为客观知识,而国际法体现的普遍主义,似乎是更大的挑战。
潘光哲:正如本书“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一章所示,以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加藤弘之的《邻艹》(1862年写成),假大清帝国之情势而呼吁日本自身推动改革,这部书的资料依据之一,就可能是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初刻于1848年),略可想见东亚知识人同润共享“知识仓库”的场景。而且,《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书在朝鲜同样深受重视,朝鲜“开化思想”先驱朴珪寿,即将前者视之为“外洋事不可不知也”的读本。1876年2月,《日鲜修好条规》签订后,朝鲜李朝政府派遣修信使金绮秀等一行访问日本,金绮秀此行撰着《日东记游》,记录参访心得,便提到《万国公法》乃是“诸国缔盟,如六国连衡之法”。正可想见,这些“共同知识文本”之影响。不知道外国之所在及其情势,焉能据《万国公法》规范的国际秩序,彼此往来,乃至据而争取国权?(参考本书“‘世界史地’与‘国际法’知识和‘近代东亚地理想象’的生产、流通与嬗变:回顾与思考”)
况乎,知识人如何各逞巧思,构拟国族处境与其未来,更有赖于一定知识基础和认识。此正为本书“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一章描摹晚清士人如何凭借既存的地理学知识,作为在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里在融铸真假,逞其幻思的思想动力根源。也正是对世界讯息的掌握理解,愈发广泛,激发的思想反应,多重多样。正如是章述说五四时期知识菁英得悉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结束,“欧战”告终之讯息遂成“喜报”,原因所在,与他们怀想中国的现实处境(及其改变的可能性),和世界局势(与其变化),密切相连,世界格局的变易,必然影响中国。
在您看来,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借用“知识仓库”这一概念,辨析近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对我们的研究会有怎样的启发?
潘光哲:本书“自序”有言,“我们的前行者,究竟如何企图突破既存的知识囚牢,眼观寰宇,为追觅‘世界知识’,奋力以行?”这部小书,仅止选取若干个案,以为考察之资,自有不足。然而,烛照一隅,光亮应在。本书的研究所得,力以史料为基础,不尚空言,特别是个人之研究,往往铸造新词,以示新意;然而,亦如本书“导论”所言,只要仔细考查中国近代史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史,即可发现,既存的知识状况与研究视野,既是后继者开展知识生产之旅起步前行的基点,却也可能是妨碍其放眼四顾的无形眼翳。一言以蔽之,我们仰仗的既有的知识基础,未必坚实稳靠,不可动摇。在口号宣示层次批评既存的史学知识的成果,是一回事;在具体的史学实践里如何展现,却是另一回事。本书诸章,冀望透过具体的研究例证,既能阐明近代中国历史的另一方面向,又可以为我们承受的历史知识,提供反省思考的可能路向。
想要调整转换研究与认识的视野,不受既存知识的束缚,确切掌握思想观念变化的具体历史脉络/场景,期可还诸历史本身,绝对不应徒为空言,实须有赖具体史学实践的展现。否则,呼卢喝雉,图画鬼雄,不过是包装着学术外衣的资料堆积,对实质历史知识的增长,必然无所帮助。即如本书讨论西方政体(political regimes)的类型知识在晚清中国时期的导入和传布,就以比较细致的“脉络化”研讨取径入手,所以,如本章特别比较列表展现蒋敦复、王韬对政体类型知识的前后变化,以显示他们对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之贡献所在;也就具体时间定点析论“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杂音与同调”,意向所在,即欲深化吾人对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多重样态之认识,进而反省,中国/中国人开始走向“民主之路”,竭力欢迎“德先生”,并不是由于前行者对“民主思想”进行积极“宣传”或“宏扬”的必然结果。各方知识人的思考与言论,都各有其演变的脉络,应该返诸它们问世的本来场景,进行理解;而不是将这些繁杂的历史现象/事实简单概念化,甚至于成为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因此,笔者的研究路数,不免繁冗,意向所在,期可提醒中国学界同好,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综合及其书写,应该以比较稳固的知识基础,对我们继承的历史思想传统,进行无穷尽的诠释追索。凡此所为,是否名副其实,如可得到同好的批判指教,必将是笔者最大的荣幸。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