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睡眠日:今晚,你还在失眠吗?

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调查显示,这些混迹在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居民之中,有80%的人忍受着低质量睡眠带来的躁郁,有50%的人严重睡眠不足,还有40%的人倍受“失眠”的煎熬。城市熄灯之后,仍有不少人面临着一场睡眠与黑夜的赛跑。
同样,美国国家睡眠基金曾做过一次全国性的“睡商”测试,其中超过83%的美国成年人不及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智商在成长,睡商却逐渐下滑。怀念童年那一觉睡到天明的昏天黑地,却在长大时把清醒看得比睡眠更重要。
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并将每年的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WorldSleep day)。
今天,是第十个世界睡眠日,而你,还在失眠吗?
编辑 | 马纯琪 王欣怡
论“脑洞少女”失眠时的全部心理活动
@一天两天好几天都睡不着的牙牙乐

作为一个长期失眠+晚睡晚起+嗜睡少女,对于失眠有很多话想说。
吃多了睡不着,太饿了也睡不着。压力大事情多睡不着,事情太少也睡不着。太困了睡不着,一点也不困也睡不着。睡太早睡不着,睡太晚也睡不着。生理期痛睡不着,没来生理期有点恐慌也睡不着。喝奶茶睡不着,想喝奶茶也睡不着。
总之,我是个容易睡不着的人。
躺上床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预设一个场景,比如我和易烊千玺是同桌,期待着和他发生一些故事的情景,比如我在月亮上荡秋千的情景,也比如我在面包树上数羊的情景。但是这种情景在失眠的时候经常“xiu”地一声被切换,然后和现实有关或无关的各种画面就在我的脑中堆积切换。
会从和易烊千玺做同桌想到自己怎么还是母胎solo,再想到20岁之前不能脱单而难过,有点后悔之前为啥不早点注意个人形象,想到和未来男朋友相遇的场景,然后想到难道我的真命天子其实是易烊千玺,所以我的等待是值得的?!
失眠的时候其实还会讲究仪式感,比如睡觉姿势和睡前祈祷。躺上床时一般会选择一个姿势入睡,平躺是一定不能睡着的,接下来就是各种姿势尝试睡着
小时候睡觉喜欢捧着妈妈的脸睡着,据我妈回忆说她的脸实在是太热了,所以都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小手移到我的脸上,我的姿势就变成了捧着自己的脸睡着(妈妈怎么这样子!)
睡前祈祷还来自于小时候超喜欢看守护甜心,每天就睡前祈祷赐我一个蛋吧赐我一个蛋吧,还会和床边的娃娃们说:晚上鬼会出没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
失眠之外,我其实特别喜欢睡觉。睡不满10小时的觉都不算真正的睡觉!还记得小时候我根本没有过失眠与晚睡,一天没心没肺哈哈哈过去,一倒上床就能睡着(现在:不可能了),也经常晚上全集看电视时睡着,记得当时热播的剧是《仙剑奇侠传》,有一次看到女主睡着,男主公主抱女主,当时我看了就好激动!(看来我的少女心玛丽苏情节从小就有)
于是,我立马在沙发上装睡,期待我爸能公主抱我到床上,结果真的睡着了,对公主抱完全没有什么印象……或许我爸是直接把我扛过去的……
成长的烦恼慢慢增多,表现为白天的没心没肺和晚上思考人生问题。睡不着或许是因为灵感兴奋阶段,pre主题、稿子选题、论文大部分都是这个时候想出来的。有时,第二天起来时这些灵感就忘了,不过后面还是能慢慢想出来,毕竟是从我的脑子想出来的嘛!
眼睛想睡觉但脑子还很兴奋的时候真的太磨人了,此时就特别希望有个清洁器哗啦啦把脑子所有想法都吸走,让我别再想了!失眠或许现在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人们的习惯与体内规律的闹钟,一到时间就开始多想。
虽然不失眠一倒上床就睡着的时候真的好开心,但是失眠也不讨厌呀!看似干躺在床上很无趣,但我的脑子里可是好有趣的噢!
失眠和生气是一个死循环
@Voldrick

我现在在写关于失眠的小短文,我大晚上写这些东西也是因为失眠,这是相互成就的两件事情。
最近我家失眠率真的有点儿高,半夜我爬起来上厕所,妈也出来了,俩人在黑暗的走廊里打招呼,听上去都挺有精神。这个假期我经常熬到天亮,伴着楼下的狗叫声睡觉,还没睡着,楼下人也开始叫。
失眠是一种死循环,情绪很差的时候我睡不着,睡不着就会生自己的气,一生气更加睡不着。如果这辈子的气像蛋一样都被半夜生在被窝里,白天的我或许就不那么容易生气了。
今年有两个无眠之夜。第一个是一月十号,南京下雪。宿舍只剩两个人,我和我的室友,趴在阳台栏杆上看雪,太冷了,人就算长十个屁股也全给冻掉了。我看看她,觉得喜欢,她看看我,说“对面楼顶站了人欸!”
我朝她探探头,她看看我,我又缩回来。过了十来分钟她进屋了,我抽了五根烟也进了屋,洗漱完上床玩手机。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离开了学校。
另一件事是前几天我把自己其中一支数位笔摔了,裂了条缝,没坏,还能用。但我后来觉得不应该摔笔,应该把我自己摔在地上才算公平,脑袋和手得同时着地,不然也不公平。
其实不怪我的笔,那天我躺在床上,估摸着我把画画当爱好约莫也有八年了,我把八年都过到了鱼肚子里去,事到如今依然什么都画不出来。我对着照片画瑞凡菲尼克斯,却怎么也不会画他身后的树,气得我把笔摔在地上。
人家都说爱好给人带来愉悦和消遣,我怎么如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呢?我记得自己初中的时候还画过班里俩男生的本子,现在连画个丁老头手都要抖三抖,是我变了还是丁老头变了?我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了一晚上。
这事被我妈知道了估计要笑话我“:你竟然因为不会画一棵树而一整晚生自己的气。”以及“你竟然因为自己画的眼睛和朋友画的眼睛太像而一整晚生自己的气。”
但我就是没办法,当你八年以来最大的爱好背叛了你,当你心灵的归属变成了一种折磨,真的没法不生气,尤其是当你想到自己除了这个也没别的任何想做的事情时。
到了后半夜我索性把房间的灯全打开了,想找点儿小说之类的看看,因为我突然想到有人在白天问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我却回答“中学的时候最喜欢塞林格。”我可能到很久之后都喜欢塞林格,但我这么答纯粹只是因为我从中学毕业后就不看书了。这让我对自己脑子里剩的东西产生了一点担忧。
我一边换着看不同的小说,一边在微博小号不停地发:“西摩格拉斯自杀了啊”、“昆汀汤普生自杀了啊”、“西摩格拉斯自杀前还和小女孩去海里玩”、“昆汀汤普生自杀前还给小女孩买面包带她找家”、“他们自杀了啊……!”
好像这些内容人家在书上看不到还是怎样的。
失眠的夜晚,脑子里确实想了很多,但我实在不能表达出来,在想法面前语言显得太单薄了,如果我某个雨天跑出去淋雨,我也不会说自己是为了体会青春的痛楚而跑出去淋雨,这太片面了,至少还要说个因为外边很凉快很好闻之类的,还要说下雨的时候天离我很近,即使已经这么啰嗦了,依然不够表达,不如干脆说“我跑出去淋了三个小时的雨,回来就病死了,才二十岁”。
于是我一遍遍地说“昆汀自杀了!昆汀自杀了!他死前还穿着自己新买的西装!”好像这些内容人家在书上看不到似的。
我老是憋着脑子里的那点儿东西,我说不出来,我画不出来,我也做不出来。
我还在气,南京雪夜里我没有亲吻她。
高考前夕的空调外机
@山城小汤圆

空调又开始运作了。
这是一台产于我出生之年的一体式空调机,留在屋里的半截吐着冷气,吊在屋外的半截就排着热气,运作一会儿间歇一会儿,轰鸣起来像一个哮喘病发的老人。
它每开始轰鸣,我就又一次被扯回这间二十多平米的单间租屋。桌上的花已被清理到阳台,储物柜里的衣物也已打包到一半,屋里出奇的整洁。我打开手机翻出微信,一点半,没有人更新朋友圈。
小时候看的一本美军士兵回忆录,说晚上躲在战壕里,黑暗就会逐渐将整个人的身体融化,最后只剩一颗心,还在惊恐地跳动着。
“我心即我,我即我心。”像笛卡尔所说,那惊恐似乎成了存在的唯一证据。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笛卡尔,只是想顺着那本遥远的回忆录继续想下去,从1942年的瓜岛到贝里琉岛;等到思绪走得够远,就能偷偷睡着。
空调又响了,旁边的碗跟着抖动起来。想象自然又断线了,手机屏幕上显示已逾两点,我眨了眨眼,果然左眼又翻成了双眼皮。好吧,我必须承认今晚我已经有了失眠的症状,现在要换一种策略尽快睡着。
如果想遥远的事情无法招徕睡意,我就开始集中精力回忆一些故事性强的往事——还是那本回忆录,是小学的某个周末在区里的新华书店看到的,那个时候货架上的畅销书还是《货币战争》,去一趟新华书店也算难得的远门。然后是雾霭里初中校门口小摊的灯,我把这本书放到了班上的公共图书角…
空调又响了,被窝却变得燥热了起来。我索性跳到了小小的沙发上,半蜷着对着空调,试图让冷风吹来一些睡意。打开手机,屏幕上瞬间结出了一层水珠,三点过了,闹钟显示还有四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我开始恼怒,头脑却戏谑式地愈发清醒,四肢有了触电一样的酥麻感:我怎么会在今天失眠呢?怎么偏偏现在睡不着呢?被自己气得发抖。
打开浏览器,搜索“人在不睡觉的情况下能够清醒多久”,各路答案都说是48-72小时,再往后翻就是苏联的恐怖实验、连续不睡眠之后发疯之类触目惊心的营销号文了。发泄完怨气,重新躺上床将思维摁进水里,今晚必须要睡着。
想起高中副校长前几天的讲话。那是高三以来的唯一一次集会,在那座1938年建成的礼堂里。没有口号和音乐、没有横幅和花束,我喜欢这样的集会。集会?这房间何不是一次最后的集会,那几束快要开败的栀子花、天蓝色小花盆里的苕花、寥寥购入的杂志和小说,是不是会趁着我睡着窃窃私语,聊一些精怪的故事。
最后一次看时间,五点过了,窗外天空的深蓝色已经开始变浅。我心里生出易水悲歌似的一句话,“大不了再来一年。”便悲凉地趁着这黎明闭眼睡去。
空调外机的轰鸣声渐渐淡去,在我意识消逝前的一瞬间似乎停了下来。
窗外的城市顺着阳光苏醒,交警走上街头,妈妈们穿上旗袍走到校门口,山东杂粮煎饼铺敲碎第一颗鸡蛋。那是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的阳光,也是我们离开之前,这座城市唯一一次为我们苏醒。
后来我就搬走了,那台老骥伏枥的空调被新主人换成了一台更新的。高考前夜的失眠,倒像是故乡的最后一次深夜耳语了。
“我在天亮时感觉到活着”
@编辑部第一仙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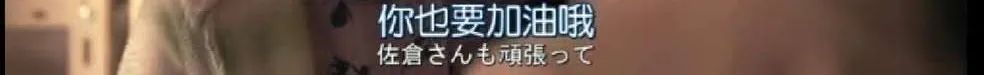
我最害怕深夜:尤其是板正地平躺在宿舍的床上,仅仅从门缝的一点生硬闯进来的光亮里捕捉“活着”的实感,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件窒息的事情。
害,如果这世界上有一种病真的被命名为失眠症,那我最好还是去看看医生。
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大一上学期快结束的那会儿,我可以从十二点上床准备入睡开始一直数羊,数到饿了(不是)从枕头底下翻出手机瞟一眼时间。手机上的时间几乎寸步不动,一次次地点开屏幕眯着眼睛等天明。
运气好的时候两三点多就能睡着,而运气最差的一次,我一直耗到了六点,冬天的复旦天亮得晚,但我还是从窗外稀疏的声音里判断出我熬过了一个彻夜。
被失眠困扰的时候最多的是恐惧感。恐惧墨水一样浓重的黑暗,并且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来气:我会觉得自己不在“活着”。有一种剧烈的对于生命的怀疑和空洞虚无感会趁着黑灯瞎火直接入侵我的思维,——是真的入侵,是那种你尝试用后槽牙咬合和一些其余的念白试图转换话题都无果的入侵。
就像看完鬼片一样。你晚上告诉自己别去想《闪灵》里的双胞胎,可还是会在突然间被吓得半死。
而且我会想一些很奇怪的事:一些在我正常无奇的早上和午后不会蹦出来的问题:我会思考世界是不是一块幕布,而我是否是一个提线木偶;存在将怎么被证明;命运的变数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会不会突然死去?”和“我身边的人会不会突然死去?”都能让我即使在夏天的夜晚也被惊出一身冷汗。
一个周末,我和父母通电话,他们正打算从贵州飞回北京。那个夜晚我就是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脑子被填满了坠机画面。我甚至因此哭泣:就好像第二天就能看见一条“xx航空坠毁”的消息。我点开手机无数次想警告父母不要登上飞机,——还好我最终没有那么做,不然他们真的可能立刻转机上海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失眠就是在映照生活的潜在面,我一直这么觉得。这也就是我试过了除了褪黑素之外的一切方法还是没用的原因:我会冲很浓的蜂蜜水一大杯灌下去,我买了助眠用的蒸汽眼罩和挂在床上的香袋,我的床上堆满了毛绒玩具。
甚至为了能证明存在的实感,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会在失眠的夜里听一些生活类综艺,例如《我家那小子》,我会把手机屏幕背过去放在枕头下,伸出耳机来听综艺里的“活着”的声音。但这也是无用的,我只能在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感到心安,而摘下耳机的再一次被深夜覆盖时,我依旧无法入眠。
这或许源于我对生活本身的隐忧——可能在太小时候被现实教会了死亡(和突然死亡),而那时候大人们忙着奔波丧仪处理后事,于是在我对于死亡的认知上出现了一个豁口:我们在奔向死亡,人生是一场倒计时。
深夜则是反应它们的最好时刻。
我很怕和别人说自己失眠。这个年头好像失眠和抑郁症一样,是一件流行的事情。好像仅仅是启齿的两个字都是一种无声的炫耀。可其实不是。
失眠的夜里不是所谓的数过星辰,听不见什么夜里的鸟鸣和单车路过的声音,更不是如思念成疾一样浪漫的。失眠是一团墨汁。它走来时都带着看不清的轮廓和压抑的影子。
我在天亮时感觉到自己活着。
可是当黑夜降临,寝室的灯光一盏盏暗下去,我再一次平板的躺在床上,虚无会再一次包裹并遏制我的呼吸。在连续几个成功入睡的夜里,它会悄悄的站在我的床前。
好的,我于是会长吁短叹,你又来了。
经过医学诊疗,我最终和失眠和解
@黑夜里的精神流浪者

我的失眠经历在大二时较为严重。曾经经历过一整个月的彻夜失眠,即使大脑疲惫到了极点,也感觉不到丝毫睡意。失眠伴随着乳腺痛、心跳加快与身体疲乏,严重影响了第二天的上课状态。更绝望的是,身体会陷入“越想睡、越无法入睡”的死循环,即使眯紧了双眼,脑部却演奏着交响曲。
入夏的6月,考试成堆,肠胃问题越发严重,形成了我日出睡觉、中午起床的生物钟。为了复习,我没有去肠胃科就诊,最后一门考试时,我倒在了考场上,被送去了医院。检验结果是严重的低血压、低血糖与心律紊乱。
大三上遇到了比失眠更可怕的东西——噩梦。情况严重的时候即使没有鬼压床也会出现幻听、幻觉,经常听到有人在我耳边窃窃私语、有人影从我身边闪过(我住的是单人间)。
失眠的危害远不止掉头发这么简单。不知道是不是性别带来的“伴生品”,连续缺乏的睡眠带来乳房疼痛,排卵期时疼痛会伴随着失眠加剧。心悸,哪怕是一日的睡眠剥夺,次日我都能感觉到心跳明显在加剧,感到呼吸困难、胸口疼痛,胳膊有放射状的疼痛。不仅是身体,失眠带来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思维变得异常缓慢,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情绪也变得十分焦躁。
常常下午一个人在卧室睡醒后,眼前像被打上了黄昏的滤镜,那种被全世界遗弃的孤独感、抽离感瞬间把我浸透。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失眠问题的困扰,我前往医院就诊,诊断报告上写着:中度抑郁症。新华医院心理科告诉我,75%的抑郁症患者会出现失眠症状,45%出现嗜睡症状。抑郁症和失眠并没有先后次序,长时间的睡眠剥夺容易引发抑郁症,而抑郁症也会加重失眠的状况。
原来,手机和奶茶并不是唯二的失眠原因。幸运的是,医生推荐的阿普䂳林见效了。
治疗失眠大约花了我半年时间,抑郁症也显著好转。现在,我的睡眠问题已很久没有复发了。事实上,比起服用褪黑素,严重的失眠状况更有效方法的是咨询专业医生,找到症结所在。
而对于我和一样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如果身体褪黑素分泌功能运作良好,就无需额外服用,因为体内褪黑素水平的升高往往容易诱发抑郁症。除此之外,增加日照时间,抽出半小时跑跑步、睡前用热水泡脚、听轻音乐做冥想,都是缓解紧张情绪的良方。
不少人仍旧陷在“熬夜干活、白天补眠”的误区当中。但是白天过长的睡眠容易让人下午头昏脑胀、影响晚上入睡时间,另外,在多人寝室中,他们的声音、光线很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深受失眠、抑郁、焦虑困扰的舍友,日夜颠倒的作息容易加重心理疾病。因此,科学的做法是:减少白天的睡眠时间,中午尽可能缩短小憩时间。
经过医学诊疗,更正了不少误区,走过弯路之后,我才最终和失眠握手和解,拥抱自己的身心健康。如果你有同样的困惑,希望我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早日康复。
删掉微博之后,我的失眠自愈了
@张小姐想喝奶茶

上网课时的我仿佛开启了“废物模式”,过着休闲娱乐和学习本末颠倒的生活,吃吃睡睡才是正业。但这几天,我失眠了。在深夜,看着手机的时钟无声地转过了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失眠的第一天,睡前我照例抱着微博撒欢。恰好也是在这一天,放下手机倒头就睡的常态被打破了。躺在床上,微博上的舆论在脑子里兜兜转转地绕圈,挥之不去。带着隐约的躁郁和生气的感觉,我迷迷瞪瞪地清醒到了五点。理所当然地,我睡过了第二天的早八。
疫情期间,我的失眠更多是源于过分活泼的大脑,它在流量中轻易地被外物挑起了情绪,整晚活跃地运转着。
逛微博像看众生相,无数的信息流像潮水向你涌来,却不太容易四散开去。站队的“对话”、情绪的喷发,泥沙褪去之后是沉默的螺旋,主流意见占据了优势地位与正当性,中间人则越来越沉默。
尤其当自己置身于舆论的讨论之中,会很容易被等待声援者的焦虑绑架。不停地在黑夜里划开手机屏幕,确认点赞数,伴随着看见评论区里情绪激昂的反对意见时候的委屈与急于辩解,情绪一点点吞噬了时间。每当此时,我就知道,今晚的睡眠又糟糕了。
离暴力最近的一次,是主流媒体发表了“带节奏”的评论来批评某位公众人物。在睡前看见那位公众人物的微博评论区里刀光剑影、口诛笔伐“打”成一片。于是,我评论道“希望主流媒体在对单独的个人批评时能更加谨慎些,扒黑历史并不明智。”然后我被“讨伐”了:这条微博被数百人点赞,也卷入数百人的谩骂当中。非黑即白,反对和支持站成了二元对立,舆论没有任何中间的缓冲余地。
最后,辗转一夜的我删除了微博。本质上,我是个怂人。但仍旧有网友在我的微博底下评论“我把你删掉的微博截图了”。
于是我又失眠了,可我根本就没说任何大逆不道的话。或许,只有远离微博,我的失眠才会被治好。
可是所有的负面情绪和遭受过的“暴力”,并非像纸巾卷一卷扔进垃圾桶那样,可以轻易消失不见。
我还需要继续一点一点地学着整理因“暴力”声音而起伏不定的情绪。希望当所有情绪都熨烫妥帖之后,我的失眠会痊愈,我也可以重新做回快乐的奶茶女孩。

尽管失眠已经和抑郁症并列成为时代的精神瘟疫,但睡眠门诊在夜间从不开门,毕竟,谁又会在夜里因为失眠而奔赴急诊呢。
世界睡眠日,今晚周报君和你道一声晚安。
祝好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