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疫情中的道德经济批判与 ……社会选择

(Peterloo,又有译作“彼得卢:人民之声”等)
,深有所感。一部质感极为厚重、叙事肌理中渗透着愤怒与呐喊的历史影片,直接重现了1819年8月16日英国军警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镇压谋求普选权的群众集会,造成十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流血惨案,最后那幕屠杀场面表现出导演高超的调度与掌控能力。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反对《谷物法》、争取普选权、妇孺老弱的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统治者以法律的名义实施镇压的无耻与冷血,整部影片具有高度的历史纪实性。后来人们以滑铁卢战役比拟这次军队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的事件为“彼得卢惨案”。去年8月16日是“彼得卢惨案”两百周年,人们沿着当年的路线游行、集会、演奏、野餐,并且为纪念碑揭幕。看着影片中奔赴圣彼得广场的人群扛着写着“自由,或死亡”的大旗,我马上联想到最近西方一些国家有民众也举着“自由或死亡”的标语集会,反对的是疫情中的强制隔离。这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自由”(Liberty)这个字是一样的,无论它出现在哪里,总是那么耀眼。由此想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中,有关“自由”的舆论场不断翻转。在疫情中,事关“自由”的“不当言论”多有所闻。法国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在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不会因为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并且对危机处理中的“政治正确”和“卫生正确”提出思考和质疑。虽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在危机局势中关于生命、自由、健康之间关系的思考总有启发意义。
其实,在“自由”与“健康”之间的转换取舍并不是那么简单、自动的让渡与获得,因为必须由政府来操控这个过程,在许诺与服从之后,政府的表现和能力是一个问题,让渡了自由之后的民众对于政府的表现和能力能否监控、是否可以重新选择这又是一个问题。在这过程中,政府行为是否公开透明、言论信息是否自由、舆情是否具有实际影响力等等都是决定转换取舍的合理性的基本要素。但斯蓬维尔只是坚持“选择的自由是一种高于生命的价值”,这与启蒙时代卢梭的观点完全相同。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由——独立自主地进行选择的能力——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卖身为奴,这是根本不能妥协的。但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当卢梭涉及国家、政治、社会的时候,他的“自由”就被“幸福”所取代,为了幸福,交出所有自由是必需的。伯林的《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认为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关键在于,伯林坚持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是不屈服于外在压力的权利,这是政治与公共的价值;与自由相比,幸福、健康等等都是在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个体价值。
顺带应该说到,伯林在几本著作中都谈到迈斯特,认为他的言论超前地“道出了我们今天的反民主言论的根本”;指出迈斯特那种迷信暴力、赞美束缚、反对自由观念、警惕自由知识分子批判的破坏性等等“先见之明”“恰好是我们这个恐怖世纪的极权主义思想(包括左派和右派)的核心所在。”;“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也是最晦暗的精神现象,而且,还远未结束。”(伯林《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29、158页)迈斯特的思想固然邪恶,但有些问题看得很准。恩格斯在解释普鲁士专制政府为何能够存在的时候说过:“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68页)其实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迈斯特就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疫情中,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新的秩序格局的展望形成一道新的思想景观。
据说中文网络上有文章说马克思讲过“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还注有出处,有学者细心核实过,发现在马、恩著作中的确常有“瘟疫”、“丧钟”之语,但没有说过“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这句话。批判的合理性当然显而易见,近四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不仅要对经济不平等的加深和生态环境破坏负责,更现实的是要对裁减公共卫生预算、公共医疗体系漏洞负责。在大卫·哈维关于“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文章(参见澎湃“思想市场”,3月23日)中,提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新工人阶级”。指那些负责照顾不断增加的病人的劳动力,他们通常具有特定性别、种族、民族,最容易因工作而感染病毒,也最容易因为没有资源被解雇,如被隔离能否带薪还是一个严重问题。对他们来说,“我们都在一起”、“在家工作”只是一个神话。二是关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大多数劳动者都被社会化为表现良好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出了什么问题只怪自己或上帝,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可能是问题所在。这次疫情造成最富裕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形式核心的全面崩溃,唯一可以挽救它的是政府出资激发大众的消费主义,这将使美国整个经济社会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可能比伯尼·桑德斯提出的建议更社会主义。的确,在疫情危机中“主义”成为舆论场的热点。齐泽克说一旦身陷危机,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也认为疫情在西方世界“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她指的是全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免费承诺。在现实中也的确纷纷出现了回应这种“社会主义想象”的措施:许多国家政府直接发钱给全社会公民、增加失业救济、持续向所有有需要者发送免费食物、暂停贷款还款、禁止房东驱逐房客、出资给企业主支付雇员带薪隔离……。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普惠措施,被称为“一夕之间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无法改变贫富悬殊的不平等,但是总能让底层的工薪阶级度过眼前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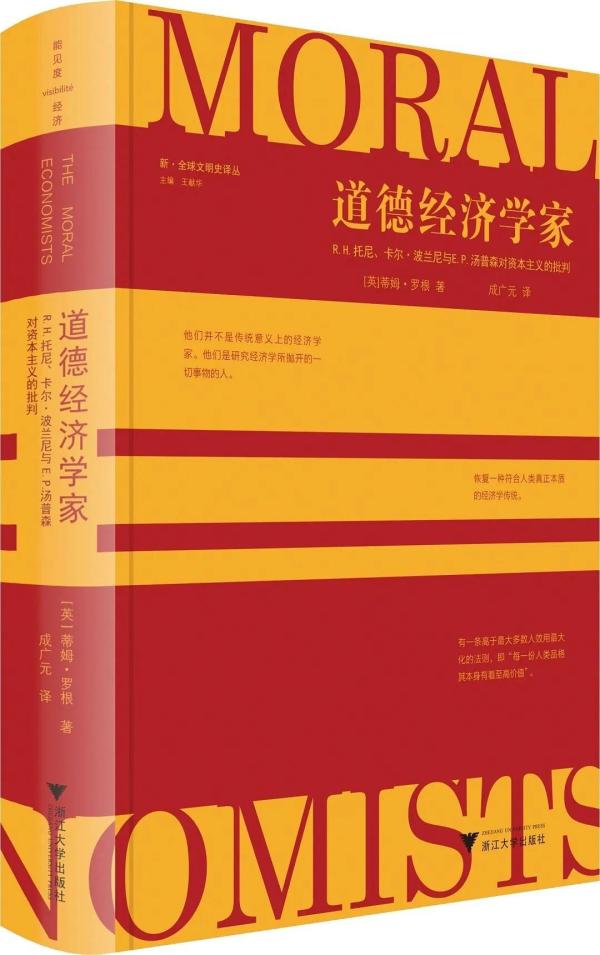
读英国经济史家蒂姆·罗根的《道德经济学家:R. H. 托尼、卡尔·波兰尼与E. P. 汤普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广元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虽然这部书原版是2017年,而且写作风格和翻译都有点烦人,但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疫情中的“批判”、社会选择与道德经济学的关系。在作者看来,过去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更多着眼于物质不平等的领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在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方面。在这里他当然要一再提到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3),对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只是在功利主义论据基础上批判经济不平等感到遗憾。蒂姆·罗根要在该书中重建一种所谓的“另类的批评传统”,他自言“本书的目的就是重构这种产生于20世纪英国对资本主义的另类道德批判的发展和沉沦。这种批判模式在失败以前也曾大获成功。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两次大危机之间,我们将要回溯的这些思想激励并且影响了改革发持续推力的产生。”(第2页)他从历史上三位重要的“道德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的另类批判方法中要继承和发展的是不能仅仅把不平等看作是物质性的,同时也要看作是道德性的和精神性的问题,对物质不平等的批判必须同时建构起道德批判的思考空间。他希望“我们的批判既强调物质不平等,又带有某种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特性。”(20页)
他聚焦在三位作者和三本书上,分别是:R.H.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1944)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他认为“这些作品是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地标,也是当代左翼作家反复提及、不能绕过的参照点。”(第3页)但是对于那些不熟悉他们的观点及语境的读者来说,这部经济思想史论著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作者自己也说在这三本书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另一些联系则是不那么明显了。他指的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主义的那种社会批判传统,这种传统对功利主义一直保持反感。他认为道德经济学家们继承并坚持了这一对功利主义的反感,甚至在今天批判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时候仍然要反对这种功利主义。(第4页)罗根在书中指出,托尼、波兰尼和汤普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中心要点,是关于人类品格的概念;他们的思想脉络除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功利主义关于人的概念的批判,还有托尼从基督教神学中提取出的人类品格的理念,以及波兰尼在斯密的作品里发现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基础”和此前他试图从早期马克思的作品中找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但是,后来的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詹姆斯·密尔却在他们的著作中舍弃了斯密的“人文基础”,完全无视人类的本质,只把人当作“仅对占有财产充满欲求的存在”。(14页)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交集来看,这样一条思想脉络是颇为吸引人的。
不过,罗根也承认以对物质不平等的批判来代替道德呼吁也是一种进步,因为这使得对问题进行合理的、经验性的讨论成为可能,促进了理性的社会改良,使历史呈现一个乐观的故事、一种进步史观。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中,物质思考同样也“显示出一种另类的批判方法的沉沦、另一种介入社会问题的途径的废弃、一种开启了关于自由和团结的深层议题的尝试的失败——而这些深层议题正是当下流行的狭隘经济主义所系统性排斥的。”(第2页)如何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批判中拯救和开启“关于自由和团结的深层议题”,这就是作者力图实现的目的,为此他要把“道德经济学家”与当代的相关思想和运动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肯尼斯·阿罗和阿马蒂亚·森是在他所认为这一批判传统中最有前途的创新人物。
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理解的社会问题与托尼为波兰尼和汤普森搭建的“社会问题”框架有相同的意涵,而森也同样显示出与这一传统的相似性。(19页)阿罗提出的著名的“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投票选举这一民主决策机制中会遇到的基本困难,认为通过理性或者其他的可接受手段实现从个人价值向社会选择的最佳转换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就是,“完美的民主”是不可能的,非独裁政治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人们似乎只能在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威权主义之间打转。阿马蒂亚·森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使道德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建成为可能。最后,罗根认为他在本书中“重塑的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设想他们能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选择系统的条款进行重新商讨的机会。道德经济学家……开启了关于自由和团结的深层问题,而这是以物质福利的术语为名的讨论所完全无法领会的。”(345页)至此我们不难理解罗根的苦心用意。
最后再谈谈皮凯蒂。一个多月前皮凯蒂又出版了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Belknap Press: An Impri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3),据介绍在这本部头更大的著作中皮凯蒂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考察了从奴隶制、封建制、殖民主义和种姓制度等这些“不平等制度”造成了经济不平等,他要继续敲响面向经济不平等的愤怒警钟,更强烈地呼吁各国实施大规模的再分配计划以减少社会不平等。关于经济不平等的起源,他认为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关于财产及其分配的观念的影响,因此要通过揭露不平等的真相而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对收入、财富、碳排放征收高额累进税。当然马上就有经济学家对他的论据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提出有力的质疑,认为重要的是机会的不平等、自我实现能力的不平等和地位的不平等,而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提高支出以及相应地提高税收可能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惩罚富人,而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找到新的机会。这需要全新的政策,而不是已被证明不可取的旧政策。(拉古拉姆·拉詹为《金融时报》撰稿)在我看来,皮凯蒂把经济不平等归结为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把不平等的程度与人们的容忍度联系起来,最后还是相信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中通过主张建立新的税收制度以消除不平等,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路径,而且也同样带有道德批判的意味,虽然他还是以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为基本着眼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曾经表示,“进步资本主义”可以极大地帮助减少财富掠夺,创造更可持续的公平经济。皮凯蒂的主张与此也是相通的。与蒂姆·罗根在书中最后部分提出的那种重返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的路径相比,皮凯蒂可能更显得有现实感。无论如何,疫情中的道德经济学批判最后必将引向对于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的批判,最起码要对侵蚀公民自由的“资本主义大数据监视”实行有力的批判。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