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叙述者与……他们的狂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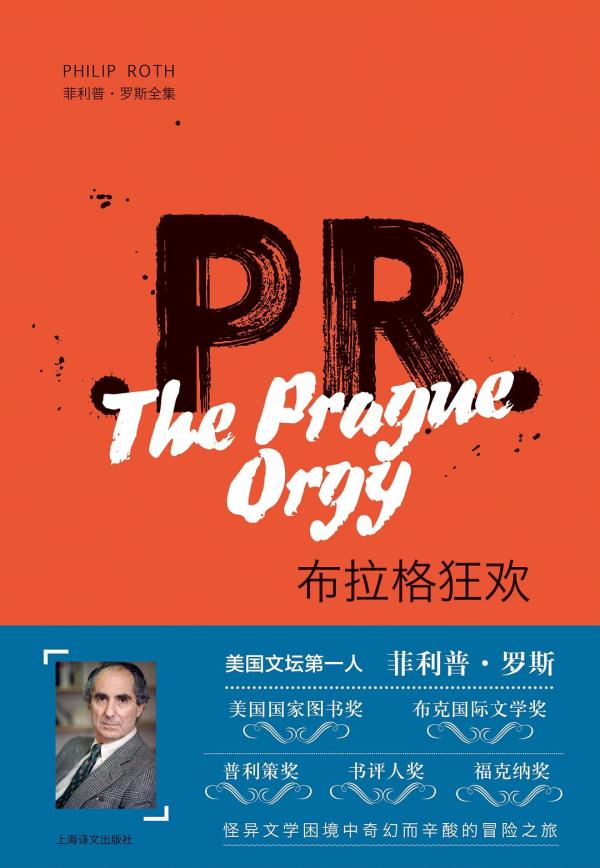
美国当代杰出作家菲利普·罗斯(1933—2018年)的祖先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他从小同时承受了东欧犹太文化的滋养和压抑。在文学上他最大的成就是书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也就是早在19世纪美国评论家德佛瑞斯特所说的那种描述美国生活的、而且描绘那么广阔真实和富有同情心的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布拉格狂欢》(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2月)恐怕难以在罗斯的文学长廊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在罗斯的东欧与犹太文化情结中,这部小说有着特殊的意味,而且在冷战晚期的国际文化氛围中更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布拉格狂欢》是以作家祖克曼的成长为主线的系列小说中的一部中篇小说,主人公祖克曼就是菲利普·罗斯本人的化身。这时的作家内森·祖克曼已经功成名就,在1976年初受捷克流亡作家西索夫斯基所托来到捷克,目的是找寻他父亲生前写的意第绪语小说手稿。但是他发现自己处处受到监视,找到的手稿被没收,被押送去机场驱逐离境,但是在登机前又被拦下……。仅仅是在四十八小时中的匆匆一瞥,祖克曼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与作家的命运困境,主要通过他与所认识的捷克作家的对话,呈现了那些被放逐的流亡艺术家或被驯服的当地作家如何在纵欲狂欢、放逐自我的同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身体、声音表达出反抗束缚的精神性的。菲利普·罗斯在这里把文学与作家的命运与严苛政治局势和社会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他的精神原乡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关注与同情。
对读者来说,全书扉页上写着“摘自祖克曼的笔记”,表明了它的日记式写作体裁。罗斯本来就擅长戏谑性和嘲讽性的修辞手法,这在日记式体裁中容易变得更为变化多端;而且对白中时而插进来的人物常常来路不明,直接引语中的引语时常使对话场转移或复位,有时又插入“我”的主观感受和议论,总之所呈现的常常是一幅多边的、多视点的对话语境,读者一不留神就容易转晕了。
小说第一部分记录的是祖克曼于1976年1月11日在纽约与捷克作家西索夫斯基和女演员伊娃的谈话。关于捷克作家与文学的命运是这部小说的核心问题,也反映了罗斯关于文学家与所处社会体制的关系的严肃思考。在对话中,祖克曼问流亡作家西索夫斯基:“虽然你的书被禁了,但你还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吗?”,“可以。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怕就得逆来顺受了。我不能写作,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质问。要想做点事,做任何事,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你必须选择屈服,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国家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命运。已经八年了。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甚至满意于自己对俄国人的恨意,大部分人的生活过的都比以前要好。” (10—11页)西索夫斯基甚至会从“谦卑”的道德训令反思自己希望发表作品的用心是否只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进而反思“我这样和他们作对,让自己和认识的人陷入险境,到底是想证明什么?但是很不幸,正如我对不计后果的追慕虚名不以为然,我对逆来顺受则更为怀疑。不是为了别人——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必须做的——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我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12页)西索夫斯基说,“最新的政策是让那些想离开的人离开。那些不想离开的人就必须保持沉默。而那些既不愿意离开又不肯保持沉默的人,就只好进监狱了。”(29页)对于这位作家来说,更大、更彻底的疑惑来自一种尖锐冲突的矛盾状况:“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待在那里,是的,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得某种力量。在那里我至少可以当个捷克人——但我无法当个作家。而在西方,我可以当作家,却无法做个捷克人。在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一个作家而已。我不再拥有其他能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祖国,母语,朋友,家庭,回忆,诸如此类——在这里,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才是一切。但我唯一能够创造的文学是关于那里的生活,而只有在那里才能让我的文字获得我期待的效果。”(13页)
罗斯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的时候说,“我第一次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突然想到,在我生活的社会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什么都可以写,写什么都无关紧要,然而对于那些我在布拉格遇到的捷克作家来说,什么都不能写,但写出的每一句都至关重要。”这就是小说中的西索夫斯基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罗斯比他书中的人物更为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会为了他们那些似乎更有价值、更严肃的主题而和他们交换个人的命运,真正值得佩服的是不处在那种命运中、也不依赖带有标识性的修辞或沉重的主题而能写出严肃的有吸引力的文学。他不同意乔治·斯坦纳认为记录人类灵魂的杰作只能产生于像捷克这样的社会中的观点,因为他想不通为什么所有他在捷克认识的作家不能像斯坦纳说的那样写出伟大的作品。他指出“一种群体性的文学如果封闭得太久,将无一例外变得狭隘、落后、甚至幼稚,尽管他们有丰富的经历可以提供素材。”(1984年《巴黎评论》的罗斯访谈,陈以侃译)罗斯的这些评论对于陷入“流亡文学”和“受压迫者文化”情感漩涡而失去文学价值判断是一种理性的提醒。罗斯在访谈中说,在七十年代早期他经常去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每年春天我都去布拉格,都快接受一点关于政治压力的速成教育。……不管怎样,我越发意识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布拉格和在自由放纵的纽约生活是多么不同。于是在最初的犹疑之后,我决定关注那个我最熟悉的世界中,艺术家的生活有哪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同上)事实上,罗斯自1973年起多次前往布拉格,与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人对话,小说中的许多对话正是源自这些真实对话给他带来的思考。罗斯还提醒我们,“每一本书背后都有这样一些读者看不见的东西,表面上毫无联系,但却释放了作者最初的冲动。我想到的是当时空气中的那种愤怒和反叛,周围随处可见活生生的例子向我展示愤怒的违抗和歇斯底里的反对。”(同上)
西索夫斯基从自己讲到那位扮演契诃夫戏剧中的人物的著名演员伊娃,他认为伊娃没有疑惑,只有仇恨,这一点甚至连伊娃自己也感到很惊讶。的确,伊娃比西索夫斯基有更强烈的反思与愤怒的情感。她说,“我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太会幻想。我们读了太多书,我们情感太丰富,我们太爱做梦一一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都是错误的!”(16页)当西索夫斯基向祖克曼讲授伊娃的故事的时候,她几次要打断他,“别再说这陈年往事了。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自己被禁的书,为了让民主回归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多人在受苦——他们为了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人性、对俄国人的痛恨而受苦,而在这可怕的故事里,我竟然还在为爱情备受煎熬!”(20页)其实在伊娃的内心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情绪,那就是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的荒谬感到彻底的厌倦甚至恐惧,“一想到我曾经是那个女人,我就会恐惧得颤抖!”(22页)但是同时,伊娃对于“他们”与“自己”有非常犀利的判断。她说“关键是我自己太懦弱。我太愚蠢,无法抵抗他们的欺负!我哭泣,我颤抖,我崩溃。我自作自受。在这个世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咬牙坚持!他们真应该把我的头砍下来。那才叫正义!”(26页)
第二部分,祖克曼来到布拉格,2月4日的笔记记录的是他与剧院经营者波洛托卡、女作家奥尔佳等人的谈话,以及他最后被驱逐出境的经过。有关窃听、监控与告密是谈话中不断出现的话题,很难说其中的内容都反映了真实的状况,比如奥尔佳说“这个国家有一半人都被雇来监视另一半人”这句话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其中的深刻与幽默确实不是罗斯在写作中所能想象和发明出来的。祖克曼在捷克感到到处是窃听器,西索夫斯基早在纽约就已经告诉他挂在床头之上的黄铜水晶吊灯是他们最喜欢装窃听器的地方,他还说在你的房间里说话要小心,到处都藏着窃听器;在电话里也最好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在电话里向她提起那份手稿。(81页)著名电影人克里尼克被禁止涉足捷克电影业,但他仍然可以在他的豪宅里呼朋唤友,而且这些朋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被当局列为头号敌人,可能是因为这有利于对外宣传,而波洛托卡甚至认为克里尼克很可能是个卧底,但他说“不过即使这样也没什么关系。没有人会跟他说任何事,他也知道没人会和他说什么,而上面的人也知道没人会跟他说任何消息。”祖克曼问:“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波洛托卡的回答似乎更能反映出罗斯曾被认为是情色作家的兴趣:“就克里尼克而言,意义并不在于刺探政治,而在于窥视性事。这间房子到处都装了窃听器。秘密警察在外面偷听,还从窗户往里窥探。这是他们的工作。有时候他们看到了某些场面还会兴奋。这是一种轻松娱乐的好消遣,让他们可以摆脱琐碎恶意的惯常工作。”(42页)
波洛托卡自己的被监控的故事听起来同样荒诞。他的童年好友布勒夏想成为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之后向波洛托卡承认当局要他监视他,每周写一份报告上去;但他的报告写得很糟糕,因而担心他们会把他开除了。于是,波洛托卡对他说,“布勒夏,我会替你跟踪我自己。我比你更了解自己一天做了什么,我也没什么别的事要忙。我会自己监视自己,然后写下报告,由你当作你写的交给他们。”这样果然有效,布勒夏还把上面给他的报酬分一半给波洛托卡,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发现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间谍和作家,要让他升官了,去监视一个比波洛托卡更大的麻烦制造者,甚至要用他的报告在内政部作为新人的教材。他吓坏了,“现在我就可能彻底毁了,如果他们知道是你自己写你的监视报告的话。”(74页)
颓废与放纵似乎既是堕落,也是反抗。“自从俄国人占领这里以后,欧洲最好的纵欲地点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了。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做爱的快乐。” 波洛托卡如是说,他告诉祖克曼说,“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这里,最坏的人也在这里。我们现在全都是革命同志了。来狂欢吧,祖克曼——让你看看革命的最终阶段。”(43页)这就是书名所讲的“布拉格狂欢”。波洛托卡在克里尼克的豪宅里向祖克曼介绍新闻记者、画家、作家的放纵情史,女作家奥尔佳要祖克曼教她讲“操”这个英文字,然后她说“操这个狗日的世界,操到它不能再操我为止。你看,我学得很快吧。”(52页)奥尔佳坦承自己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取悦监控窥视者,在到处隐藏的摄像头前扮演荡妇形象,在作出性挑逗的同时抵制性威胁,在羞耻而反抗之间挣扎地生存。她要祖克曼和她做爱、结婚、带她去美国,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么多国际名人来到布拉格欣赏我们受到的压迫,但一个都不愿跟我做爱。为什么?……你以为签署一份请愿书就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要想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就只有和奥尔佳上床。”(65页)祖克曼感受到的是,“这些一无所有的布拉格人,身处如此难以忍受的环境,面对彻底的束缚以及日复一日地遭受羞辱,过着这样压抑的生活,却还能展现出那样充满机智时尚和喜剧性的举止。他们尽管被禁止发声,却仿佛全身都在呐喊诉说。”(63页)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1976年2月5日的笔记,祖克曼在被驱逐离开捷克之前的各种谈话。祖克曼看着一群喝酒的工人,想起曾经的剧院经营者波洛托卡现在成了博物馆的看门人,想起波洛托卡的解释:“就是我们现在安排事情的方式。卑贱的工作都由作家、教师和建筑工程师来做,而建筑本身则由醉汉和骗子来干。有五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原有的工作。一切都由醉汉和骗子接管。他们和俄国人相处得更好。”于是祖克曼想象着威廉·斯泰伦在宾州车站的酒吧间洗杯子,苏珊·桑塔格在百老汇面包店里包装面包,戈尔·维达尔骑着自行车给皇后区的学校食堂送意大利香肠的情景。(106页)这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真实遭遇与想象。
查尔斯大学的一位仰慕祖克曼的学生来酒店找他,告诉他要尽快离开布拉格,否则会被当局抓起来。下面这段对话颇有意思:“我?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因为他们在罗织罪名。我是查尔斯大学的学生。他们讯问了我的教授,也讯问了我。”“可是我才刚到这里。什么罪名?”“他们告诉我您肩负着间谍使命,让我离您远点。”“罪名是搞间谍活动?”“罪名是策划与捷克人民为敌。”(93页)但是,老练的波洛托卡认为他们只是在吓唬这个学生和他的老师,他们感兴趣的也只是这个学生和老师。他还说不要太看重秘密警察的能力,他们就像文学评论家一样见识少之又少,判断错误很多,干脆说“他们就是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评论是警察评论。”(114页)那么,波洛托卡的说法究竟是否可靠?他以自己的经验回答祖克曼的疑虑。他曾经被抓起来,但是在审判前就把他放了,因为抓他的理由太荒唐了:在他的剧院里,演出中的主人公总是在本应大哭的时候哈哈大笑,这就成了他的罪名。于是他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时候学会的是“不要停止咒骂,永远都不要停止咒骂。”(117页)祖克曼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个充满叙述者的国度,我只是刚刚开始倾听他们的故事,我只是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故事像一条蛇似的正在层层蜕皮,悄然无息地从包裹我的叙事中溜走。”(145页)“在布拉格,故事不仅仅只是故事;它们已然替代了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成为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替代了他们其他的可能性。讲故事是他们反抗掌权者们高压政治的一种形式。”(112页)
在被送去机场、驱逐离境的路上,自称是文化部长的诺瓦克告诉祖克曼,作家在捷克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是国家的道德标杆,然后他说“我可以让你认识一下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明白普通捷克公民的想法和你所见的那些人不一样。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举止不同,也不尊崇他们。普通捷克人对这种人深恶痛绝。他们是何许人也?性变态。不合群的神经病患者。充满仇恨的自大狂。他们在你看来很勇敢?你觉得他们为了自己伟大艺术付出的代价让人激动?好吧,辛勤工作、希望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好的普通捷克人可不这么想。他觉得他们是反叛者,是寄生虫,是被遗弃者。至少他们神圣的卡夫卡知道自己是个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永远不能和他的同胞一起过上健健康康、普普通通的生活。但这些人呢?这些不可救药的离经叛道者,妄图把他们的道德观树为社会准则。最糟糕的是,如果让他们随心所欲,让他们恣意妄为,这帮人一定会毁掉这个国家。”(136—137页)他的确讲得非常好,接着他还告诉祖克曼关于他父亲,一个现在已经退休的机械工“这一生是如何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的”:他曾经颂扬过马萨里克、希特勒、贝奈斯、哥特瓦尔德、杜布切克,“这才是代表了真正捷克精神的人民——是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必然。他们不会嗤笑秩序,任何事不会只看到最坏处。……他们知道如何区分什么是可能的事,什么是愚蠢、狂热的错觉——他们知道如何体面地屈服于历史的不幸!这片让我们热爱的土地能继续存在下去,要归功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离群、堕落、自高自大的艺术家!”(143—144页)这就讲得更为清楚了。
叙述者与他们的故事,无论是狂欢的或严肃的,都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见证。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