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 | 一周书记:二十四桥下的……波光微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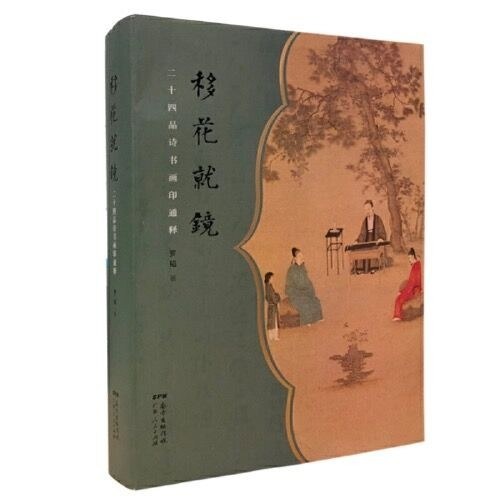
《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罗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352页,168.00元
读罗韬新著《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如漫步于繁花镜影之间的二十四桥,掩卷后恍然而觉“通释”之意旨遥深。所谓“自非灵心妙悟,感而遂通者,孰能与于此哉!”(郭若虚语)“灵心妙悟,感而遂通”,似乎说的就是这部《移花就镜》。
正如胡文辉序所言,“罗韬论学,尤其是谈艺之学,最大特色在于一个‘通’字,艺与艺的通,艺与文的通,还有艺文与世俗的通。……透过《二十四诗品》所设定的风格类型,以观照艺术,此可谓‘批评的通感’;同时,它所观照的艺术,并不限于一端,而是打通了诗、书、画、印,囊括最有‘中国特色’的四大古典体裁,此又可谓‘鉴赏的通感’”;“入于诗,出于艺,堪称《二十四诗品》的升级版。”说得相当简括精准。周松芳序则从中西古今文论的背景以及罗著中的“移花就镜”各例详细阐发了罗著之异于时流与创见迭出,谓其“于每一品均选取从古到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诗篇以为例证,纵向的史的观念是非常自觉的,所引近百首诗,其中多有不常见者,也可见作者对传统诗歌浸淫之深广。又每一诗,必知人论世,及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写作的特定事件与特别心绪,更显作者识见之高明。……论诗如此,移书法、绘画、篆刻之‘花’以就各品风格之‘镜’时,作者也无不站在各体艺术史的高度,以胸次通观而得精见卓识。”何谓“移花就镜”,也讲得很清楚。
花语绵延,镜影恍惚。二十四桥明月下波光潋滟,未可忽视的是,倒影中并非都是风花雪月或仅仅是文艺现象学。作者博览群籍,精研文史,于劫巨变奇之近代国史犹熟于心,平素心所系者文化精神之兴废聚散,纲纪民生之火热水深,时发风寒血沸之慨,绝不是岁月静好、玩花丧志、持镜阿世之人。如谈“薄戎奴”印,讲完其人物背后的“舅父、姨父们,或居拥立之功,或受顾命之尊,但因审势不当,终难逃被绞杀、刀诛、炮决之灾”的故事之后,作者提醒我们“既要以读新闻的兴致去读历史,也要以读史之眼光去看新闻”。然后才是“此印是玉印,工艺精湛,构字揖让有情,点画委曲尽致,是汉代鸟虫篆印的上品”。(243页)能够把鸟虫篆印与绞杀、刀诛、炮决捆绑在一起,能够把读历史与看新闻联系在一起,这“花”所移就之“镜”已经不是什么二十四品所能囿限的了。谈“宝廷诗绮丽背后之沉痛”,作者指出“宝廷处于末世,未免颓废之绮。但通过这颓废之绮,却能让我们较深刻地领略清廷式微之征”。意犹未尽,最后干脆以“欢场干净于官场”作结:“后世有人评价说,这件事的背后,是宝廷失望于当时政治,有意以微过自劾,其实正是颓废背后的清高。陈宝琛说他是‘梨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温柔乡原来才是清净土啊!……当此末世,江湖崇高于庙堂,渔妹贵重于浊吏,欢场干净于官场。则‘绮丽’一品,寄兴深微,足以观世,这又何尝亚于雄浑、冲淡之属?”(121页),快语真言,崇高、贵重、干净,刹那间庙堂三观尽废。罗韬由“绮丽”而能“寄兴深微”,以观彼末世,可不是随便的触着磕着而已。所谓知人论书,二十四桥曲径“通释”,还是会回到那句老话:“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况周颐《蕙风词话》)明月下的二十四桥,观花揽镜之余,我相信罗韬未能忘情的是花镜之外仍有万不得已者在。
讲到这里,霍然想起罗韬对胡三省和陈垣颇有研读心得,会不会在此“移花”镜像中也有《通鉴胡注表微》的微光闪烁?谓予不信,试看一例。罗韬论唐初书法之尚王羲之、尊虞世南,先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纪》“武德九年九月”所言“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继而点出“后人但知太宗独嗜羲之,实内蕴军事上以北征南、以胡征汉,文化上以南化北、以汉化胡之大策略,此太宗之所以为‘华夷父母’也,亦唐初政治文化之大关节也。于是天下习书者,逢迎君好,共尊江左。王羲之书法之所以见重,虞世南地位之所以尊崇,皆书法背后之大政治。此点治文学史、书法史者一向忽之,在此特加拈出”。(153页)此“背后之大政治”之中,除了“化”的策略心机之外,或可补上的一是虞世南的博闻强记、直言敢谏亦是太宗所倚重的原因;二是胡三省的知识分子论——“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无论如何,罗著每于易被人忽视处“特加拈出”而表之者,或多与风雨江山中之“大政治”相关相连。
陈垣先生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开始写作《通鉴胡注表微》,时年六十五岁,其写作初衷自然有抒发身处沦陷区、目睹山河破碎的抑郁悲愤之情,与胡三省的宋遗民情结当有同感,故而“援古证今”。他在对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作探微式的解注、归纳和分类之外并有寄怀,所涵咏抉微者实为胡三省“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虽然陈垣表而出之者究竟是否完全契合胡注原意,见仁见智,但是其于辩误考证中借以发微者有二:一是述其史学研究的识见,二是观照现实,融进感时伤势之情怀。更使人感慨的是,史界向有义宁、新会“史学二人”之说,然而似乎真是时势弄人,几年之后二陈言述分途有别,令人不忍。“表微”者无非阐幽抉微,关键是何谓幽、微,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和不同的语境中当有大不相同的指向与性质。由此想到罗韬在花镜之间的“通释”其实是“双通”:不仅是在艺、文、史之间的领域之“通”,亦时有在艺文书画与价值信念、纲纪立场和睹时感世之间的精神之“通”,而后者或限于时风而只能是二十四桥下微澜之中的潜思默诵。无论是在哪种层面上的通释与表微,罗著“无不一与诸古人血脉贯通,……乃独夺神抉髓,使之重开生面”。(王时敏语)
由“含蓄品”而谈诗中寄托,选张之洞《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确是目光如炬:“张之洞此诗,是一首清朝覆亡的预言诗。……说南人为相会带来祸乱固然是不公的,但纵然是贤相如李、虞、文、陆,也挽回不了宋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147页)具体言之,“到宣统时期,满汉危机突显,人心乖离,张之洞从中感受到王朝的危机。……这缘于他对摄政王载沣等新一代最高统治者极度失望,以及他的救亡之道——速行立宪的建议一再被否定,于是末世之感日增”。继而“我们还可参读张之洞作于同一时期的《读白乐天句》‘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到他病危时对客感叹‘清社亡矣’,这四个字,正是《读宋史》的根本注脚”。(148页)能作此解,既要熟悉古典(“邵雍闻鹃”),亦须明白宣统年间的“今典”,但是更不离开“对时政的判断与识见”。(149页)何谓寄托?作者说这是一个诠释学的问题。要理解寄托之诗,不但要从语句上弄清其义,还要充分语境化,从而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即陈寅恪说的“发皇心曲”。“尤其在朝代更替之际,敏感的文人内心每每有巨大的痛苦,他们往往用诗来表达这种痛苦,这些隐晦的诗,引发后来读诗者的深沉回味,也引起笺注家的纷纭解释。就像陶渊明的《述酒》诗,内里有很多隐语,长期得不到解释。到六七百年后,南宋韩驹指出了此诗的解释方向,大家才慢慢读懂它。此诗其实记述了刘裕谋弑晋恭帝一事,寄寓了陶渊明的愤慨之情。又如钱谦益的许多诗,也隐藏了他在入清以后,参加复明运动的行事心迹,经陈寅恪先生的笺注,才让人们读懂这些诗的历史内容。再到陈寅恪本人的许多诗,也包含了不少他对时事政治的褒贬,又经过余英时、胡文辉等学者的笺释,才让人们走进陈寅恪的内心世界,理解他的情感和观点。”(148页)——这是中国旧体诗中所谓“寄托”的魅力,不也正是“移花就镜”中的通释与表微的魅力吗?
“奇托”中常有春秋之议,直白说就是深刻的历史关怀与道德批判。“沉着品”中论黄庭坚《书磨崖碑后》七古,在“骨力坚苍”之中更重其历史纵横议论中之沉痛之情及春秋笔法,谓“歌作变徵之声,词见春秋之钺,骨力坚苍,具见于此”。(51页)由“沉着”而“骨力”、而“春秋”,已让人有豁然而开之感,然更进而“附说”,则把胜利者史观也扯了进来,才是真正的春秋之议:“此诗痛责肃宗越位登基,陈衍评为‘议论未是’,那黄庭坚之议论是也未是?……黄庭坚观点与司马光、欧阳修一样,崇尚‘得天下以正’、严守忠孝大伦,所以‘春秋责备于贤者’,褒贬昭示于后世。而陈衍所谓‘议论未是’,观点近于《旧唐书》,就颇类似斯大林所说‘胜利者不应受谴责’。黄庭坚等人不以成败论是非,正是春秋之大义啊!”(同上)成王败寇、英雄史观,虽然自古而然,但是的确于今犹烈,故罗韬深感佩于黄庭坚之议,特以“附说”而彰显坚执春秋大义之心曲。
统观全书,各品风格之“镜”,先在解说、引论中有所论述,然后从诗、书、画印中“移花就镜”,相互观照。但是品之为“镜”、为赏花之话头,其涵义也不绝非是固化、扁平的,仍然有待于综揽古今之中阐发“品”之幽奥。换言之,“移花就镜”之外,别有一种意旨是“以花言镜”,以艺文实例拓展了读者对“品”的理解与思考。试举书中一例。以陈寅恪写于1945年的《忆故居》(“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河山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论“悲慨品”,自然很恰当,但是罗韬却进而从中拈出一个“深刻的悲观论者”:“陈寅恪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社会进化论。在他看来,结束帝制,不是什么新时代开始;抗战胜利,也不是翻开新的一页。他最警惕的,是万民欢呼进步的过程中,实隐含着严重的退化。悲慨,在陈诗中有很深的历史内涵。”(262页)由悲慨诗品中的历史内涵而引申到时代的严重退化与义宁陈氏的悲观主义,可谓发人深省,而“悲慨”之内涵义蕴亦缘此而有扩展,“必有超越一己利害之感慨在”。(259页)
谈到悲慨品,不能不谈聂绀弩诗,此“花”恐怕只有罗韬才会移至二十四桥明月之下。这首《精神界人非骄子》原题为《悼胡风》:“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作者“既悼友人,亦以自悼”,而罗韬则“乍读悼诗,如闻一代知识分子之苦韵哀弦,为之下泪”。(262页)好一个“苦韵哀弦”!今夕何夕,听当年诗人忆梦、观罗韬移此花于镜前,益发怆然于“如此梦境,包含了一代‘精神界人’的苍茫悲慨”(263页)而涕下!
“悲慨”之后,竟然在“旷达品”中再次与聂诗相逢,该节小标题是“聂绀弩把流放当高隐”。
“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聂绀弩《推磨》)作者看出此非一般的个体于苦难中悟切生死之旷达,而是“履艰危以旷达,化冤恨于嘲诮,实一代知识分子之曲折心史,其意义有浊世才子所不可比者”。(340页)除《推磨》外,聂绀弩还有《搓草绳》《放牛三首》《拾穗同祖光二首》等咏叹在改造中日常劳动的诗篇,除了旷达、幽默之外,应更有“曲折心史”。诗如“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放牛三首》之二)、“鞠躬金殿三呼起,仰首名山百拜朝”(《拾穗同祖光二首》)、“何物于天不刍狗,此心无地避鸡虫”(《赠雪峰》)、“东方红要诗千首,豆麦开花等你题”(《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等,虽然它们都是出自咏叹搓草绳、放牛、拾穗等日常劳动的诗篇中,但其意旨在今天看来已是“昭然若揭”,实让人有“大梦谁先觉”之叹。可知所谓高隐、旷达,实非真的“尘心消尽道心平”,而是于无声处聊听“春雷隐隐”。此期聂绀弩与胡风的唱和诗篇可算是旷达中的“歌”与“哭”,正如木山英雄所讲的,“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充分认识到严酷命运的人,事到如今已用不着恐惧了。而且,感情好像已经被铸型固定住,所以对于老朋友躲避自己的事心中毫不介意。”(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 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182页)
流放边陲,旷达中的悲慨或不难理解;而能于飘逸的墨迹中发现悲慨,如果没有对作者的语境、心情的细心体察,恐怕很难。白蕉《致邓散木札》墨迹飘逸萧散,确如门人孙正和所论,“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但是作者却深知其潇洒脱俗背后的郁抑难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白蕉以右派之身,名入另册,此时他的书法理论和创作正达到高峰。他郑重抄出其中两章寄给老友邓散木(钝铁),邓氏以朱笔加批。全书白蕉墨迹淋漓潇散,邓散木朱批温雅俊逸,堪称合璧。文末白蕉嘱道:‘病中偶写数节,不能示人,寄我铁老就(正),此稿请改后寄还也,千万千万。禾矢女人上。’以‘禾矢女人’署名,实藏‘矮人’二字,这是‘矮人看场’的自谦,还是‘矮人一等’的自嘲?这飘逸绝伦的字迹背后,有多少郁抑待舒?这一篇《述书赋》,对于白蕉来说,当视之为‘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飘逸之品,不无悲慨,此所以让人低回不已,味之无尽。”(321页)白蕉曾被划为右派,这不难查知;而文末所嘱之“千万千万”与署名“有多少郁抑待舒?”,这就不容易体察了。罗韬以《说难》《孤愤》视之,所低回不已、味之无尽者,大概亦如司马迁之“每念斯耻,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故此而证飘逸之品亦不无悲慨。堪与“矮人”相比的是齐燕铭之“无咎”印,罗韬直接把它置于“悲慨品”。齐氏曾是文化部的实际最高负责人,1965年被撤职,此印刻于是年8月。“此印语出自《易经》‘夕惕若厉,无咎’,这是对动辄得咎的自辩?还是对平安无咎的自祈?一定还包含了对国运的忧虑和祝祷。但他在款文上,却以谈艺的方式来掩盖他的真实心境。”(272页)
论“李可染得力在‘深沉凝重’”,作者认为“李可染是‘新山水画’的代表。他的成功是‘迫’出来的。新时代、新话语,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迫使他摒弃‘旧笔墨’,于是他一方面在写生中寻找新图式,此所以‘现实’;另一方面向毛泽东诗词取意象,此所以‘浪漫’”。(55页)于此或可补充的是,李可染于1950年发表的《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是新政权建立后较早由画家撰写、并及时发表的重要文章之一,开宗明义地从国画市场之颓败和国画家生活之困境而引入检讨自己、改造国画的主题,此所谓“迫”者之真实语境也。《谈中国画的改造》的重要意义在于从一个传统营垒画家的嘴里说出了“旧国画如何为新政权服务”与中国画存亡之关系,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不过仍需细心分辨的是,李可染并没有如当时许多文人那样口口声声地把“改造自己”放在第一位。1979年李可染检视自己作于四十年代的山水画稿,题记中有言:“是时钻研传统,游心疏简淡雅,尚能见前人规范,与今日所作迥异,判若两人。”因时代巨变而致使艺术“判若两人”自是实情。至于向“诗词”“取意象”,固然不无“浪漫”之想,然更有“现实”之需:红色山水画与领袖诗词画既为作者们提供了政治评价中的保险系数,也为图式语言的探索提供了合法性的出口。政治和艺术的冲突与矛盾既表现为题材的选择,也表现为对于艺术上的精英意识的压制和改造。由此回看李可染的“深沉凝重”,或许亦别有所感耶?
波光微澜,花移镜转。“通释”之下,诗书画印与古史今闻之通亦是一“释”。而所谓“释”者,互证互诠自是其中应有的议题。自清以降,诗史互证互诠的研究方法经近代刘师培、陈寅恪等学者发挥完善,已成为打通文史研究的成熟方法之一。诗书画印与史之互证互诠,也在画史、书史诸领域生机勃发;从艺文作者个人“心史”的角度见证历史,“移花就镜”之用大哉!若借用刘咸忻史学中“风”的概念,表微者虽然可以夺神抉髓,终是“小风”而已,用今天历史学家的话说无非是“执拗的低音”。但是倘若微澜奔流不息,或许也会有“长风万里送归舟”、移花就镜始自由的一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