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话】施传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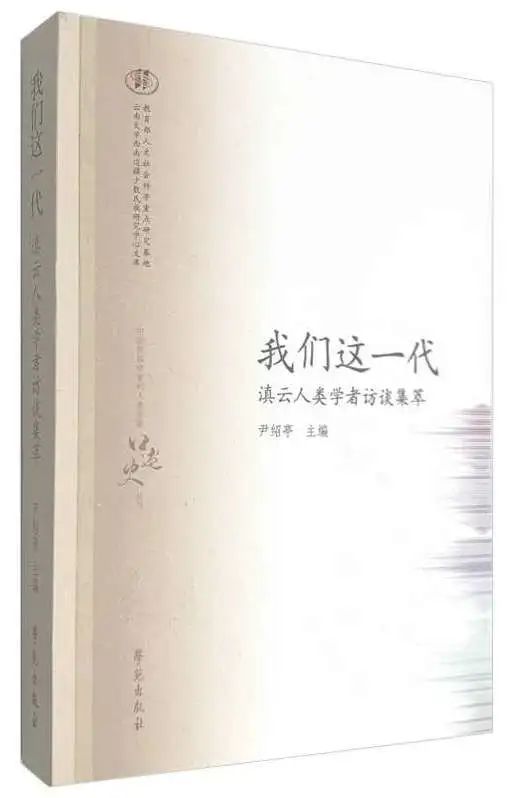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施传刚,男,1951年生,云南大学历史学学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硕士、博士。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等院校和机构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现在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任教。
采访者:赵翰超,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从历史学转向人类学
赵翰超:这篇访谈录的题目是您定的。是否可以请您先谈谈为什么用这个题目?
施传刚:你一定知道,这是《中庸》里摘出来的一段语录。我是云南大学历史系七八级的本科生。1982年毕业前夕班里决定做一个同学录。我当时并没有现成的座右铭,就从自己更年轻时做的读书笔记中选了《中庸》里的这段话作为印在同学录上的座右铭。我从来没有刻意遵循过某种指导思想,平时也没有经常温习四书五经。但现在面对自我总结的任务时,我惊奇地发现,几十年来在我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下意识中引导我的竟然一直是这段话表达的理念。今天看来,谈到治学,我最服膺的还就是这15个字。所以我觉得就用这句话来做这篇访谈录的题目是非常合适的。
赵翰超:您刚才说您的本科是历史专业。您是怎么会从历史转到人类学呢?当时中国就有人类学吗?
施传刚: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世界上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四个重镇之一(其他三个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是在50年代初就中断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恢复。80年代初,只有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有人类学专业。我是到美国以后才读人类学专业的。
赵翰超:您又是如何到美国的呢?
施传刚: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我从短波广播中得知美国国际交流总署在中国的7个省图书馆中放置了美国各级大专院校的介绍,鼓励有志于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前去查阅。云南省图书馆刚好是提到的7个图书馆之一。1981年的中国还非常封闭。见到大量美国学校的介绍堆在自己面前,就像无意中推开了一扇原先紧闭的大门,突然闯进一个新奇而又令人神往的园地。我们班最后实际报考美国学校的同学只有我和后来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谭乐山。我申请了4所学校,两所申请的是历史,其他两所申请的是人类学。结果很幸运,4所学校全都录取了我,而且都给了奖学金。我就是这样来美国的。
赵翰超:您申请攻读人类学的是哪两所学校?为什么选择那两所学校?
施传刚: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人类学而言,美国的人类学系一般都注重自己阵营的多样性和区域文化覆盖面的广度,而避免教授们研究区域和研究方向的重叠。当时全美国只有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系各有两位研究中国的教授。斯坦福大学有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P.Wolf);哥伦比亚大学有莫顿·H. 弗里德(Morton H. Fried)和孔迈隆(Myron L. Cohen)。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资深人类学家。这就使这两个系成为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强的两个人类学系。
赵翰超:那您为什么选择去了斯坦福而不是哥伦比亚呢?
施传刚:我在云南大学读本科时,省政府决定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亟须充实科研队伍。从为本院吸引和培养人才的角度着眼,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邹启宇先生到云南大学历史系讲授东南亚史。邹先生的学术视野极其广阔。他在课堂上把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各国学者都逐个向我们做了盘点。其中对施坚雅先生关于泰国华人的两本著作做了重点介绍。可以说,从我刚开始接触学术研究时,施坚雅的名字就在我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是选择斯坦福最主要的原因。我到现在都认为,我这一生最好的运气就是有机会在斯坦福完成我的本科后教育。

2012-2013年访学期间摄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赵翰超:您还没说您是怎么从历史转到人类学的。
施传刚:在老舍的话剧《北京人》中第一次听说过“人类学家”这个词。那个剧中提到的人类学家是研究古人类化石的。少年时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也读到过费孝通先生的回忆文章,记叙他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的往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先生的自我认同是社会学家。他当时努力推动的也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复兴。我当时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什么是人类学毫无概念。真正把这个学科介绍给我的还得说是谭乐山。我们同学时,他十分偏好民族学和民族史。记得有一年暑假他完全泡在图书馆里,结果写出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民族学的最高刊物《民族研究》上。本科生就在学科最高刊物上发表论文,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他也告诉我人类学是一个比历史学更广阔、更有趣的学科。我记得他对我说,搞历史就是翻故纸堆,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历史。按照他的看法,像我这样兴趣爱好广泛、语言基础扎实的人,人类学比历史学更能满足我求知的好奇心,也能更充分地利用我在古代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等方面已经下过的功夫。他还借了一本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cliffe Brown)写的关于社会人类学方法的书给我。我的这位同班同学就这样成了我走向人类学的指路人。
通过和谭先生的交谈以及阅读,人类学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已经逐渐清晰起来。联系到自己的故乡是云南这个做人类学研究的宝地,到需要做决定时我就不再犹豫了。
摩梭文化研究缘起
赵翰超:您对摩梭文化或与摩梭文化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您是怎么选中摩梭文化作为自己研究的题目呢?
施传刚:这就说来话长了。前面说过,我来美国攻读学位之前对人类学的认识非常肤浅,申请学校时必须提交一篇英文的写作样品,我就写了一篇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的多样性和民族关系的文章交上去。我虽然生长在昆明,但基本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感性认识并不多。文章根据的都是已经出版的二手资料。到临动身到美国前,我想到应该带一点有用的书过去。当时刚好有两本关于摩梭的民族学专著新近问世了。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著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另一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严汝娴、宋兆麟著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两本书我都带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不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都可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我一进去就算是博士生,但还不算博士候选人。进入博士班后要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提交一篇被称为“春季论文”的文章,由四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通过之后,才能获得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如果通不过,奖学金和学生资格都将被取消。对我这个基础极差的学生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进入学习过程后,系里没有给我丝毫缓冲适应的机会。教授们把所有学生一律当作最优秀的人才来要求。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在应付每学期功课的同时,我实在没有余力为春季论文做广泛的研究之后再定题目。在上一门有关文化性别的课时,我联想到了从中国带来的那两本关于摩梭的书。根据两本书一致的叙述,传统社会中的摩梭女性享有比男性还高的地位。这和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对所有文明社会中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论述不符。于是我就抓住这一点,又做了很多图书馆调研后写成了一篇题为“A Challenge to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Male Authority over Female”《质疑男性普遍对女性拥有权威的概念》的春季论文。60多页的论文总算是如期交了上去。话说到这里,还得折回头去交代另一个头绪。
除了春季论文之外,第一年我还得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博士论文写什么题目。有一次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翻阅资料,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云南西部中缅边境上的一个佤族社区和一个拉祜族社区在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一段25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拉祜族的人口翻了4倍,而佤族人口却呈现出负增长。我在为申请入学的写作样品做研究时就知道拉祜族和佤族的继嗣制度和家庭组织不一样。看到这个报告后就想当然地以为两个民族人口增长的反差是继嗣制度和家庭组织造成的。我的两位导师武雅士和施坚雅都很重视人口问题,都是人口学领域中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他们对我的研究兴趣有很大的影响。我找到这个切入点后非常兴奋,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博士论文题目。于是我写了课题申请提交给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获得批准后,我就利用第一年结束后的暑假回云南去进行前期调查。滇西实地调查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原来人民大学报告中提到的佤族的人口负增长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原因造成的。真实的原因是,那个佤族社区就在边境线上,居民在边境两边都有亲戚。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政治运动不断。中国一侧的佤族边民往往利用地缘的便利,运动一来就逃过边境。我被告知,有时村里各家各户正在吃饭,听说工作组来了,丢下饭碗就跑。工作组进屋后,矮桌上的饭菜还是热的,人已经不见了。因为人口调查时这些跑出去的人无法计入统计数字,所以这一地区佤族的人口报表上才出现了显著的负增长。而拉祜族居住的地方却不具有这样的地缘便利。所以不存在政治原因造成人口统计严重失真的情况。既然真实情况如此,比较拉祜族和佤族的人口与家庭制度也就失去了人类学的意义。我为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所做的探索又被打回到原点。
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学校并向导师报告了前期研究的坏消息。武雅士教授只是轻轻皱了一下眉,略微沉吟了一下对我说:“你何不就以摩梭作为你博士论文的题目呢?”说着他把我回中国前交上去的春季论文递还给我,并告诉我论文已经通过了。我松了一口气,急忙查看附在后面的评语。当时的系主任Harumi Befu(别府春海)教授在他的评语中写道:“He already has a dissertation in the making.” (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在写作过程中了)。既然老师们的意见都是如此,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摩梭也就此成了我长期研究的对象。

2013年与合作二十三年的研究伙伴合影
摩梭文化的学术价值
赵翰超:从您开始研究摩梭文化到现在快30 年了吧?摩梭文化为什么值得您花费毕生大部分的精力?它的学术价值究竟是什么?
施传刚:我是1987年10月第一次到永宁开展田野工作的。我研究摩梭已经超过30年了。我曾经在自己的一些中英文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摩梭文化的人类学价值。如果你想比较详细地了解,可以查阅那些出版物。这里我只是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20世纪60年代,摩梭文化刚进入中国民族学家的视野就立刻引起了轰动。这个案例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它被认为是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史宏观学说的证据链补上了原先缺失的一环。简单说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所依据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恩格斯和摩尔根关于“血缘家庭”和“群婚”的判断是根据推论而不是民族志的例证做出的。这就为后人质疑整个社会进化论的架构留下了很大质疑的空间。中国民族学家发现“永宁摩梭”的实例后,认为这个新发现的案例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进化论的证据就像猿人化石作为人类体质进化过程的证据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重大意义自然不言而喻。我在这里重提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回顾摩梭研究的学术史,而是因为你问到摩梭研究的价值,所以我想告诉你:摩梭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同凡响。还有一点想要告诉你的是,以不同的眼光可以看出不同的价值来。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80年代初出版的两本关于摩梭的民族学专著确实在理论和方法的各个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是摩梭研究的奠基之作。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内,后来的摩梭研究都绕不过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民族学家们对摩梭研究做出的贡献(包括那两本书和一系列内部流通的调查报告)。下面我再简要归纳一下摩梭研究在我眼中的价值。

与云南母校学友和学生合影
全人类的任何一个文化都存在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变化的速率会有快慢。变化的幅度有可能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很微小,但文化传统不会是恒定不变的。我们在估量一个文化的研究价值时,必须把文化变迁的因素纳入考量。从20世纪50年代摩梭地区被完全纳入中国大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以来,摩梭文化经历了比此前可知的历史性文化变迁的总和还要更大的变化。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摩梭地区也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卷入全球化的洪流。摩梭人的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也是摩梭文化和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趋同的过程。换一个角度讲,也就是摩梭传统文化的特征逐渐消失的过程。所幸我开始对摩梭文化展开全方位探索的时间是在80年代后期。虽然研究的条件已经比不上60年代进入摩梭地区的前辈民族学家,但我还有机会多年和大量对摩梭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并在摩梭传统社会中有切身体验的老人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谈。长期的田野工作使我对摩梭的文化传统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感性知识。对比摩梭文化的传统和现状,摩梭文化传统的人类学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其现状的价值。所以我所说的摩梭文化的人类学价值指的是摩梭传统文化的价值。
概言之,摩梭传统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走访制、没有父系称谓的亲属制(kinship terminology)、母系继嗣、没有婚姻单元(conjugal unit)的大家庭、女性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等方面以及与这些文化实践相应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由于这些核心特征的相互作用,摩梭社会还有诸如人口发展率相对较低等其他一些附属特征。在已知的人类文化中,摩梭文化是集中了上述所有特征的唯一的鲜活案例。正是这些独特性使摩梭文化闪耀出珍稀的光芒。和其他所有文化一样,摩梭文化是摩梭先民在不断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摩梭文化的存在说明其中体现的文化价值和宇宙观对摩梭民族的合理性。在传统时代,摩梭社会和外部世界很少接触。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成批的外来商贾进入永宁。除了佛教僧侣出外求学和马帮到外地经商以外,很少有摩梭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这些因素形成了摩梭文化长时期的稳定性。
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摩梭社会的分水岭。自那时以来,摩梭社会和外部世界融合的步伐日益加快。全新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被引入摩梭地区。摩梭人也通过参军、上学、提干、劳务等各种途径走出自己的家园。20世纪60年代初,民族学家开始在摩梭地区展开系统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开始进入摩梭家庭。2000年,摩梭人开始使用手机。现在,我工作了20多年的4个摩梭村落绝大多数青年或有过打工经验,或正在外打工。分布的地区从内蒙古到海南、从深圳到丽江。有的摩梭人甚至到过缅甸、印度和北美。与外界的交流不可避免地会使摩梭人反思自己的文化。千百年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外部世界的映衬下突然成了问题:“我们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摩梭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理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还在继续。我们可以看到,摩梭文化本质中的独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举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我曾将传统的摩梭走访制的性质归纳为三点:非契约性、非义务性和非排他性。今天,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性联盟,只有第一点,即非契约性,仍然适用于摩梭走访制。其他两点都已经成为过去。因为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的改变,摩梭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亲属制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变化。父系的亲属关系和亲属称谓都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因为和其他文化制度日益趋同,摩梭走访制独特的研究价值也逐渐丧失了现实的借鉴意义而停留在历史的和理论的层面上。(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