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丁修真评《人在棘闱》︱谁的科举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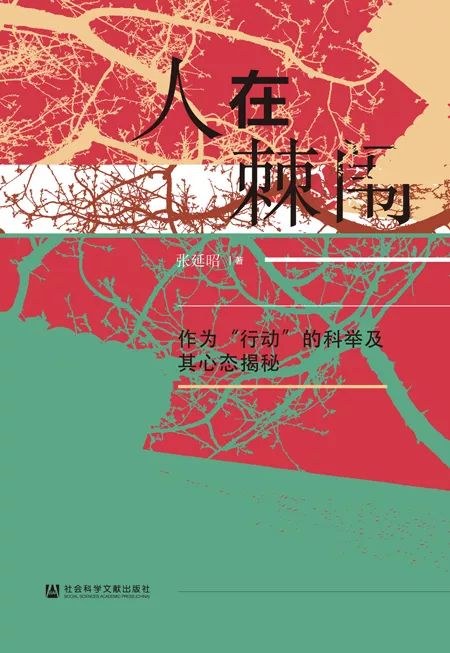
《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张延昭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版,391页,148.00元
科举史上,有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唐太宗微服出访,走到宫廷南面端门时,恰逢新科进士连缀而行,鱼贯而入,熙熙攘攘,热闹之极。见此景象,皇帝喜上眉梢,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的故事很短,但却由此开启了此后长达一千多年“英雄”们的故事。
北宋嘉祐二年,欧阳修时主文省试,出题“丰年有高廪”,谓出自《大雅》,其实为曾巩诗,结果“举子大哗”,欧阳修也是遭到御史弹劾,最终被罚铜五斤。
明代,某科乡试之前,两为平日交好的秀才,相约同赴考场。考前一日夜,其中一人将同伴拟用誊真之笔尖嚼去,以致该考生在场中无法应诗,恍惚之中,幸亏得神人相助,以秃笔应完卷,后竟得高中。
清同治年间,翁同龢出任会试考官,锁闱后发现日常供煤不够,过了几日,日常供水也出现问题,一度逼得考官们“伐树为薪”,自立更生。
直至科举废除,“故事”中断近半个世纪后,清末探花商衍鎏在自述中,记忆犹新的,是“炊煮茶饭靠对号墙,至为逼仄;况复蚊蚋嗜肤,薰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尤不可耐”。
以上几则小故事,汇集成辑,大概可冠以科场典故之类的标题。今日视之,又以其碎片琐忆,似更难博通人一笑。然而诚如学者所言,非碎无以立通。能够在杂芜丛脞之中,拈得一千古通透的命题,不正是历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张延昭教授新著《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以下简称《棘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棘闱》共分导论、序篇、正篇、末篇(结语)四个部分。序篇“表征与规训”,旨在介绍全书的理论依据,正篇“人在棘闱”分为四章,分别就考官与考生两个群体,描述其入闱、在闱的活动与心态。张延昭教授教育学背景出身,在书中,充分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学说,尤其参考了法国学者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相关概念,对科举史中常用的贡院、科场、棘闱等表述的内涵加以重新审视,其论述,既与笔者熟悉的历史学路径不同,也与当下教育史的通行观念有别。
何为贡院?
在一般人眼里,贡院,就是科举时代的考试场所。事实上,除中央外,地方贡院的兴建,可能要迟至南宋时期,此前士子应试大都借于官舍、寺庙等地。即使朝廷出台了规定,各地具体实施的情况也很难统一。明清时期,仍可见不少地方借寺庙、官舍考试的事例。清顺治初年,山东一地乡试,仍以芦苇草棚搭盖,可见虽有其制,地方限于财力,往往难副其实。因此在一般的科举史叙述里,不太会将贡院单列,往往一笔带过。倒是随着近年来,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潮的兴起,贡院遗址遂成为科举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式,受到各级政府颇为重视的资源。一些学者就地方贡院的发展、贡院修缮的经费来源做了讨论。
《棘闱》的作者则认为,贡院并不单单是一个考试的“场所”,更是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表征”。其建筑空间的布局,时刻传达着诸如“大一统”“至公”的政治理念。例如,“贡士于天子”这样的表述,本身代表着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明远楼”“至公堂”“衡鉴堂”的命名与设计,分别传达着国家“求贤”“取士”“至公”的理念,而挂在贡院门口那些看似装饰用的门楹对联,则时刻起着对士人、考官的训诫作用(29页)。作者认同英国学者萨迪奇对于建筑“是统治者用以引诱、感召以及恐吓的工具”(第3页)的定义,将贡院不再视为功能性的建筑,而是一个需要被“解构”的空间。
不过,如果只是将贡院的“至公”表征加以剖析,多少有“炒冷饭”之嫌。毕竟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平公正理念早已为人熟谙。即使在那些激烈批判科举桎梏人心智力者眼中,科举对于促进社会流动,实现社会公平的功用,仍持肯定态度。即使如一度被唾弃的八股文,也因有利于考官公正评阅,而获得了政治正确意义上的“解放”。
显然,作者的意图并不仅限于此,在主体没有更换的前提下,“贡院”的叙事开始转向“棘闱”。
何为棘闱?
在作者看来,区别于贡院、科场等概念,棘闱不仅能够体现此空间使用者微妙复杂的心绪,更能够体现科举考试的两大特点,封闭性和防范性。如果说“贡院”体现的是科举追求“至公”的政治表述,那么“棘闱”更关乎支撑这样一种理念的技术与行动。作者认为,在“棘闱”中,充满着“现代性的时空建构”,闱中的时间得以细致划分和利用,闱中的空间被人为的改造、化解、分割。以“封闭”“隔离”“监督”为特征的“规训空间”被制造了出来(54页)。历史上逐渐形成的“锁院”“内外帘官”“考生分号”等制度性规定,正是规训意义不断强化的体现。随处可见的高墙,层层围合与分割出一座严密防范意味的封闭式建筑群,空间围场一旦建立,有待训练与监视之“个体”将确定分派(37页)。
这样的分析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福柯的影响。福柯认为规训的达成,需要四种个体的形成,即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年,188页)。在“棘闱”之中,号舍无疑是最能体现“规训”的制度化设计。号舍为士子应试作文的“空间”,屋顶盖瓦,每间隔以砖墙,无门,高六尺,举手可及檐,舍内砌成上下砖缝两层承板,板可抽动,日间写字,夜间抽上层入下层,伸足而卧,饮食皆在于此(69页)。众多应朝廷“求贤”而来的士子,在完成点名、搜检等程序后,入场方能知晓自己的号舍,一条号巷被分割成几十、上百间,每间号舍就是一个格子,每个考生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试题。无门的敞开式建筑,使得考生一切行动均暴露在他人监视之下。一排排低矮的号舍,与高耸的明远楼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着“规训”与“被规训”的权力结构(49、52页)。
读者可能会有疑惑,福柯借助规训,意图在于来揭示现代文明对个体的剥夺和压迫,科场之中,“规训”的依据又何在呢?对此,作者的答复有二:其一,“棘闱”其实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幽暗意识”的集中体现。贡院本身就是各种不信任,是通过制度化的空间建构来进行防弊而建构起来的空间(66页)。在其背后,充斥的是以富贵诱人、消弭社会不服从因素的统治者的考量。正因为如此,求贤反而无礼,求公反而无信。其二,作者似乎对时下科举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并不“感冒”,对那些“平民开放”“抑制权豪势要”的论断颇有些隔膜,而更愿意从“微观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评价科举(67页)。
人在棘闱
至此,作者的写作意图已经很明显。其要关注的,不是大写的“公”字,也不是科场中那些“规训”的表征,而是那些在“规训”的空间中,实实在在的个体。这些个体,可以分为考官与士子两大类,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逸事”,便不再只是笔记小说中的断篇残简,而成具有“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构成的规训实践。所以在全书主要内容正篇“人在棘闱”中,作者分列四个章节来处理那些看似相当琐碎的科场细节。
先来看考官。考官是“棘闱”之中握有话语权力的群体,国家为体现抡才大典的庄严,于考官入闱也是极为重视。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各省乡试官,可以根据道里远近,出发前由户部支给相应的路费盘缠,入闱有明确的仪仗规定。每逢乡试之期,考官所过之处,往往也会引发“人山人海”,“立观者欣羡不已”的盛况。作者则注意到,在极尽显赫的排场背后,考官更是一个功能齐备、分工严格、等级分明的群体,往往呈现出荣耀、激动、恐惧多种复杂的心态(133页)。拟题有风险,考官会因出题不当而遭到皇帝奚落、士子嘲讽,乃至丢官革职。清代皇帝往往以帝师自居,《棘闱》援引雍正皇帝将考官行径与考题内容结合审查之例,揭示考官亦是待考之人的窘境。衡文有压力,书中所引周叙于正统九年主持顺天乡闱的事例,颇可见阅卷工作的繁重:一千二百余名士子,六名考官,三场下来,一人在十五天内,大概要审阅六百余份试卷,一天计之,也要在四十至五十份之间(明制,科举考试,头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等一道,三场时务策五道),以致最后“生杀机关都不管,手如雨点白珠跳”。至于考官在闱所面对恶劣的居住环境,随时而来的病痛等,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此不赘。作者通过考官们入闱前后的反差,意在说明其衡文过程,也是在棘闱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在严格制度规训下的行动,甚至还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对罚俸、丢官甚至丧命的结局,故其所受规训与蜷缩在号舍中的士子并无二致。
至于士子,入闱之前,必须经历的“点名识认”与“搜检怀挟”便是难以言语的苦况。作者的有心之处,不仅在于罗列具体的描写,更注意到古代士人对“名”与“身”的自我标识与遭受吏卒“点名”与“搜身”规训间的紧张。例如直呼其名氏,在士子看来往往视为对本人纵慢侮辱的之举。唐进士李飞,就礼部试赋,因吏大呼其名,熟视符验,感觉受辱而径返江东。至于搜检,作者认为宋明理学在传统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身体的人伦观,自蒙学起,便有对身体行动的严格要求,“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比如同窗、朋友,也只是拱手、鞠躬表示一种诚意而已,尽可能避免身体之间发生接触,从而保持身体上的独立”(117页),在这样一种教育观念下成长的士子,面对“摘帽去履,解衣露体,被其由上至下、由外至内进行细致拿捏,甚至搜及亵衣”的规训,或俯首帖耳,或愤然离场,乃至反抗。
进入号舍的士子,似乎只需面对智力上的考较,但在作者看来,这恰是科举士子群体性“失语”的开始。“失语”表现为大多数记载往往只呈现士子服从考场纪律的状况,而非其具体的行动,即使考生事后回忆,内容也大多简略。为此作者翻阅大量清人日记,尽可能地拼凑出士子所在的规训空间。首先,号舍是一个被给予的“位置”。这样一个随机的安排,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考生十几日的命运。宽敞严实的老号犹如“肥缺”,有助于文兴,若碰上临近厕所、厨房,或是漏屋篷号,则如畏途险境,甚至弃考。其次是号舍中的标配,号板。号板是考生坐卧写作乃至饮食的主要工具,在棘闱中,号板数量不够,质量低劣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士子所苦。然后就是天气。乡试虽称“秋闱”,但在南方地区,低矮且不通风的号舍中,士子往往要与潮闷酷热斗争,若遇阴晴不定的时节,更是要经历暴热至暴凉的煎熬,同治六年顺天乡试,病暑者十之五,死号中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如饮水、污卷等对于号舍士子应试的影响,作者也多有描述,在此不一而足。总之,作者希冀通过对士子号舍中身体与心理的探究,来揭示缜密制度运作下举子的真实感受。在作者看来,棘闱本为朝廷表征求贤取士的礼乐空间,但在现实中,士子在不断地规训中,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与失败感,进而对科举本身产生了怀疑,“若不是广寒梯跌了脚,蓬瀛路迷了道,郁轮袍走了调,因甚价年年矮屋中,唤不醒才子英雄觉”。这样一种揭示,正是作者试图为科场中的“失语者”发声。
谁的科举史?
如果要指出该书存在的一些缺憾,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把握上稍显不够。例如考试群体方面,考官的评卷、阅卷过程,如张连银《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中便曾有过很好的分析,考官入闱前后的情境,陈时龙《崇祯元年会试考释——读明人蒋德璟〈礼闱小记〉》(《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4期)有相当细致的分析。另外从作者熟悉的时段来看,主要集中于唐宋和晚清,以致遗漏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元代的情况,申万里《秋闱校艺——元代乡试的过程》(《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文均未曾寓目。而宫崎市定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日本民众所写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尽管为通俗读物,但该书的写作思路,实与《棘闱》有相合之处,作者似也未有参考。不然,自可使全书增色不少。当然,由于作者并非史学专业出身,这样的要求或许有点吹毛求疵。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读后触动较深的,倒不是作者能够在各类专业语境与科举场景之间娴熟的切换,而是在书中抛出了一个关乎史学的命题。作者在书中对于福柯的参考,并非是要建立起一套有关科举的规训理论,而是要借此来关照那些在棘闱之中的“微观权力个体”,将科场“求贤”“至公”背后的“幽暗意识”还原成一个个被规训的个体行动,以此来关注那些“失语者”在棘闱中的真实境况。故从此意义上论,《棘闱》一书,更多的是为科举史上的“失败者”立画像。在科举史中,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仅以明代为例,据学者统计,大概产生了十余万的举人,但成为进士者只有两万多人,终身不获一第者在八万人之多,遑论数量更为庞大的生员群体了。而也正是这些科场上的失败者们,构成了“棘闱”运作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如果借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注意科举史的主体问题,《棘闱》一书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此外,如果结合近年来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事件’到‘事件路径’,从‘人物’到‘群体传记’,从‘典章’到‘制度运行’,使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个人行为、制度规定本身延伸开来,进而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互动,关注其文化意义”(邓小南:《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从制度到人事,《棘闱》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科举制度研究深化的一个方向。如果暂时抛却制度背后的那些“幽暗意识”,《棘闱》可以视为一幅生动有趣的考试绘画长卷,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