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瀛寰新谭|百多年前一场跨国遗产纠纷:晚清官员真的怕洋人?
【编者按】
近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的《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十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丛书第一辑聚焦晚清时期的中外交涉与交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特邀这批史料的几位整理者,基于史料对晚清外交和中外交流做更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在以更丰富的细节尽可能还原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希望能激发对当下中国外交与中外交流的一些思考。
今日刊出的这篇,讲述了晚清对外交涉中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胜利,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与我们以往所知的“常识”略为不同的近代外交画面。而要理解历史的鲜活与复杂,像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近代中外关系,蒋廷黻曾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鸦片战争之前是我们不给洋人平等,之后则反之,他们不给我们平等。这个说法尽管细究起来也没什么道理,但大体可以代表一般民众对这段历史的整体印象。如果说有人以一个“宠”字来概括汉代“信-任型君臣关系”(见侯旭东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那么以一个“怂”字形容晚清外交,恐怕会得到相当的认同。

很多“80后”的童年回忆——《渔童》
若说更为直观的形象,大抵就类似小时候动画片《渔童》中的官老爷,在洋人面前完全直不起腰杆,帮着传教士抢夺老渔夫的鱼盆。其实,这部动画片又可以带出当时另外一则类似的通俗说法,即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当然,关于这一说法的由来、内涵和所蕴含的深意说来话长,此处便不赘述,不过关于“官怕洋人”一条却未必尽然。
《外交辩难》中的一场外交胜利
总的说来,鸦片战争后,依然不怕洋人,或想让洋人怕的官大有人在。这其中自然有相当部分是与洋人完全没有实际接触下的高谈阔论,或者迷信怪力乱神后的莫名自信,却也有官员是知己知彼,从容应对涉外事件,并让洋人咄咄称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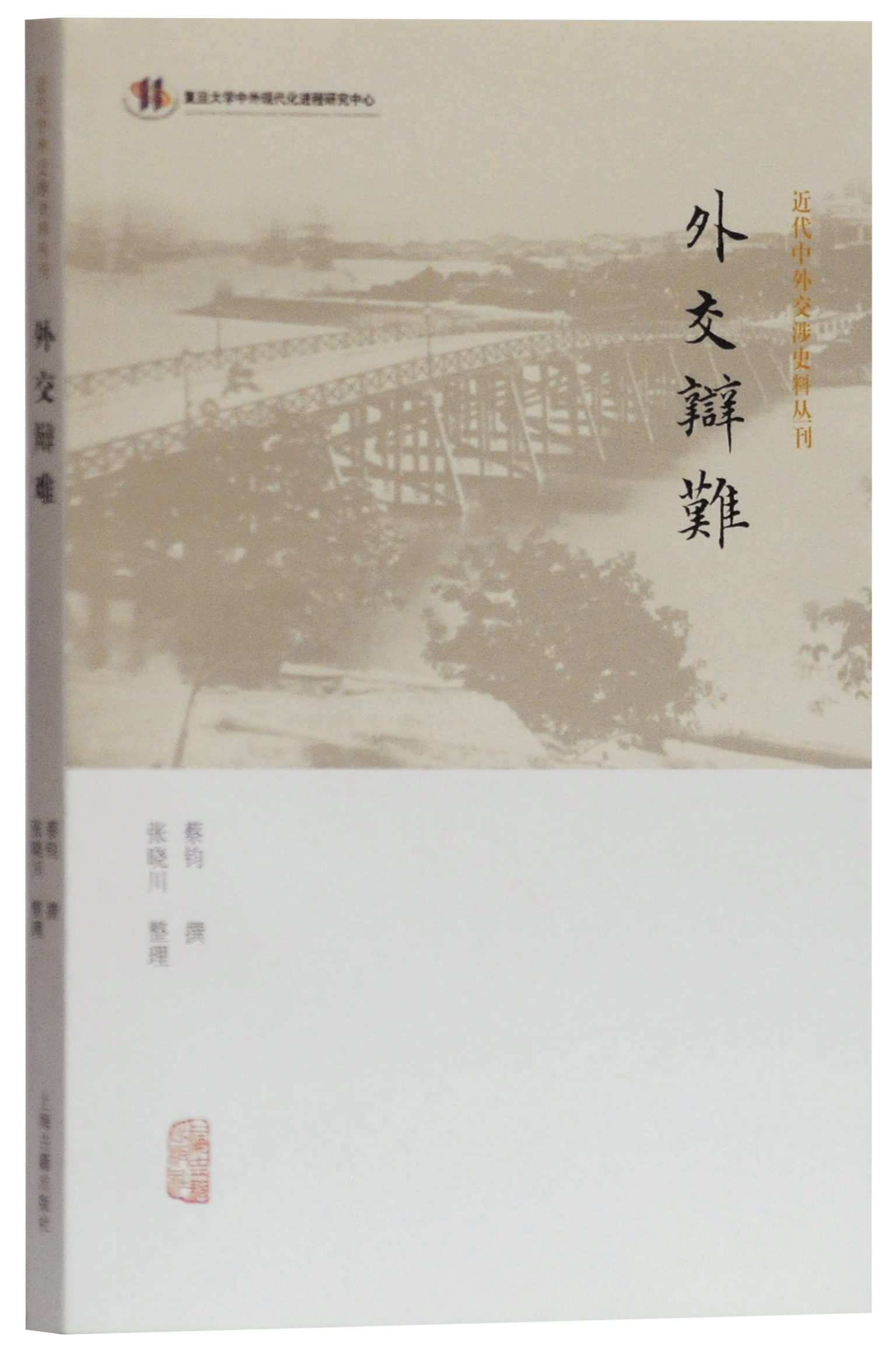
《外交辩难》,蔡钧撰,张晓川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接下来所谈的一场跨国遗产纠纷案便是其中一例,此案被当日的中方谈判人员蔡钧记录了下来,载于其所著《外交辩难》之中。蔡钧,江西上犹人,早年在广东捐官出仕,受到刘坤一赏识,专门处理一些涉外事件。此后,被奏调跟随郑藻如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由于当日的兼使机制,驻外公使分身乏术,会委派随行人员常驻其中一国,蔡钧就长期留驻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与当地官员士绅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中法战争期间,蔡钧称病回国,随即被两江的曾国荃和善庆看中,去北京待了两年后,又南下在两江当差。因其善于与西方人打交道,在督抚之中还颇受青睐,时不时被借调往闽浙办理交涉事务。这一跨国遗产案即是蔡钧被派往福建所处理的一事。
话说明清两代,福建人下南洋谋生者甚众,其中有一个叫叶畴的人,本名林登铁,后卖入叶家,所以改了姓名。他常年在菲律宾(当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做生意,在菲又娶了两女,共生下子女三人。之后叶畴携资产约3万多银元回国,不久在籍病逝,财产遂成遗产。西班牙驻厦门领事濮义剌将遗款全部收缴,欲带回菲律宾,叶畴族人叶燕满上控官府要求分得遗产。地方官与濮领事交涉未果,蔡钧奉命来办此案。
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初七日,两人甫一见面,濮义剌即明扬暗抑地来了个下马威,称本来可以看在蔡钧情面上妥协办理案子,因蔡来迟,此案已经上报西班牙驻华公使,故而碍难通融。蔡钧亦不示弱,表示与公使认识,且公使非常公正,只要照章办理,无所谓来早来迟。他也明扬实抑地送出高帽子,说本来佩服濮领事公正,不知何以对此案如此偏执。接下来蔡钧将领事与地方官交涉无果之咎归于濮氏,抬出“西律”和“万国公律”,讲解只要两国不失和,总需协同商处各类事件,濮义剌不见地方官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一通指摘之后,蔡钧即以天时已晚为由告辞。
此后直到十月二十五日事情协商解决,其中经历了数次辩论。蔡钧一方面坚持叶畴是中国籍,且银钱资产带回中国,本已说明问题,且其菲律宾子女不孝。濮义剌将钱款扣留乃是“置公法、西律于度外”,并暗讽领事乃是见钱眼开。
另一方面,蔡钧在谈判中使用各种手段:其一,时时宣扬自己办理外交十多年,又有游历各国经历,每事照章办理,问题皆迎刃而解,以此凸显对手之不讲理,为十余年所未见,故此简单之案迁延甚久;其二,常常在谈判中摆出撒手不管的姿态,或顾左右而言他,一会畅谈外国风景,一会抚琴娱乐,或以事务繁多,不可能在当地久留,若濮义剌继续坚持,则到时候自己就不管了,以此施加压力,又或爽约不赴招待晚宴以表达不满;其三,在遗产金额分配谈判时“得寸进尺”,讨价还价,从本来可能分文不得,或得四分之一,力争到一半,又以化零为整之由,将分得的一万九千余元提至两万。最后,还顺便惩戒了当地挟洋自重,招摇生事的通事买办。
濮义剌在谈判中,屡屡示弱,称蔡钧熟悉西方法律,又擅长说理辩论,且利益上斤斤计较,态度上咄咄逼人,自己招架不住,只能看在情面上予以退让。蔡钧亦借此标榜自己是外交熟手,不图名利等等。
在蔡钧的叙述中所展现出的情景,乃是西方人一让再让,赔笑示好,而中国人趾高气昂,咄咄逼人,甚至有些蛮横。先且不论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但言这种双方的态度,似乎与通常认识中的晚清中外谈判大相径庭。
从蔡钧看晚清外交的另一面
首先来看蔡钧本人,他在当日西人眼中属于又现代又强硬的中国官员。一个德国记者曾如此描述作为上海道的蔡钧,称其平日里对西方人很和善友好,对谁都口称朋友,但是——
“可以看得出来,道台作为外国人的朋友,其情份也是有限制的,一旦他们(外国人)要求从道台那儿得到什么,道台就不再是他们的朋友了。蔡先生的欧洲观念主要引出了这样一种结果,即他非常清楚,每次对欧洲人要求的满足,将会给他们带去多大的价值。因此,他谨慎提防,绝不轻易松口让步。这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员是所有北京政府派往上海的代表中最为固执的,欧洲列强与他的前任们打交道,比跟这个‘外国人的朋友’容易得多。”
西方记者的“恶评”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更何况蔡钧在上海道任上,正是由于不配合西方在上海租界扩张谈判而被施压离职的。所以他在遗产案中熟悉相关律法的专业性和相对强硬的态度,是符合其一贯交涉水准和风格的。

蔡钧 照片由徐家宁先生提供
其次,再来看蔡钧的对手和遗产案本身。西班牙在当日西方国家之中,列强属性稍弱,并没有太多实力可以威压中国,且遗产案本身较小,牵涉利益较少,不属于重要交涉事件。在较为常见的近代外交叙事中,一般得以呈现的自然是中国与英美法俄等大国的关系,牵涉的利益也较为重大。正因为有这两个前提,“炮舰外交”才得以实施。一方面,只有拥有相当实力的列强才具有兵临海岸线的实际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即便强如当时的日不落帝国,也不可能随便什么事情谈判不成,便下旗撤使,断交开战。只要吃准了这两点,不被洋人吓倒,蔡钧等晚清外交官自然可在相关谈判中比较进退自如(当然也有料定不会动兵,结果现实中翻车的,话长不赘)。更何况蔡钧因曾驻马德里,的确与西班牙外交界关系匪浅,一个西班牙驻厦门领事,可能还真不放在他眼里。所以总而言之,蔡钧尽管时不时有大言夸谈之处,但关于此案的叙述,于情于理,基本应该是原貌。
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的一桩跨国遗产案,似乎遥远而微不足道。不过对于当日办理此类事务的官员来说,这便是其较为常见的工作,那种日后被写入教科书的大事件,反而离他们较为遥远。既然落实到日常经见的事务,自然有其处理机制和手段,往往不一定与日后因大事件而得到的整体印象相符。就拿本案来说,洋人并没有怕百姓,百姓甚至在谈判中基本失语,而官也不怕洋人。
跨国遗产纠纷,在今日自然有国际私法和协议来规定,而当日并不具备。叶畴遗产案本身是民事纠纷,无谈崩开战之虞,且从情理来说,双方似也各有道理,这样的案子,让交涉官员可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包括中外之间一些影响并不太大的冲突和教案,关于损失的估算和赔偿也多类此。那么当事官员处事的懒与勤,态度的“怂”与“杠”,也就往往在个人的“一贯”和一念之间了。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