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琼颖评《韦伯与德国政治》|时代的韦伯与超越时代的韦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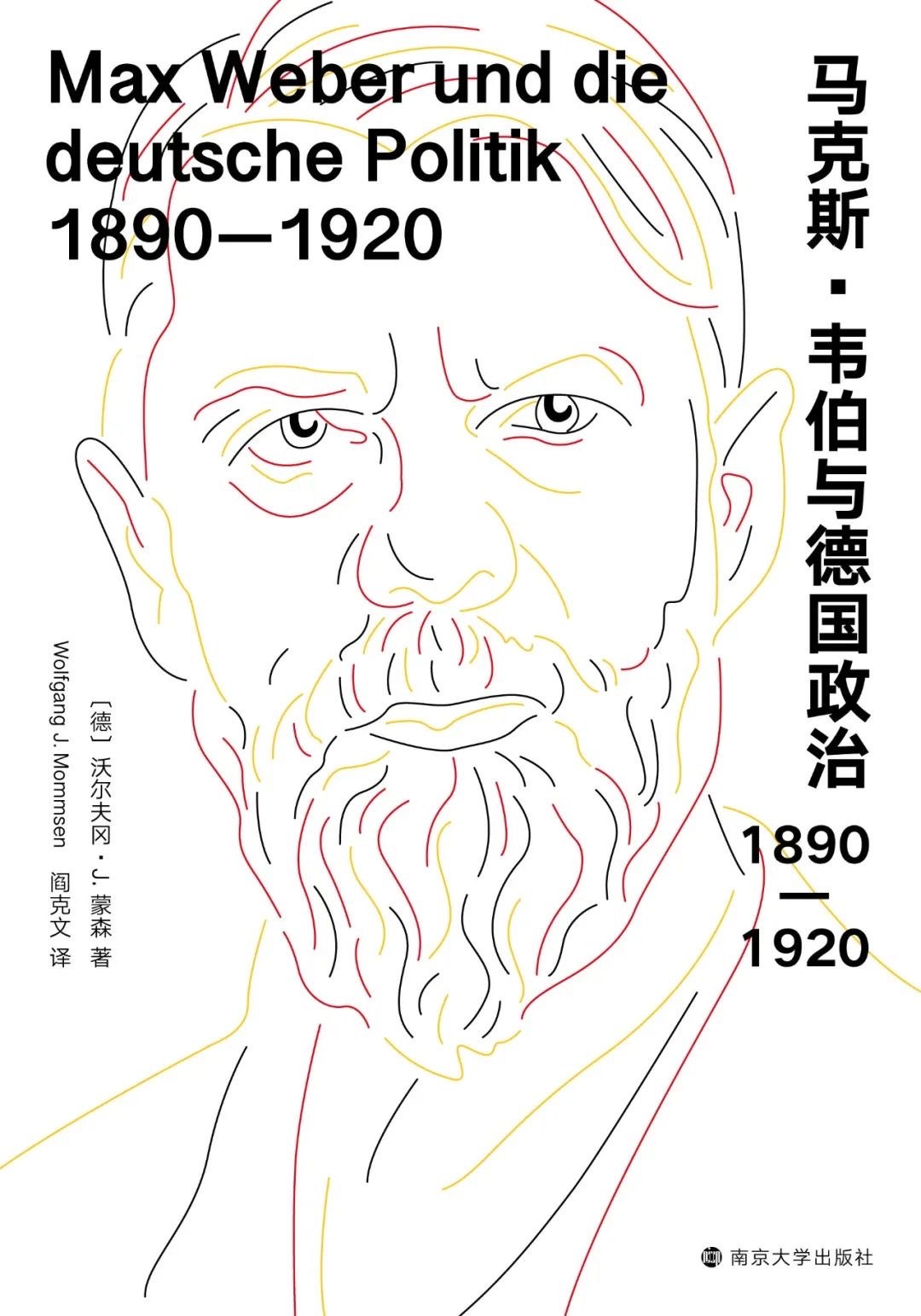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德]沃尔夫冈·J.蒙森著,阎克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610页,98.00元
1959年首次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下文将简称《韦伯与德国政治》)是韦伯研究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鉴于钱永祥、阎克文两位前辈已为本书增添了两篇重量级导读,其中对韦伯的政治思想以及一战前后德国政治生态提纲挈领的把握,读来令人受益匪浅。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我对本书的关注更着眼于作者沃尔夫冈·J.蒙森对韦伯政治观点的历史考察。作为历史学家,蒙森似乎始终坚持并强调从时代出发理解韦伯的立场,他在自己编纂的韦伯全集第十五卷的导言中写道,韦伯“终其一生深度介入政治”,也“从未摆脱过日常政治对其所提出的要求”。一方面,韦伯深度介入政治的年代适逢德国政治出现重大转变并引发后续系列影响;但另一方面,青年蒙森辗转求学并以韦伯政治思想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德国又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二战后同盟国对战败德国采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尤其强调在西占区(及日后的联邦德国)思想领域通过推行“再教育”以西式民主思想重塑德国社会。职业与生活的经历显然影响了蒙森对韦伯的理解,并最终参与形塑了本书的主要观点。也正是文本所呈现的观念与这种特定时代氛围、作者所处的知识分子代际之间的互动,让这次阅读之旅变得高度紧张,但同时又充满趣味。
一、沃尔夫冈·J.蒙森其人
沃尔夫冈·J.蒙森的曾祖父是德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父亲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是魏玛共和国杰出的政治史学者。他的孪生兄弟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则是当代著名的第三帝国史学者。虽然家学渊源深厚,沃尔夫冈·蒙森却一度想要放弃延续父祖辈的事业。不过经历了在大学修读物理和数学未果、在工厂当了六个月普工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马堡大学学习历史,并最终于1958年在科隆大学以题为“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蒙森谋求改变的职业尝试,首先与他这代人受到的时代影响有关:蒙森兄弟生于1930年,至二战末年因年龄尚小而免于应征入伍,然而他们的年纪又“足以让他们体会到暴力统治与战争的持续影响”。其次与其家庭的变故相连:1945年12月,父亲威廉因在非纳粹化审核期间被指控曾持有反犹观点而失去了马堡大学的正教授职务,全家从此陷入经济危机,一家六口每月收入只有三百马克,不得不依靠变卖家产(其中还包括特奥多尔·蒙森的手稿)度日,年轻的蒙森兄弟甚至“在高中毕业时都不清楚自己是否还应该去上大学”。除了经济的窘迫,他们的父亲“从未从被大学开除的阴影中走出来”,而母亲则因始终无法适应这种简朴的环境,“最终摧毁了家庭和婚姻”。
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绝大多数德国人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在战后想方设法活下去,生存的欲望与千疮百孔的生活交织,蒙森的家庭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正如沃尔夫冈·施温特克(Wolfgang Schwentker)所言,这种与当代史直接相连的个人经历是“1930年左右出生的德国历史学家所共有的,并促使他们在五十年代完成学业后或多或少会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放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即德国如何又为何会形成纳粹恐怖统治?”汉斯·蒙森后来成了钻研纳粹德国史的大家,而沃尔夫冈·蒙森虽然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斯·韦伯,但他不仅完全没有回避当时还深藏于这位智识伟人背后的德意志连续性问题,更在五十年代后期将之公之于众——由他撰写的本书甚至在著名的“费舍尔争论”之前就已经敏感地触及这个问题。
二、蒙森视野中的韦伯政治思想
蒙森在本书的首版前言中直言不讳地给出了自己的写作“野心”,亦即“为分析马克斯·韦伯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奠定牢固基础,并厘清其主要政治理想的历史背景”;同时还要“提供一部1890-1920年的德国政治史”(XVI页)。而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呈现韦伯的政治立场与政治理想,蒙森除了深入研读韦伯有关社会学和方法论的著作,还极大发挥了自己作为职业历史学者的专长:通过发掘并鉴定出大量当时尚不为人知的韦伯政论作品,与韦伯的同时代人建立直接联系,熟练识读韦伯遗稿中宛如天书般的手写体,再加上编辑有关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批判性经典时积累的经验和敏锐度,让蒙森基本梳理出韦伯政治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
蒙森声称自己在《韦伯与德国政治》中尽量以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形式呈现韦伯的政治观念,因此可以确认,韦伯的政治思想总体上立足于早年所接受的政治熏陶:坚持狭隘民族自由观点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强烈批判俾斯麦“恺撒式煽动主义”的历史学家兼父亲的政治搭档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 Baumgarten),以及更为著名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政论作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作品。蒙森认为,这些人的观念,代表了帝国时代相互竞争的政治与宗教观、物质利益与制度秩序,无论青年韦伯是接受抑或是反对,最终型塑出他政治思想中的“矛盾”。但全书又明确围绕若干专题展开,涉及韦伯在德意志帝国至魏玛共和国初年对民族国家、强权政治、德意志的文化任务与使命,以及“领袖民主制”的理解。
民族国家、强权政治、德意志的文化任务与使命,这一系列概念背后昭然若揭的是韦伯的帝国主义观。蒙森在1964年德国社会学家大会暨韦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上围绕“马克斯·韦伯与强权政治”所做的汇报中,更为精炼地指出,韦伯的帝国主义观表现为“以一种不明说的方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但这些观念“在其时代(又)并不罕见”的特征。例如,韦伯并不认为单纯靠不断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就可以扩大国内市场,因此他支持对外经济扩张,并且提出应“在必要时通过强大的军队在各地给予保护”——显然韦伯在这里的初衷并非建立全球经济联系,而是支持狭义上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但韦伯的帝国主义观念在一战前后又存在明显变化。按照蒙森的考证,韦伯在战时改变了自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看法,他以民族和强权政治考量取代了对经济的强调。在韦伯看来,一战是一场决定德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斗争,而这种文化的载体是民族国家。一方面,奥匈帝国的发展、演变坚定了他有关民族国家在欧洲的扩张不可逆转的看法,但他又不认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认为小国的独立只有在大国霸权的庇护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韦伯民族国家观的基础是“民族”,而非国家,因此他更强调语言共同体的重要性。他认为德国在一战这场涉及历史使命与文化任务的斗争中,所要承担的特殊任务是形成由德意志人决定的中欧文化圈,抵抗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习俗”“拉丁理性”与“俄罗斯暴政”。而要达成这个目的,韦伯认为,经济的作用就出现了变化,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不再是领土或殖民地的规模,因此通过战争吞并土地变得愈发无关紧要;反而是国家资本的储备规模以及其在未来的大国经济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经济效率成为关键。具体到德国,在韦伯看来,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德国经济能否在战后募集到足够的金融资本,以便在面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霸权时继续保持独立”。
《韦伯与德国政治》中另一个重点议题则是“直选领袖民主制”,它涉及韦伯对权力和民主的理解。根据韦伯1919年在《以政治为业》演讲中所流露的观点,“直选领袖民主制”应当是指由“煽动家凭借个人素质的实力进行统治”,并且他希望“一个由政党机器、联合体官僚和利益集团支配的社会能够允许那些独立不羁的天才领袖人物脱颖而出”。但韦伯的这一倡议并非支持卡里斯马领袖式的威权统治,恰恰相反,韦伯试图以主导性的政治家通过直选成为卡里斯马领袖的方式,反对现代政治制度与结构。韦伯坚信一切政治都是权力政治,且本质上是关于“命令”与“服从”。一方面,即使是在合法的统治类型如议会民主制的形成过程中,韦伯也并未看到其中对“人治”的限制,更遑论消除它。因此,在他看来,议会民主制不过是一种“利他的寻找从‘服从’转向‘命令’的机会”。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工业化大众社会的定型,韦伯也日益发现一种全面僵化的社会秩序正在出现,且这种秩序“最终将窒息一切自由的创作力和个人的自由流动。在政治领域也不例外”(468页)。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以“法治”取代(或至少是减少)“人治”,在他看来不过是天方夜谭。虽然态度悲观,但韦伯依然给出了改变的建议,亦即搭建直选式的大众民主框架,为具有领袖天赋的新型政治精英掌握权力提供最大可能性的上升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毫无疑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倡导通过负责的政治领袖,遏制组织严密的政党机器和纯物质利益的集团对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理想的破坏。然而,在蒙森看来,韦伯用于遏制这种戕害自由主义的大众社会手段首先是一种“恺撒式”民主的形式;其次,虽然韦伯认为可以凭借个人的超凡能力以及合法化自身目标的方式吸引政治追随者,并以此作为行使权力的形式,但蒙森认为这里面临一个界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及在这种体系下合法化权力的努力没有成功的问题,因此他提出,韦伯“只是纯粹从形式上制定了规则,但仍存有空白”。最后则是韦伯提出以直选领袖民主制取代“无领袖”的议会的根本动机。韦伯支持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反对从资本主义获利立场出发的自由主义“法治国”,显然是要求所有国民都有机会参与政治事务。表面来看是对德意志政治传统缺乏完整公民权的修正,但如果从韦伯有关“主宰者民族”的表述出发,则不难发现与他追求的世界政策的联系,“只有人民能在自由权基础上决定国内事务的民族,才有内在的正当权利提出伟大的世界政策”(45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倡导的民主本质上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创造国内政治的前提。
三、蒙森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韦伯接受史
在蒙森的笔下,韦伯的政治形象从一开始就包含双面性:一方面,韦伯确系自由主义者无疑,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专制的帝国权力结构并犀利地指出现代议会民主制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德国世界权力政策的倡导者和领袖民主制的理论家,由于他从始至终都梦想推动德国成为一个“非君主制的立宪框架下”的强国,并将德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与超国家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
然而,这一双面韦伯的形象及由蒙森呈现出的韦伯政治思想中尚待发展或自相矛盾之处,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即《韦伯与德国政治》首度付梓之时)至六十年代初的德国乃至国际韦伯研究界引发轩然大波。虽然蒙森对韦伯在一战前后观念变化的分析,让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在1963年将韦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国在一战前的内政发展是否事实上也属于德国并未克服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而再次联想到德意志连续性的问题。但弗伦克尔之前的德国学者却大多不愿面对这个问题,卡尔·勒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认为,“蒙森对韦伯卡里斯马概念及直选领袖民主制理论的诠释,建立起了其与法西斯理论的联系”,应“严词予以拒绝”。也正因为如此,蒙森才会在1964年德国社会学家大会上遭遇激烈批评,以至于本书的再版以及他的韦伯研究不仅搁置近十年之久,在多年后的访谈中他依然“念念不忘”自己当时被美、德国社会学家攻击为“材料造假者”的经历。
围绕蒙森的韦伯诠释争论既是学理之辩,亦有代际之争:例如在1964年的大会上,当蒙森试图通过建立起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与韦伯之间的观念传承,以证明韦伯“将几乎所有政治现象都解释为权力行使的各种修正”及其在魏玛之后的延续,却遭到同组讨论的阿道夫·阿伦特(Adolf Arndt)和爱德华·鲍姆加滕(Eduard Baumgarten)的批评,二者均认为这种绑定既不公平也无根据——原因不言而喻:施米特曾对魏玛宪政发起猛烈攻击,并且还是知名的纳粹信徒。蒙森的学生、历史学家迪尔克·布莱修斯(Dirk Blasius)还补充道,针对蒙森和《韦伯与德国政治》发起进攻的大多是“人生经历与二十世纪上半的德国历史相重叠”的老前辈;而蒙森则属于虽然拥有纳粹政权的生活经历,却能逃离纳粹主义的“45年一代”(特指生于1926-1931年的德国知识分子)。
而在代际差异的背后,真正涉及的核心是韦伯形象之于二战结束后至1968年间的西德的政治价值。正是蒙森在《韦伯与德国政治》中敏锐分析出韦伯政治思想中自相矛盾的部分,首先打破了西德将韦伯确立为民主象征的一切努力。在经历了纳粹统治,战争以及战后初年的困顿之后,无论是联邦政府抑或是那些被埃利亚斯称为“局内人”的西德政治与知识精英,除了迫切想要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将纳粹主义者与德意志民族作切割;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更是竭力从德国历史中找寻可以证明其曾具备民主传统的证据。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韦伯,就成为西德民主传统的最佳代言人。不仅如此,作为同样构建庞大社会学知识体系与方法论的思想伟人,韦伯甚至还被用来与民主德国以类似的逻辑推崇的马克思“对峙”。
1959年,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以论文《德国的战争目标》(“Deutsche Kriegsziele”)掀开的“历史学家之争”(也称“费舍尔之争”)扭转了联邦德国保守主义甚至是带有“辩护”色彩的历史编纂,进而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主流历史意识。费舍尔的论文连同1961年出版的专著《称雄世界》(Griff nach Weltmacht)不仅明确了德国必须为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及其进程负责,更提出德国的历史传统塑造了德国统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并最终扼杀了德国走上议会民主制的现代化政治道路。而蒙森对韦伯帝国主义观念及领袖民主制的解读,恰为其增添了论据。哈贝马斯在1964年社会学大会上对《韦伯与德国政治》的评述,则进一步声援了蒙森和费舍尔:正是韦伯在一战期间“在当时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创造出恺撒式的领袖民主制”,但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观念最终在魏玛时期产生的后果,并不应归咎于韦伯,而应归咎于我们自身。
同为“45年一代”,蒙森和哈贝马斯对自己这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道德立场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蒙森曾在访谈中提到:“我们必须把(象征纳粹主义政治遗产的)旧辫子割掉,发展出一套适应西方传统,符合民主秩序的历史形象。”但不同之处在于,蒙森仍以历史学家的天职为先,因此他才能从韦伯对1920年卡普暴动的强烈谴责推断出韦伯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同道中人,但这一主观推断又不影响他对韦伯的“直选领袖民主”理论存在反议会民主倾向的客观评价,他甚至直言韦伯当时尚未意识到卡里斯马在极权统治下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蒙森才能在本书中呈现一个完整的智识形象,一个深受德国历史传统影响且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的韦伯。
而在“68年运动”之后,西德学术界对韦伯的关注度不高,是不争的事实。韦伯的理论普遍被认为无法解释当下的问题,甚至韦伯本人都已是“过时的学术丰碑”。就理论而言,韦伯的观念尤其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挑战:哈贝马斯就明确提出韦伯的观点既不足以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具备足以采取行动的、对社会进程的足够洞察力;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对韦伯“理性”观念中明确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提出质疑。《韦伯全集》的编纂工作正是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于1977年正式启动,并最终让学术界重新意识到“在科学和对现代社会文化自我肯定日益紧密交织的过程中”回归马克斯·韦伯的重要性。而蒙森作为韦伯诠释者与编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客观上,他对韦伯存世文献的深度发掘及严格按照文献学编辑开展的大量工作,构成后人了解韦伯学术、政治乃至私交的重要指南——如他本人所说,“《韦伯与德国政治》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蒙森在七十年代重新回归韦伯研究领域,其研究视野已超越了在五十年代后半期撰写的《韦伯与德国政治》,更明确地进入韦伯普遍的政治和社会学思想领域;不仅如此,他还在立足韦伯文献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似性,并韦伯的观点能为“基本开放的分析提供范式,以此分析过去和现在的的社会行为并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
结语
卡尔·施米特本人也曾在1960年简短评价过蒙森这本处女作中的韦伯,他写道,“韦伯并没有跳出时代的阴影,他是时代之子”。毫无疑问,这就是蒙森和他的《韦伯与德国政治》所呈现给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的韦伯形象。但如果从蒙森撰写本书开起,到他七十年代全面投身韦伯全集的编纂与研究工作,我们又会发现一个跨越时代存在的韦伯形象,而这同样是由蒙森所传递,并结合他对历史学的理解和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自觉。关于蒙森以韦伯研究为志业的大半生,或许可以用他1970年在杜塞尔多夫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历史学作为一门批判性的社会科学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当代社会在面对自己的过去与他者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下,正确看待自己,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与力所能及。”
——————————
参考文献:
1. Carl Schmitt, “Rezension Mommsen,” Das Historisch-Politische Buch, 8(1960), S. 180-181.
2. Otto Stammer (Hg.), Max Weber und die Soziologie heute. Verhandlungen des 1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Tübingen: J.C.B. Mohr, 1965.
3. Karl Loewenstein, “Max Weber als ‘Ahnherr’ des plebiszitären Führerstaat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13(1961), S. 275-289.
4. Ernst Fraenkel, “Book Review: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by Wolfang J. Momms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6(1963), H.2, S. 418-424.
5. Wolfgang J. Mommsen, “Einleitung,” in Max Weber, Zur Politik im Weltkrieg. Schriften und Reden 1914-1918 (=Max Weber-Gesamtausgabe, Bd. 15), Tübingen: J.C.B. Mohr, 1984, S. 1-20.
6. Interview mit Hans Mommsen zum Thema “Neubeginn und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1950/60er Jahren” von Hsozkult,03. 02. 1999, 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beitrag/intervie/hmommsen.htm (2023年9月7日访问)
7. Interview mit Wolfgang J. Mommsen zum Thema “Neubeginn und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1950/60er Jahren” von Hsozkult,25. 02. 1999, 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BEITRAG/intervie/wmommsen.htm (2023年9月7日访问)
8. Wolfgang Schwentker, “Geschichte schreiben mit Blick auf Max Weber: Wolfgang J. Mommsen,” in Alfons Labisch (Hg.), Jahrbuch der 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2004, Düsseldorf: 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2005, S. 209-219.
9. Dirk Blasius, “Deutsche Kontinuitäten. Wolfgang J. Mommsens Buch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59,”in Christoph Cornelißen (Hg.),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Geist der Demokratie. Wolfgang J. Mommsen und seine Generation, Düsseldorf: Akademie Verlag, 2010, S. 147-158.
10. Edith Hank, Gangolf Hübinger, Wolfgang Schwentker, “Die Entstehung der Max Weber-Gesamtausgabe und der Beitrag von Wolfgang J. Mommsen,” in Christoph Cornelißen (Hg.),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Geist der Demokratie, S. 207-238.
11. 范丁梁:《从过去通往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抉择》,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