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重读经典背后的……“文化战争”与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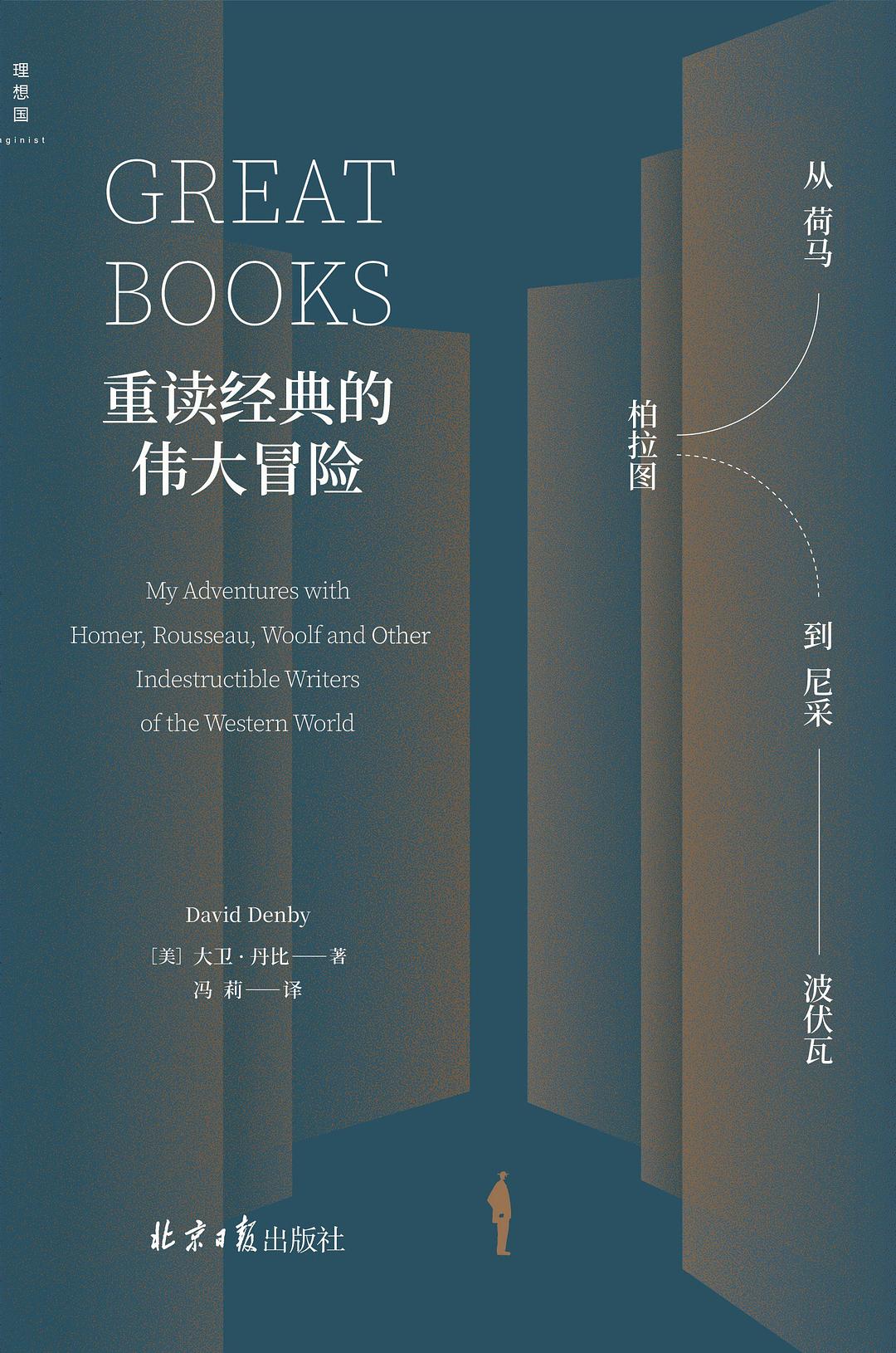
《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从荷马、柏拉图到尼采、波伏瓦》, [美] 大卫·丹比著,冯莉译,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4月版,608页,108.00元
作为一个教名著阅读课程的教师,读美国记者、评论家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原书名Great books: My Adventures With Homer, Rousseau, Woolf, and Other Indestructible Writers of the Western World,1996),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有感觉了,而且我相信选修这门课的同学如果读到这本书,也可能会有同感。因为它不是讲如何读那些西方经典名著——那些书太多了,而是以一个三十年前修过这门课程的老学生身份,重新回到哥大的课室听课一年,然后讲述今天(其实是1990年代初了)在这门课程上那些老师如何介绍与评论经典,学生如何在讨论中接受、质疑和反驳,以及在美国的大学教育语境中这门课程背后的政治文化冲突。虽然在我们的语境中,这门课程的教学背景与美国大学有重大区别,但是在全球化与当代性的共同时代景观面前,关于经典阅读课程教学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这一年的课堂听课与讨论的记录中,作者针对教师与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鲜活的。据介绍,该书此前已经有过两个中译本出版,但已绝版十余年,我是读之恨晚。这次理想国推出的是更新译本,订正了此前版本中的错译、漏译问题,刚出来三个月就二刷,似乎也可以说明“重读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说到为什么要重读经典,似乎没有人比伊塔洛·卡尔维诺的那句话说得更经典了:“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页)。我也把这句话录入我的课程教材中,意在向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强调“重读”与经典的关系。卡尔维诺还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第3-4页)。真是言简意深。在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定义的感召下,我在教材中把经典延伸到“在伟大的美国传统歌曲中注入诗意的表达”的鲍勃·迪伦(Bob Dylan)—— 小标题就是“这也是经典!在风中飘扬的经典!”。从他的《时代正在改变》到《答案在风中飘扬》,曾被认为是一代人成长的精神象征。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说1974年鲍勃·迪伦和他的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摇滚音乐演出竟然象征和再现了一个文化阶段,摇滚乐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方式代表了六十年代的文化。他甚至说“仿佛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在一段时间里落到他的双肩上”(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186-189页)。这不就是经典在摇滚中呈现的时刻吗?
在读大卫·丹比的这本《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的时候,我感到把鲍勃·迪伦也拉进来是对的。因为丹比在书中不断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代上大学时参与反越战抗议运动的时光,看纪录片、听演讲、静坐、示威抗议,看着一个梅尔维尔研究专家拿着霰弹枪去参加反战会议,他自己作为“学生推动民主社会”(SDS)团体的一分子,向站在加州州政府台阶上的罗纳德·里根州长扔了一个番茄。他说扔番茄是受让-雅克·卢梭的影响,当时卢梭的精神在激进的学生运动中随处可见。后来的保守派愤怒地指责学生反战运动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多毁灭性影响,丹比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为了终止越战所做的努力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知性经验之一”(359页)。当教师讲到“卢梭质疑我们此时此地所有的东西”时,他想到当年学生“要的不再只是改革,而是对社会摧枯拉朽的激进改变”。“那一切全是胡闹吗?不,当然不是。”(同上)再后来,SDS沉迷于暴力推翻政府的妄想,激进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多。他于是脱离了运动,回到文学和艺术中寻求抚慰,“无论如何,关闭大学会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如此自由?”(363页)虽然在当时他就知道自己注定要当一个中产阶级,而且是纽约式的,但是他仍然无法忘怀在经典课程上讨论的卢梭,因为卢梭永远是强有力的、扰动人心的(364页)。的确是这样。在我的教材中也写道:“卢梭一生酷爱学习,热爱自由,向往共和民主。他崇尚自然、自我,尊重人的自然感情。……马克思说:‘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从历史上看,所有卢梭所坚持的思想主题,如对理性约束的反叛,对情感的高扬,对浪漫理想的追求,对自然状态的赞颂等等,无一不可以在欧洲思想文化中找到它们的回响。”(参阅《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在丹比的前后跨越了30年的经典阅读课堂上,卢梭总是让他想到一个问题:那种伟大、先验的时刻,那种更宽广、更自由的生活在哪里?”(364页)这也是从卢梭到鲍勃·迪伦共同发出的追问。
1961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大一新生的丹比上了两门必修核心课程,一门是文学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即欧洲文学经典选读;另一门是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选读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在过了整整三十年之后,1991年秋丹比又回到哥大校园,重读这两门课程。这个《纽约客》杂志的影评人,四十八岁的事业有成的“老白男”,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直接原因是在1989-1990年发生的一场关于美国大学教育的论战,简单来说,学院左派激进分子、一些女性主义和非裔美籍学者激烈批评经典阅读课程是为了灌输西方文化霸权,保守派学者则把文学经典说成是神圣得不可言传,根本不可以动摇。丹比和他当作家的妻子都在关注并且在精神上深深被卷了进去,于是他妻子建议他干脆重回哥大上课。间接原因则是他遭遇的精神危机,指的是身处媒体时代深处的种种烦扰,感觉到自己在媒体生活的浓雾中衰退,仿佛成为一个旁观者,没有活过真正的生活。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无论是重返大学的思想前沿的战场还是在精神上“回到纯粹的阅读”,都带有一种驱使自己逸出生活常规轨道的冒险性,而重新进入思想争论的漩涡和开展一场重新认识自我、重新为自己找到方向的思想跋涉更是堪称一个人的伟大冒险。
“但为什么不坐下来读书就好了?为什么要回大学?”(vii)这的确是一个读者不应忽视的问题。“因为我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读书,或不读书的。这些学生都在媒体的包围下长大,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在文化论战之中未受波及,但仍听得到炮火声的校园一角,现在是怎么教学的?要赶走那些‘文化战争’的粗糙笼统和言不及义,方法之一就是去发现课堂上真正的情形。”而且他说要参与到辩论之中,不脱离那些书籍本身(viii)。实际上,作者在书中对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讨论的记录和思考是该书非常有价值的组成部分,重要的还不是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黑格尔、尼采、波伏瓦、伍尔夫……这一份名单,而在于被这一串依照年代顺序排列的重量级名字、“有如脑海中某个荣耀的名人殿堂里的大理石胸像”(楔子,i)所激发的师生论辩,其中出现的观点与情感冲突更能诠释“伟大冒险”的真实涵义。这也提醒我们不要把“重读经典”搞得像一锅打着“传承人文”标签的心灵鸡汤——用作者的话来说,“‘经典’这词让人想起皮面镶金的精装套书,还有那些势利眼的杂志和报纸上强力推销的广告。如人们所熟知,经典之作的书单常常染上消费主义和平庸品位的色彩……。”(同上,v) 这也是为什么哥大只称这两门课为“文学人文”“当代文明”,而很少有人称“经典”课程;另外在课程设置上选读的内容都非常难,还有就是授课教师来自不同系、专业组成的小组,我想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理解原著的跨学科视野。
在全书中,作者不断谈到来自任课教师和学生的激进“文化左派”观念或恪守学院正统的保守观点与课程设置主旨的尖锐冲突,始终关注在这门课程背后一直进行的“文化战争”,使这本书通过阅读经典的教学折射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学受政治文化冲击的思想光谱。当代文明课和文学人文课在哥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帮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进入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但是在后来却被攻击为使移民后裔或少数民族或女性等边缘化,丹比说这实在是件很讽刺的事。他要追问的是“原先的意图或影响仍残留在这些课程中并起作用吗?这是我开始时的一个疑问”(xii)。教当代文明课的教师安德斯·史蒂芬森可以从“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3日遇刺”这个句子开始就批评西方历法的霸权,力图说明在西方的观念、体制中没有什么是客观的、自然的或放诸四海皆准的,而都是由武断的、政治的因素决定的。这就是“文化左派”的主要信念(21页)。哥大要求所有人文学科以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新任教师都要教核心课程的科目至少三年,但是有些教授敢于抗拒,把当代文明课讲成是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史,或摒弃希腊文化、启蒙运动,把《当代文明》变成一门关于殖民与反殖民主义的课(244页)。非裔美国学者H.L.盖茨虽然并不鼓吹瓦解传统的经典,但是也认为经典的形成并非必然的,而是一种审美和政治秩序的传授,女性和有色人种从未在其中找到他们自己形象的投射,或听到他们自己文化声音的回响。因此要求扩大经典的范围,容纳那些未被听到的声音。更多的激烈声音则是认为所谓“经典”“就是白种欧裔美国男性‘霸权’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带着伪装的意识形态,推进或好或坏的西方模式,如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22页)。这些激烈的观点在我们听来也不陌生,问题是教这门经典课程的教师敢于如此尖锐地在课堂上批判这门课程内容的政治性倾向,这种自由讨论的思想环境恰好证实了在那些经典中包含的自由传统精神转化为公共政治理念的强大力量。也是教当代文明课的历史学家斯密特(J.W.Smit)教授耐心地向一位激动地质疑黑人作家为何不在经典之列的女学生解释说,维持阅读古典作品的理由是立足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影响,没有人否认其他族群创造的文化同样重要,但是产生的作用不一样。1988年,哥伦比亚大学增加了两门非西方文化课程,要求所有学生都要选修。丹比认为这些安排既是一种平衡的需要,同时也确实扩大了学生的学习视野。但是他也注意到一些非裔美籍学生的另一种真实想法,他们认为要是文学人文课或当代文明课的书单上出现一两个黑人作家,会觉得是别人在对他们施恩,是企图安抚他们的“表面文章”,因此他们更宁愿接受由历史塑造而形成的经典书单(463页)。丹比自己也认为,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或者后殖民时代重要的非洲作家如尼日利亚小说家、评论家契努瓦·阿契贝为例,“ 我们能否说他们和柏拉图、康德、尼采一样适合列入这门课程?道格拉斯是个伟大的作家,但他和黑格尔的伟大之处不同。他不像当代文明课里讲到的作家那样,普遍对西方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大学里读他,有其他的方式(在美国文学、非裔美国文学、历史等课程中)比在当代文明课上读他来得有道理”(464页)。应该说这是比较中肯的看法。
无论从重返课堂的起因还是在这一年课程中的思考来说,围绕着经典课程发生的“文化战争”一直是丹比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全书最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在学校里待了一年之后,我知道左派和右派的文化理论家大部分都在胡言乱语。这两个团体都简化、丑化了西方传统。”(574页)在课堂讨论中他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的历史知识只是浮光掠影,而在他们的生活里所谓的“霸权话语”就是大众传播,因此在他看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学生状况与需求的评论都是错的。一位教文学人文课的教师抱怨大学生阅读文本有相当的困难,“他们没办法找出信息所在并加以消化:来自不同时期的书有何意义,从一种文化讲到另一种文化又有何意义。他们根本吸收不了”(245页)。丹比对此也是同意的,但是他说这正是这门课程的伟大之处,一头栽进这些著作中的学生总是会学到一些东西。另外,他从这门课程本身的教学历史变化中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在二战以后教这门课程的教师深受现代主义经典和对极权主义和战争记忆的影响,这种特别意识进入了教学,带来了对文化内部的冲突、黑暗、毁灭力量的揭示和对经典之间相反观念的介绍,使学生不再相信单一的、一致的观念和意义。因此,“学生读了这些书,便是接受了强健的伦理教育,接受了提振人心的心智习惯,其中包括怀疑论和自我批评。也许他们也会受到推动,去主张和相信一些事物,但他们不会被推动去接受某一种特定的教条,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西方教育是一种很有用的经验这一观念,因为它同时打开了很多扇门。简言之,原先企图对西方所做的‘霸权’赞颂,变成了对西方持续的质疑(同时也有赞颂)”(576页)。这话说得很到位,在我看来是说清楚了阅读经典为什么是伟大的冒险——它们不是为了让学生接受教条、统一思想,而是培养怀疑、批判的智性精神,因此对于所谓“西方霸权”的真正有意义的批评者还是出自被攻击是为“西方霸权”服务的核心课程。
如果说由于大学思想语境的不同,我们或许无需像丹比那样高度关注在经典课程背后发生的“文化战争”的话,我们也仍然面临着同样伟大的冒险。那就是如何面对丹比从正面论述经典阅读的意义中包含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一个好老师会开启学生通过最复杂的乐趣来认识自我、通过对社会之建立原则的基本分析来认识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辈子的事。我同意威廉·贝内特等传统主义者做如下表述:要在一个现在深为恐惧和不信任所苦的共和国里重新发展道德和社群,这个令人却步的任务若由受过西方传统教育的男女来尝试,可能比较有成功的机会。这些或任何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书,最为有力地告诉我们人可以怎样活。它们戏剧化地呈现了我们当中任何一人所能爱、所能承受苦难、所能接受的知识的最大限度。它们对文明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最直接的再现,也显现出文明生活解体后会有什么灾难。学生们阅读、讨论这些书,便是开始了重新获得的过程。他们扫去了媒体带来的二手资讯迷雾。”(577页)作为同样是教这门课程的教师,我反复体味着这段出自一位重返课堂的老学生的概括性表述,发现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要素:重读是一辈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人理解生活的可能性;推动社会进步的善良意志必须要有人文传统教育作为基础;针对当下媒体时代的负面影响,经典是很好的解毒剂。这些无疑都是我在教学中高度认同的看法,在下一年度修订教材的时候,我会把这段话增添进去。
说到受过西方传统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建议哈维尔总统最好能在国家的主流日报上连载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东诺夫、加缪或乔伊斯的书籍,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这个民族转变为文明的民族;他在1987年诺奖演讲中说:“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54页)这与丹比所讲的是同样的意思。而且,这恐怕是所有热爱经典的人都会想到的。我想起2008年我写的一篇呼吁保卫广州老街道、老骑楼的报纸时评中,也曾提出应该把伟大的经典文学介绍给管理这个城市的官员,“应该尽一切可能培养我们社会的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具有更多对于历史的人文温情与敬意” 。当然也有朋友觉得过于理想化了。
丹比在重读中谈到教师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学生的讨论和他自己的重新认识,有很多具体议题都很有启发性。比如关于柏拉图《理想国》,丹比重新思考了其中包含的反民主政治理论的观念及其危害性,虽然以前我们早就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在教学中与学生交流讨论,这仍然是一种冒险和挑战。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之所以特别被激进的经典反对派憎恨,是因为它承载一个政治的使命:用关于起源的神话自我赋权,把帝国赞颂为天意注定的胜利,因此它“被尊为罗马的开国史诗,也变成帝国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道具”(176页)。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上所有建国时刻的自我赋权问题,以及文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真实关系。与这些议题相比,学生中存在的更复杂问题是相对主义的迷雾在蔓延:在反对绝对主义和先验规范的同时,如何才能不会跌入相对主义的谷底?丹比观察到在学生中的确有不少人正是亚伦·布鲁姆在他那本严厉谴责相对主义的《美国心灵的封闭》中所讲的,以为美德就是对所有文化、所有观点持开放态度。丹比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由于凌虐人民而受到西方国家批评的萨达姆和其他独裁者,也都抱怨‘西方人文主义’的骄傲自大……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在合乎自身目的的时候,可以说出一套媲美美国政治正确的论述语言。这些不愿意冒险做出批判的学生,等于愚蠢地和狡诈的独裁主义者站到了同一阵线,而这些学生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自由,那些人会毫不考虑地加以限制。”(311页)在重读经典背后的“文化战争”发展到这里,这种冒险性已经逼近到价值观念的底线,如果没有学术讨论的自由环境,恐怕哥大的很多教师只能选择闭上自己的嘴巴。对于这种“文化战争”的惨烈景观,丹比看得更为深刻,他说“课程的辩论不是茶壶里的风暴,而是风暴里的茶壶。暴风雨在大学之外仍然肆虐”(579页)。真不愧是做媒体的和写时评的。
无论是丹比还是我自己,都能体会到上这门课程“是一个费力而痛苦的经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核心课程震动了那么多学生的思维习性,违反了那么多当代的信条,挑战了那么多种形式的懒惰,以至于它们不但一点也不保守,反而是大学部课程里最激进的科目。”(577页)说得太对了!全书最后引用惠特曼《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 的诗句作为结语:“我细读过它,景仰过它(在它当中流连了一阵),/ 想到没有东西能比它更伟大,没有东西能比它更珍贵,/ 极为用心地注视了它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驱散它,/ 我才能站在我如今所站的这里。”(580页) 这也可以说明,阅读经典这场伟大的冒险是值得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