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纪念格丽克|李雨轩:“会爱的那部分,会死的那部分”——格丽克的死亡之诗

露易丝·格丽克(1943.4.22—2023.10.13)
2020年10月8日,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凭借自己“无可辩驳的诗意之音”,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后,也即2023年10月13日,格丽克因病患而离世。其实,死亡本身构成了格丽克诗作的一个核心主题。下文试图以其诗集《阿弗尔诺》(Averno,2006)和《村居生活》(A Village Life,2009)为中心(两部诗集的中译本均收录于《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以下引自同书诗句只标明页码),兼及其他,探析格丽克对死亡的复杂之思和应对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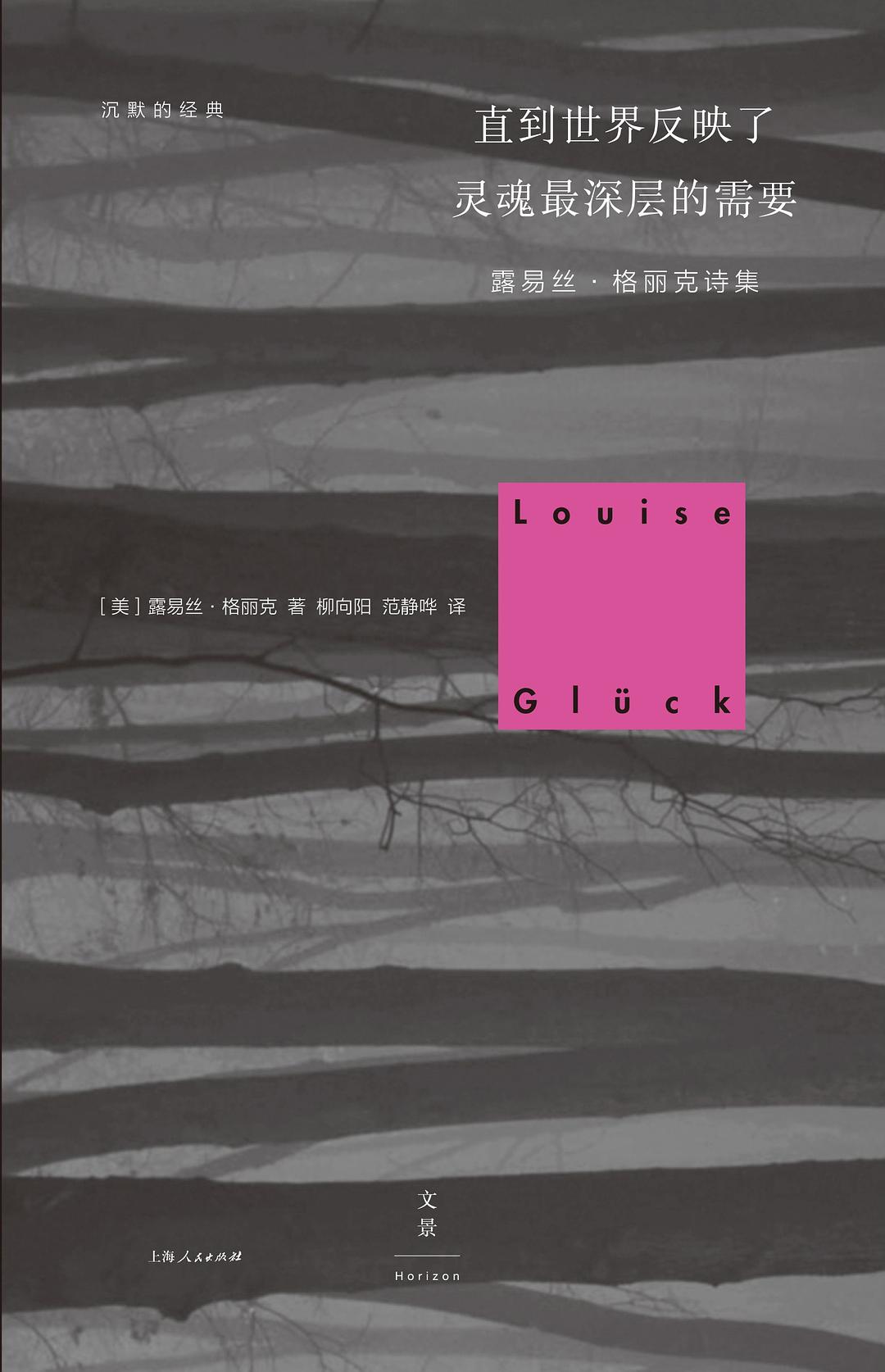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美]露易丝·格丽克著,柳向阳、范静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4月出版,363页,65.00元
一
就在格丽克出生前七天,她的姐姐已不幸离世。姐姐的早夭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她的父母,也使她的童年笼罩在“幸存者”的负疚感中。十六岁时,格丽克又因厌食症而获得濒死体验。童年和青春、自我与他者,这些交织的死亡体验使格丽克过早地直面死亡,而这又是她无力应对的。因此,对死亡的浓烈恐惧成为她最显在的心理状态,死亡意识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无法纾解和排遣。
对于格丽克而言,死亡是一个普遍事件,每天甚至每刻都在发生。在《阿勒山》(1990)中《幻想》一诗的开篇,诗人就写道:“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337页)并且,每个人的死亡都自出生起就已经开始了。“生出来,身体便与死亡定了约。/从那个时刻起,要做的一切都是欺诈——”(184页)“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252页)这种即生即死、生为死源的观念从她的诗集处女作《头生子》(1968)就已经产生了。
在《村居生活》一诗中,诗人写道:
死亡与无定等着我,
也等着所有的人,阴影揣度着我,
因为它并不急于摧毁一个人,
悬疑
是需要保留的因素——(242页)
这种将来而未来却随时可能到来的状态,正是死亡的永恒悬临性。在诗集《忠贞之夜》(2014)中《冒险》一诗的结尾,当朝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启之后,诗人所疑惑的仍是,“我们已经逃脱了死亡——/还是说,这是来自悬崖的景象?”([美]露易丝·格丽克:《忠贞之夜》,柳向阳、范静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页)这种悬临性无时无刻不侵蚀着诗人的神经,以至于她多生无常之感。“今天,你是还缺一颗牙的金发少年;/明天,就是气喘吁吁的老人。/到一无所有,真正是,仅仅是/世上的一瞬间。不是一句话,只是一口气,一个停顿。”(340页)由盛而衰只是一个瞬息,一切成功、辉煌,青春、热情,都受到无常的挑战。这是一种借由时间对意义发出的挑战,将此刻之鲜活与未来之衰朽相联通,从而消解了每一个此刻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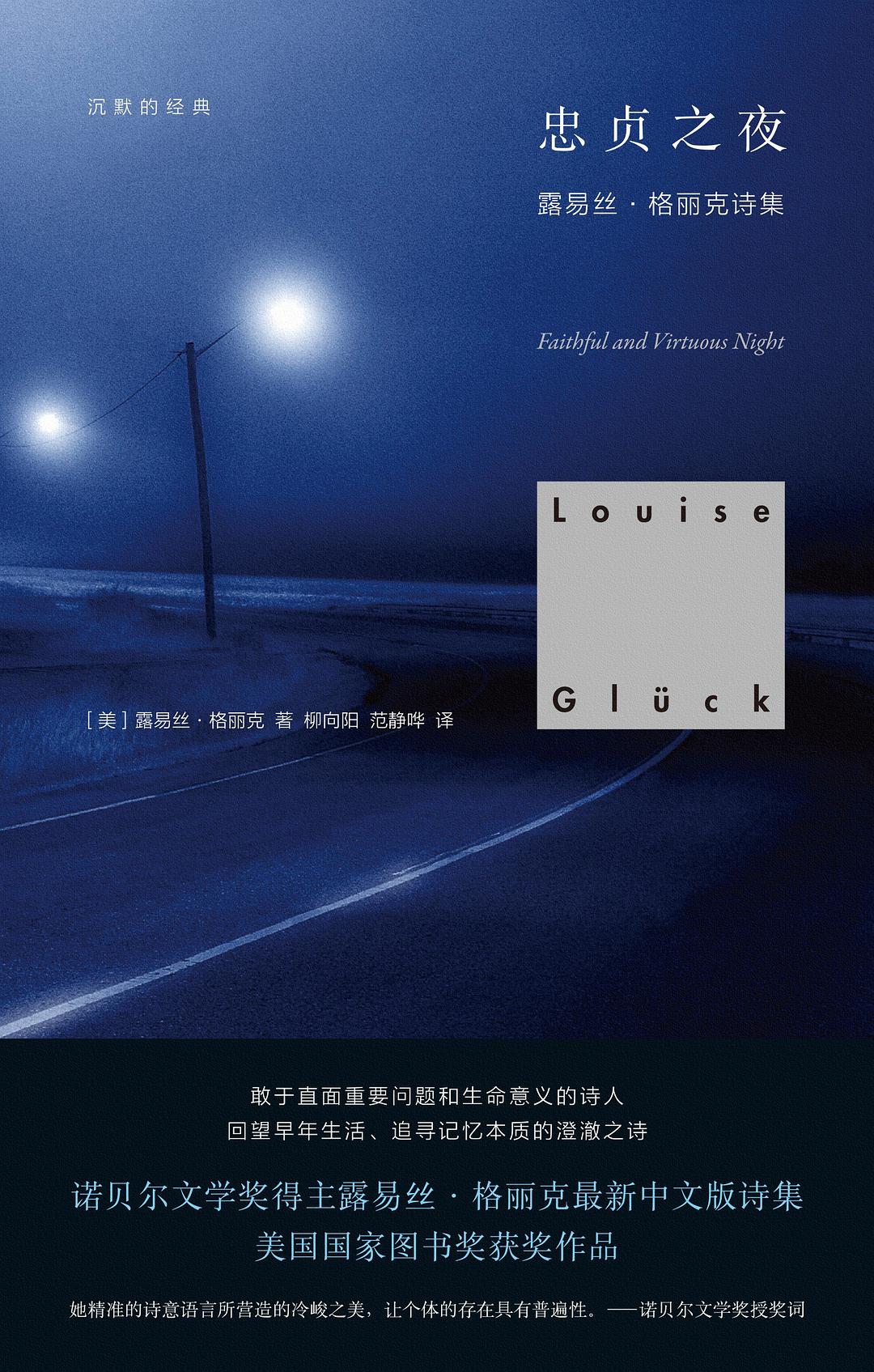
格丽克著《忠贞之夜》
但是,格丽克对死亡的书写总是与生命相交织,生命与死亡在其诗作中呈现出某种悖论性关系:一方面,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死亡时刻威胁着生命;另一方面,两者又呈现出某种界限不明的含混性,这突出表现在“燃烧”这一意象上。《村居生活》中有两首名为“烧树叶”的诗作。在第一首中,诗人将烧树叶这一行为解读为“死亡为生命腾出空间,/尽量地腾空”(173页)。这集中展现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冲突乃至斗争,还展现出一种残忍的本体性法则。而在第二首中,诗人揭示了火星这一意象在生死属性上的二重性,“那些火星显然没被击败,/只不过是在潜伏或休憩,尽管无人知道/它们到底代表着生命还是死亡”(189页)。“燃烧”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象,连接着生与死,一方面是生命的疾速消耗、死亡的庞大聚集,一方面又是生命的浓烈勃发、死亡的相对退场。这种居间、含混、阈限的状态,就是格丽克对生死的深层体验和认知。
二
从更深的层面看,格丽克对死亡的恐惧,恰恰是以她对生命之可贵、生活之美好的深刻体察为背景和依托的。“生命”和“生活”英文中都是life,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基底,后者是前者的延展状态。从生活的角度看,“生活”不仅指人的社会性活动,还指人寄居其间的整体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格丽克之成为诗人,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捕捉这种自然之美。在《回声》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还记得一种宁静
我再也不曾经历。
不久以后,我开始想让自己
成为一个艺术家,
替这些印象发出声音。(64页)
这是“诗人”身份之自我生成的最初起点,它来源于对一种印象的记忆及其追溯。而诗人所体验到的这种宁静,主要来自于她在“湖国”的生活。这里的自然背景——群山和积雪,涌动着审美的情愫,安定了诗人的心灵。诗人将美称作“导师”,美既是诗人对生活和世界的积极体验,又是诗人对自然的直观感受和切身体认。在《十月》一诗中,诗人写道,“别人在艺术中发现的,/我在自然中发现。别人/在人类之爱中发现的,我在自然中发现”。自然构成了与人为、人造的世界的对照,为美感提供直接的来源,也为生活的魅力提供深层的支持。在同一首诗中,诗人写道,“死亡也不能伤害我/像你已经伤害我这么深,/我心爱的生活”(32-33页)。恰是因为生活的极端美好,才显示出生命不能存续的难以忍受。
而从生命的角度看,生命不是纯粹的灵魂性、精神性存在,而首先是身体性存在,具有感性维度。从整体来看,身体是格丽克体验爱与性的重要媒介,而对爱与性的体验又与她对自我的追索紧密相关,因此身体构成了其诗作的重要元素。在《回声》一声中,诗人不无消沉地感慨:“我的身体维持。/不是健壮,而是维持。”(63页)死亡不但意味着身体的根本毁灭,还以自身的接近性造成身体的损耗和虚弱,这种消极状态可能更令诗人感到窒息。
在与诗集同名的《下降的形象》一诗中,诗人从远距离观察自己年幼的妹妹,“远远地我妹妹正在婴儿床里爬动。/死者是这样,/总是到最后才安静”。婴儿总是先闹腾一阵,再归于平静,诗人由此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人由生入死的过程。即使最具希望、活力的婴孩,似乎也无法燃起诗人对生命的热情,而被关联为一个死者的形象。如此看来,诗人对生命的态度是异常消极的;但诗人也始终处在矛盾中,她在诗的结尾写道:“我应该到她旁边;/也许如果我唱得轻柔,/她的皮肤那么白,/她头上覆盖着黑色绒毛……”(295-296页)白皙的皮肤、可爱的绒毛,集中表现了婴儿身体的惹人怜爱,这是幼体生命本身的无限魅力,连带着某种物种的基因和集体的记忆。面对这样的事实,诗人的内心发生了轻微转变,“也许”“如果”这些词表现出诗人保持生命、张扬生命的愿望,伴随着那轻柔的吟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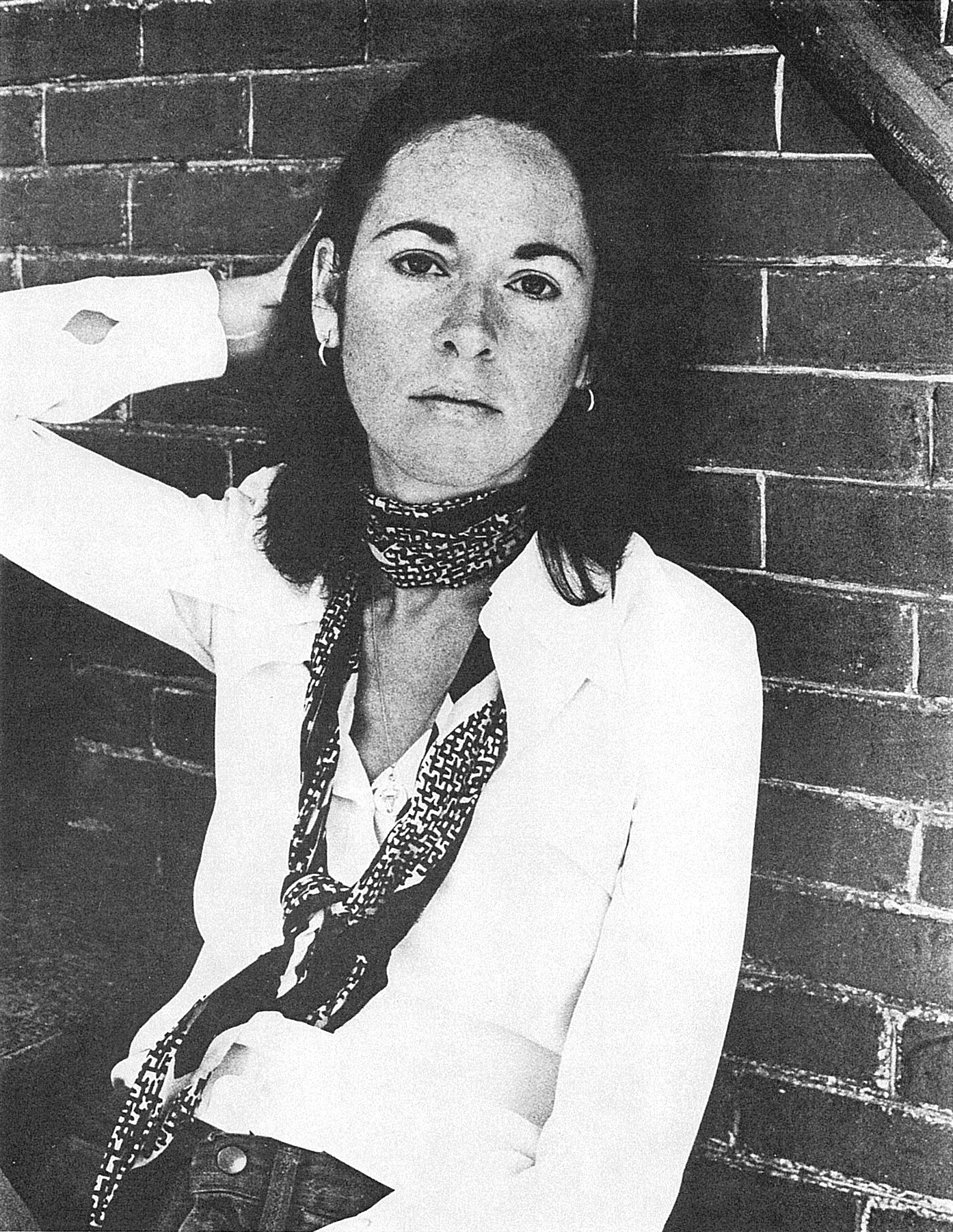
格丽克,1977年。
三
如何克服或超越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格丽克必须面对的问题,她选择了一条颇具冲击性的道路,不是逃避死亡,而是进入死亡,与死亡相“同化”。这是她非常迷恋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这一神话人物的重要原因。在希腊神话中,珀尔塞福涅是宙斯与德墨忒尔的女儿,被冥王哈迪斯劫持为妻,后虽得到母亲的营救,但由于误食了哈迪斯的石榴,每年必须有四个月的时间返回冥界。从神话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解释了四季的起源;而对于格丽克而言,这则神话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格丽克将自己化身为珀尔塞福涅,如此一来,经历死亡就被进入冥界这一行为所替代,而冥王正是自己的丈夫,这就在无形中营造了一种安全的心理体验。在《忠贞的神话》一诗中,诗人借哈迪斯之口说:“你已死,没有什么能伤害你。”(106页)在《蚯蚓》一诗中,诗人以蚯蚓为喻:“一旦进入泥土,便不会恐惧泥土;/一旦你栖居于你的恐惧,/死亡也不过是织一张地道或暗沟的网。”(161-162页)进入到所恐惧事物的内部,就消弭了自我与它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也就象征性地完成了对恐惧的克服,这正是格丽克应对死亡恐惧的一个方法。
同时,珀尔塞福涅不断往返于冥界虽意味着不断经历死亡,但也意味着不断重生。从这个角度看,珀尔塞福涅就是循环和永生的象征,她早已超越了生与死。《漂泊者珀尔塞福涅》一诗中写道,“春天就会回来,一个梦想/基于一个谬误:/死者归来”(127页)。将死者归来称为“谬误”,既显示了它的不合常理,也显示了它的难能可贵,诗人恰需要这个“谬误”来应对死亡。在这首诗中,诗人对珀尔塞福涅的不断重返与春天的不断来临做了同构性处理,从而为诗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值得关注的是,格丽克在《村居生活》中特别关注蝙蝠意象,其中有两首名为“蝙蝠”的诗作。诗人为何如此着意于蝙蝠?因为它在很多意义上与珀尔塞福涅类似:它们昼伏夜出,白天就栖居在漆黑的山洞中;它们完全与黑暗相同化,并且生活得自如、自得。“蝙蝠在黑暗中环飞——但人类对死亡/一无所知。”(231页)不论是蝙蝠还是珀尔塞福涅,都是诗人所倾羡的对象,它们不惧黑暗及其象征——死亡,并与黑暗相浑融。
但应追问的是,格丽克通过化身为珀尔塞福涅,是否真的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其实不然。诗人在《画眉鸟》一诗中写道,“我想你睡一会儿,/你就沉入到来生的恐惧之中”(121页)。实际上,这首选自《阿弗尔诺》的诗虽名为“画眉鸟”,但依然遵守整部诗集的规律,即保持与珀尔塞福涅的隐性关系。珀尔塞福涅虽然不断“重生”,但也同样地不断“死去”,她的宿命没有终结,恐惧依然俘获着她,让她无法脱身。她真正渴望的或许尚在无尽的未来:
在生生世世之后,也许有什么变化。
我想最终你可以看到
你想要的东西——
那时,你就不再需要
第二次死亡和返回。(122页)

格丽克,1968年。
四
那么,格丽克的诗中是否还蕴藏着其他超越死亡的途径?细细推究其诗,真正引起她疗愈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被动的,即以自然的永恒性、不变性为参照点来观照人类,并在这种观照中消弭人类的有死性所造成的创伤。在《棱镜》这首思索爱的诗中,诗人却忍不住关注那“湖水的声音”,“抚慰的、非人类的/湖水拍打码头的声音”(54页)。在《望远镜》一诗中诗人写道,“你不是一个有身体的生命。你像群星存在那样存在,参与着它们的寂静,它们的浩瀚无际”(119页)。还有《阿弗尔诺》一诗的片段:
那时他明白了大地
并不知道如何哀悼,而是将要改变。
然后,没有他继续存在。(117页)
自然在这里显示出第二重意蕴,不是为人类提供美,而是与人无关。它广袤无垠,无欲无求,不依赖于人,也不馈赠于人。但这本身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只有同化于自然,参与群星的寂静与浩瀚,人类才能体验到这种意义:不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是将自己融贯到浩渺的宇宙和自然之中,安顿自己的内心。格丽克对自然的这两重建构,本身就是对人类与自然的心理关系的深刻揭示。
第二个方面是主动的,即从人的有死性中建构积极性。在与诗集同名的诗作《阿基里斯的胜利》中,诗人对阿基里斯(Achilles)进行了一种存在论意义的思考。在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是凡人珀琉斯与女神忒提斯之子,乃是一个半神。史诗《伊利亚特》正是由歌唱阿基里斯的愤怒开始的。阿基里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的英勇显示了他作为“神”的一面,而他的愤怒和同情则表现了他作为“人”的一面。也正是作为“人”的这一面,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营帐里,阿基里斯
整个人儿都在悲痛
而众神看到
他已经是个死人,一具牺牲
因为会爱的那部分,
会死的那部分。(318页)
在诗中,明明阿基里斯仍活着,正哀悼着帕特洛克罗斯,可诗人为何写众神看出他“已经是个死人”?这是因为众神的眼光超越了时间:阿基里斯的同情已经揭示了他作为“人”的存在,而人与神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死的,而神是不朽的。在这里,格丽克将她诗歌的两个主题——爱与死做了链接:人之所以会死,乃是因为会爱。或者反过来说,人之所以会爱,乃是因为会死。爱与死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两者都作为人的本质要素,彰显着人的尊严和痛苦。
这里可与许多现代理论产生对话。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死亡构筑此在的本真性之基,强调了死亡的“向来属己性”(Jemeinigkeit),也即死亡构成了此在的独特性所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76页)。围绕于此,列维纳斯将他者之死确立为第一性的,欲唤起自我对他者的责任意识;德里达则将“属于自己”的死亡作为建构独异性的责任主体的基础。这些影响深巨的理论向我们昭示着,死亡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积极因素,作用于活着的生命。事实上,唯有正视死亡,甚至把死亡作为人类命运的馈赠,才能真正发掘死亡的正面价值。
德里达非常关注“幸存”这一概念,这是以死亡为尺度对生命所做的全新界定。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格丽克的立场?格丽克在《回声》一诗中听到“沉默”向她答复:“如果你的灵魂已死,那么/你正活着的是谁的生命?/你什么时候变成了那个人?”(65页)这一质疑是如此掷地有声。格丽克唯一不能否认的,是她还活着这一事实本身,即使在死亡的悬临与威压之下。这个活生生的、独异性的身体性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灵魂、一个主体,它应承担起生者全部的快乐、痛苦、责任和尊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