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以戏剧作为方法的……社会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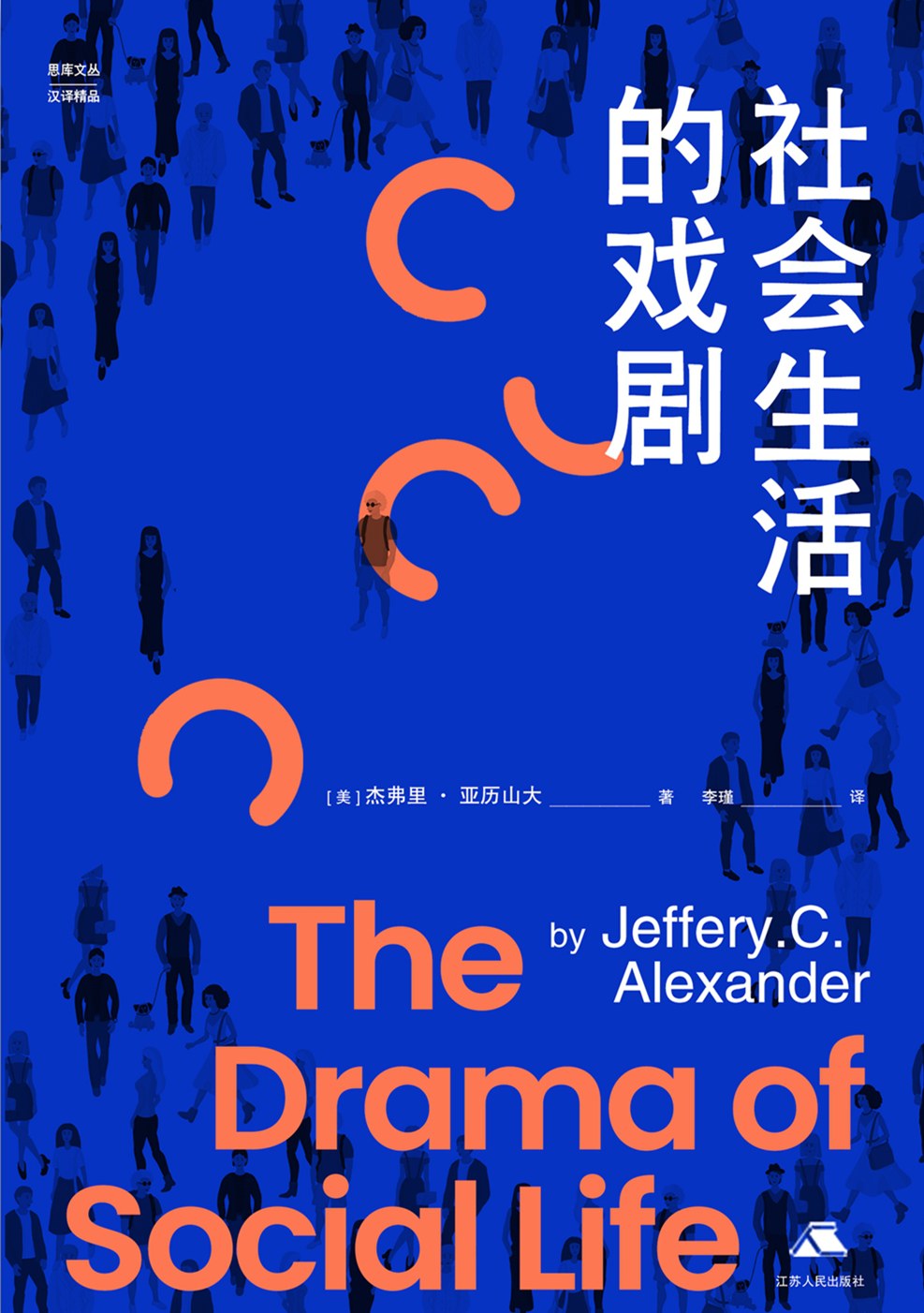
《社会生活的戏剧》,[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著,李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版,312页,56.00元
在传统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重大事件、社会运动和舆情动向中的戏剧性变化无疑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当某一重大事件令人猝不及防地发生的时候,许多人会期待和关注随之而来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更是值得研究。但是在这里的“戏剧性”仅是对变化的一种描述或隐喻,而不是作为视角与方法。
从文化社会学的前沿研究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从西方社会表演的意义上分析和揭示社会运动、重大事件中的“戏剧性”因素,由此更有效地阐释其胜利或失败的原因。这是在传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框架之外增添的新视角和新的阐释方法,使关于西方社会运动的历史叙事更为贴近真实现场、微观细节和情感力量,从而在宏观叙事上更具有阐释力量。这样的研究视角不仅带来西方政治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新的西方社会正义运动的操作指南。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 的《社会生活的戏剧》(原书名The Drama of Social Life: A Dramaturgical Handbook,2017)就是这样一部出色的文化社会学著作。该书从“文化语用学”和社会表演的视角研究西方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与演变,从社会结构的仪式根源到社会政治运动中的表演性元素与结构,以一种融合了政治社会学理论与戏剧表演研究的社会表演模式解读社会运动及重大事件的得失成败。其研究案例包括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2012年开始的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反抗运动和2012年奥巴马获得美国总统连任的竞选表演等。这些案例研究既表明了以社会性戏剧表演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有效性,同时也反过来启发人们思考在西方社会如何以社会性戏剧表演作为视角和方法,积极介入争取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运动。
“在现代生活中,无论是虚构传闻还是实况报道,一遇关键事件,都会调用戏剧这一隐喻。…… 认定一个事件具有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无疑就会加剧紧张气氛,让人产生期待感。戏剧性使日常活动因此而变成表演,读者变成观众,普普通通的人物变成戏剧中的角色——男女主角和反面人物,他们明争暗斗,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剧情的更迭。……为制造关键时刻(critical moment),人们将取景和突出体验这种审美方式从临时设定的技巧世界中转移至社会现实,以产生真实的社会生活戏剧的效果。”(第1-2页)全书开头这段话精准地表述了社会生活中的“戏剧性”从隐喻修辞变为实践性概念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就是从审美方式转变为产生真实社会效果的创造性力量。
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和社会表演中的文化语用学(cultural pragmatics)是该书的两个核心理论概念。“文化社会学的基础是:个体和社会均与意义密切相关。社会戏剧和戏剧形式处于现代社会的核心地位。”(第4页)把“意义”和“社会戏剧”视作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元素,由此延伸出来的就是社会表演文化语用学,其支点是在仪式与表演之间存在连续性和张力。因此,“我一直认为,社会理论家必须使用拟剧论、戏剧理论以及戏剧批评等工具来发展社会表演中的文化社会学,并与时俱进,由此而发展出一种崭新的、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学。我把仪式界定为一种特别的社会表演,一种能‘卓有成效’地促进演员、观众、脚本等各种元素进行大融合的表演。在表演中,那些观看表演的人不是把表演当作表演,而是把自己看作男女主人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舞台上的敌对状态,丝毫不存在把自己视为观众的感觉”(第7页)。
这是文化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由此想到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文化史视角。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的《革命节日》(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1789-1799,1976;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把作为文化习俗的节日与发动革命、掌控革命的行动联系起来,打破了传统史学中的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因而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奥祖夫认为旧的节日、仪式无法满足革命的需要,因此革命者必须创造自己的新的革命节日,作为人民赖以交流思想、统一情感、促进认同的新形式。“革命作为节日”的首要象征就是“人民登台亮相:这是节日的第一个形象……人民是以某种未经安排的、不假思索的方式出现的……由自发性所造成的这种充满活力的形象本身就差不多了:人民在前进,这就足够了……”(《革命节日》,30页)这话说得真有点激动人心,令人想起当攻下巴士底狱之后,有人马上在这座专制堡垒的前面竖起一块木牌,上书“人民在此跳舞!”这种情景同样发生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中,奥祖夫在她的书中也谈到了这次运动。奥祖夫通过分析在革命节日中人们的着装、游行路线和庆祝活动等内容,揭示了法国革命时期的集体行动及其心态的真实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正是亚历山大研究社会运动中的戏剧性表演的先声。可惜的是亚历山大在这部书中并没有提到奥祖夫的革命节日研究。
关于戏剧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关系,作者说得非常明确:“戏剧就是有组织地把集体行动戏剧性地融入政治生活。作为公共政治领域,剧场出现的时间与古希腊的波利斯(polis,城邦)大致相同。”“如果说戏剧是想方设法将难以抑制的情感冲突戏剧化,那么公开组织的政治运动也正是力图将迫在眉睫的社会冲突戏剧化,公开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也就是说,戏剧和政治运动两者都或多或少地通过象征性艺术表演向远处的观众投射自己的意图。……诸如此类的表演,如挑战被拆解的、存在冲突的、碎片化的社会状况的表演,可能会激发新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形式,这种表演就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同上)对于关系、意图和主题,这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该书前两章集中讨论了那些“旨在进行彻底变革的社会运动”。第一章的第二节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民权抗议: 一个新的社会角色”,讲述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发动蒙哥马利的民权运动、最终使肯尼迪总统废除种族隔离法的故事,阐释了马丁·路德·金如何利用戏剧的象征性的力量而产生真正的影响。在论述二十一世纪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时候,作者明确提出:应该把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理解为社会表演,要想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抓住集体的想象力,把反映正义胜利的戏剧搬到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与远方的观众强力融合,这样一来,连危险的起义都变得合法了(68页)。把历史事件或者民权运动视为具有戏剧性的社会表演,诠释了作为书名的“社会生活的戏剧”的关键意涵。
重要的是,这些斗争案例都说明了自觉的戏剧表演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没有能够上演非暴力抗议,没有将南方白人的暴力投射给因惊讶而几近窒息的北方观众,那么在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法案中,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就不会从法律上发生根本动摇。同样,今天由‘黑人的命也是命’领导的运动也是如此。……如果要想赢得公平,就必须有组织地发动抗议,这就要编写剧本,然后上演;此外,还要有导演,向持怀疑态度的观众面对面地进行表演。社会不公必须要戏剧化,而恢复民众的希望也需要戏剧化。毫无疑问,社会媒体对BLM 抗议警察的杀戮行为而产生的怒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真正引发这股怒潮的并不是社会媒体。”(12页)应该注意到,亚历山大关于必须有组织地进行戏剧化斗争的论述是有其具体语境的,在不同的语境中,非组织化和自发性应该也是在亚历山大的社会戏剧研究中应有的议题。
谈到社会媒体,这是与社会表演的效果紧密相关的重要方面。作者认为在2011年的埃及动荡中,社会媒体就是一把双刃剑。手机和互联网确实能让策划者和抗议者进行即时的、直接的交流,但是国家掌握着技术力量,可以关闭互联网和手机通讯。但是,“……表演诸要素已经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天衣无缝地接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制造了一种强烈的逼真感和真实感,这使得表演无须与社会媒体接触也能继续”。自上而下的现代性……没有富有奉献精神的专属演员和对埃及公民观众的感情,他的表演无法进行(13页)。在埃及的案例中,还有一个语言问题值得思考。在解释为什么英语是除了阿拉伯语以外题写解放广场上各种标语的主要语言时,一位学者表示那是因为用英语“能权威性地显示这个国家是现代性的,它的公民了解全球语言”,他极力反对“西方对埃及的刻板印象,即落后的、传统的”(176页)。
在上述这些跨国跨文化的政治运动案例中,引起我思考的是西方世界政治抗争中的戏剧性表演同样有着深刻的民族性差异,所传递的信息和情感力量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体内部具有不同的效果。开创“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理论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深刻地指出,“在抗争的形式、动力和后果上,都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性差异”(《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6页)。他曾经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以双膝跪下的姿势给美国学生演示在广场上的抗议者“跪谏”的情形,那是令人多么唏嘘动容的一刻!他要说明的是,具有独特文化涵义的“跪谏”形式是如何塑造和极化了社会抗议,它们经常被抗议者作为象征符号而利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蒂利在课堂上的演示也完全契合他关于抗争政治的“斗争剧目”理论。他在研究1989年至2003年间发生在秘鲁的抗争政治和政权变化的时候,引入了“剧目”(Repertoires)的概念,指的是人们表达抗争诉求的内容形成了斗争剧目,人们会根据松散的剧目脚本来行动;这些斗争剧目具有灵活性,可以针对不同政权类型和各种条件、机会而发生变化。(参见查尔斯·蒂利《政权与斗争剧目》,Regimes and Repertoires,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从这个角度来看,查尔斯·蒂利关于“抗争政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也正是亚历山大的社会表演与社会生活研究的先声,但是他也没有在书中提到。
从戏剧的角度,或者说以戏剧作为一种方法,来观察和研究社会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这是第四章“戏剧与知识分子”论述的重要问题。作者说,“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把知识分子作为重要思想的创造者,而是重要思想的创造者在社会舞台上成为引人注目的演员。 无论是生龙活虎地活跃(他们确实活得虎虎有生气)在舞台上,还是在肉体离开社会舞台之后,他们所创造的思想都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大事件。”(202页)知识分子通过“表演”使思想被观众所接受,从而实现思想的社会意义。因此,“知识分子表演者以意义为导向,他们想要扮演神话,并参与象征性的行动,但他们也必须对语用学和策略极其敏感。社会表演理论把这种文化语用学概念化了,它发展了一种宏观社会学,探讨在偶然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下,社会意义如何变得富有戏剧性”(207页)。思想、社会意义和戏剧性,这几乎就是走出书斋、有志于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扮演有影响力的社会角色的三部曲,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就是能否使被转化为社会意义的思想为群众所掌握,从而激发他们投入社会运动的积极性和建立新社会的创造力。
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讲的:“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16 页)这句话同样充满了激情、想象力和戏剧性,放在亚历山大这一章的上下文中也很适合。“一旦满足了这些条件,在其思想所创造的影响深远的表演中,知识分子就会粉墨登场,成为引人注目的戏剧性人物(dramatic personae)。那么,这样一来,他们所塑造的角色就会成为他们自己提出的转型模式的标志性的、浓缩的、简化的、有超凡魅力的集体代表——在真实时间里,代表着当下;在记忆中,代表着对过去的回顾。”(207页)
另外,作者也研究了一些西方国家政党的党派斗争事件,会被当权者挂上政治标签成为公共表演。亚历山大以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大规模的公审秀”为例:“其供词就是经过精心策划,并由记者报道,以录音和电影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的。由于精心编排过,具有仪式感,所以产生了神话一般的效果;同时,又因为它唤起了英雄主义情感,所以这些因素混搭在一起,再经电影制片人之手进行美学重构,超越眼前的事件,将之投射到数百万潜在的观众那里,结果自然是令人观后振奋不已。”(18页)这是在西方世界“抗争政治”性质的社会运动之外的另一种社会表演类型,在跨国、跨意识形态政治的比较中,这种另类性质的戏剧性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从剧本和演出的视角研究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是一种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新方式。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新要求,从“别写砸了”到“别演砸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新考验。亚历山大在书中有一段话集中说明了知识分子应该到社会生活中去:“我们为什么会痛苦? 为什么社会安排会如此不公正? 为使社会和个人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需要有何种作为? 马克思、弗洛伊德、凯恩斯、萨特、兰德、法农等人的理论有力而简洁地解决了这些存在兼政治问题。但是,如何使这些理论在社会上,而不只是在理论上变得强大,那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分子的社会权力取决于他们获得的执行力(亦即表演力)。深奥的理论必须简化成以行动为中心的剧本;必须制定行动计划,招募有领袖魅力的演员,组织培训员工和追随者,准备好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详细计划,并将强有力的、公开可见的行动置放到实际场景中。知识分子的理论力量通常具有表演性,但是思想的社会力量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一定要在学术圈子之外来进行组织,向观众展示思想力量,因为观众感兴趣的东西没有那么深奥,更多的是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息息相关。”(15页)
但是,不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往往有非常不同的存在问题。由此想到一本与研究社会生活中集体的戏剧性表演刚好相反的书,就是那本研究集体沉默的书。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The Elephant in the Room,胡缠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从英文谚语“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引申出来的社会性集体沉默议题。这一联想的合理性,首先是因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戏剧”需要共同关注、集体发声,因此与“房间里的大象”所指向的那种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害怕被认为是关注者、心照不宣地集体沉默的现象刚好相反;其次是因为在亚历山大的社会性表演理论与实例分析的启发下,应该思考对显而易见的事物避而不谈的合谋性沉默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戏剧性的社会表演?从自发、默契、相互配合从而使各种公共政治表演如仪举行的角度来看,不也是亚历山大所讲的“一种能‘卓有成效’地促进演员、观众、脚本等各种元素进行大融合的表演”(第7页)吗?或者更应该说,不正是因为有了“房间里的大象”,亚历山大研究的那种“社会生活的戏剧”就永远不会上演吗?
在该书最后一章作者从社会回到了剧院,主要阐述剧院的表演发展史与戏剧革新的美学创新主题。在新体裁、戏剧文本创作的新方法、不同的表演技巧、蓬勃发展的道具和舞台设计等专业性趋势之上,是全面接管戏剧制作的组织、结构化和场面调度等工作的“导演”。那么,“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生活中,戏剧都非同小可,切不可等闲视之。每个人都要助一臂之力,努力使演出获得成功”(16页)。
一旦回到剧场里的表演,对于像我这样从未导演过一部戏剧的读者来说,从创作剧本到最后完成演出有太多的具体问题要学习和思考。刚好最近看了美国戏剧教师和导演玛格丽特·F.约翰逊(Margaret F.Johnson)的《戏剧教师实用手册》(The Drama Teacher's Survival Guide: A Complete Handbook for Play Production,2007;刘阳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该书的对象是指导普通高中学生创作、排演一部戏剧的老师,详细论述了从创作剧本、策划组织、筹集资金、选择演员与场地、组织观众到舞美化妆、排练演出乃至具体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作者用实际事例、具体方法、图文并茂的详细信息全面讲述了如何成功地策划和运作一个戏剧项目,完成一次师生合作的充满智慧与激情的戏剧探险。在很多微观的技术运作中可以看到对于一次表演成败的影响,同时更能理解作者所强调的一名戏剧教师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组织能力、激情和想象力(导言,10页)。回到亚历山大的社会运动与表演理论,“如果说戏剧理论和社会戏剧理论是相互映照的,那它们实质上也是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正如我在全书中所阐明的,各种各样的美学技巧与手段已经深入到当代社会制度和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深入到各种权力斗争及其垂直运作中……审美表演和社会表演共同的奋斗目标不是空洞的奇观,而是虚构故事中那种鼓舞人心的鲜活体验。”(《社会生活与戏剧》,274页)
德国著名戏剧理论家汉斯-蒂斯·雷蒙(Hans-Thies Lehmann)曾经宣告戏剧已经终结,亚历山大进而阐释说“目前我们正处于后戏剧性事件发生的时代”——上演的节目没有情节和文本,占据舞台的角色没有感情,一切都是孤立的、不透明的、临时排列组合起来的,缺乏有意义的关联……雷蒙断言,后戏剧艺术明确体现了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危险转变:戏剧的想象空间正在缩小,以致“戏剧和社会无法走到一起”。当今社会不再有冲突性的情节和戏剧形式,在“去戏剧化的现实”中,权力集团(power blocs)主宰一切。雷蒙不禁哀叹“公民观众”(citizen spectator)只能“旁观”,无法对社会产生影响(243-245页)。
对于亚历山大和西方读者来说,关键问题就是: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戏剧死亡了吗?他没有这么悲观,他认为“我们必须看到戏剧所发生的变异(variation),而非戏剧的衰退(declension)”(245页),以文化为导向的社会表演理论仍然可以使社会行动者(actors)找到新的途径去思考社会冲突、社会批判与政治责任等问题(253页)。在新的社会表演中,“极具倾向性的民主理论家已经转而求助于观众的独立性”,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在写给“解放了的观众”的颂歌中,赞扬了那些“进行观察、作出选择、试图比较、作出解释”的人,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表演、重新设计表演的人”(261页)。在他看来,对于独立的、解放的观众来说,“没有戏剧,集体和个人的意义就无法维持,罪恶就无法被识别,正义就无法得到伸张”(275页)。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