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桥本秀美评《义例与用字》丨理解何休,发明何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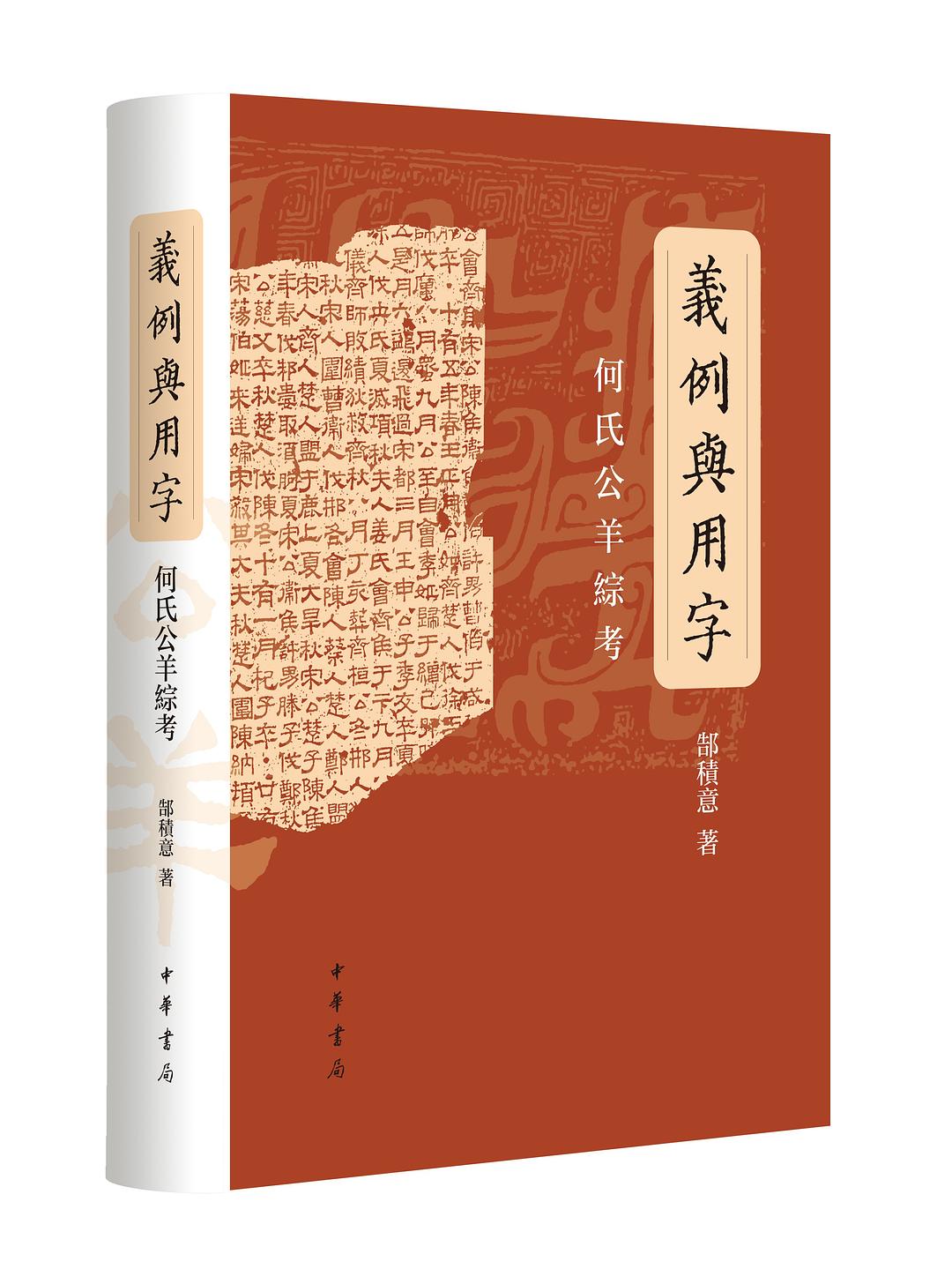
《义例与用字:何氏公羊综考》,郜积意著,中华书局2023年6月出版,491页,88.00元
确切时间已经不记得,在1990年前后,我第一次到台湾地区拜访林庆彰老师。林老师将我介绍给周围的学者,说我“也是‘学经’的”,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我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认为研究经学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应该要否定的“封建思想”。日本学术界近代以来标榜客观研究,更明确强调我们要研究经学史,不要研究经学。所以我学过几年经学史,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学经学。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台湾地区的经学史研究有民国以来的传统,像林老师即屈万里先生的弟子,其他学者也都师从民国学者,经学与经学史并没有分得很清楚。当时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就一个学者或著作进行分析,指出其优缺点,算是固定模式。因为当代学界对经书形成一套共同的理解,并且认为那一套理解是正确的,所以能够对古代学者的解释指出优缺点。这就是经学与经学史没分的研究方法。我个人很早就对这种研究感到厌烦,并且认为几乎没有意义。“你都知道正确答案,你已经最厉害了,还对古人评分,有意思吗?”这是我真实的感受。
经学史要将古代经学家及著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理解,要讨论那些古代经学家的观点,必须知人论世。这种想法是自然的,我也不敢反对。但一提“历史背景”,很多人想的往往是政治史,很多论述都将古代经学家与某一种政治势力结合,将经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理解。我也很不喜欢这种论述,因为我对政治史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例如渡辺信一郎先生是位笃实的史学家,大约四十年前,他有一篇论文认为《孝经》的编者是“韩诗学派”的人,根据是《感应章》引《诗》作“自东自西”,不作“自西自东”。这四十年我们对经学史的认知毕竟有些深化,我们认为“自东自西”还是“自西自东”这种文本的微小差异根本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相信现在没有人认同渡辺先生这种推论。但他在一部经书的背后要假设一个“学派”的存在,恐怕是因为他太习惯于政治史的思维方式。而且我怀疑至今还有很多人比较习惯这种思维方式。
经学史研究,必须要先读懂那些古代经学著作。这固然是废话,但我们读懂古代经学著作是相当困难的,实际上有很多著作都从来没有人真正读懂。我自己先后阅读郑玄注《论语》《礼记》《孝经》,意外地发现有很多内容过去一直被曲解或忽略,没被真正理解。我不认为我的理解都很精确,究竟该如何理解还需要今后的学者继续探索讨论,但就是郑玄这样最有名最重要的经学家的经典作品,一千几百年来无数学者都研读过的注解,其实都没被真正理解,这一点已经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我这种说法或许令人感到很荒唐,但我也能提供这种诡异情况所以发生的合理解释。简单说,南北朝以来一直到近代,阅读郑玄著作的学者本身都是经学家,都有自己一套学术方法,他们并不以理解郑玄的思路为目标,所以曲解或忽视郑玄的意思都不觉得有问题。
人的思维通常都有一定的逻辑,所以读书要探讨作者的逻辑。不过古代学者的知识结构、认知基础与我们不同,所以要探讨作者的逻辑,必须先了解这些学术前提。对郑玄学说有丰厚的研究积累,使得我们比较容易探讨郑玄对具体经文作注时的思路。相较而言,以往的《春秋》学研究与古代《春秋》学之间有点距离,这让我们探讨杜预、何休等人的思路更加困难。我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杜预的《春秋释例》,近几十年来没有影印出版,要看都买不到书。我以前复印《丛书集成》看,后来买到早年日本的“中文出版社”影印殿版丛书本。我们要理解杜预的《春秋》学,《春秋释例》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资料吗?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家出版社都没出版过?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将《春秋》当作历史资料来看。无论是政治史、社会史、语言史,都是历史学的兴趣。所以中华书局出过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而没出过杜预的《春秋释例》。不会有人认为杨伯峻比杜预更重要,但很多人要看《春秋左传注》而对《春秋释例》没兴趣。
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了郜积意老师的《义例与用字——何氏公羊综考》,让我感到学术风气的转变,经过一百年的“科学”热,终于开始转向“人文”了。汉代学者研究了《春秋》经传的义例,现在郜老师研究何休的义例,十分有趣。《春秋》既然是经书,应该要有义例,但孔子没有明确说明义例,所以各《传》发明义例。但《传》中有关义例的明确叙述仍然有限,所以汉代学者各自发明义例。何休发明的《春秋》义例,在《解诂》中有一部分明确的表述,但不够全面,这就需要由后人来探讨。义例靠归纳,但现象很复杂,所以设立一个义例,往往要碰到不符合义例的众多现象。对此,历代学者都要各自想出各种解释,所以各家义例都不相同,而且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义例是唯一正确的。
郜老师努力发明何休注的义例,自然有很大的困难。例如据郜老师介绍,《汉石经》无论《春秋》经文还是《公羊》传文一律用“殺”,不用“弑”字。因为“弑”字后起,所以传世文献当中“殺”“弑”分用不严,混用两字是常见情况。但隐公四年《解诂》有“弑者殺也,臣弑君之辞”,所以何休所据传文应该有用“弑”字,而且何休对两字分用有明确的认识。但何休当时的文本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只能阅读南宋以后刊本,经、传、注中“殺”“弑”互见,都不足据。考虑到《汉石经》的情况,也不妨想象就算何休所据的文本,也未必一一符合何休心中的分用原则。僖公九年“冬,晋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齐”,《公羊传》“此未逾年之君,其言‘殺其君之子奚齐’何?弑未逾年君之号也”。何注云:“不解名者,解言殺从弑,名可知也。”据何注知,所据经文作“殺”,传文作“弑”。郜老师认为徐疏这样理解,实失何意。何注当读“解言殺,(句)从弑名可知也”,“从弑名”意谓“可从弑君当名之例推知奚齐是名”。若如徐疏理解,何注当作“解言弑,名可知也”,不当言“从”。我个人认为当时“殺”“弑”既然分用不清,表达“弑”的意思也会写“殺”字,那只是用字不同的问题,所以何注才用“从”字。我怀疑徐疏的理解恐怕符合何休的意思。郜老师否定徐疏的理解,认定何休所据经文作“弑”,传文作“殺”,根据是他对何休用字义例的理解。然而因为何休的注中能够从文义上确定是“殺”是“弑”的情况非常有限,所以也要参考南宋版本的文字。这不得不降低郜老师推论的确定性。试想连依据徐疏文义可以确定的“殺”“弑”分用情况都被认为不合何休义例,南宋版本的文字能有多大的确定性?再说,假设何休的义例如郜老师推论,那只能说是何休对这些文字的认识,并不代表何休所见或所写文本都符合这种义例。因为义例是一种思想,可以贯彻原则,而现实抄本的文字极其不稳定,更何况“殺”“弑”不分在当时是常态。例如上引隐公四年注“弑者殺也,臣弑君之辞”,我怀疑本来应该是“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辞”,尽管版本都作“弑君”。
探讨义例很困难,是义例的本质如此。经传也好,注也好,不一定所有地方都符合义例,所以义例只能是一种假设,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为了理解作者的思想,我们还不得不探讨这种假设。而且这种探索需要综合考察整体经、传、注的所有内容,所以需要一个学者长期专心研究。本书就是郜老师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成果,非常难得可贵。第一次拿到本书翻看内容时,我发现郜老师极少参考引用近代以来学者的研究论著,颇有好感。我作为一个爱好者,喜欢看注疏,喜欢看郑注而已,没有精力多学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郜老师是学界公认的一流学者,而沉浸在《公羊解诂》的世界里,控制自己不要让别人的议论分散注意力,我认为是十分值得敬佩的学术态度。对一部书的深刻理解,只能靠一个人直接面对作品得来的体会,别人提供的信息没有太大的帮助。
老实坦白,我没学过《春秋》,没有能力理解郜老师的论述。就算如此,我认为本书出版是天大的好事。因为郜老师在真正探索研究何休个人的思想,与过去评论何休注说的是非,或者叙述何休的政治社会背景等研究不一样。我知道这本书不会畅销,因为一方面很难懂,另一方面很啰嗦。可是我要替郜老师解释,这是不得已的。难懂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没有认真学过《春秋》学,自己没有细读过《公羊解诂》,就是外行。何休在汉代《春秋》学传统的基础上,用其高超的学识写下的《公羊解诂》,自然不是外行一下子能够理解的。也是因为如此,所以郜老师必须多花笔墨做详细说明。换言之,本书难懂、啰嗦的两大弊端,问题不在作者,而在读者。不过我也相信本书的出现必定会产生一批读者,通过本书加深对《公羊解诂》的理解,在郜老师到达的高点之上,再继续探索,使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何休及其《公羊解诂》。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将来还会有很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