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让-米歇尔·傅东对话贾樟柯:新浪潮与电影自由
2012年,恰逢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际,上海师大电影学堂曾邀请到法国电影评论家让-米歇尔·傅东(Jean-Michel FRODON)与中国电影作者贾樟柯从电影多重角度展开对话,带领观众深入了解国内外电影的发展形态。
2020年,上师大【电影学堂·SH 7ème Art】将于11月15-29日举办《法国纪录片经典展》和相关大师班系列。本次活动以法国现当代纪录片史为背景与基础,观照自“二战”后延续至今的世界走向、社会命题、文化地理、思想体系以及个人事件等纷纭脉络,聚焦于1947年至2019年跨越七十多年来的法国重要纪录片作者和作品。
此次法国纪录片经典展期间,电影学堂邀请让-米歇尔·傅东先生连续主讲3期学堂大师班,就《电影人》、《日月无光》和《四姐妹》三部作品展开分析和精读。
傅东与贾樟柯的对话

贾樟柯
让-米歇尔·傅东(以下简称JM.F.):首先我要感谢王方老师,感谢她组织策划这样的关于法国电影的放映、见面以及对话活动,另外我还要感谢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马伊容女士。是他们的工作使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欣赏这些电影并和大家分享经验。同样也要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才得以有机会和你们分享这些法国电影。我不太喜欢谈论电影本身,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先看再谈,所以我想跟大家主要讲一下法国的年轻导演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生存空间。
我也希望我非常欣赏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先生能随时打断我,和我分享、跟我产生共鸣,当然这种共鸣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那就是——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生存空间和处境。
贾樟柯:我认识傅东先生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导演,大概是在1998年的时候。我的第一部电影《小武》要在法国上映,傅东先生那个时候代表《世界报》来采访,我们认识之后,他开始对我的工作进行很热情的介绍和推广。此后我们也不时有过见面,很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电影节、还是在中国,见面之后即使是很短暂的时间都能够有很好的交流,从他那我能得到非常好的观点和信心。最近的一次就是几个月前在北京的一个影展开幕式,那天阿涅斯·瓦尔达女士也出席了。没想到很快我们能在上海再次见面,来讨论中法年轻导演生存空间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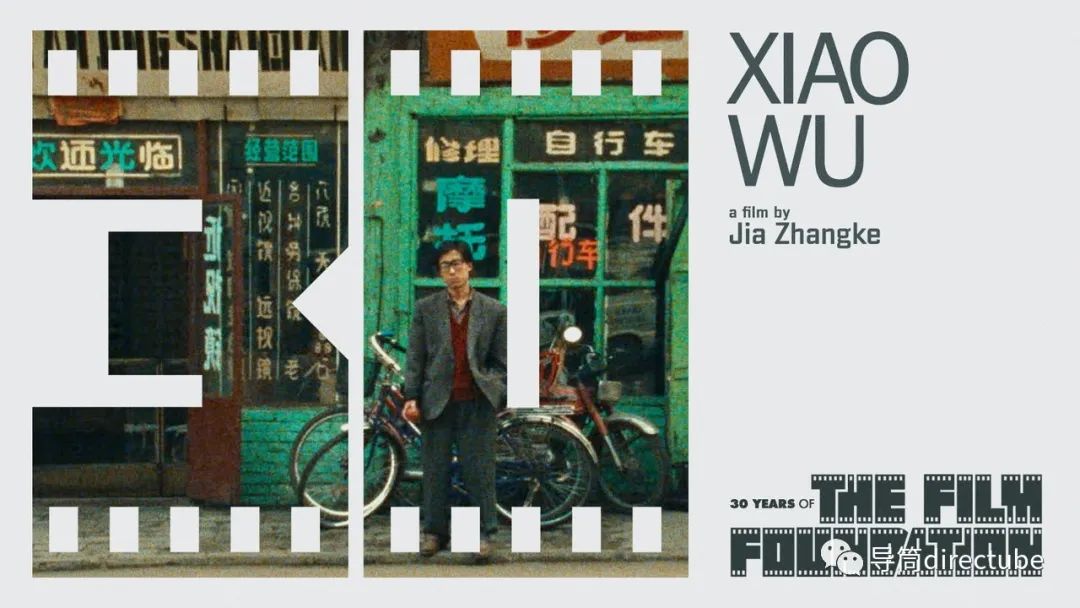
JM.F.:我很高兴贾樟柯先生一上来就提到了阿涅斯·瓦尔达,我们刚和瓦尔达女士在北京见过面。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来讨论一下法国的年轻导演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当然这不能说是负面的——他们同时和他们的前辈,甚至非常年长的一代电影人生存在同一个空间内。我不知道在上海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在北京,大家都称呼瓦尔达女士为“新浪潮的老祖母”。当然还不止瓦尔达这一个例子,阿伦·雷乃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出现时已经有九十岁高龄了,当时戈达尔就提到阿伦·雷乃正在筹备一部3D的新片,同时也在为互联网拍摄影片。看到这些伟大的高龄电影人们依旧充满了活力,而且具备物质条件去拍摄新的影片是一件很积极的事情,但同时这也勾勒出当今的法国年轻电影人的生存现状。
要了解法国年轻的电影导演实际上你还要了解一下法国公立机构的一些政策和行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他们帮助法国的年轻导演去拍摄他们的处女作,在法国每年生产230部左右的电影,有四分之一的影片实际上都是处女作。除了CNC以外,还有不少特别的项目专门用来资助年轻导演完成处女作。
CNC工作非常重要的,这个资助体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把所谓的商业电影、作者电影、主流电影或者非常特立独行的电影完全地割裂开来,或强调他们支持哪一类电影人,而是保持电影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同样,我们这个主题单元——“法国新电影·当代作者”,将分别在【人文·法国·电影学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一些法国年轻导演的影片,这些影片不只是有所谓的作者电影,还有多种形式和类型的影片,有故事片、喜剧片、警匪片或者是音乐剧。
实际上,我们这次给大家选送的这些法国影片——其实我们还可以选出很多,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导演——都和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浪潮”运动是法国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这个时期的一次伟大的电影运动,像一朵非常大的浪花一样,横扫整个法国电影界,同时也影响了法国电影以外的世界影坛,以及后辈的电影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二十一世纪的法国年轻电影导演实际上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孙辈或者重孙辈。
我们要知道,“新浪潮”运动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电影拍摄方式的运动,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它质疑传统的拍摄模式,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每一个“新浪潮”导演都发明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电影拍摄方式。

如果说法国“新浪潮”运动给电影工作者带来的影响是呈现一种追求电影自由精神的话,那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的是对自由的寻找。我们不停地在突破对自我内心的约束或者外部环境的约束,来寻求到这样一种自由。
如果说中国的电影人与我有机会见到的法国导演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我觉得法国的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研究一直在背后发挥它巨大的作用,比如像”新浪潮”时期《电影手册》的那种作用。一直到现在,在我能接触到的年轻法国电影工作者中,他们对电影史的了解、研究以及对电影本体理论的思考都有一种自觉性,可能在中国年轻导演中比较紧缺的就是对理论的兴趣,以及因此缺乏的对电影的一种自觉的理解。也许我不太清楚更年轻一代法国导演对电影理论的兴趣和关注。

所以我们在法国实际上是非常幸运的,有这么一批电影评论家和大学里的研究机构一直做着关于电影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同时全法国还有大概四百多种的各式各样的文化节,使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地点,抱着不同的期待去聚在一起——不仅仅是娱乐的期待——去欣赏电影。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整个的法国电影生态里面不止有导演艺术家,还有能够保证他们生存的一批人,也就是制作人。他们可能是一些很小的制作人,有的是中等的,慢慢会成长为大的制作人,这样一个专业的经济管理人网络的存在对电影导演的生存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贾樟柯:既然谈到制作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电影人,我也有很切实的感受。过去中国电影一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电影的策划、制片运作体系都是在国营的制片体系里完成的。大概到九十年代以后,国营制片体系开始衰落,各种各样的制片公司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很多制作人也就从这样的体系里分化出来。而目前中国每一年大概有一两百部——具体的数字我很难给出,但是肯定不少于一百部年轻导演的处女作诞生,基本都是极低成本的个人制作。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电影环境里,导演数量增长的同时,同一个年龄层、具有同样电影热情、社会关怀和美学品味的制片群体的崛起比较滞后,于是,中国年轻导演不得不自己承担着制片人的职责。当然,我们更为缺乏的是一个由政府所设立的鼓励和帮助年轻导演的机制。由于缺乏这个机制和相应的制片人群体,中国电影就出现了一个两极化的情况:一边是所谓的大片,一边是极低成本的,艺术质量可能非常好,但制作质量达不到水平的影片。这是很现实的一个困境,我们需要有更多年轻的制片人。
电影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了器材匹配上的自由,这是目前制约着一类电影进入电影工业或商业系统中的大障碍,因为大部分年轻导演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在无法获得必要的制片体系支持的情况下制作电影,令他们使用的设备在技术质量上不能达到技术审查的指标。在中国,电影需要接受两个审查,一个审查是内容审查,另一个就是技术审查。技术审查就是按标准审核每部影片的设备质量、技术质量和声音质量等,所以,大量的电影作品因为技术原因而无法进入市场。因此,在这个工业体系之间出现了脱节,年轻导演不得不在一种精简模式里面工作,这可能也是目前中国年轻导演面临的困境之一。
JM.F.:那我继续接着刚才讲。“新浪潮”对今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当今的年轻电影导演不能再去拍他们老一辈电影人那样的作品了,比如说戈达尔在四、五十年前拍摄的那种影片。因为作为“新浪潮”的孙辈、重孙辈,他们必须去寻求一些全新的、个人化的拍摄方式。这种特殊的、年轻导演的创造力实际上和当今的一些新的电影工具的发明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数码工具。
就像贾樟柯先生刚才提到的,电影工具的进步使我们可以随意使用轻便的、不那么沉重的摄像机。我们就可以不再孤独,不用再做简单的作者电影,而可以跟更多的大众进行交流。实际上,数码技术是一个非常暧昧,甚至是有些矛盾和悖论的事物,一方面它使电影的低成本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又把小制作的电影和超大制作的电影完全地割裂开来。而我有一个观点,大家可以和我意见相左,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拍摄,而是你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播放。
实际上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们有了更多的电影播放的模式。可以在影院播放、在电视里播放、DVD播放,甚至在互联网上播放。一方面,需要同时存在这些不同的观影模式,但是仍然要把电影院——作为最首要的与观众见面的电影场所,之后才让它在其他媒介上放映。

但如果单纯靠市场调节的话,很多小规模的电影根本不能进入电影院线,所以,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支持,使得这些小成本电影也能进入到电影院播放。
贾樟柯:我想接着傅东先生话说下去,就是电影播出模式的变化的确带给我们很多挑战。电影阶段性地出现新的播出渠道,比如说电视,然后是DVD、再是网络,过去一个家庭可以在电视机前看电影,到后来变成一个人在电脑面前看电影。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整个新媒介它做的都是分流的工作,也就是说从一个500座的影院变成了家庭影院,由家庭影院又变成了一个人的欣赏。但是我觉得电影在公共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特性是聚众,是聚合。当一部影片在播放,大家头朝一个方向看一个银幕,100个或200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面对电影的形式在它的背后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信息和情绪能够产生。我觉得分众实际上它将电影在魅力层面的和社会层面的作用都削弱了。大量的纪录片,由于用DV拍摄、用数码拍摄因而无法进入影院,而恰恰是这些电影更需要电影院来进行聚合,使我们有面对这些影片的机会。电影院不仅是提供好莱坞电影声画体验的场所,也应起到聚众的文化作用。
JM.F.:我补充一下。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方面有着非常令人瞩目的,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电影导演,特别是勇气可嘉的独立电影导演出现。他们实际上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变革和成长,向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外国人展示了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当然,法国年轻电影导演的处境很难和中国进行比较,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法国当代社会的变迁。我在这里讲到的法国当代电影不仅包括纪录片,还有那些直接描述社会事件的影片,包括爱情故事,或一个关于警察和小偷的故事。不同的影片给我们阐释了法国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外国人和法国本土人群的关系、和司法部门的关系、和电视的关系以及和权利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法国整个社会的样貌。
贾樟柯:我认为中国目前是处在两个银幕世界。一个银幕世界是常规电影院,能够通过它见到一些影片,特别体现这几年快速的商业化。这个银幕世界有一部分影片能够触及到现实,无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影片,就像傅东先生说的一样,它可能是一个爱情电影,可能是一个古装片,但是它跟现实都有某种联系,但是在这样一个银幕世界里面,这一类型影片的空间实际上还是非常小的。那另外一个银幕世界的影片,它是被隔离在视线之外的,我觉得中国的年轻导演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生产积累了大量的影像财富——电影财富,但这一部分的财富基本上是沉默的,对它们的放映、研究和公众对它们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JM.F.:实际上,贾樟柯先生刚才的描述和我们从外部感受到的大致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一个观点,我认为也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唯一的方法,那就是把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和操作,而不是把它分为所谓的商业类还是艺术类的电影。
贾樟柯:我觉得目前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大概若干年前中国开始大量地盗版DVD,然后街头到处都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电影。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当然我们是盗版的反对者,但是当时突破的是我们无法接触当代电影的困局,因为以前外国电影的引进数量没有那么多甚至不允许引进,突然有这么多的盗版,我觉得它突破了这个困局,感觉我们可以接触到真正当代的电影了。多年下来,我们能看到的电影已然非常丰富。中国到处有电影资料馆,你从爱森斯坦到特吕弗到费里尼一直到当下电影都可在资料馆里找到。然而经过了那一段时期以后,我发现我当时的乐观是盲目的,因为这些电影没有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系统里面进行有效的放映,那对于一般的公众来说,目前依然只有两种电影,一种电影就是中国电影,一种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实际上,我们仍然没有在公众层面——而不是说在电影工作者、研究者或者说影迷的这个范围里面全面推广当代电影,而仅仅是当代的中国电影和当代的好莱坞电影。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电影的发展方式跟语言上缺少当代性,因为有的电影只是在满足本土市场,能够形成当代观念的电影就显得非常少。当我们想谈年轻导演的工作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巴黎生活过,我们会发现那个城市它可以看到法国电影、好莱坞电影,同时也可以看到欧洲其他地区的电影,还可以看到泰国电影、伊朗电影、哈萨克斯坦电影——也就是说当代最有创意的这些影片它都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跟公众见面,这样的话,年轻导演面对的就是一群有电影阅历的观众,而由这部分观众培养起来的媒体系统、评论系统反过来也会建立一个对电影认识的基础,鼓励导演的实验和创造力。也就是说,正因为我国欠缺这样一个能够分享世界各地电影的体制,致使我们的观众面对过的电影数量少、种类单调,我们的电影导演,面向市场或者面向观众的时候就可能相应的要保守,在创造性上受到制约。所以我们不能抱怨观众,这源于一种文化限制。
JM.F.:贾樟柯先生能提到这样的外部影响非常好,因为当谈到法国年轻导演所继承的文化遗产,我也是想说他们不仅有“新浪潮”这一法国内部的文化遗产,同时还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国家的电影文化遗产。
对法国电影导演的影响来源是非常众多的,不止有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也不只来源于电影,还有电子游戏和电视剧等等,所以他们的艺术是非常多元化的。在想象力方面,在视觉的创造和再现中,这20年以来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有亚洲电影以及中国电影。这二十多年以来,我们越来越关注那些重要的亚洲导演的影片,比如说小津安二郎、台湾导演侯孝贤以及香港武侠电影,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先生。而这些电影导演的作品各不相同,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节奏、把不同的人物整合在一个画面里的不同做法以及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一切都丰富了法国电影导演的创作,丰富了法国电影,因为我们到头来还是要谈这些法国电影导演的作品。

所以说这些法国的年轻电影导演和全世界其他的年轻电影导演都是一样的 ,关注当代的世界电影,能够丰富他们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说要模仿贾樟柯先生在法国拍一部这样的电影,那样做将是很愚蠢、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说他们能够继续关注这样的电影,消化掉,然后在自己的国家拍出自己的影片。
贾樟柯:这就是说,一个导演无论面对的是电影传统还是电影经验,都应该是来自全球整体范围内的资源。因为在电影世界里,所有的影片都是我们可以去分享的。另外,就是电影导演与当代艺术的一种关系。我不清楚法国导演是单纯地进行电影工作,还是也会涉及到现当代艺术的领域,从而使其电影艺术的实验性与当代其他艺术类型有了横向联系,或者说他们是否会经常关注其他艺术领域。那么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存在着这样一种融入到当代艺术整体中去的努力。 这并不是说要去尝试用其他艺术手法,而是说在知识范围内与同时代其他类型的艺术家——绘画、行为艺术或录像装置艺术范畴的,与电影一起作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来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JM.F.: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至于法国的情况,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笼统的回答。可能电影导演还是分成两种的吧,一种就是和当代艺术非常亲近的, 他们可能游走于电影院、美术馆以及画廊之间,他们可能本身既创造影片也做装置艺术或者影像艺术,而且这样的电影导演实际上不限于年轻的法国电影导演,比如说阿涅斯·瓦尔达,她就是常在美术馆展出她的装置艺术,也在电影院里面播放她的影片。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存在的。

以下是对话实录节选,对话全文已收录于《法国电影在上海》一书,201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电影学堂·大师班】
Master class
主 讲
让-米歇尔·傅东
Jean-Michel Frodon

巴黎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1953年生于巴黎,研究领域包括电影史和当代世界电影。1995年起任法国《世界报》电影主编,2003-2009年任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发表并出版近30本权威电影专著。相继任教于巴黎一大-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为巴黎政治经济学院艺术系教授、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电影系教授。
时 间
11月15日17:00
11月22日17:00
11月29日18:00
地 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礼堂
上海市桂林路81号东部文苑楼二楼
大师班线上通道
原标题:《让-米歇尔·傅东对话贾樟柯:新浪潮与电影自由》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