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女性主义,不该作为一种边界存在 | 直播实录

编者按:私领域影像的重新组合,一部自发记录的家族史,在异乡逐渐老去的舞女,一个女性怀着对爱情的热望向父权制猛烈冲击……这是我们在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上看到的女性主义纪实群像。在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浪潮时,纪录片能够呈现的景观是什么?我们在谈论纪录片里的女性主义时,又在聊些什么呢?澎湃新闻·眼光栏目邀请了资深影评人张献民和苏七七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纪录片里的女性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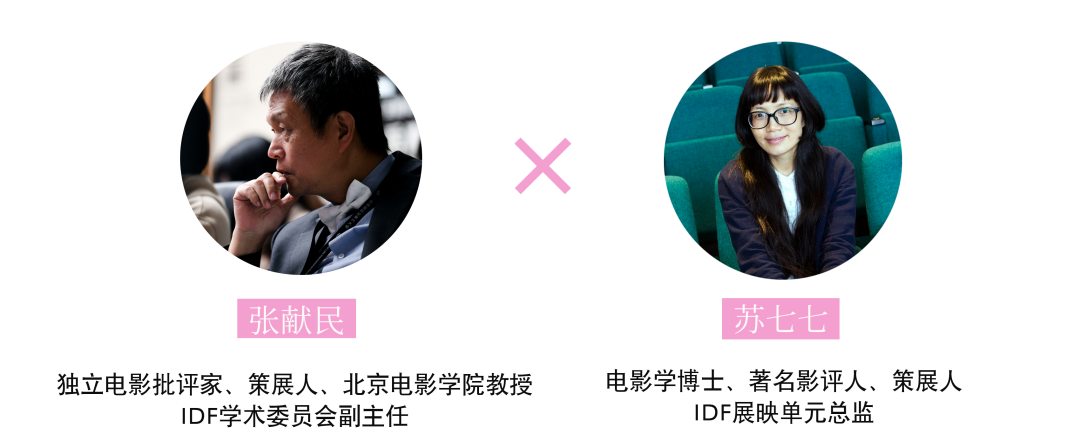
眼光:两位老师都参与了本次IDF的选片环节,苏七七老师参与了初选,张献民老师参与了终审。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选片经过?
苏七七:女性相关可以分成为三类:女性导演的/以女性为拍摄对象的/女性主义的。可能重合,但也有可能完全不重合,一个男性导演可能是女性主义者,拍出女性主义纪录片;也有可能一个女性导演她的观念是男性中心的,或者她拍的电影并不涉及性别议题,不应当放在女性主义纪录片中来讨论。
D20单元19部纪录片,有5部是女性导演执导,另外有两部,《妮诺丝卡》和《穿过雷火》,是男性导演导演的,但主体是女性的。在展播影片中,有4部是女性导演执导的。的确占了相当比例。
但我作为初选评审,并没有在初审中将女性导演乃至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衡量或平衡的尺度。最终只是一个自然的数据呈现。当这个状态呈现出来,作品们可以作为一个集合出现在观众面前时,IDF也很愿意将这个角度带到更广阔的公共话语平台上,引发更多的共鸣与思考,并推动女性主义纪录片的呈现与创作。
张献民: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一个结果,在表述这个结果时,必然会介绍一些过程,但这些东西不是前提。
IDF的选片跟我做过的其他选片或评审工作是一样的,有些原则在公共领域里面应该永远坚持,不应该有任何偏向,比如说除了女性的话题之外,是不是要照顾一些老年题材或者儿童题材?实际上这里面没有照顾的问题,只是要求选片的人或者是评审,他们要把自己的全部都拿出来摊在桌面上,可以是他的爱恨情仇,也可以是完全知识分子的视角,几个选片人和几个评委在小组内部进行讨论。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出现仅仅为了平衡的考量,起码我们力争没有这样平衡的部分。IDF展出现的这些纪录片有很强的女性主义性质,不是我们刻意的。我会认为它反映了女性制作纪录片越来越活跃,它们的产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
眼光:我们来聊聊具体的影片,《妮诺丝卡》获得了本次的年度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当时是怎么入选的?
《妮诺丝卡》剧情简介
五年来,导演彼得·托比恩松一直在记录圣费尔南多与尼加拉瓜小镇上的生活。原本是为描绘小镇风貌,却成为一个关于妮诺丝卡的故事,一个女人逃离了家暴的丈夫,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欧洲,为维持家庭而寻求生计。然而,为独立而奋力斗争的她,必须去面对她那充斥着中美洲大男子主义文化的过往。

纪录片《妮诺丝卡》海报
苏七七:这个片子初审的时候恰好分在我那个组里,也是我在初审的时候把它给挑出来的,然后进入了张老师的终审环节。《妮诺丝卡》片子是很抓人的,它是一部很容易给人很大共情的纪录片。它是男导演拍的,但拍的是一个女性的生命旅程,把生命旅程放在社会变化的宏大背景中去展开,可以说它具有某种史诗性。它关注了女性遇到的各种问题,贫困、家暴、抚育孩子的不易、工作创业的艰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呈现了女性的美与坚韧。
我在看片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感受,这位男性导演拍关于女性的影片的时候,有一种把女性看作比男性更了不起的性别的倾向:更无私,更坚强,更乐于奉献。但对这种倾向,我也有某种内在的警惕,诚然这种坚韧无私都是真实的,但它也是一种塑造和引导,一种道德上的隐形定义。
张献民老师有评论到这个片子,说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男性对一个无产阶级女性数十年的拍摄,我依然想听张老师来说说这个事情本身怎么理解。从我的角度看,一方面觉得它很好,一方面也有一定保留。这种持续性的关注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彼得·托比恩松肯定是女性的友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我对这样的一个导演是抱有敬意与谢意的。
张献民:拉丁美洲是一个特殊的背景,社会学或者经济学上讲的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拉丁美洲可能是最典型的,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也在其中。
它的革命或者政变,来自于左派还是右派,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多说无益,但纪录片讲的时间的分量,四十年的分量确实很重。我想如果是拍一个男性的命运,这个纪录片会不会分量就太重了,以至于它得是社会学或传记的一个非虚构的文本,没有办法用纪录片这种相对轻盈的方式来做,不太好说。
我想讲的是纪录片的传播环境,《妮诺丝卡》是一个做了四十年的纪录片,是一个瑞典人拍摄一个尼加拉瓜人,每5-8年就会产生一个纪录片作品,在过去四十年当中诞生的这些纪录片作品,在欧洲的电视台都是正常播出的。我希望我们不仅能够生产创作一些高质量、有分量的纪录片,同时也能创作出非常轻盈,创作者和被拍摄者的生命和生活都能够被涵盖进去的纪录片。我也希望大众能看到这样的作品,并且展映这样的作品。希望这样的纪录片不止能够在各种大会或者展映当中出现,也有机会出现在像电视台那样的大众媒体当中。
眼光:除了《妮诺丝卡》以外,还有没有哪部女性议题的电影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苏七七: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是《永远的瓦尔辛湖》,它也有涉及到一些女性议题,但它没有集中在某个问题上做许多逻辑上的推演。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很独特,里面讲了四代女性,第一代在瓦尔辛湖边盖了一个咖啡馆,第二代女性受过教育,但基本上一直生活在这里。就是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成;第三代的两个姐妹在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浪潮中去过世界各地,过嬉皮士的生活,追寻生命的意义;第四代的女儿用这个纪录片回溯了整个家庭的历史。
《永远的瓦尔辛湖》剧情简介
在这部家庭传奇中,导演展开了一场跨越世纪的探索之旅:她带着我们从巴伐利亚瓦尔辛湖边的家庭咖啡馆到旧金山,再到臭名昭著的“爱之夏”。这是一个关于寻找身份、自我实现、爱情、痛苦、精神病、出生、死亡的永恒的家庭故事,也是一部关于生命轮回的纪录片。
这个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直接地去应对某个性别议题。电影里的女性过着中产之家的生活,这个母系小社会为什么延续了四代是有偶然性的,因为刚好每一代的孩子都是女孩,女性成为财产与家业的继承人,也从事摄影、音乐这样的艺术活动,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因为这个家庭四代一直稳定在瓦尔辛湖边生活,所以家庭史的资料保存得非常完备,像照片、日记、录像、第三代在世界各地浪游的纪录,这个乌托邦显得有凭有据。她们也面临男性对她们的一些控制,比如对家庭的控制,或者观念上的引领与强势。但总体而言,跟她们一起的男性也是艺术家型,比较边缘的男性,所以并未颠覆或占领这个小乌托邦,而成为这个小乌托邦的过客。
这个纪录片呈现了一种存在的可能,即在有财产的前提下,在自然与艺术的环境下,女性可能有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生命历程。她们其实也在文化潮流的发展中随波逐流,也并不觉得她们在灵修中得到生命的奥义。但这种无拘无束的尝试,产生了很多美的瞬间,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诗意,所以这个片子看上去是美的。这不光是女性追求的东西,我觉得男性也追求这个,但在父权制社会里,不论对女性还是男性都是很困难的,它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的小乌托邦状态,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它很独特,虽然这个东西出现很偶然,但它依然有一种美和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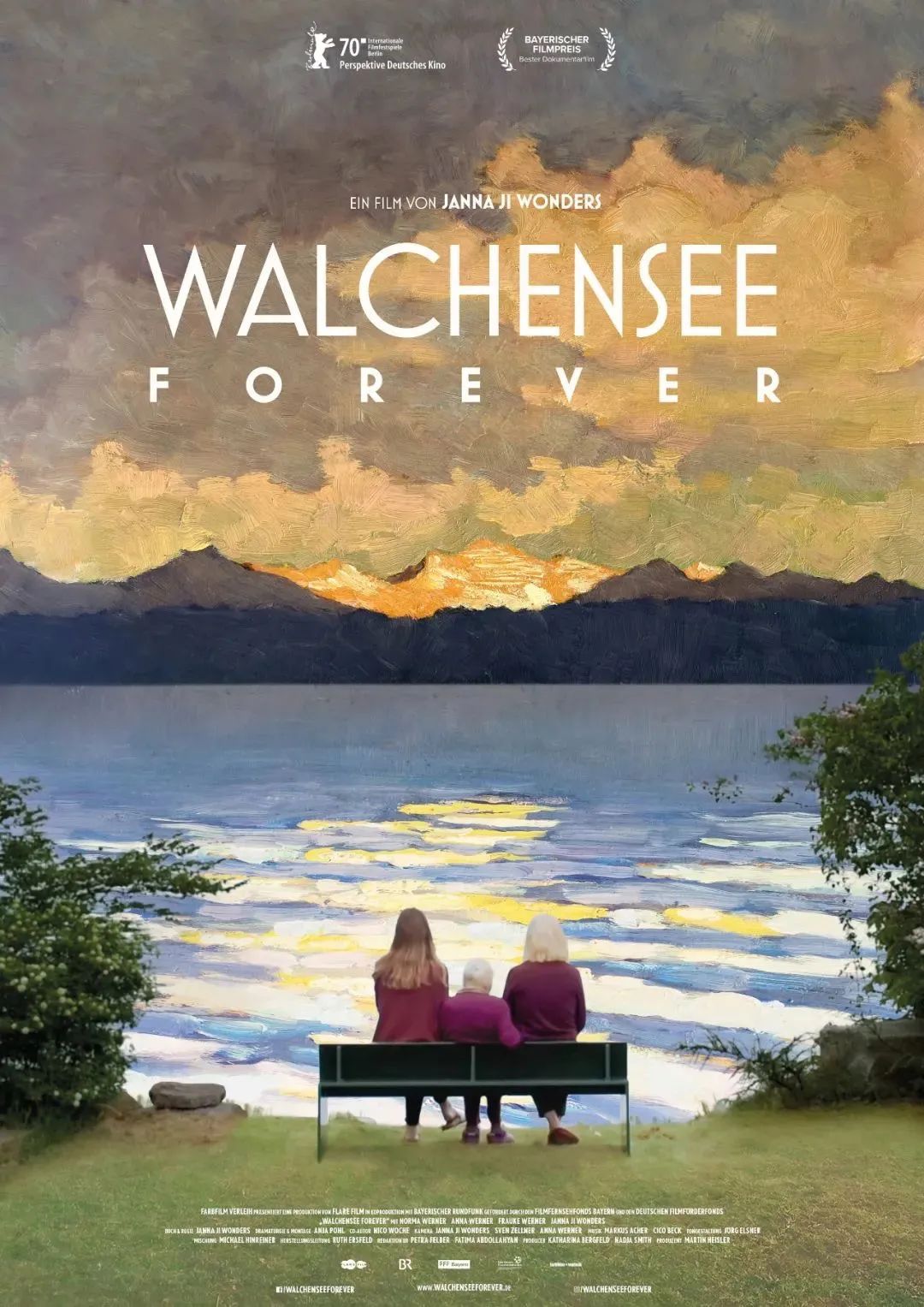
纪录片《永远的瓦尔辛湖》海报
张献民:在今年我看的纪录片中,《永远的瓦尔辛湖》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在旁观评委们进行评选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干预,不过我很遗憾它没有得奖。
这部纪录片并不是酷儿作品,我们看到的这些女性都是异性恋,她们有长时间或短时间的婚姻。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来描绘,这些女性需要一些男性的友人,但我不会把它描绘为多元家庭或者是开放婚姻。她们需要一些友人,这些友人是以时间为限定的,每一位友人的介入深度不一样,跟她们共处的时间也不一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可能是现在社会学或某些社会运动中描绘的多元婚姻或者是开放关系。说它不好讲,是因为它的核心感觉还不是很清楚,一个风景秀丽的湖,有山,湖边只有她们这一所房子,这些前提条件还是有点太奢侈了。
不管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是什么样的阶级身份,牵扯到中产阶级的话题就比较麻烦,它跟IDF的组织方式是相关的,跟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在文化消费上是否逐渐在接近中产阶级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平台和电视台在做一些什么,这些都是问号,我只是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另外,如果是一些展映活动,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起码是知识和文化上的交流,城市的中等阶级来观看这样作品,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苏七七:就像张老师刚刚说的,在这个女性群体中,不停有男性友人的介入,我们难以用友人还是伴侣来定义这些男性的角色,他们或是生活中的友人,或是性的友人,或是宗教信仰上的友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但总体而言,无论是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还是女性之间的关系,开放性都很大,互相的理解和沟通是比较畅通的。
特别是第四代的女孩,她与外祖母和母亲之间的交流缝合了整个家族史的叙事。很多面对社会议题的影片,会显得紧张、尖锐,这个片子比较特别,它呈现了一种不那么紧张和尖锐的可能性,当然这个东西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眼光:这次IDF展映的纪录片中,还包括俄罗斯女导演阿黛尔·沙伊胡洛娃的《与你同在》。这些影片都是将私领域的影像进行编辑以后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可不可以就“私影像”这个话题来聊一下,它是不是女性议题纪录片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方式。
苏七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部是《为我哼首摇篮曲》,一部是《与你同在》。因为这两部片子蛮像的,一个是华裔移民在加拿大,另一个是俄罗斯女孩在法国。前一部是女儿为她的母亲找回亲生母亲过程的记录,后一部是对在法国俄罗斯女孩的家庭状态的描述。《为我哼首摇篮曲》讲的是从哪里来的追溯,《与你同在》讲的是这种状况要到哪里去的困惑,它们的类型和主题是有交叉和对照之处的。
《为我哼首摇篮曲》剧情简介
汝文五岁时和她的亲生父母分开了,四十五年过去了,她仍然无法将童年的碎片拼接起来。对汝文来说,生存意味着将自己的好奇心永远埋藏—为什么自己会被父母遗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好奇心已逐渐变成一种无声的渴望。直到她的小女儿Tiffany开始问起一些她从未有机会问出口的问题。《为我哼首摇篮曲》通过女儿和母亲相互交织的旅程,揭示了爱与牺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讲述了一段关于爱与疗愈的家庭故事。
《为我哼首摇篮曲》拍得非常温情,她的母亲是一位很坚强的女性,一代代女性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扶持让人动容,这个片子不长,但是放映结束之后,导演跟观众交流了很长的时间,是让好多人很有共情的一个影片。《与你同在》中的家庭已经不是在一个共同的实体空间里头了,而是在一个虚拟的视频通话中间,在这个空间中又放进了死亡这样一个很沉重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来讲,在现在的这种空间关系里,经验和情感怎么延续。这位年轻的女导演很敏感,她捕捉到了某种状态或某种气息,但因为它是个短片,我觉得还不是非常的充分。
《与你同在》剧情简介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一起离开俄罗斯去到法国,离开了父亲和其他家人。由于每年只回来一次,我们只能在视频中相见。我开始偷偷记录下我们的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了表妹索尼娅患了癌症。我们之间的距离从未曾如此遥远。该如何与你们相聚,和离开的索尼娅在一起?
总而言之,这两个私影像都挺好的,但你说私影像是否是女性导演或者女性主义纪录片比较好的方式,一旦你引入某种对照,都是比较危险的。对年轻导演来说,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和技术资源都不太多,所以个人经验中的某个困惑或某个痛点,就很容易成为他们创作上的推动力,可以直接的从个体经验中找到一个深入的角度。所以对于女性和男性青年导演来说,私影像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觉得有很大性别上的差异。比如说《出·路》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就是中国年轻人从学校踏入社会的成长故事,也有女导演拍过教育问题,拍得都是很公共的议题,我觉得都可以,只要能拍,私影像还是公共性更强的纪录片都没有关系,还是看你自己是哪一类的创作者,更擅长哪一个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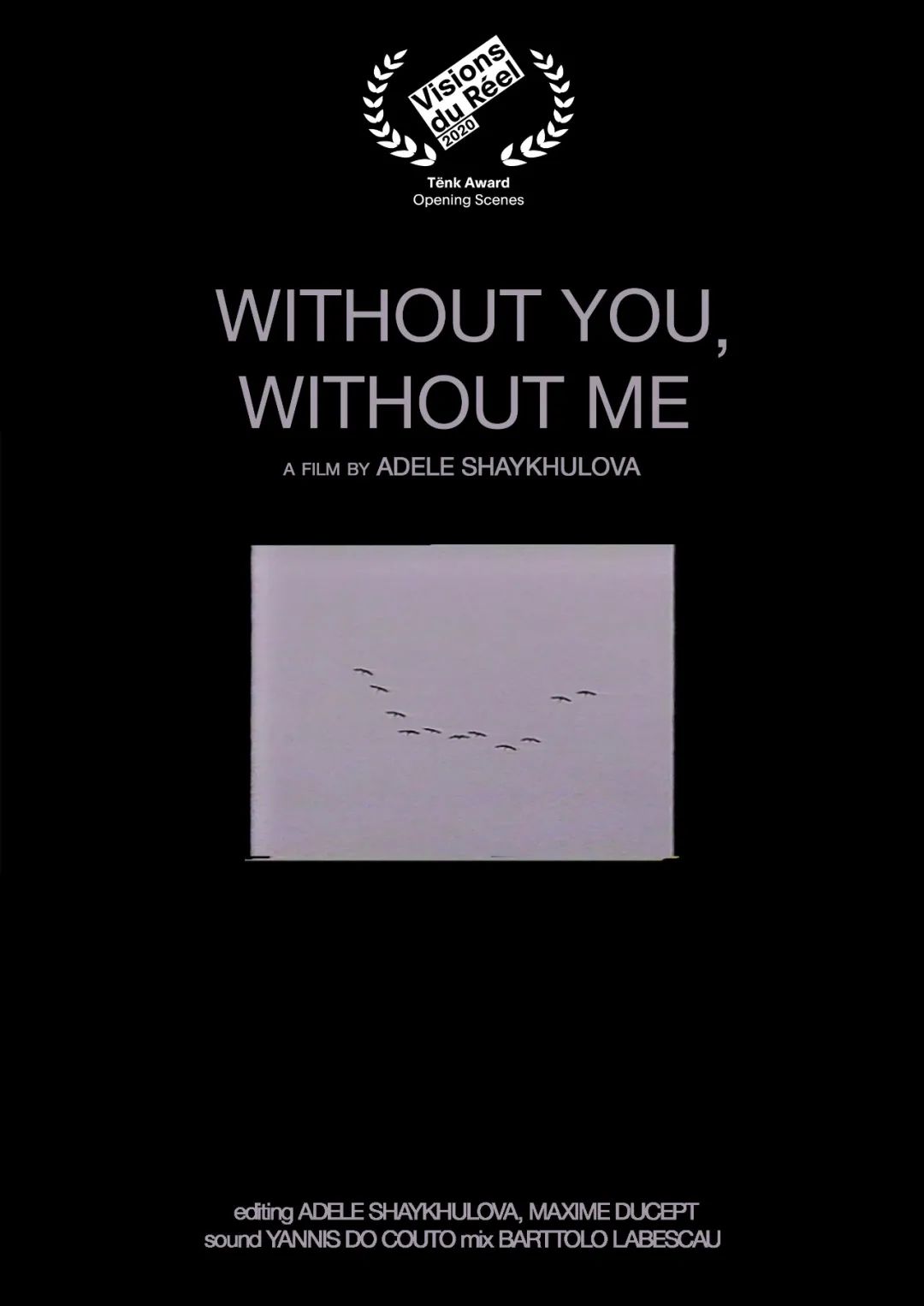
纪录片《与你同在》海报
张献民:这两个角度都是可以的,但同时都会让观看者有一些疑惑,这是非常正常的。
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我们习惯的叙事都是第三人称。当大家看到第二人称的时候,就会略觉得有点奇怪。比如说,新闻节目基本上是第二人称,它是直接对你说话,所以有很多主持人的画面,主持人和电视台都尝试说这不是我的,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不像小说、电视剧和虚构的电影,主要还都是第三人称。所以,纪录片当中如果经常出现第一人称,就是“我”在说话的话,很多观看者可能会不太适应。
它的矛盾在于,当我们看见一个人长时间地去拍摄另一个人,拍摄者是否对被拍摄者有过深的介入,是否过度影响乃至引导了被拍摄者的生活?观看的人会有一种道德焦虑,这个东西它应该这个样子吗?但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只拍摄自己的生活,又会产生另外一种道德焦虑——这是他的隐私。作为一个不认识他的人,我为什么要去看他的隐私呢?
逐渐发展出来的一些艺术形式,可能有非常多的“谬误”。从一个观看者到另外一个观看者,可能观感非常不一样,观感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是一种谬误,觉得这个东西拍错了,不应该这样拍。但这种东西在我们看来,像IDF的举办地浙江,在中国是相对文艺气息比较浓,经济环境好,科技很发达的省份。这样的省份,还有像中国美术学院这样的大学,如果接受并且展播一些更具有实验性的作品,我个人不管是作为一个艺术影片的推动者,还是作为教师这样一个纯粹的身份,都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私影像可能会让一部分人觉得非常不适应,但有一种前现代的观点,觉得女性拍了私影像,那里面会不会有点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去看看。就像苏七七刚才所讲,私影像绝对不是女性的专属,男性做的私影像是非常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第一人称来拍摄纪录片,拍摄自己的事情,不算时髦,但正在被大量实践着。
像《为我哼首摇篮曲》的拍摄者,之前用了大概八年还是十年的时间拍摄慰安妇,她就是作为一个晚辈,去拍摄老年女性,关心慰安妇的命运,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影片几个不同的版本我都看过,她拍摄完别人的命运之后,又回来拍一个家族的命运,就是这部摇篮曲,家族命运当然比较私影像了,是她自己和亲人的画面,是真实的声音记录。实际上慰安妇的影片是更工业水准的一个纪录片,但私影像又回到非常个人的一种记录方式,是没有工业水准的。从制作水准上来说,《为我哼首摇篮曲》这部影片是没有问题的,私影像是拍摄这些人物蛮合适的题材与方式。

纪录片《为我哼首摇篮曲》海报
眼光:我理解的私影像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拍摄的影像,它比较依赖于创作者自发进行的影像素材积累。他们拥有大量的影像储备,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行业。两位老师怎么看待“非专业纪录片导演”拍摄的影像?现在纪录片行业里女性导演的占比是什么样子的?
苏七七:女性导演确实占了相当的比例,今年“IDF创投”提案单元一共有13个提案提交上来,其中男性导演提案5个,女性导演提案6个,还有两个是共同的,他们两个导演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这是一个不完备的例子,但从这个例子还是可以看出女性导演确实是有很多了。至于“专不专业”这个问题,怎样算专业?受了纪录片教育的才叫专业?还是拍过几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片子的算专业?我觉得存在着一些边界的模糊性。
我们难得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作品,看到一些实验性和作者性比较强的作品。我们最好不要以专业和非专业来定义它的高度或者价值,对于一个作品而言,永远都是用它的思想、方法、语言来界定它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张献民:补充一下,“私影像”这个词来自于日本,是日本语言和汉语之间相互的借用。从西方角度以及中国的实践来说,“私影像”这个词不是特别的准确,它实际上是一种“活动影像自拍”,涉及到比如说家里有几代人,积攒了一些什么样的资料,拍摄者自己要不要进入画面等问题。再就是叙述者的问题,即叙述者是谁,自拍的这个人是否愿意做叙述者,还是退回传统的叙述方式,用第三人称“他”“她”来叙述。所以,更学术或更准确的说法,它应该叫“第一人称纪录片”,就是自己拍自己的纪录片。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自恋或自大,是否过度暴露了隐私,是需要观看者去判断的。
就东亚来说,第一人称纪录片的浪潮已经接近二十年了,但第一人称纪录片并不一定是私人领域的,与公共领域也可能有非常多的交叉。原一男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多时候拍的是公共领域,不是私人领域,他只是以第一人称拍纪录片而已。
就日本来说,再举两个例子对比一下。首先是荒木经惟,荒木经惟拍的是他的妻子,他自己也会进入影像之中,但荒木经惟本人并不一定是他图片的必然叙事者,他作为叙事者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必须是由别人来进行分析的。和这个例子相反,河濑直美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一再说私影像不是女性的专利,但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日本文化而言,虽然荒木经惟是非常私人领域的,但是他不太第一人称,可是河濑直美永远是第一人称的,河濑直美有一些作品是有关她个人的私生活,有时候是她居住地附近的邻居,不完全是私人领域,但也都是第一人称。这样讲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要破除道德焦虑,私影像或第一人称纪录片,并不是对别人进行窥探。
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活动影像作为一个表达手段,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的作品生产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这可能和短视频的创作是相反的。影像以怎样的拍摄和编排方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从影像的历史上看也是这样的,现在去看最早的纪录片影像,我们再怎么修复,它的像素都很差,但它非常有魅力,跟观看的人非常容易交流,看过的人都觉得非常宝贵。
影像质量不是问题,专业性可能会改变作品素质的10%到30%,但它不是根本性的东西。一个影像作者做纪录片,有专业素质的问题,有必要做一些自我提高的工作,但觉得自己水平不行不是不表达的理由。
以下为网友提问:
Q: 在中国的电影和文学圈内,两位还有比较欣赏的关于女性主义的创作者或者是作品吗?
苏七七:李玉、杨荔钠、杨明明、黄骥,这几位女性导演的影片我都推荐的,纪录片的话,马莉导演的《囚》是非常好的。
张献民:七七谈了一些影像方面的,我从作家方面来说,铁凝早年有一些小说,穿透力非常强,那种效果和能够收取到的东西都很直接,在感知和深度层面都挺好,跟贾平凹早年的小说一样,非常好。丁玲老师的《莎菲女士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间有十几年的跨度,我觉得做文学的人都可以阅读,也可以进行一些研究。
Q: 女性主义的叙事与创作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有哪些东西是最好不要触碰的?
张献民:这位是想要自我审查吗?
苏七七:之前有一个问题是问女性主义是否有一些独特的构成元素、操作偏好和语言方法,可以作为这位听众的一个镜像问题。什么是该拍的,或者什么是不该拍的,我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不应该归纳女性主义的边界,更应该开发它的可能性。不管是影像的还是文字的作品,对于构成元素、操作偏好、语言方法,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和素养出发的,就可以做不同方向的探索。
如果女性主义纪录片都在一个范畴内,在相近的观念倾向下,你还是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我再举个例子,今年的创投有几个女导演的方案,比如郑陆心源的一个片子叫《错落斑驳的》,用艺术电影的语言来做纪录片。还有李柯靓的《生死一课》,讲的是亲人的过世,这就是张老师刚才说的第一人称的新影像的范畴。另外一个是吴越的《拳后妈妈》,是一部社会公共性很强、直面性别议题的影片。你看我随便举的几个例子,互相之间都完全不一样,各自在寻找可开拓的领域,而不是边界。
张献民:如果我再说一句的话,我是对自己进行自我审查的,所以我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一个责难。自我审查意味着这个审查只能自己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建议要给。
嘉宾 / 张献民 苏七七
编辑 / 宗辰
运营 / 实习生 吴雨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