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施展《破茧》:破除信息茧房的束缚,理性平和看世界
在施展看来,今年最大的关键词就是疫情,以及还有伴随疫情不断起飞的“黑天鹅”。
2019年,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写作《溢出》,并在今年除夕之夜出版。在出版前一天,武汉因疫情封城。在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夹击之下,施展对国家的现状和面临问题产生新的思考,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与朋友之间探讨产生的思想火花,逐渐完善并体系化后,集结成新书《破茧》出版。
施展提到,将新书命名为《破茧》有双重内涵:在大洗牌时代,一方面必须突破信息茧房对视野和格局的限制,否则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无法理解真实世界;另一方面,既有的治理秩序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现实,新的治理秩序也正待破茧而出。“破茧”一方面是对现实的诊断与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畅想与期待。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很多人都隐隐感觉到,很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与其哀叹怀旧,何不努力去创想更有前景的未来?”施展的研究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点,跨越学科与领域的界限。在《溢出》中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未来之后,在《破茧》他重点探讨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以及当今社会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时代的未来秩序做出探讨。

施展
美国撕裂,牵一发而动全球
澎湃新闻:今年的中美关系无疑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你在书中有一章写“美国力量的源头”,提到“美国人很难被惹急”,以珍珠港事件举例说明美国“一旦被惹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然而也有很多论调表示,特朗普在此前当选美国总统,表明美国社会如今的一种分裂。你觉得美国现在仍然如同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时候一样,可以被凝聚成一股力量吗?
施展:当然是这样。二战时美国被日本激怒,然后突然间爆发出巨大力量,这是书中我所举的例子。其实当时在被日本激怒之前,美国内部也很分裂,那时美国仍笼罩在大危机的影响之下。大危机本身已经使美国社会产生巨大的撕裂,而罗斯福当时用来应对大危机的那些政策,又被很多美国人视作对自己的自由权的侵犯,引发很多反对和质疑声音。
再换一个越战之中的例子。越战时期美国的撕裂比今天严重多了,当时黑人民权运动的规模、呼声以及人们对它的认可程度,我个人认为是要超过现在的。这种有着很强正当性的反抗力量,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强烈的撕裂效果,美国当时的撕裂比今天更严重,但是后果是怎样的?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时候,看上去苏联正是如日中天,美国却被内部撕裂折磨得奄奄一息。然而,那正是美国浴火蜕变、破茧成蝶的时刻,一系列伟大的创新、伟大的公司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奠定了嗣后美国发展的强劲基础,而苏联在十几年之后却急剧地衰落。
当下美国内部的撕裂并不是太过出人意料。任何国家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之后,内在秩序都会出现某些不均衡。因为制度是几十年前制定的,而几十年中社会秩序、结构、内在一系列财富分配等问题,不断在分化和变化。此前的秩序安排无法有效地应对新的这种社会变化,因此社会内部一定淤积了很多矛盾。有些政体弹性比较大,能够较好地适应这种矛盾的释放,重振起来的能力也就更强。有些政体的刚性比较强,从外观看来,矛盾的释放可能不那么激烈,但超越这些矛盾的过程也会更加漫长,由此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对于美国,目前撕裂的状况是释放矛盾的体现。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内在矛盾,只是美国的这种矛盾释放表现得更鲜明直接罢了。
澎湃新闻:今年的美国大选在从辩论到投票的过程当中,舆论的声音也是很摇摆不定的。在大选之前,你预料过是拜登胜选吗?
施展:这个结果我是没有预料到的。从上一次大选的经验来看,大选前的民调不一定能反映结果,所以我一直更加关注义乌指数,也就是义乌那边发出的两边应援产品如何“站边”,义乌指数显示川普具有压倒性优势,然而这次义乌指数也失灵了。我开玩笑说,现在就是历史的一个量子跃迁时期,义乌指数时灵时不灵,这也是测不准的一个表现吧。
二战后,美国一直是世界的“老大”,而且此前它做老大的姿势大致是确定的,人们认为无论谁当总统,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变化,美国大选的结果并不是影响世界秩序走向的关键变量,所以人们对美国大选的关注相对有限;但是在今天,美国虽然仍是老大,但是它做老大的姿势第一次变得非常不确定了,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会直接影响这一点,美国内政就此成为影响世界秩序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这对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很现实的影响,所以这一次的美国大选获得了各国前所未有的关注。
要想更有效地理解、把握这些问题,理性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当下社会太多人都困在信息茧房里的情况下,社会观念严重撕裂,理性的思考与讨论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我写《破茧》的初衷,是想分析中国,重回理性的前提,是搞清楚当下导致人们难以理性思考的原因,因此我在书中首先分析信息茧房的产生和突破的可能。人们在信息茧房中本来享受着各自的岁月静好,享受着被营造出来的一种虚假舒适,但是在公共事件的冲击之下,信息茧房的墙壁被不断击穿,人们被迫要面对让自己非常不快的问题,一肚子怨气没地方撒。于是就与观点不同的人剧烈争吵起来,轻社交时代人们的社交关系非常单一化,没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顾虑,也就没有节制自己释放情绪的动力,争吵就有可能不断升级,网络上戾气横生。疫情时期最能让人们撕起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际政治问题,我也是在这一系列思考的背景下,在《破茧》的第二部分花了较多笔墨来讨论,理解国际政治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论。国际政治远不仅仅是键盘政治家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那么简单、那么非黑即白,背后有一系列更加复杂深远的逻辑。
澎湃新闻:书中你有一节是专门探讨海洋领域的。你在书中是提到美国是海洋军事霸主,而中国在海洋领域主要优势是贸易,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施展:对于什么样的国家能成为海洋霸主,我们必须要分析具体的逻辑、条件、前提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不能光凭一厢情愿。
海洋霸主首先是军事霸主,但是海战和陆战有个重大区别,就是陆地上基于山川险阻,会形成各种拉锯战,最后各国基于山川险阻而划界,多雄并立;海上则没有山川险阻可以依凭,所以公海上的海战打起来就是歼灭战,海上是军事独霸的结构。
然而,对海上的军事霸主来说,如果把海洋完全封锁掉的话,并不是一个真正符合它利益的做法。开放海洋让所有人上来做贸易,军事霸主最大化地收租,这才是最符合它利益的做法。要想更好地收租,就必须提供基础的海洋安全和担保基本的海洋行为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在军事层面上是独霸的,在贸易层面又是自由的。
今天的海洋秩序和过去有个巨大区别。在过去,海洋的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通常是一个国家,这不是因为军事霸主垄断贸易,而是因为军事霸主的实体经济通常也是最强劲的,它在贸易上也就占有最大份额,这就有点类似于海洋霸主开了个大商场收租,同时自己在商场里还有个面积最大的商铺。但是今天,实体经济的最大份额转移到了中国,面积最大的商铺换主了,但是商场的大股东没换主,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分离了,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作为海洋军事霸主是很烧钱的,过去它可以通过贸易霸主的身份获得必要的财政能力,但是在这个身份分离出去之后,很多逻辑可能就会变了。
不过所谓的逻辑变了,并不是说贸易霸主应当去争做军事霸主。海洋军事霸主只有岛国才能做,因为它无需分出资源来投到陆地安全问题上去,海上投放资源的自由度是最大的,美国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就是个超级岛国。作为大陆国家,至少得分出一半资源去应对陆地问题,那就不可能在海上军备方面竞争得过海洋霸主。
这是我们必须理性分析的一个逻辑,不能用情绪替代理性。这也是我的书名《破茧》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得破除一些信息茧房对我们观念上的束缚,更加理性平和地去看待国际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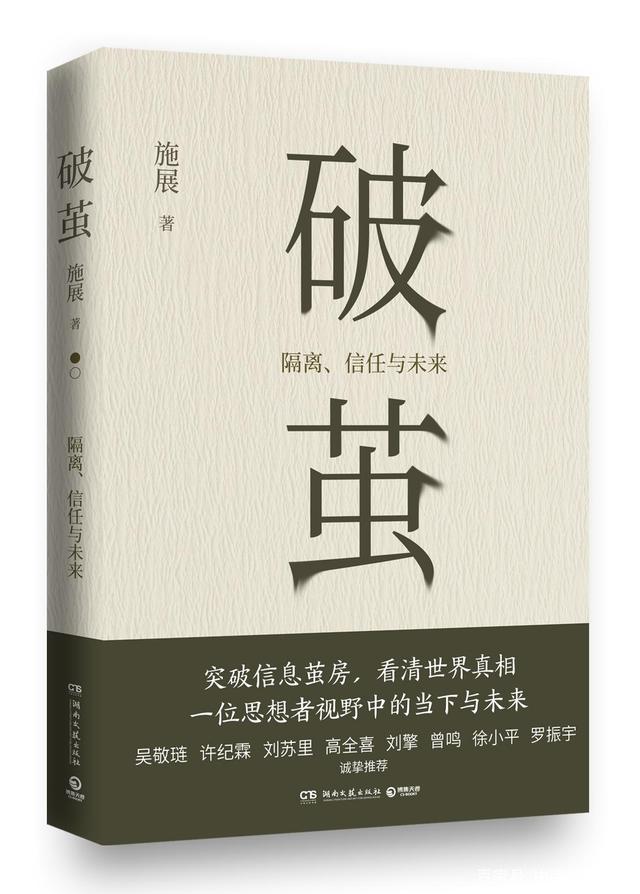
公共事件:击穿信息茧房的厚壁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的前两章也提到了信息茧房的问题,你是怎么定义“信息茧房”的?你觉得为什么当今社会信息茧房现象会如此严重?
施展:信息茧房的很大原因在于媒体传播方式跟过去有实质性的变化。过去人们共享物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而且公共媒体有着公共议题设定的功能。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流媒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的出现,过去那些共享的时间空间格局、公共议题设定的机制都不存在了。
推荐算法让人们只看到自己最喜欢的信息,人们在其中感到愉悦,有限的时间都被自己喜欢的内容占满,在一种心理舒适的状态中,觉得自己似乎在了解整个世界,但实际上陷在了信息茧房中而不自知。信息茧房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塑了,我不觉得我们会很容易地再回到10年前的状态。十年前网上对于社会话题也会有争吵,但那主要是为了说理,而今天的争吵只是为发泄。
情绪宣泄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我们仍然需要能够进行某种基于理性的争论。但这种争论的的可能性何在?过去是基于公共领域人们能够进行理性辩论,今天可能只有通过公共事件不断击穿信息茧房,击穿的次数多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会开始反思。
澎湃新闻:你说到公共事件可能会击穿信息茧房的墙壁,我有点好奇,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要去打开信息茧房,就只能依靠公共事件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恢复这样人与人之间公平的讨论?
施展:目前我觉得很难。因为推荐算法有点类似于精神鸦片,人们很难从中脱身。直到鸦片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浑身出毛病,人们才有可能会开始反思。哪怕鸦片已经危害到身体,再多抽点鸦片,可能就把毛病给掩盖住了,同时真正的疼痛也掩盖住了。还需要更多的公共事件,使得连精神鸦片也遮掩不住身上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反思才会开始。否则的话,就现在推荐算法的商业模式而言,能够击败精神鸦片的只有另一种更好的精神鸦片,我们是很难简单地回到过去的那种状态了。
澎湃新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就要适应这样一个信息茧房大量存在的社会?
施展:倒也不一定这么悲观。信息茧房的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黑天鹅会频繁地起飞,在这种历史的量子跃迁期,一切都测不准。可能当下看似很严重的事件,两个月之后烟消云散;可能当下毫不起眼的小事,三个月之后演变成滔天大祸,一切都有可能。
如果黑天鹅频飞状态持续几年,很多人都被迫不得不从信息茧房里面抬头来看一看怎么回事,也许到时候新的公共讨论机制会出现。具体形态会是什么样,现在我还想不清楚,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

新汉萨同盟:重建全球数字经济秩序
澎湃新闻:《破茧》延续了《溢出》中提到的“新汉萨同盟”的设想,并且介绍得更加全面和完整。 新汉萨同盟以商人为秩序,颠覆了很多人的观点。这样的设想,在落地时是不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呢?
施展:肯定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我个人觉得它不会简单地就此停止推进,因为新汉萨同盟是基于对现实秩序演化的一些具体观察。从我的观察来看,数字经济早已穿透国界,实际上不仅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也已经是高度地在穿透国界运转了,这在《溢出》当中有很多讨论。过去以国家为单位来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已经无法应对新的经济模式了。这就意味着,在真实的经济运转过程中,商人们处在一种规范缺失的状态。
规范缺失,在某种意义上对商人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差异来进行套利。但从长远来看,规范缺失对商人们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任何收获都无法在法律规则下被确定下来,是不稳定的。所以,商人们会内在地形成一种需求,希望能有一种超国家空间的治理机制。
关于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只能去做一些大胆的想象,不过这样一个需求已经是隐隐浮现出来了。在需求浮现的时候,这种对于未来秩序的想象就是有价值的。我在书里举了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例子。在拿破仑战争时,德国还不统一,境内是几百个小邦国,这些小邦国各自的经济非常之脆弱,一方面无法应对法国的外部挑战,另一方面要想发展经济进行工业革命,由于市场太过狭小,也都没有机会。李斯特意识到小邦以及其中的工业家是有建立一个更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的,但是这个需求还没有被人们明确地意识到和表达出来。于是李斯特主张要推动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他把这些需求明确表达出来,并不断地呼吁、推动,人们逐渐对问题形成共识,之后就能想办法共同实现。到了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终于现实地落地了。
同样,我认为新汉萨同盟会成为21世纪下半叶的一种可能秩序,因为它不是基于我的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一种现实的需求,只是该如何满足这种需求,现在还说不清楚。我在《破茧》中开了一些比较大的脑洞,对于这个需求究竟是什么,它又该如何现实化,构想出了一种粗糙的可能路径。粗糙没关系,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只要人们在这方面的观念和想象被激活了,就有可能引导通向未来的基础,就像当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一样。
历史上人类尝试以国家为主导,来笼罩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空间,仅仅是法国大革命之后200多年的情形。但这种尝试并不能真正地让各种空间都被政治所笼罩,只不过人们会在观念上如此想象而已,我在书中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封装式思维”,用政治来封装一切。在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等等,都是各自处在不同的次元里面,各有各的空间结构,各有各的层面逻辑。人类历史一直都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也不会尝试用政治去封装一切。只不过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200多年里,人们会形成那种“封装式”的观念。今天我们经常会觉得这种“封装”是理所当然的,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刚好就生活在这200年里,我们的观念是被这200年所塑造的,但这200年的经验当然不能穷尽人类的可能性。

站在长城看中国
澎湃新闻:在《溢出》出版时,你提过可能会对丝绸之路地域做一些调研,疫情阻止了你的调研吗?
施展:没有,我一直坚持在做。 不仅仅是丝绸之路,是整个中国的走廊地带。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通常都把中国史等同于中原史,但实际上中国是一个远远超越中原的概念,它是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等多个板块共同组成的一个大的体系,所谓的中国史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联结众多板块的重要地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走廊地带。所以要是从体系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史的话,长安、洛阳都不是最好的中心视角,真正的中心视角应该是走廊地带。就像过去从中原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但这种说法非常成问题,因为如果长城是中国北部边界,那就意味着长城以外那就不是中国地盘了,这是很荒唐的。
所以从一个真正的中国视角来看,长城不应该是北部边界,相反,长城才应该是中心。站在长城上面向大海方向,右手农耕左手游牧,背后是西域和高原,此时看到的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中国,否则的话看到的仅仅是中原。中原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恰恰是在它和草原、西域、高原不断的互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以走廊地带为中心切入视角,尝试重构一种对于中国的解释框架。我这几年做的这方面的调研,也是想从宏观微观、各种角度来把这种新的解读框架落实。
实际上在《枢纽》里面,我已经建立起了大的框架,现在想在微观层面把它进一步地坐实。所以我这几年不停地在各种走廊地带调研、行走。这个研究跟我在《溢出》和《破茧》里做的研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得看到它对内对外两个面向。对内:研究多元中国的多个板块之间如何“多元互构”,多条走廊之间如何“多廊联动”,从而历史性地演化出今天的中国;对外:要梳理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构关系,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这两个方面结合,才能够共同构成我们对于“何为中国”的理解和解释。
澎湃新闻:你最近新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施展:未来我会从走廊角度入手,进一步的把中国的“多元互构”,即中原、草原、西域、高原这几个板块“多廊联动”的逻辑说清楚。基于此,我才能找到中国在内部该如何实现整合的基本历史前提,这可能是我未来几年会花许多精力的写作方向。同时我仍然会关注中国和国际间的关系,以及数字新秩序对人类的可能意义。就像我刚才所说,内外始终是联动的,不可能脱离开其中一方来说另一方;技术则对内外联动的逻辑提供了新变量,可能会推动联动逻辑的一些变化。对我来说,这些关注始终是一个同步进行的状态,可能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