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被猎杀的“杀马特”:只因贫穷是“原罪”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看理想

非主流、火星文、杀马特……这些词语是否也出现在你的年少回忆里?
80、90后一代,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将夹杂着各类字符的“火星文”、“非主流”视觉系图片等视为前卫和酷炫的象征;一段时间后果断将之抛弃,并视为某种黑历史。
再提及火星文和非主流,我们更多变成了自嘲、玩梗和消解,用以调侃和缅怀。但顶着一头艳丽的头发,被视为非主流的“杀马特”们却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消失在互联网中。
随着2013年前后针对杀马特的调侃、报道甚至“网络出征”等事件,他们逐渐在网络上沉寂,成为了历史。

直到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出现,才从另一个视角提醒了我们。原来被很多人弃之如敝屣的“黑历史”,却是另一些人的精神支柱;原来当年自以为是玩梗、嘲笑甚至“正义”的网络风潮,竟然对他们造成了想象不到的巨大伤害。
更重要的是,这次对于“杀马特”的讨论和梳理,让我们去反思,到底“杀马特”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何我们对他们曾经视而不见?我们对于贫困又到底有着怎样不自知的歧视?
01.
发型是自己唯一可以主宰的东西
“有时候感觉这个头发给了你一种勇气。而且在大家印象中这就是坏孩子,坏孩子感觉就是不会被欺负。有时候自己会也想成为一个坏孩子。”
“想通过穿着打扮来发泄,弄得吸引人。让他们感觉想跟你交朋友,感觉你很独特。就算别人骂自己两句也有人跟自己说话啊,只要有人愿意跟自己说话,无所谓啊。”
“头发让人觉得,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个性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一开场,没有想象中的强视觉冲击的画面和以人物视角切入的主线故事,只有一个个曾经的杀马特,平视着镜头讲述着各自迥异又相似的经历。
他们全都是90后农村乡镇务工人员,多是农民工二代,有着留守儿童经历。绝大部分人中小学就已辍学,初次进厂打工平均年龄在14岁左右。

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安晓蕙(网名)到广东打工时才12岁,还扎着两个小鬏鬏。每天打几千上万个螺丝到凌晨一两点,赶工时要做到第二天早上5点,趴着睡五分钟再继续做。
不久安晓蕙发现,把她们从家乡带到广东、所谓介绍工作的远方亲戚每个月都从他们的工资中抽成。她拿那些被克扣剩下的微薄工资把头发染色、做了杀马特发型,从第一家工厂逃了出来,投靠在另一家厂里做工的堂姐,两人一起玩起了杀马特。
大工厂对工人的头发是有要求的,尤其在2013年以后,随着舆论的恶化,不能奇装异服、不能染发烫发是明面上的规定。
安晓蕙不愿放弃自己的发型,饿着肚子也要玩杀马特,对着镜头,她笑呵呵地讲出了那些又好笑又心酸的往事:有一次她饿得不行,就盯着一个路边卖甘蔗的摊子,甘蔗摊老板看见杀马特打扮的她盯着自己,便十分警惕,以为要做些什么。结果安晓蕙只是捡起削甘蔗剩下的又老又硬没有人吃的头部,拔腿就跑,甘蔗摊主先是一愣,随后捧腹大笑。
还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位小弟弟向她搭讪,夸奖说姐姐你的头发好酷啊,她便说,能不能给我们买几个馒头,弟弟说怪不得杀马特们都这么瘦,原来是因为你们都爱吃馒头。在“骗”小弟弟给自己买了10个馒头后,安晓蕙就靠着这些度过了一周。
吃不饱,是许多杀马特都曾有过的经历,另一位男孩,说他靠着一碗方便面吃了两天,吃不完的面放到冰箱,第二天接着吃。
“连饭都吃不饱也要玩杀马特”,如果光看这句话,许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甚至会有些鄙夷。但如果了解了杀马特们的真实生活,或许也就理解了他们的选择。

纪录片的许多镜头,是三个竖着的手机拍摄影像拼接而成的画面,里面是一段段类似的工厂生活——这都是导演李一凡从杀马特们手中买来的真实生活片段。
大批务工人员拖着行李箱、排着长队,像菜市场里被挑选的蔬菜一般,被招工的人呼来喝去的训斥着;剩下的则是枯燥的流水线生活、杂乱的生产车间,杀马特们或流利而机械地操控着机器,或累得睡倒在台子上。
不愿放弃发型的杀马特们,基本只剩下几条出路:规矩少的小厂、发廊、酒吧舞厅、快手抖音,或者回农村种地。
从山区来的杀马特小孩们,在第一次接触这种打工环境时,被骗和被抢都是常有的事,更别提来自工厂老板的压榨和克扣。
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流水线工作,连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被规定得死死的,有的地方连上厕所都需要向经理审批,迟到和做错被扣钱都是常态。杀马特们工作的地方大都是小厂,工资常常被作为押金抵扣。例如一位杀马特半年8千多的工钱,被七扣八扣后竟然只剩下20块。
这样的劳动者在社会学中被称为“常规劳动者”,他们的临时性和可替换性都很强、往往被用完即弃。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难提供足够的的安全感,这里的人际关系也本就不牢固,而工厂为了防止他们集结起来,还往往会把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打散。在这样的生活里,压抑、无助和孤独成为了常态。
一些不花费什么成本的刺激和快乐,就可以让他们忘记现实生活中的艰难不易,摆脱心理上的孤独和焦虑。在城市发展前进的洪流里,他们的身份微小,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更像是一粒小小的灰尘,微不足道。
在这台枯燥运转的工厂大机器里,在城市发展前进的洪流里,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杀马特只是一粒小小的灰尘。
不用花费太多成本的发型和造型,便成为了许多杀马特仍然留有一丝丝“人味”的存在,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主宰或者改变的东西,是他们自我价值的一种确认形式,也是许多人的保护色和坚硬的外壳。
《杀马特我爱你》里有一个“大场面”,一年一度的东莞石排镇公园的杀马特大聚会又来了。对于习惯了影视套路的我们来说,这可能是想象中惊心动魄的高潮。

在纪录片里,明媚的阳光下,头顶着各式发型的杀马特们,只是站在棕榈树、草坪、人工湖旁——在再普通不过的公园里,三两成群,说说笑笑,普普通通地在那里聊着天、压着马路。
这个看似普通的镜头,却揭示了杀马特们的命运:一年一度的大聚会,是因为杀马特们大都是小工厂里做着没日没夜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十一是他们少有的假期;杀马特们经常被工厂克扣工资,吃了上顿没下顿,别提精致的野餐了,就连正常吃饱也会有些困难。大聚会,也只是他们在望不到头的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喘气窗口。
02.
真正的杀马特不会“自黑”
在后来的采访里,《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经常会提及,最初想拍摄杀马特纪录片时,他根本联系不上任何一个杀马特。
直到后来联系上了被许多媒体报道过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但后者也依然十分谨慎,在李一凡反复联络之后才勉强打消疑心。被称为“教父”的罗福兴,并非作为纪录片的主角,更多则是帮忙联络和劝说曾经的杀马特们接受采访。
但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李一凡回忆,有一次他们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个杀马特,在走了两小时抵达一个偏远的工业区后,那个人非说他们是“同城代打”(帮忙上门打人的人),打死不见。这在拍片过程中是常有的事情。
还记得近十年前对于杀马特们的调侃、恶搞和嘲讽吗?或许我们都经历过这一网络风潮,但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在愈演愈烈的网络风潮之下,多少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做着恶意之举,也可能没有想过,当这些恶意落在每一个真实的杀马特身上时,究竟有多么可怕。

2011年,出道时曾作视觉系装扮的花儿乐队原主唱,在微博上传了一张“杀马特”造型图片,并揶揄其为“农转非”——农村孩子转非主流(“农转非”原指城市化后农村户口迁出,因而这一说法带有双重恶意)。
虽然名为愚人节玩笑,但这一行为代表着当时的某种界限划分,原本自诩来源于“高级文化”的视觉系玩家、曾经以非主流和火星文为潮流的网友们,甚至也包括曾经的杀马特玩家,都与这些“农村杀马特”正式割席了。
许多人卖力发掘着杀马特与其他“亚文化”的不同,并仔细梳理杀马特的起源,视为对某种亚文化的拙劣模仿。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教授滕威曾撰文指出,对杀马特的排挤,也并非权威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鄙夷,也有许多是月收入五千以下的人群内部的相互倾轧。[3]
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区隔”(Distinction)概念来说,层层区隔,不断于内部划分出他者,不断在“我们”中指认出穷人,才能建构起社会的安全感与秩序感。
只有不断地嘲笑用国产杂牌手机、抽劣质香烟、穿地摊服饰、听口水歌的“杀马特”,人们才能刷出自己一丝的存在感。
而这种鄙夷和厌恶,甚至成为了某种思维定式,延续至今。为什么要大篇幅地描述杀马特们的工厂经历,正是因为了解了他们的处境,才会理解他们为何会追捧这种外形,又为何会形成一个个“家族”,才更能理解对杀马特们的喊打喊杀意味着什么。
杀马特们其实对自己的处境清楚得很,在工厂里面,他们只能默默无闻生活着,不会有一丝上升的机会。更高职位的工作跟自己无关,工资是计算得出来的,罗福兴说,他甚至很多时候不敢看城市里的高楼,因为那“跟自己永远无关”。
于是,他们干脆选择了另外一种渠道,在杀马特的世界里,他们可以组成为家族,也可以“上升”成为贵族。“只要是玩杀马特,都是我的家人”,“它是一个信仰,支持着我,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我很开心。”
因为渴望“被看见”,所以他们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来自“家人们”的点赞、转发或是打赏,是他们平行世界里所能找到的重视和温暖,从而达成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杀马特的精神世界,就在这种焦虑麻痹和渴望“被看见”的交织中,每天周而复始。
对于他们来说,发型是确认彼此是同类的一种象征,而家族群,则往往是他们在贫乏的生活中唯一有些亮光的交流之地。这种心情,跟我们在网络上因为一个小众的亚文化,便确认对方是自己“同好”的心情并无两样。
在2010年前后,杀马特家族开始被主流论坛所关注,有人伪装成杀马特发帖挑衅论坛用户,并引来仇恨;有人靠着网上偷来的照片信息潜伏进入家族群,成为管理员后将群解散;杀马特的贴吧也很快便被李毅吧吧友所占领,并删除了大量的帖子。
而在网络上游走的杀马特们,因为头像和ID就遭受了一场大型猎巫。纪录片里有人回忆,当时有人因为他是杀马特,就专门弄了骂人软件来骂他,每0.1秒刷新的一条骂人信息,很快就把他的手机刷到发热卡死,而杀马特们哪里买得起昂贵的好手机呢?
除了网络交流的唯一窗口被破坏了,现实中的杀马特们也遭受到诸多恶意。一位杀马特回忆,他有个朋友只是正常在路上走着,就被人摁在地上,把一头的头发给烧光了。
看过纪录片,便会知道杀马特们对于自己的头发有多珍爱,比如两个“家族”要打架时,先约定好:不许抓彼此的头发。又比如,为了保留自己一头眩目的头发,宁愿放弃待遇好的大工厂,也要去一个能容忍这样发型的小工厂。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样的事情现在仍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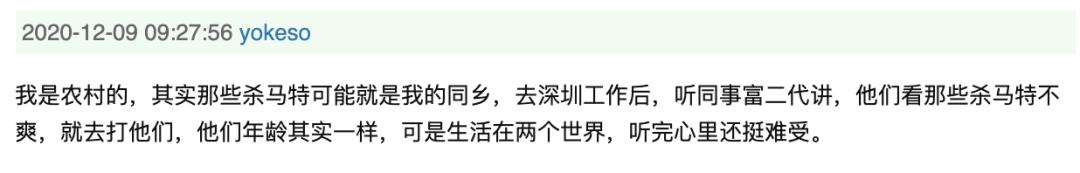
豆瓣网友@yokeso 在《杀马特我爱你》的评论区里留言
后来,杀马特们为了抵抗骚扰,大都默默将qq空间上锁,交流起来更加小心翼翼。安晓蕙描述了自己被迫剪掉头发的过程:“第一次剪长头发,心里很苦,感觉自己的自尊都被剪掉了”,“这就像一个明星变成了一个过气明星的过程”。
在纪录片里,另一位曾经的杀马特李雪松平静地对着镜头,说出了他们心中的痛楚:“以前玩杀马特,我们只是想在网上找到一片净土。甚至不需要你们认可,我们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行,这样都不可以吗?”
2014年之后,再在网上搜索“杀马特”“葬爱家族”,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杀马特家族群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恶搞的群,许多游戏公会也以此起名,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假的,但没人在意。
在大型猎巫之后,“杀马特”这一带着暗号式的身份认同符号,成为了大家用以调侃、自黑的玩梗,在一段时间腻味之后又果断抛弃。却全然不觉,这一身份可能是另一些人生活中唯一喘气的窗口,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因而《杀马特我爱你》描述,杀马特中有一句名言,“真正的杀马特不会‘自黑’”。
03.
“他们连保护自己都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
2012年,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时,李一凡非常兴奋。虽不同于当时社会的普遍鄙夷,他认为这是底层嬉皮士的审美自觉,通过自我糟践来抵抗时代景观。
在深度接触和采访之后,李一凡对自己想当然的评判做出了反思,即使是用“朋克”这个看似中性的词语来评判杀马特,但这背后的内核其实也是大不一样的。
“朋克”是西方进入消费社会后,工人阶级们对于“狗屁品牌”的反抗,但杀马特却是从“农耕文明里出来的”,用消费符号来“消解工业社会对他身体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杀马特是90后农民工对都市消费行为的简单模仿,似乎只是城里人的傲慢想象,将他们与土地割裂、从工厂抽离。
“我以为的(杀马特)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李一凡说道。
知乎上一个高赞回答写着“他们是穷丑却自我感觉良好的loser”,代表了曾经评价杀马特的主流声音。事实上,杀马特们的穷困早就被人所知,但这似乎却变成了他们的某种原罪。
2014年,大热的动画视频《飞碟说:杀马特青年的忧伤》便仔细拆解了杀马特的成因。动画一开场,便是一名杀马特忧伤的背影,他站在铁丝网制成、仿佛牢笼一般的工厂大门前。

《飞碟说:杀马特青年的忧伤》
然而当他转过来脸来,除了标志性的头发和破旧的衣服,动画还特地给他画了两个巨大的鼻孔——这更是一种夹杂着地域和外貌歧视的刻板印象。
“杀马特穿地摊货/吃路边摊/护着黑丝袜粉安踏的乡村步行街名媛/一部国产二手杂牌手机行走江湖/卡擦一下放到QQ相册里…
杀马特是21世纪的新闰土/低下的教育/微薄的收入/残酷的生存环境/逼仄的上升渠道,他们不能/也不想在文化方面提升自我…
杀马特明明很穷/却非要打扮成潮男靓女的样子/这跟小白领拼了命要买个LV包一个性质/过度的装饰/其实是希望提升品味、层次…”
2010年,一份对于90后农民工的调查报告中指出,90后农民工对于土地和农村的依恋减少,进城打工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难以接受被歧视,已经具有了某些朴素但盲目的平等观念。
但在许多语境下,这种描述转变为,90后农民工没有了父辈农民工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无法持续干高强度的重活。他们被认为“不努力,还要追求有的没的”,这暗含着一种歧视:穷人就应该规规矩矩赚钱,他们不配拥有精神追求。
旅美学者赵思甜曾撰文指出,悲哀的是,当城市中产阶级“玩剩下”的生活方式、文化元素开始被低收入群体模仿的时候,往往还会招来城市中产阶级的无情嘲笑、被斥为“低俗”(例如“农村重金属”的音乐品味和“洗剪吹”“杀马特”的造型风格)。
但许多文化符号,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美学价值。它究竟是“高雅”还是“低俗”、“无可厚非”还是“不可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文化符号由谁表达、由谁评判。当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是低收入群体、社会边缘群体时,其中的种种元素更有可能被城市中产阶级贴上“低俗”、“不堪入目”的标签,甚至上升到“社会问题”和“病态”的高度。
这里体现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在审美领域的双重标准和阶级之间话语权的严重不平等。[4]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提出过著名的“新穷人”(new poor)概念,“穷人如何成为穷人,如何被视为穷人,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和被视为穷人,取决于我们——这些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赞许和反对这种生活”。[6]
在这样的定义里,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不只是“失业者”: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消费社会最重要的责任——消费,ta就是一个穷人,一个没有存在意义的人。
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是“零容忍”,不仅通过各种物质手段将他们驱逐,让他们的身影从眼前消失,更通过持续不断地书写、命名等文化手段,将他们描写成无知、愚昧、粗俗、堕落甚至邪恶的群体,从而在精神上隔离他们。
这种“污名化”的策略,使得消费社会的新穷人不再有道德,也不再值得同情。这也正是许多人对杀马特们进行着广泛的歧视、鄙夷甚至伤害,却又要行驶着“反对低俗”的正义之名的原因。
参考资料
1.《可是没有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李一凡,一席第814位讲者
2.《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张淼,the Initium Media
3.《“杀马特”:另一种穷人的困境》,滕威,《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0165期
4.《<残酷底层物语>疯传的城乡阶级想像》,赵思甜,the Initium Media
5.《荒原上的杀马特 | 封面人物》,邱苑婷,南方人物周刊
6.《工作、消费、新穷人》,齐格蒙特·鲍曼
图:《杀马特我爱你》、李一凡
撰文:苏小七
监制:猫爷
原标题:《被猎杀的“杀马特”:只因贫穷是“原罪”》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