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朱嘉明、何怀宏谈《亚当·斯密传》:在焦虑时代重遇启蒙
3月19日晚,经济学教授朱嘉明和哲学教授何怀宏在单向空间·大悦城店,结合《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这本书,畅谈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易被误解的世界里,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以及如何借鉴斯密的思想以应对这个人人焦虑的时代。本文为对谈内容的节选。

活动现场。
主持人:提到亚当·斯密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他被冠以“经济学之父”的殊荣,即使大家并不了解他的生平,也很少有人没听说过这几个词: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与其相关的著作及研究汗牛充栋。不管我们是否认可,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亚当·斯密建造的理论体系所影响,因为关于市场的思维和逻辑深入每个现代的毛孔,是亚当·斯密让我们注意到市场的经济价值哺育并提升了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我们今天对亚当·斯密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他经济学家的身份,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亚当·斯密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在《国富论》的光环之下,我们往往忽略了他其他的著作,比如说《道德情操论》《法理学讲义》,还有他终其一生尝试建构的人的科学。
过去一年,我们每个普通人都遭遇了不同以往的困难。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遭遇了更加严重的挑战,并且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到:“所谓发达国家对现在的全球化没有答案,因为他们没有超越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界限。我们没有见到历史的终结,思想却反而走向终结。”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思想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两位老师一起跟我们聊聊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
朱嘉明:亚当·斯密是1723年出生,1790年去世,1723年和中国有什么关系?给大家一个想象场景,1723年是雍正继位。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对应的是中国的清朝雍正、乾隆年代。 回到今天的主题,“在焦虑时代重遇启蒙”。亚当·斯密在1759年35岁时写了《道德情操论》,之后又写了《国富论》,那么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不是焦虑时代?在我看来,那也是一个焦虑时代。1789年,也就是在亚当·斯密死的前一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大革命是社会焦虑的极端反应,不焦虑怎么会革命呢?在这之前,大西洋彼岸还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焦虑特征,在这样的焦虑状态下,才有在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在讲理性,讲人如何摆脱被各种各样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来解决在焦虑时代所有的困境。
从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一直到发表《国富论》,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多次修改,这反映了他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他遵循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状态和经济特征。后面我们还会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亚当·斯密有那么多的误解,为什么这个误解在中国显得那么严重,造成了值得重视的后果。
何怀宏:在今天这个时代回顾200多年前,当时开启的一个时代对我们今天的时代造成了深刻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亚当·斯密。我很怀念,也很喜欢、欣赏那个时代,只要看看亚当·斯密的通信集,就可以了解到:在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当时激烈的战争与社会动荡很少,经济贸易发展得很好,知识分子的交流很密切。尤其是18世纪的苏格兰还发生了启蒙运动,包括亚当·斯密、休谟、哈奇森、弗格森等一批人。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其中又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苏格兰有足够的和平与安宁,像休谟这样的学者也有足够的财富。比如说休谟很早就写了《人性论》,但是出版、发行不是很理想,他后来就写散文、写历史,通过出版作品积累了不少财富。再后面有人找他说,你再写本书吧,他幽默地拒绝道,“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有钱了”。在那个时代,休谟和亚当·斯密结下了友谊,休谟的哲学对亚当·斯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充满希望的,也比较单纯。有一点像我们的八十年代。
到今天这样的时代,流弊开始出现,希望也许多变成失望。当今的中国人有很多焦虑,这些焦虑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说启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反省这些问题。而亚当·斯密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传》这本书,我感觉它中规中矩,它肯定了亚当·斯密提到的商业社会市场,这是它的中心议题,但也论及了另外的方面,比如说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是否应站在富人一边,还有平等的问题。亚当·斯密的问题还与他的两本书有关。有人说,亚当·斯密左手拿着《国富论》,右手拿着《道德情操论》,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它们看起来很不一样。这两本书是冲突的吗?是分离的吗?
我觉得并不冲突,但可能有一些分离。它们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不互相支持,两书之间很少交叉引用。《道德情操论》不是想为商业社会建立一个道德基础。而《国富论》也不多讨论道德问题,它们是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很有思想价值。而且因为这两本书是交替进行修改的,如果它们是冲突的,亚当·斯密肯定要在修改中要努力弥合这种冲突,而事实上并没有,两本书各走各的路线。《道德情操论》出了6版,在亚当·斯密去世的那一年出了第6版,《国富论》出了5版。这是分别展开的两个领域。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一是亚当·斯密本人更看重哪一本书?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国富论》产生的影响远比《道德情操论》要大?
第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他本人可能更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却没有《国富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当然有时代的原因,因为在后面200多年,很明显的,各个文明社会都越来越以经济为中心,大家关注的、追求的是经济、物质、财富。这是一个时代的原因,但是也有本身思想的原因。《道德情操论》是从人的情感出发的,凡是情感都会讨论。你可以说《道德情操论》多了一点,也少了一点。多了一点是什么呢?虽然是《道德情操论》,但是里面不全是单纯的道德情感,包括愤怒、抱怨在内,各种各样的情感都有,还包括共鸣、共乐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同情,亚当·斯密也承认,同情最初的含义是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同情的指向是积极的——关心别人,但是内容是负面的——主要是关心别人的痛苦。由此来引发行动,所以如果加上同乐等等,不纯粹是道德感情、道德情操,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可能就多了一点。少了一点就是说,我们除了同情心,还有同理心。同理心就是强调道德的理性。那么这恰恰是做得不够的地方。当然这本书不是完全没有弹性的,比如说亚当·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的概念,这里是包含理性的,即设身处地,假设你是第三者,是利益无关方,你怎么去看待别人遇到痛苦。亚当·斯密终身未婚,但是他对各种感情非常细腻和敏感,而且不脱离健全的常识,我们去读读那些书就会有很多体会。
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在生活中体会到类似的境况和情感?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问题,在道德、伦理学上,亚当·斯密的影响为什么不如比他晚一年出生的康德。康德提出三大批判,当然还有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还有法学等,影响加起来就比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大,康德强调的是理性。比如说著名的普遍立法,也就是说,你做任何行动,或者不做行动,都要考虑到你的行为准则是否能够成为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做的普遍原则,这是一个很理性的提法。另外康德抓住了现代伦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现代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传统伦理学,无论是儒家还是古希腊,都是在讲怎么做人,以人为中心,成为一个正义的人,甚至高尚的人,这是完整的、全面的,它包括情感、直觉、意志、理性,即我怎么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全面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到了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每个人对好、善,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意见不一致。而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你很难说谁是善、谁是恶,甚至谁高谁低,因为价值平等,也就是多元。在这个问题上很难统一,因为绝对的统一变成了一个不对的东西,但这个社会要存在,还是要有道德基础,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就在于行为。你影响到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到底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所以康德的理论集中到行为规范的正当与否上,而不是价值第一,或者情感丰富与否、充沛与否、合宜与否,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伦理学走向平等、多元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行为,就是道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
这个时候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就显得有些不足了,因为情感很难成为这种判断的根据和标准。情感本身就易变,包括我们最赞赏的情感,比如说对他人痛苦的同情、怜悯、侧隐之心,我们觉得肯定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理性的引导和调节,那肯定也容易犯错,或者过度,或者不足,或者是陷入一种选择两难的困境。究竟是应当同情自己身边人的痛苦呢?还是要关注全人类的、远方的、非洲的,甚至还有动物的痛苦,这类问题你就会碰到很多,它本身很难取得标准。所以我觉得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可以处理为道德动力的源头,也就是像孟子所说的端、发端。如果我们没有同情心,即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我们可能也没有动力去做。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头,但是它本身不足以成为标准,不足以成为我们基于判断道德对错的根据和标准,我们还需要另外的标准,需要更明确的规范。理性的、普遍的,当然也是底线的规则和标准,我觉得这一点是从《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自身的原因谈起,亚当·斯密不足以像康德这样,成为现代伦理学之父或者说主要奠基者的关键。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更多是描述性的,这个描述非常生动、充实、具体,但是也存在不足。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想法。
接下来谈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有他其他的一些思想。可以从分工开始谈。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来源,财富怎么来的,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怎么来的呢?亚当·斯密认为主要是来自分工。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做一个钉子,从头到尾一个人做,他一天可能做不了几颗钉子。但是通过分工,产量就能大大提高。但是我们生产钉子,却不能吃钉子呀?所以必须要交换,斯密认为人也有这样一个天性,他愿意去交换,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分工交换,或者分工合作,人类文明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农业文明的分工还不特别明显,那么工业文明的分工就非常细致和明显了。
一谈到分工,大家也会想起《理想国》,《理想国》也是谈分工。苏格拉底也讨论一个城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个城邦最少需要几个人?比如,需要种粮食的吧,需要盖房子的吧,还有需要做衣服的吧。人数慢慢增加,其中就产生了分工。通过分工合作,然后建立起一个城邦。但是更重要的,《理想国》的整个政治哲学可能都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社会的三大阶层是什么?人数最多的那个阶层,就是手艺人、商人、农民等。比他们更高的阶层是武士,捍卫城邦。最高的阶层就是哲学王。这也可以对应于人的内部,每个人有三种本能或者所灵魂的部分。一是欲望,没有欲望不能生存;二是意志,或者说激情;三是理性、智慧。这三个是并列的呢?还是处在差别当中,一个要服从另外一个呢?就像个人应当用智慧和理性来节制欲望,社会也可以考虑处在这样一个等级的次序中,这样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优良的,这种分工是从政治学意义上的分工。《理想国》后面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就是如果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特性、长处,能把什么事都干得最好的话,那么为何不让他们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各得其所,不互相僭越,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亚当·斯密讨论的分工是在经济学上,没有这种分工将无法合作,也无法创造出财富了。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看不见的手”,斯密在三个地方谈到了,天文学史中的讨论可以不管它,在《国富论》谈了一次,《道德情操论》谈了一次。在《国富论》中,斯密是从生产角度谈的,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他并不是抱着为客户谋利益、谋幸福来生产。他更多考虑我要谋生,我要致富。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平台、制度的规范,这也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也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如果有好的制度平台,自然而然,各种各样自利的动机,产生的行为,会自动有助于公益事业。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谈的,我们觉得大地主好像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奢华也给制造奢侈品的人,服务他的人带来了很多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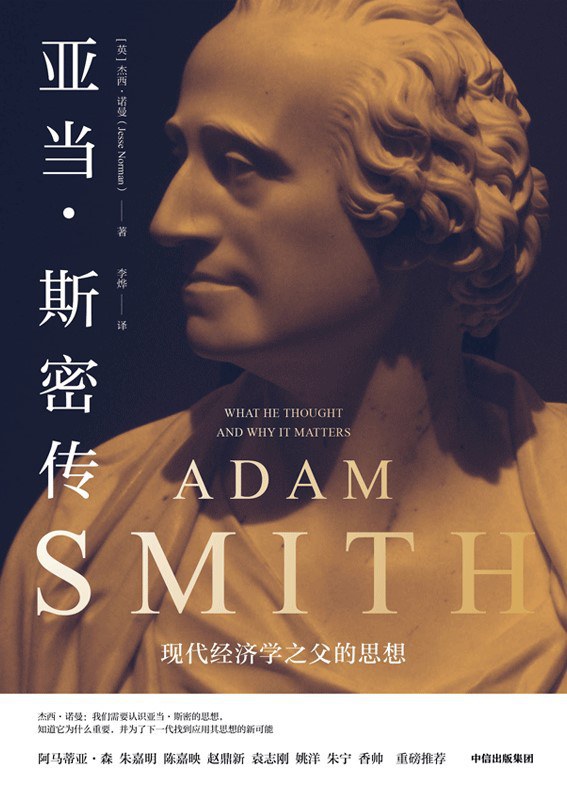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英] 杰西·诺曼 著,李烨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
主持人:我们一直有这种疑惑,也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关于“两个斯密”的问题。一个斯密是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倡导私利与自由,另一个是以《道德情操论》为代表的,重视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道德观念。为什么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大行其道,被我们推到非常高的位置,而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的理念,在今天处于边缘。
朱嘉明:我想说首先亚当·斯密和康德是不可比的。首先因为亚当·斯密被定义为经济学家,而康德被定义为哲学家,康德没有染指经济学,而亚当·斯密靠哲学起家。然后我们也看到两个人都讨论了法律问题。亚当·斯密对法律问题的理解显而易见比康德更接近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康德和亚当·斯密简单地比较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在我看来是不公平的。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由一个三角形构成的。这个三角形首先是道德情操论,第二是经济学,第三是法学。人们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伟大思想家的印象,常常以他最突出的成就作为标准。但事实上,他没被关注的东西,甚至比其他同行更加了不起,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和一个《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我们要讨论他是怎么样交叉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怎样讨论经济问题,他在《国富论》里面怎样讨论道德情操的问题,这是我和何教授分歧的地方。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最痛恨的是谁?就是奢侈品。因为他批判的是曼德维尔所写的《蜜蜂的寓言》。他发表第一本小册子的时候是1712年,正式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1720年。也就是说在这本书影响英国的时候,亚当·斯密还没有出生。但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蜜蜂的寓言》做了极为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评,曼德维尔讨论的是一种恶德是否可以被视为公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曼德维尔的书中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有一个蜜蜂的王国,国王是大坏蛋,其他的蜜蜂也都是大坏蛋,每个人都贪婪、自私、卑鄙无耻,每个人都在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蜜蜂王国繁荣昌盛。后来有一天国王良心发现,说这样不行,我们现在要讲讲道德,我们要讲讲所谓的节俭,我们要讲讲所谓的朴素,于是大家都要压抑自己的贪婪,于是这个蜜蜂王国就崩溃了,从繁荣走向箫条,从箫条走向衰落。这个结论在当时的英国是争论不休的,大家在想这样的一个悖论,即恶德能导致公益的结果。是不是因为私人的恶德能导致公益的结果,就承认恶德。
首先我把我的立场告诉大家,我不认为恶德可以造成公益。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对贪婪、自私、无耻来实现构成客观上的繁荣,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成本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只有参加恶德的游戏,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呢?道德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很难衡量出来,是没有办法计量的,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亚当·斯密对所有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他对恶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认恶德的集合,他不承认恶德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正义和公益的后果。这是本质问题。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他是怎么来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最大的分工,不是《理想国》的分工,因为理想国是一个太小的事业,人类最大的分工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这个也是理性,即所谓康德讨论的问题。康德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他讨论的是,人是唯一能够控制和抑制本能的。人最大的理性就在于人有可能自我约束,而约束的底线是道德。约束的实现靠法律,法律的体现是秩序,这是康德的理性。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体系是嵌入到社会体系中的。所以经济需要被一个更大的形态所控制,这个形态是社会,这个形态的底色是道德。因此当你超越所有经济行为的时候,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够触犯的,这个底线就是良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利益不是在损人的基础上实现。恶德在经济行为中必须被扼制,市场不应该是放任的。
在理解亚当·斯密的时候,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经济行为,只要是人类的行为,就必然是一个道德的行为。”在整个经济行为,所谓的市场行为中,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彻底歪曲为放任自由。我为什么为《亚当·斯密传》这本书写序,我为什么对这本书这样肯定,道理很简单。这本书其实告诉我们,亚当·斯密不是被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之父。他支持商业社会,他看到了商业社会的积极一方面,但是他同时对商人做非常不客气的批评,他主张自由贸易,但他坚决反对奴隶贸易。
我相信能够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人并不多。你们知道他最后一部分讲什么吗?他的《国富论》大篇幅地讲教育,讲了对贫民的教育将使整个社会受益。富人不需要去考虑,因为富人他们自己会发愁后代的教育问题,他讲了国家、公益社会、公共产品,讲所有这些今天我们认为是必须的问题,他就差讲退休金的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他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多么媚俗。他在修改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论》时还加了一章,即在第一篇第一卷第三篇里,《论嫌贫爱富、贵尊贱卑的倾向所导致的道德情操之腐败》。道德情操之父,在他垂垂老矣的时候想的是这个问题,道德腐败,在他生命最后阶段,他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如何面对贫富差别,面对穷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中被鄙视的状态,如何改变他们的无助,这是亚当·斯密关心的问题。亚当·斯密讲“看不到的手”,在他的整个著作中几乎不占一席之位,但是这一点却被庸俗化和绝对地放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亚当·斯密时代,也就是18世纪后半叶的焦虑和今天的焦虑到底有哪些差别,我们今天的启蒙和那个时候亚当·斯密,包括康德加入的启蒙到底有哪些差别?差别非常明显。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从农耕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在亚当·斯密死了之后,才有狂飙性的工业革命的开始之后的商业社会,是重商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伦敦遍地是垃圾,到处是污水,泰晤士河脏得一塌糊涂,到处是雾霾。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焦虑是什么焦虑呢?人们焦虑生存的问题,是不是能活下去的问题。后来才有恩格斯谈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不是充满诗意的田园般的时代。
当时,所有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资本正在影响整个英国的走向。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所以他首先写的是《道德情操论》,呼吁人们把同情心放在首位。没有同情心,人何为人?同情心是一切道德的前提和本原。我们为什么看到有财富的人,大家对他缺少尊敬呢?因为越有财富的人越缺少同情心。所以在那样的时代,他写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觉得不够。在这个社会,我们怎样用道德来解释经济问题呢,于是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的本质是怎么样建立道德的基础和秩序,而不是放任自由。不是通过所谓的市场经济把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曼德维尔的蜜蜂王国,用恶德最后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平等和幸福,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也没有看懂。但他还认为不够,所以他强调法律。
回到今天,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我们的焦虑有什么差别?我们是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经济、向信息化改变,这个社会的焦虑不是绝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问题,而是所有人被科学、被技术、被一切迅速的改变所推动的时代,是一个怎样学习都跟不上的时代,这是另外一个焦虑。那么在这样的焦虑下,到底靠什么?我认为现在只能靠理性。不靠理性,靠浪漫主义?靠民粹主义?都不行,至少它们都有巨大的缺陷。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启蒙就包含了:第一,我们要呼唤理性。我们需要沟通,我们互相信任,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新的标准,要诉诸于一些秩序,这是理性,不这样怎么办呢?没有理性,疫情怎么控制?这次对疫情最大的证明就是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理性。第二,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相信科学、引导科学,和科学共处,甚至和科学创造的机器人共处。第三,我们必须把人文主义的东西坚持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焦躁的时代、焦虑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才能够得到相当的改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会理解亚当·斯密和我们原来听说的是不一样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