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话语圈到考古学的公共阐释
文 /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不久前某位诗人的诗歌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纷纷作诗调侃,同时也不断有“专业”的诗人出来辩解——“即使是再有名的诗人,一辈子也会有几首烂诗”“非专业的诗人没有资格评价诗歌”“要整体地看诗作,不要拘泥于几个词语”……但公众对此似乎并不买账,每个人都发现了回车键的妙用,把一句话多敲几次回车键,就仿佛创作了诗歌!在这个现象中,我看到了诗歌话语圈与公众的矛盾。公众是否有资格评论诗歌?曾几何时,《诗刊》的发行量超过50万份,可以想见诗歌并不是只有专业诗人才能评论的。诗意人生是很多人的追求,只不过有人把这种诗意写了出来。但是不知自何时起,诗歌成了只属于特定圈子的话语,似乎只有这些人写的诗歌才能被叫作诗歌。他们有专门的发表渠道,想成为诗人就必须进入这些渠道;然而,进入这些渠道,似乎又有一套特殊的话语与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与其他话语圈的规则未必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参与者必须明了,所有圈内人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于是,诗歌的话语圈就形成了。确立话语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交流,但现在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话语圈成了社会的边界或藩篱。
话语圈几乎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2021年寒假,我去了中国美术馆与798艺术区,这是两个在北京颇有代表性的艺术场所。我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工作者,只能说是欣赏者。我去这些地方是为了接受艺术熏陶,寻找感悟与启迪。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两个地方离我(或者说我离它们)有点远。中国美术馆是官方机构,它的展览主题宏大、作品技巧精湛,我能看出这套话语很专业,但总觉得它离真正的社会有点远,形式也不够新颖。798艺术区是商业性的,我原以为这里会更接地气一点,结果有些失望。看了几个展览,较之中国美术馆要前卫得多,但是我发现,这里的艺术表达更像是沉浸在自己的话语中。虽然策展人也设置了一些解说词,是中文的,其中的每个字我都认识,可是连缀起来,却不知所云。我想不会是因为我的文化程度太低吧?我于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对艺术也并非完全的门外汉,为什么当代的艺术话语发展成了这个样子?当然,我相信艺术工作者自己是能够读懂的,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个话语圈是不是已经封闭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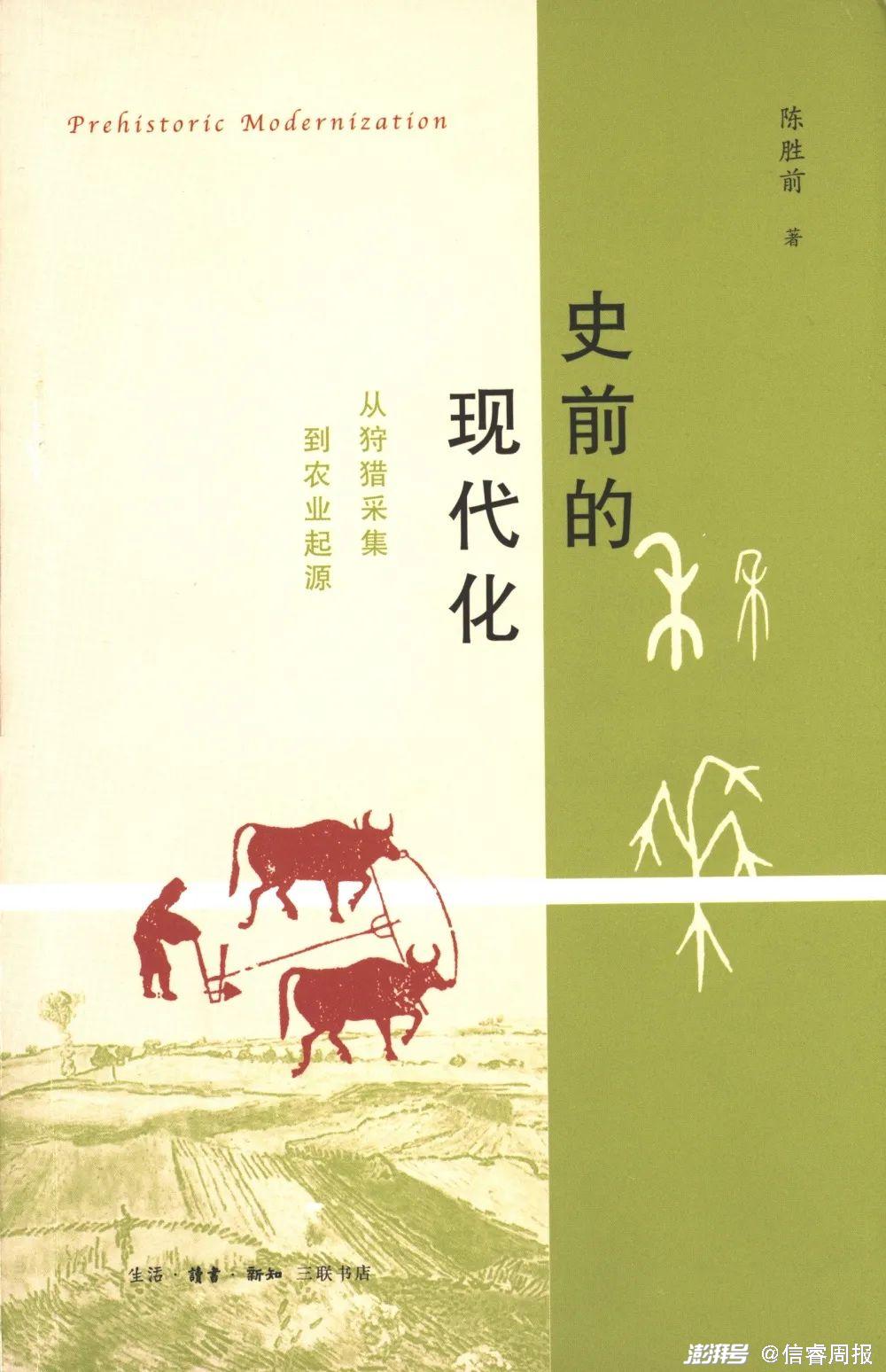
史前的现代化
陈胜前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对于艺术圈而言,我是圈外的公众,而在考古学领域,我是圈内人。我是怎么看待自己所在的话语圈的呢?反躬自问,突然感到有点汗颜,似乎严格的标准都是针对他者的。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实物遗存揭示远古的历史,因为研究对象是实物遗存,所以考古学研究有很强的专业性。考古学的话语圈也是相当封闭的,即便是相邻学科的学者,在面对考古报告时,往往也是深感无奈,实在读不下去。考古学者似乎从未想过在博物馆、考古公园之外的场所与公众发生联系,2009年曹操墓的发现便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曹操是中国公众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陵墓的发现自然受到万众瞩目。然而,事情的发展有点混乱,从怀疑发现的真实性到批判考古报道的可靠性,质疑者众多,考古学者最后则挂起“免战牌”,选择了回避争论。后来在对此进行“复盘”时,大家普遍认为在曹操墓的热烈讨论(其实是争论)中,考古圈应对得不是很好。再比如,最近几年有关夏代的有无也掀起了一番激烈的论战,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广,不仅有考古圈,还有历史圈、海外汉学圈,更离不了公众。论战还在继续,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应该让专业的学者来回答,公众则免谈。实际上,考古圈似乎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回应来自公众的质疑,唯一的办法就是竖起高墙,不说话、不接招。说到这里,考古圈跟艺术圈、诗歌圈又有多大区别呢?
回首历史,知识与阐释的公共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早期,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比如巫师,只有他们才有权力解读龟甲上的裂纹、划过夜空的流星……此外,还有一些足迹宽广的首领,他们见多识广,享有相对高的威望(这些首领经常就是巫师)。在这样的时代,受制于传播手段(缺乏文字或识字的人很少)与人们的活动范围,知识是高度稀缺的资源。到了中古时期,西方识字的主要是教士,相比而言,中国不是宗教主导的,拥有较为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其中有不少士大夫来自民间,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在这个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家之一。从技术层面来讲,中国又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故乡,因此知识的传播范围较广,知识与阐释的范围达到了中古时期的顶峰。等到近代教育发展起来,小学、中学、大学等公共教育开始普及,巫师、教士乃至于士大夫都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地位,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被叫作“专家”。专家的本义是指在不同领域接受了专业训练的优秀人士,其存在的前提包括:知识领域的划分、专业训练、专业的评价体系。究其根本,三者都依赖一个利器——话语圈。有了它,就有了地盘;有了它,就有了话语权。
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大大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公众参与阐释的机会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在社交媒体、公共论坛、文章评论区里,公众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专业的话语圈频频有被攻破的危险。前文提到在诗歌领域不断有专家出来为“屎尿体”诗歌辩护,我倒不认为这中间有多少人情关系,更多的原因恐怕是他们阐释诗歌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互联网是公众创造的乐园,截至2021年3月,由公众撰写的英文维基百科的内容几乎等于2869本《大英百科全书》,且其质量并不逊色。互联网是一个平台,在众多人参与创作、讨论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涌现出某种公共性——大家共同关注的内容。它可能是某个问题、某个观点,也可能是某个抓人眼球的词语。之所以说公共性是涌现的,是因为它是所有参与者在各种互动中产生的整体性的反应,很难被人为设定。公共性属于所有参与者,互联网成就了这种可能性。而当公共性与话语圈针锋相对时,公共性打破了话语圈,挑战了话语权。
“破圈”是大势所趋,不是某个人能改变的。其中的区别仅在于,这个话语圈是被公众攻破的,还是被专业人士自己捅破的。当然,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可能会存在不合理的“破圈”,即公众过度地“掺和”。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西方民众将是否需要戴口罩的问题政治化,声称戴口罩便没有了人权。就考古学而言,所谓公众之中颇有一些“民科”(不少“民科”可能是另一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的阐释没有科学性可言,更多的是在混淆视听。在互联网上,从来不乏“杠精”与“喷子”,他们为反对而反对——除了增加矛盾,很少有正面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把作为整体的公众与个体区分开来。当我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就其整体与历史大趋势而言的。整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不可否认这其中会有愚昧无知者、无赖,也并不排除在某个时期民众会被愚弄。但公共阐释的整体性是合理的、必要的,与作为个体的“民科”“杠精”等有本质的差别。

思考考古
陈胜前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在“破圈”时代,作为专业人士的考古学家应该如何自处呢?相对于许多学科而言,考古学界不甘落后,提出了“公众考古”(在某种意义上,称其为“公共考古”也许更合适)。历史学界也相应地提出了“公共史学”。显然,公众考古不是科普,因为科普早已有之;也不是让公众来考古,因为不可能把每一位公众都训练成考古学家。按照当代考古学理论的说法,公众考古的目的是沟通公众与考古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主张公众要参与到考古学的阐释中来。如果考古学家的阐释与公众的阐释是截然分开的,考古学家仍旧坚守自己的话语圈,绝不让渡一点点话语权,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公众考古。历史与文化遗产都是大家的,公众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没有理由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公众考古必然意味着公共阐释!然而,专业人士对此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公共阐释?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难道你生病之后会让不懂医学的人参与诊断?公共阐释让知识精英很不舒服——这难道不是相对主义?人人都发表意见,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
事实上,公共阐释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公共阐释有明确的结论,最终会接受实践的检验。比如在“五四运动”前后,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涌现出了无数的观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语言文字救国(改汉字为字母文字)、文学救国、逻辑救国、革命救国……每一种观点都有几分道理。不同的观点交锋后,在近现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有些观点胜利了,有些观点部分胜利了,还有些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文字救国)。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谁说了算呢?谁说了也不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时代大潮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后,最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后是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失败……谁决定了历史呢?是历史自身而已!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对于复杂系统而言,不确定性是其基本特征,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最终会形成确定性的趋势。我们无须担心公共阐释会走向相对主义,也无须担心那些参与“疾病讨论”的公众,有句话说得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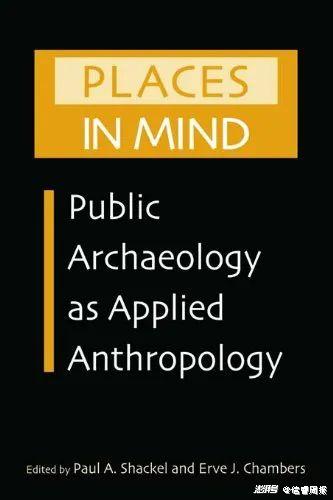
Places in Mind
Paul A. Shackel, Erve J. Chambers
Routledge 2004
公共阐释害怕垄断的话语权,害怕封闭的话语圈。公共阐释类似于人民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中的军事民主十分发达,所有士兵都会参与军事讨论:怎么突破、谁主攻、谁助攻、火力点怎么办、壕沟怎么办。人民群众也会参与进来,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没有用的信息会自动被排除。如果军事只是军官、参谋说了算,士兵就没有话语权,群众更不可能参与。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阐释反而会加强道理与事实的重要性(看谁说得更有理、更符合事实),更加肯定实践的必要性(说得对不对看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公共阐释呢?我想不少人担忧的是“暴民政治”——无知者或民粹分子受到蛊惑,有知识的人反而遭了殃(苏格拉底就是这么死的)。
公共阐释是有条件的,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形成公共阐释。就物质条件而言,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公共阐释的成本,并成为公共阐释必不可少的平台。可能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像当下的知识分子这样落寞,因为知识并不难获取。以问答社区“知乎”为例,大家的讨论与评论会把一些看起来特别“高大上”的问题梳理清楚。其中有许多人可能并不是专家,但是他们有切身的实践,他们的体会是很宝贵的。
开放、平等的平台是公共阐释的基本条件。当然,胡说八道、试图“带节奏”的人也是有的,这就要谈到公共阐释的另一个,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公共性的形成。如何才能促进公共性的形成呢?面对一个人们共同关心、都想解决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一起想办法解决,最终形成共识。换句话说,公共阐释是建设性的,其建设性正来自其公共性。胡说八道、试图“带节奏”的人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添乱、搞破坏,他们的阐释没有建设性,也就没有公共性可言。
然而,公共性来自哪里,如何才能获得公共性呢?我认为,公共性来自整体性,来自共识的涌现。西方学者在讲公众考古时只强调互动,就好像民主只倡导自由表达一样,忽视了共识的形成,但议而不决就不能形成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代表公共性的共识来自自组织的过程,而不是被某个人或某个阶层所设定的。
当代学科高度分化,每个学者掌握的知识其实都是非常片面的。表面上看,一些专业学者好像掌握了许多知识,实际上可能缺乏基本的常识;而且,这些看起来很可靠的知识赋予人一种虚妄的自信,可能导致刚愎的认识惯性,即相信只有自己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这样的专业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实际,更远离了公众。学者追求的目标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得到官方的承认,一种是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也就是来自学术话语圈的认同。大家恰恰忘记了学术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认识世界,解决世界存在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世界,是实践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人,立足于实践。遗憾的是,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我们获得的是一套套专业的话语,反而失去了把握真实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我想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脱离大地,如何才能把握世界的真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打破话语圈,有必要发展公共阐释,有必要发展公众考古。
通过上面的思考,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 公众考古的本质在于公共性,它强调专业人士与公众的互动,而真正重要的是公共性的形成。
• 知识与阐释公共化是历史的趋势,考古学的公共阐释是不可避免的,互联网促进了这种趋势,为它提供了物质平台。
• 公众考古既不是传统的科普,也不是让公众来考古,它是在公众与专业群体的互动中涌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反应,即公共性。
• 失去公共性的结果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继续筑起高墙,形成自己的话语圈;另一个是“暴民运动”,所有的知识与阐释彻底瓦解。
• 公共性源于社会实践,作为整体的社会实践避免了专业群体的一些缺陷:片面、书本化、缺乏常识、不接地气。
• 公共性事关社会矛盾的协调,没有公共性就没有公众考古。当前,公众考古还在路上。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49期,题图主要元素来自“神秘的古蜀王国”特展海报 @三星堆博物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